新史学 新青年︱苗润博:《〈辽史〉探源》题外话
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获奖作者所撰写的自述文字,向读者讲述其作品内容及创作思路和过程。
获奖作品: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
作品简介:元修《辽史》是有关契丹王朝历史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本书的核心工作即在于探索这部重要典籍的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学术旨趣与实质贡献主要有三。其一,系统深入地考证了元修《辽史》各部分的文本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史料价值,呈现出《辽史》本身的生命历程,尤其注重对元朝史官编纂建构的叙述框架加以离析,开辟了全新的问题空间。既在相当程度上批判乃至颠覆了既有辽史研究的框架,又有望成为新探索的起点和基础。其二,将《辽史》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变的大背景下,凸显其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意义,反思正史的经典性,对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细作具有示范意义。其三,透过《辽史》这一典型个案,对传统的史源学研究作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展示出历史学视野下文本批判的新路径。始于《辽史》而不止于《辽史》,是书中一以贯之的追求。

《〈辽史〉探源》(以下简称《探源》)出版将近三年了。关于这本小书的核心关切和写作过程,我曾在绪言、结语及后记中有所交代,后来又在《上海书评》的访谈《〈辽史〉与史源学》中做过补充,差不多算得上“题无剩义”了。这次有幸奉到“新史学青年著作奖”组委会的命题作文,再谈此书,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思量再三,决定稍稍跳出拙著,简单聊聊与之相关但又多少有些距离的几点感想。
一、“是非”与“源流”
《探源》一书的写作,依托于此前参与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修订工作。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二十四史的第一次点校,确立了当代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那么2007年启动、至今仍在进行中的修订工作,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在我看来,这一转型或可大致概括为:从是非式校勘到源流式校勘,从是非性考证到源流性考证。
传统校勘学多注重轩轾异文,判别正误,做出非此即彼的裁断,或对底本不足处加以改动,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努力恢复尽善尽美、惟一正确的理想文本。随着修订工作的深入,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诸多看似舛乱、不够“正确”的文字,未必是后世流传之讹误,而很可能指向创作者当时无意间留下的文本缝隙。对于这类问题,不仅不宜贸然校改,还可以此为突破口,窥见相应文本的资料来源与编纂过程。《探源》对于《辽史》各部分的讨论多建立在此类源流式校勘实践的基础上。
举一个小例子。《辽史·太祖纪》与《兵卫志》都胪列了阿保机陞任契丹可汗以前的早期战功,记事基本相同而纪年体系迥异。前者称“唐天复元年(901),岁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继以“明年”复“明年”的形式缕叙战功,直至所谓“太祖元年(907)”;后者则称“遥辇耶澜可汗十年,岁在辛酉,太祖授钺专征”,其下系“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云云。中华书局点校本及修订本均以同书《世表》《仪卫志》曾记耶澜可汗事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断定《兵卫志》系年有误,当以《太祖纪》为是,论者多从其说。不过在我看来,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孰是孰非问题,而应从文本生成的角度加以解释。二者内容大同小异,只是纪年方式不同,一个以耶澜可汗纪年,另一个则以痕德堇可汗纪年,说明在元朝史官所见原始资料中并没有出现可汗纪年的形式,而仅有唐朝年号及干支纪年(如作唐天复元年,岁辛酉……明年……明年……明年……)。也就是说,关于天复元年辛酉岁对应遥辇时代契丹的哪一任可汗,元朝史官实无定见,且因分头纂修,未及统稿,负责《兵卫志》的史官系之于耶澜可汗十年,而主修《太祖纪》者则以其为痕德堇可汗元年,同为编撰之时所增入,恐怕都没有太充分的证据。参考五代时期史籍可知,天复元年契丹可汗确为痕德堇(钦德)而非耶澜,然其任职期限应始自光启年间(885—888)而至于天祐三年(906),约二十年,并非天复元年方才即位。由此看来,《太祖纪》与《兵卫志》的两种系年皆不无问题,单纯的是非校勘显然无法解决。这种矛盾与混乱实际上反映出元朝史官所据史源关于遥辇可汗世系的信息十分匮乏且语焉不详,《辽史》相应记载的可靠性亦有待系统地重检(如上文所称《世表》《仪卫志》关于耶澜可汗时代的记述亦皆为元人新撰,本身就未必可信)。
不难看出,源流式校勘与源流性考证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谓源流性考证,除了文献本体的生成过程,还应充分考虑历史叙述的演化过程。在研究一些重大的历史关节时,面对不同文献乃至不同系统之间的记载分歧,如仅着眼于史料的截面或者说现存的终端文本,往往会认定二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忽略了历史叙述本身可能存在的前后变化,既往关于契丹开国年代、阿保机即位方式等问题的讨论即是此类典型。如果从动态、生成而非静态、现成的角度加以重审,看似不同的历史叙述未必始终方枘圆凿、难以融通。与此相关联的是,如果在是非性考证的基础上,增加源流性考证的维度,则会有助于从看似确定无疑的单一线性叙述中剥离出原本复杂多元的图景,提出全新的历史学问题,这也是《探源》实现由文本批判进入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说到“源流”,从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到张元济的《校史随笔》,再到陈垣的“史源学实习”,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涉及。不过仔细揣摩就会发现,前贤所述校勘、版本以及史料学方面的源流,重在“源流有别”,即区分文字优劣、版本高下和史料原始与否(如通常所说的一手或二手材料等),落脚点仍然在于价值评判,在于如何利用。现在看来,这样的源流意识显然是不彻底的。《探源》中所称“文献源流”概念的核心在于将文献看作有机的生命体,“文本”首先是文献本身,其背景、来源、纂修、结构、抄刻、流传、被接受、被改造等各个环节都可以作为剖析的对象,每一个文献环节背后都牵涉到实际的历史情境,包括整体的文献环境、具体的人书互动关系乃至宏观的书籍社会史图景,连贯起来就是文献的生命历程。换言之,文献源流本身在学术意义上是独立的、自足的,并不依附于使用者的价值评判,亦未必需要舍流而从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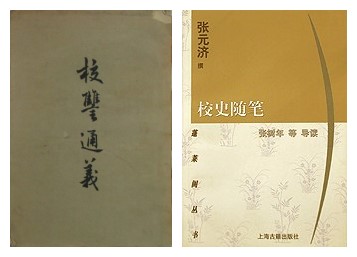
二、“史料熟”与“文献熟”
“史料熟不等于文献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断代,而文献熟则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一旦文献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从容处理。”这是先师刘浦江教授多年前的教诲,曾由笔者记录在《走出辽金史》一文中。近年来,不止一位学友问到,这段话究竟是何义涵,史料熟和文献熟到底有何不同。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增进对此说的理解,《探源·结语》中所强调的“碎片”与“整体”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这一脉络之下的延伸思考。
在刘师原本的语境中,史料熟和文献熟最直观的差异在于断代与通代的分野,是外在格局、气象的不同,除此之外,二者内在的核心区别还在于研究本位与路径的不同。所谓“文献熟是一种整体的感觉”,并非要求读遍历代之书,而是要对文献的本质或者说文献本体有一个贯通的把握,理解其生成、衍化的机制和通例,特别是文献内在的复杂性、丰富性及约束性。而“史料”一词本身就隐含着为我所用的取向,由此产生的史料学主要介绍研治某一断代史应该看哪些书,某一部书中有哪些内容可以用来分析具体问题。在此脉络下,“历史(史籍、文献)被作为供史家采摭、筛汰、利用的材料(对象),其中呈现出的逻辑主体是史家而非文献本身,先天就可能隐含着史家主观方面的工具性、功利性诉求。(《探源·结语》)”由于对材料所在文献母体缺乏关照,孤立、零散地利用成为常态,这种漂萍式的碎片感可能会令研究者忽视文献源流本身所具有的规定性,增加文本解释的随意度和自由度。
此类情形在传统文史研究领域屡见不一见,譬如近来被重新热议的《满江红》真伪问题,前人的某些具体论断就可以从上述视角加以审视。或以清初沈雄《古今词话》及康熙朝《钦定历代诗余》等书所引陈郁《藏一话腴》论证该词已见宋人记录。按传世诸本《藏一话腴》皆云:“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夷狄不情,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门,功无补于涓埃……(引者按:以下亦为表文内容,不录)’”从中可以看出,陈郁原书仅分段摘录岳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全然不及其他,而《古今词话》相应条目则作:“《话腴》曰:武穆《收复河南罢兵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悬犹之可也,欲远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故作《小重山》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指主和议者。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除了原书即已节录的《罢兵表》,还多出有关《小重山》《满江红》二词的评说。有论者以此条全为沈雄引《话腴》之文,故将《满江红》云云视作宋人佚简。这样的论据恐怕是站不住脚的,症结正在于只盯住史料碎片的内容,而对其所在文献本身的大体、通例缺乏关照。通览全书可知,《古今词话》采用引述资料与沈氏评断相结合的形式,惟所引前人论说与作者自家心裁之间常无明显区隔,多有混杂,读者稍不留神就会被其误导。上文所引《话腴》至“故作”前实已截止,内容与今本无异,其后多出的文字实乃沈氏自道,而与陈郁原文无涉。然沈书影响甚大,《钦定历代诗余》等后出之书多以之为据,终致陈陈相因,积非成是。倘若从文献大体着眼,这其实只是一个标点断句的问题。
又如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曰:“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发冲冠……(引者按:以下全载其辞,不录)’”潘氏此条未标出处,有研究者因开首“最工”以上文字略见罗大经《鹤林玉露》,而推定此条全部出自罗氏书的另一版本,亦可为宋人已见《满江红》之一证。按此说亦属单独拎出孤立史料,而全未顾及《宋稗类钞》及《鹤林玉露》两部文献本体的约束性。翻检《宋稗类钞》不难发现,潘永因抄书并非拘泥于每段记载止录一部文献,而常常会将出处不同但内容相关的资料杂糅、拼接在一起,此亦合古人抄书之通例。同时,《鹤林玉露》原本十八卷具存,《永乐大典》引文皆见今本,知其至少自明初以来即无散佚,又怎会偏偏到作《宋稗类钞》时凭空横生出一段他人未见的文字?《满江红》云云显系潘氏据明后期以来通行文本所补。这一案例生动地反映出,源头文献的流传过程与最终文献的编纂过程,一纵一横,构成了文献源流分析的基本坐标(详细论述见《〈辽史〉与史源学》),其中所蕴藏的实实在在的约束力,规定了学者不能根据研究需要而擅为损益。文献自有义例在,说的正是这种整体的感觉。
文献熟的整体感当然需要在不断积累中逐步确立、强化。前贤多以熟读先秦典籍为积累文献根基之要途,诚为确论,不过就个人体会而言,阅读明清以后书似亦十分必要,因为参证资料越多元,细节越复杂,约束性条件就越明显,自我驰骋的限度也就越容易把捉。况且这一时期的很多文献具备深入分析背后历史情境的充分条件,有的甚至尚未被从原生的脉络中抽离出来,此类个案无疑会深化我们对于人书互动关系的体认,携此认识再来反观前代文献就会有更审慎、切实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库全书总目》的确是一个绝佳的训练场,除了历来所称治学津逮、按图索骥的功能外,《总目》本身的生成过程,尤其是其间所用种种精微细致的编纂技艺及宽阔广博的社会历史背景,集中呈现出文献生命历程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文献内在的源流脉络。
三、个案与方法
如果说源流式的校、证实践与贯通性的文献理念,构成了《探源》一书的学术底色,那么个案的典型性与方法的适用性则是在此之上关心的核心问题。
我曾尝试从三个层面总结《探源》的研究旨趣:“其一,系统深入地考证元修《辽史》各部分的文本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史料价值,呈现出《辽史》本身的生命历程,尤其注重对元朝史官编纂建构的叙述框架加以离析,开辟出全新的问题空间。其二,将《辽史》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变的大背景下,凸显其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意义,反思正史的经典性,推动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细作。其三,透过《辽史》这一典型个案,对传统的史源学研究作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探索历史学视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径。(《绪言》)”具体的实现情况,当然由读者来批评,不过“始于《辽史》而不止于《辽史》”,确实是写作此书过程中力图一以贯之的追求。
近尝撰文提到,目前分科断代治史的模式和格局,未必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而更可能是学术传统遭遇现实政治挤压后的产物(《“四把钥匙”与治史格局》,《读书》2022年第11期)。断代研究可以呈现历史的剖面,训练深入史料的技能,但不应成为自我设限的藩篱。研究者的首要着力点当然在于个案的处理,展现真切的历史场景与演变脉络,但透过个案去探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摸索互通性的方法,进而照亮整体历史的面貌,亦是好的个案研究的应有之义。能否真正跨越断代藩篱,尝试通贯的思考,关键之一或许在于,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否足够尖锐,所选择的个案是否足够典型。
就探讨正史的文本生成问题而言,《辽史》大概有以下三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史料地位足够重要。《辽史》一部书承载了契丹辽史研究九成以上的资料来源,奠定了整个断代领域的基本认知框架,剖析《辽史》本身就是在从根本上冲击既往的研究体系。其次是文本足够粗粝,留下的缝隙足够多。元修《辽史》成书仓促,且素材匮乏,须新作大量的二手文本,拼凑杂糅、捉襟见肘之间破绽百出,为拆解工作留下较大的发覆空间。再次是质证材料相对丰富。唐五代宋金元明乃至高丽文献中均存有与分析《辽史》文本来源直接相关的记载,特别是宋元文献辗转保存的辽人著述如赵至忠《虏廷杂记》、史愿《亡辽录》等书之片段,正构成对判明源流至关重要的枢纽性文本。以上三者,孤立地看,或许亦分别适用于其他正史,但若论集三方面特点于一身,则恐无出《辽史》之右者。这种独特的综合属性正是《探源》所处理个案的典型意义,也是得以对史源学方法有所反思、有所更新的内在依凭。
通常认为,中文语境下的“史源学”最初由陈垣先生提出。这在当时只是一种训练学生的手段:清人引了某条材料论证某个史学问题,陈垣就让学生去查证原书,发现清人引材料很不老实,往往会曲解文义。可见史源学的最初功能就是验证对错、不被人诳,并没有变成一种自觉的研究方法。后来人逐渐发扬光大、提炼总结,使得史源学似乎具有了某种方法论的色彩,即做研究要用原始材料,二手材料不能随便用,要找到其来源。截至目前,史源学研究的主体路径还是一条一条地追索材料来源。从碎片式的挑错到碎片式的溯源,其中的思维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史料学的取向,即将史书看作一条一条供史家采摭的材料。
从实际效果看,史料学框架下的史源学研究可能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在可以找到文字类似的参证材料时,往往笼统依照不同文献的时间先后,论定其间存在直接线性的传抄关系,而忽视了同源异流或者存在“中间文本”的可能,原本更为复杂的文献脉络与历史情境由此遭到遮蔽。其二,对于缺乏现成、大段参照文本的情况,孤立的溯源往往会服务于研究者的论证目的,一条材料对论证有利,就使劲往早期的、可信的来源上靠,很少考虑文献编纂时能否用到、是否真正用过这种原始资料;如果不利于论证,就尽量把它的来源引向相反的方向。这种碎片式的史料溯源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因为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研究者手中。以上两点的共性在于,缺少了对文献源流的通体关照,不清楚史书作者当时实际的书籍环境和编纂技艺,研究结果就很难得到有效的验证。其三,如果仅将文献看成一条条史料,做出真伪、正误、价值高低的判断,可能导致对于文本本身的结构、层次和缝隙反而缺乏省思,对整体的逻辑脉络不够敏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经意间为其中隐含的叙述框架所左右。这一点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尤为深广。
关于《探源》所摸索的史源学的新路径,《结语》与《〈辽史〉与史源学》中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说,此处仅稍作总括。宏观而言,是从史料取向到文本取向、从碎片到整体的转型,是对文献源流本身与历史权力话语两个层面的拆分;中观而言,是对文本结构、文本单元、文本层次、叙述框架的强调;微观而言,是“同源异流”与“线性传抄”的对举,“中间文本”的突显,“文本缝隙”的发现等等。倘若这些探索可以为正史文本分析乃至史源学、文献学的更新提供某种桥梁或曰对话工具,则幸莫大焉。就我个人而言,上述方法层面的尝试专属于《探源》,亦未打算将此推展到对其他正史乃至其他文献的分析。时常向往这样一种理想的学术状态:研究者每完成一部著作,每处理一桩典型个案,都能首先提出独属于该个案本身的问题与方法,而不是用全新、独立的个案去验证、填充既有的研究范式——窃以为这正是从根源上避免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泥沼”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