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丹丹评《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丨书写富人的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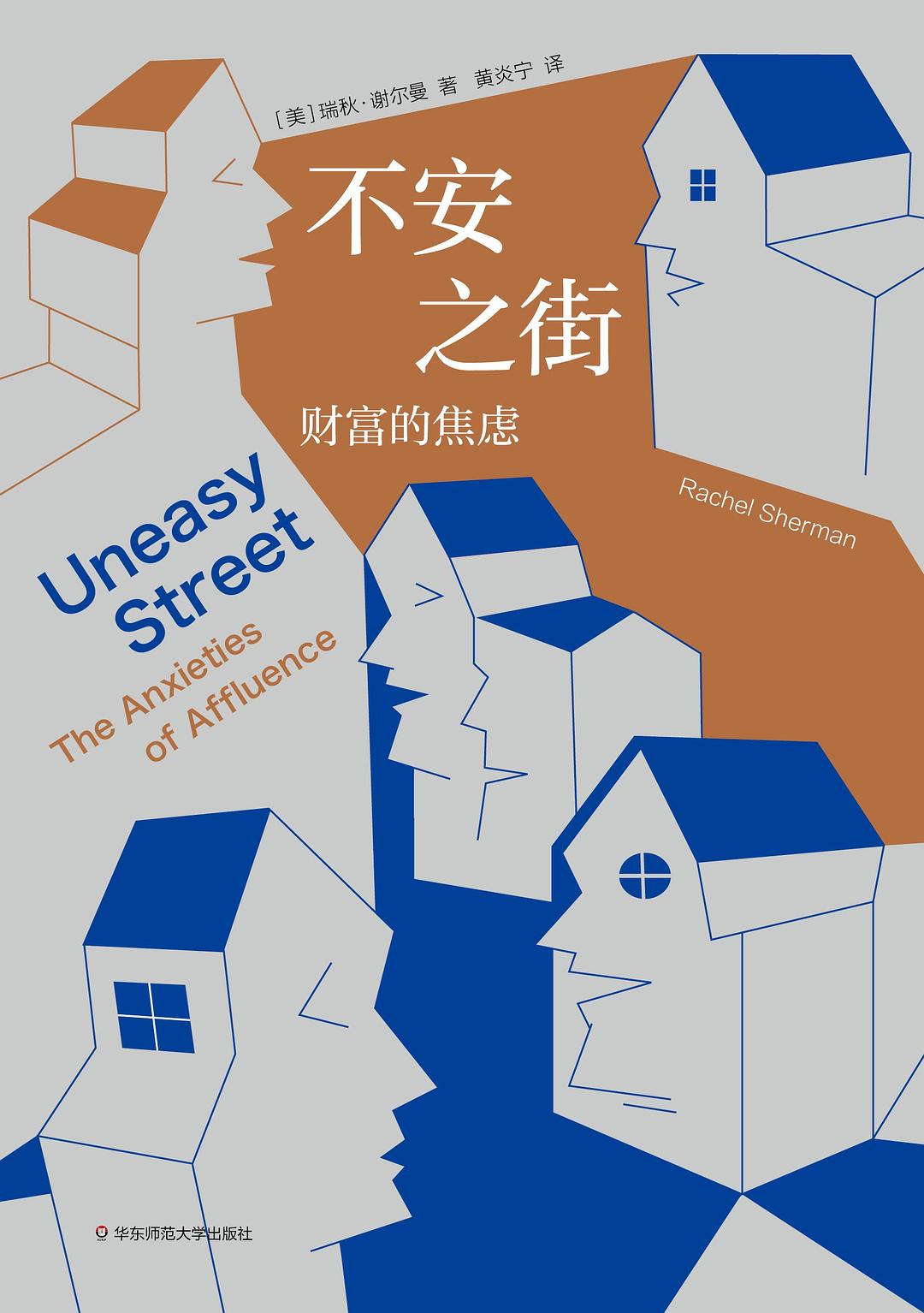
《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美]瑞秋·谢尔曼著,黄炎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2年5月版,69.80元
电影《商海通牒》(Margin Call)讲述的是华尔街一家金融银行逃过金融危机的惊险前夜,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威尔一年赚两百五十万美元,当同事问起他是怎么花的,他开始算:
税收拿走一半,这样,就剩一百二十五万了。
房贷得还个三十万。
又给父母十五万拿去花。
“这多少了?”他问同事。
“八十万?”同事说。
“没错,八十万。”他说。
十五万买车。
七万五千花在吃上。
大概五万买衣服。
然后四十万存起来,以防万一。
“明智。”同事夸赞道。
“嗯,看起来金融风暴快来了。”他说。
“还有十二万五千呢?”同事问。
“我花了七万六千五百二十美元在荤场子上,主要是嫖妓。”
两个同事低头笑起来。
“七万六千五百二十?”一个同事抬头想要确认。
“一开始我也很震惊,但后来我发现,可以用娱乐名义报销一大部分。”
这个插曲让富人的钱是怎么花的变得具体,或许如果不是在共度危机当中,这两个职位较低的同事不大可能了解到管理他们的企业高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不过这毕竟是电影,现实生活中的富人是怎样一种生命体验与存在方式呢?《不安之街》完成了这样一项不太可能的研究,因为当富裕、十分富裕以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它的研究难度远远超过社会学、人类学对贫穷、贫穷文化等经典议题。与之相对,从社会分层领域涌现的中产阶层研究尽管在近二十多年收获了瞩目的研究成果,仍旧面临对凌驾中产群体之上、让其感受到相对剥削感的权贵或富豪等“塔尖人物”往往以大而化之的形象出现,口诛笔伐,而又总是难免隔靴搔痒。由于特权阶级对自身隐私的极佳保护,真正的富人是看不见的,隐没于大众视野之外,于世俗社会留下若干流光溢彩和彩云易散。像是N年前我在西餐厅打工,在晚上快打样时,一位食客总是准时出现,在半小时之内吃完一块牛排。这种神秘感丝毫不影响大众对精英人物的调侃,例如“给自己设一个小目标,先挣它一个亿”,和马云的合照等。大量的“真人秀”节目将镜头对准了富人、明星群体,展示他们的豪宅和奢华的日常消费,“一顿早餐五百块”的段子迅速流传开来,名人们令人咋舌的生活水准呈现在大众面前,而且带有戏剧性效果。在抽象和具象之间来回转换,真实的富人群体是怎样的?真正的富人生活是怎样的?似乎也超过了人类学对中产阶层开展田野调查的可能性的极限。
而比方法论更具挑战性的是书写问题,如何书写富人群体?如果抛开“豪奢”“奢靡”等糜烂词汇,也不打算采用“石崇斗富”这样带有强烈戏剧效果的叙事情节,书写富人在社会分层的民族志储备中成为一个近似高原反应的缺氧状态。当然并非如此贫瘠,也有将精英与底层连接起来的实验之作,例如《流动之城》,努力追逐两个世界的人不经意把手触碰在一起的场合,连接他们的是性产业。作者对底层人物喧嚣、动荡生活贯之以活色生香的泼辣写生,对上流社会那帮光鲜靓丽的男男女女的书写则显现出犹豫和凝涩。他们的面目表情一律“冷漠”,他们喝醉酒呕吐的姿势也特别,他们“向前看”的价值观影响从纽约底层爬上来的职业妓女对江湖义气的抛弃、拿到进入高级色情业的门票。他们出场,尤其是女人,其描写是用穿衣、配饰的品牌(logo)堆砌起来的。这样的写作策略加剧了人们对上流社会的刻板印象,其原因是研究者看待研究对象并非“平视”。在遗憾之余,《不安之街》带来的富人研究某种程度上开辟了书写富人的实验,作为研究者,来自特权阶级的一员,克服了语言的犹豫和凝涩,也克服了修辞上的讽刺与蔑视,而这两种倾向均是书写富人容易陷入的情绪和情感暗示。这当然可以看作家庭出身带来的免疫力,富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内化为她的生活经验,所以她能够辨识访谈对象言及生活方式的某些术语,这些信号标注了不易察觉的阶级鸿沟。不过正式开始研究仍旧困难重重,“滚雪球”的方法在寻找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不甚适用,因为总是遭遇线索中断,深描的方法也被放弃,因为出于隐私的考虑同样不甚适用,为了避免访谈对象被提供线索的文化中间人认出,作者还要刻意替换某些细节。作者一再说明她的样本选择包含了多样化背景,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群体:白手起家的富人和继承遗产的富人。按照受访人如何定位自我、是怎样的富人等自我感知,作者将这两大群体又划分为“一心向上”和“心系下层”。“一心向上”指向的是即使身处百分之一的行列,也还有比自己富裕的顶尖精英。作者发现一个相当无趣的说法:“自视中产”,如果不够有信服力,最多是中上层。“心系下层”指的是认识到多元化阶层的社会现实,总有没有自己那么有钱的人,但“没有自己有钱”是一个过于稀释的说法,比如“住在拖车公园的人”。对于富人而言,即使心系下层,贫穷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他们的世界接触不到穷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想想“非洲贫穷儿童”,就知道自己生活多么富足。
瑞秋·谢尔曼(Rachel Sherman)采访了来自四十二个家庭的五十名家长,这一人群的年收入从二十五万到超过一千万美元,资产在八万到五千万美元之间。达到家庭年收入二十五万美元及以上的人群在纽约市的占比为百分之五。年收入二十五万美元是什么概念,不久前发生的加州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后大罢工提出的加薪诉求可以帮助做一个参考,争取博士生底薪五万四千美元,博士后底薪七万美元,“纽约市家庭收入整体中位数是五万两千美元”,可以想见,四万八千多名“学术打工人”还在为达到“总体中位数”的生存权利奋起斗争,而“本研究样本家庭的收入中位数约为六十二万五千美元”,几乎可以看作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的人群样本。按照她的说法,富人如何言说富有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探索的事情。她发现,人们对于自己手握巨额财富有着难以掩藏的不安,对于未来财富一夜蒸发的风险有着坐卧不安的焦虑。这是大众想象中的富人吗?在谈话弥漫的不安和焦虑中,人们如何在特权的理所应得感(entitlement)意识当中赋予逻辑的自洽,让自己心安理得,不再被富有带来的困扰内耗,这种逻辑自洽往往在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又总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于是特权阶级的意识就好像在一个得体地占有财富、恰当地使用财富的百般努力中变得合理化,就好像“我做全职太太也是尽职尽责,不亚于玩命工作”等自我言说,就好像“我反对私立学校,但经过百般挣扎我还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样理想与实践的出入。有关特权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否思与内化在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出意识形态的辩证法雏形,实际上又是特权合理化的模糊地带,“它折射出一个更宏大的观念问题,即我们的社会认可怎样的特权阶级”(33页),构成全书的话语分析核心。
由于全书采用的是访谈,这意味着有近一百个名字出现在各个章节中,让阅读的体验变得支离破碎,犹如“脸盲”在一大堆符号中辨认一些连贯的首尾。而且作者特别喜欢“见下章”“前文第X章提及”“后文X章X部分还会展开”这样的论述句式,常常激发我不尽的懊恼,好像是阅读一份说明书,只有读者自发地将中缝、骑缝、眉批等散落在各处的小字信息搜集汇总,才有可能把说明书搞懂。这恐怕是抛弃作者随着江湖人物的流动而流动起来的方法——让流动的人群带着自己走,说不定在哪里又与其他人不期而遇,以及抛弃人类学者擅长的深描技法而串联起来的民族志叙事,依靠言说和话语支撑文本在阅读体验上的折损。显然这也正是作者追求的方法论的完整性。让她找到样本人群除了家庭年收入、总资产等统计数据的筛选,还有一条辅助线:聚焦那些正在装修房屋的人,“因为这个问题兼具审美、家庭关系和经济考虑等多个元素,而且也算是一个较为清晰的访谈出发点”(21页)。通过收入、房产等资产调查(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调查,因为受访人非常忌讳“富裕”等说法,忌讳谈钱)和装修处境等多元因素,通过进入受访人家里或在咖啡馆,或邀请受访人来自己家,结合访谈场景,大量信息已经让读者大致了解富人家庭的笼统“标配”:他们几乎都来自精英院校。目前从事的行业包括金融、企业法、房产、广告、学术、非营利组织、艺术,还有时尚行业。有十八人辞去工作,全职在家照看孩子。住在城郊别墅、市区宽敞的公寓房(往往把原来的两三个单元打通)、曼哈顿联排别墅、布鲁克林褐石建筑,拥有在汉普顿和康涅狄格州的第二个家。家庭装潢的私人定制程度如此之高,竭力透过装修体现出他们的个人审美。有几个人一次性付清了房款,或者只动用了很少的贷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或者正打算购买第二套房产。他们的孩子大都在私立学校上学。女性担负着照顾家庭事务的首要职责,其中包括负责装修计划,维护第二个家庭住所、照顾孩子等,作者将其称为“生活方式的劳动”。所有受访家庭都雇用清洁工,一些家庭还雇了奶妈、厨师和私人助理。所有的受访者都聘用过“文化中间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这一专业服务人员,例如理财顾问、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房产经纪人、私人厨师、个人助理等。“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得有钱的消费者能够方便地做出选择”(25页)。由此,书写富人的开端从这一系列具体化的财富拥有配置开始,而转化为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隐藏财富——不想“哇”的一声
我以为场景描写是该书在书写富人方面取得的可贵收获,常常是寥寥几笔就将富裕的现实勾勒出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往往“不近现实”。场景是受访人开始言说之前的铺垫与前奏,往往也是寥寥几笔就带过,例如“乌苏拉的公寓位于上西区,宽敞气派的客厅俯瞰着哈德逊河”,“米兰达和她的老公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一栋五层楼的褐石建筑内。在把房子彻底翻新时,他们在家里装了一部电梯”(42页)。“我和露西访谈的地点是她家宽敞的开放式厨房,与客厅及起居室相连,而他们的公寓由三套小公寓打通、合并而成”(251页)。我以为场景描写是书写富人重要的写实基础,使普通读者了解到富人的某些生活细节和消费习惯。他们有一套说服自己为什么非要如此奢侈的理由,这些理由打着孩子的名义,或者为了家人考虑建一个带网球场的房子,更啼笑皆非的是宣称“房子的墙面都是我刷的”。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在于他们在装潢方面豪掷六七十万美元,在保留个体权利的私人领域、渗透个人品味方面不遗余力,但又在某些家装环节上“抠门”,抗拒奢华带给自己的幻象,美其名曰“让自己吃些苦头”,吻合自己反复定位的“虽没有钱的烦恼,但日子过得照样精打细算”。受访人坦言,自己能够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装修、并且能够住上自己心仪的房子,这就是有钱。“有钱可以任性”有夸大的成分,放在“过日子”的角度指的是经济基础可以支持“有品味”的生活。尽管书中没有具体描述,不过品味的彰显离不了艺术品展示和绝版书收藏,尤其是艺术品关系到主人的鉴赏、学识和身份。然而更进一步,这种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统一形态在装修工程竣工时也要留下一个不相称的尾巴,不要显得如此奢华,使朋友来家里做客时纠结不已,因为“我不想听到那一声‘哇’”。例如厨房放一个一般的灶台,能做饭就行;在高档家具中塞入一堆宜家和特力家居的东西,“因为这样显得很节约”。不会在天花板上镶嵌金色的镀层“炫富”,因为这笔投入不可能在卖掉公寓的时候回收。尽管有车载吸尘器的新车型号非常动心,但十万美元的价格还是“算了吧”。房子焕然一新,但对于用了十年之久、夫妻俩都很讨厌的沙发还是倔强地留着,为的是放在那里警告自己“不要放纵自我”。装修最奢侈的决定是新家有两套洗衣加烘干机。还有,虽然六十万美元砸在装修上,但不是豪宅,“没有廊柱和蜿蜒的车道”。
不止家具家装如此,这种“抠门”还延续到消费领域:在话语和符号层面,这些受访者将自我描述为占据美国道德高地的中产阶级(127页)。不会去巴萨泽餐厅这样的地方吃饭,自己开的是二手车,衣服都是Zara和H&M等经销店买来的。每样东西都货比三家,比如一样东西在Target和Costco的售价各是多少。为买一个八美元的墨西哥卷饼纠结。为频繁打的内疚。只是借着生日才给自己买一件五百美元的皮衣或者一个心仪已久的两千美元的包。这种“抠门”,这种“淘便宜货”的满足,这种为“奢侈一把”的心理挣扎,作者称之为“谨慎消费”,它竭力与他们批判的“土豪”区分开来,也坦言如果失去了这样的生活,照样也可以过穷日子,不过受访人能想到的是穷日子是吃吞拿鱼罐头。与“抠门”相对,他们特别看重消费体验,这叫做“奖赏”,例如度假旅行去哪里、住什么酒店、“蜜月”旅行怎么安排,极尽奢华,极尽享受。俗话说“由奢入俭难”,他们真的能接受有一天突然发生的变故,靠着平时富贵荣华中注入的一点“抠门”习惯适应中产阶级的普通生活吗?还怎么奖赏自己住一千美元一个晚上的酒店呢?
书写富人的得与失
相较于纽约第六大道的无家可归者(《人行道王国》)与充斥暴力的黑人社区(《在逃》),《不安之街》是我读得最为艰难的有关富人的民族志。一方面是话语分析占据了全书的中心,在叙事的连续性与写实的饱满度方面总是支离破碎;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这种阅读困难来自我与作者所置身的富人世界存在遥不可及的天堑与鸿沟。我不能理解那种不安,为什么拥有巨额财富而坐立不安、焦虑难眠,这种焦虑和时刻担心失业、房贷即将崩溃、为了孩子营养忍痛一个多月消费一百多块水果的家庭所承受的煎熬一样吗?这种焦虑和凌晨四点聚集在密密麻麻的劳务市场、有活的时候吃三顿、没活的时候吃一顿的不确定性一样吗?这种焦虑和女性选择动辄上万元的试管婴儿技术、充满挫折的求医道路无法自拔的生育焦虑一样吗?这种为照顾他人与自己的差距而良心不安和“亲不在而子欲养”的内疚与自责一样吗?反过来,出身特权阶级的一员,也可以说自己刚好是幸运的,出生在一个百万收入、千万资产的家庭。由于孩子从小接触的是由财富编织的上流社会,虽不至于“何不食肉糜”,贫穷对他们而言亦是抽象的,慈善对富人而言是“洒洒水”的象征性身份。为了一年一万块学费去工地干活的学生身上有自食其力的精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回馈社会、资助大学生完成学业又有何不可呢?正是阶级出身和生活经验的天然劣势,这些不安与焦虑几乎是矫情,刺激着我褊狭的神经,耗费二十多天陷入下笔有如受虐的空档期。我甚至猜想在英国女王看来,该书所呈现的“富贵病”不过是万里晴空掠过的一丝乌云,略显造作,但的确得体的待人接物和礼仪教养,是如此重要,如此重要,如此重要。也因此,合理享有特权的惯习就像刻在身体里的DNA需要遗传下去。
如果说该书通过话语分析揭开了特权阶级难以逻辑自洽的精神征候、需要找到让自己享受奢侈生活的顺理成章的道德依据与心理疏导,那么该书在书写富人方面留下的一个遗憾是话语分析的瓶颈。它无法替代阶级分析,回答触及底层社会与上流社会真实联系的问题,再分配制度是怎样塑造不平等的阶级社会的,财富是怎样从百分之九十五的大众手中流到百分之五的一小撮“金字塔”顶端的人群的。该书在富人写作上是一个具有开辟性的尝试,借助话语分析显现了少许的富人世界的消费惯习与审美癖好;再进一步,书写富人有无可能超出话语分析进入叙事本体呢?虽然匿名性给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但以“财务自由”之身“平视”富人已经是罕见的写作优势。叙事从装修话头切入,窥见在富人家庭当中,夫妻之间的“一地鸡毛”和富人小孩养尊处优却又处处规避优越感外溢的惯习养成,有无可能再进入离婚官司撕开的财产矛盾升级、伴侣出轨、夫妻信任破裂以及特权阶级犯罪又操弄媒体欲盖弥彰等等“暗黑”世界浮动的礁石呢?“做一个好的富人”是一种理想与现实交织的话语真实,人性的真实是在表述中完成呢,还是在触及核心利益时的恐慌与暴怒等失态中暴露呢?
大卫·格雷伯告诉人们,很大部分的办公室工作已经现出原形,纯粹是狗屁,包括书里提及的为富人服务的、从事私人订制的形形色色“文化中间人”。“如果工作被迅速去狗屁化,但金融系统或更普遍的财富与权力结构没有真正改变,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大卫·格雷伯,Arts Of The Working Class,2020,王磊译)。富人破产的几率微乎其微,他们还时刻不安与焦虑。瑞秋·谢尔曼说得好,在社会保障缺失的危机面前,“这些社会问题一方面制造了富人的危机感,但另一方面也恰恰源自他们的行为。那些在金融和相关产业工作的人一手制造出那个同样让他们焦虑的不稳定的市场”(296页)。
电影《在云端》(Up In The Air)讲述的是专门为其他公司提供裁员服务的瑞恩的心路历程变化。实习生娜塔丽找老员工谈话,告知他裁员的决定。实习生明显经验不足,瑞恩在一旁看着,掌控大局。
“没有了公司福利,我女儿哮喘发作时,我只能抱着她。因为我付不起医药费。”
老员工略显痛苦地把头撇到一边。
实习生顿了顿,微笑地回应道:“研究表明适度受挫的孩子,在学术上会更有建树。”
瑞恩扭头看了一眼娜塔丽,而老员工眉头紧锁,用不可置信的眼光瞪着她。
“去你妈的吧。”
实习生不安地垂下眼。
“这才是我孩子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