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穆太子与崔浩——北魏太武帝废佛前后的政治风云
引言
标题提到的北魏太武帝,是终结五胡十六国时代、让极度混乱的华北重归统一的帝王。中国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法难”的四场废佛运动,太武帝乃第一位断然执行者,亦因此著名。对这一次废佛前后的北魏历史,学者从宗教史、思想史、政治史等各方面开展了研究,推出了以塚本善隆氏的论著为首的大量成果,因而本领域给人已臻完满之感。不过笔者认为,在根本性问题上还遗留着未阐明的地方。这种质疑来自对当时政治动向之实态的专门探察,本章就将揭示此疑点,并尽力做一解答。

太武帝拓跋焘像
众所周知,北魏的废佛是以皇帝太武帝、崔浩以及新天师道的倡导者寇谦之三人为中心实施的,崔浩乃实际的筹划者、推进者。另一方面,反对势力的核心为皇太子拓跋晃(以下称景穆太子),当时他因监国占据朝廷行政的枢纽。然而,从寇谦之死时的太平真君九年(448)到太武帝死时的正平二年(452)三月,短短四年内居于政局中央、左右政治走向的此四人相继亡故(崔浩被杀于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景穆太子死于正平元年六月)。
从现存史料无法推定寇谦之之死存在政治因素(参见《魏书·释老志》)。崔浩被杀与时局密切相关,大量先行研究已经指出。太武帝则因宗爱谋逆而死。这三个人的情况在《魏书》《北史》以及其他关于该时代的史籍里记载明确,恰可形成对比的是,史书围绕太武帝嫡长子景穆太子之死的表述颇为含糊。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正平元年六月条云:
(A)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于金陵。
同卷末《恭宗纪》云:
(B)恭宗景穆皇帝讳晃,太武皇帝之长子也。......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于东宫,时年二十四。庚午,册曰“:呜呼......隆我皇祚,如何不幸,奄焉殂殒,朕用悲恸于厥心......”
该纪末“史臣曰”谓:
(C)史臣曰:世祖(太武帝庙号)......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闻,夙世殂夭,其戾园之悼欤?
引文(B)中诏书表达的是太武帝面对其子早亡的悲痛心情。但引文(C)“其戾园之悼欤”之语却传达出景穆太子乃异常死亡的意味。基于后者再回看引文(A),景穆太子死于非常这一观点可以得到支持。因为据引文(A),戊辰日景穆太子死,仅四天后的壬申日,他便被火速下葬于北魏历代皇帝长眠的金陵。这与(B)中诏书所见内容构成极强的反差。那么,此事实情究竟为何就有必要加以探明,考虑到景穆太子乃当时政局中一方的核心,北魏权力构造的问题亦将被触及。同时,景穆太子反对废佛,与崔浩等人针锋相对,因此这一问题还关系到北魏史上最大的疑案——崔浩被杀事件。
接下来就从以上疑问出发,走近北魏太武帝时代后期政局与权力构造的实态。
围绕景穆太子之死
首先尝试论证景穆太子死于非常,并探讨其原因。《魏书》卷九四《阉官·宗爱传》载:
恭宗(景穆太子庙号)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为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时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
较先前材料,该引文更具体地说明了景穆太子之死异乎寻常。《魏书》作者魏收所谓“其戾园之悼欤”大概由是而发。“戾园”意为汉武帝之子戾太子的园邑(《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也就是说,魏收基于《魏书·宗爱传》所述史实,把景穆太子的死视作西汉时期因所谓巫蛊事件而“自经”的戾太子之死的重演。将《宗爱传》“时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与“其戾园之悼欤”的表达结合起来考虑,在景穆太子死于非常这一认识之上,我们还可以推定,景穆太子的死出自太武帝之命。魏收通过微言传递的正是此等信息。这么说是因为,围绕景穆之死的记载相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来说极为特异。比如,当时监国的太子作为总揽朝政的人物,其死亡始末不见于本纪,只在宦者列传中以“时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简单带过;本纪则留下“其戾园之悼欤”这一暧昧表述;在景穆死后仅四天,本纪便记其被匆匆埋葬。
那景穆太子事件会是冤案吗?据史论中“其戾园之悼欤”之语,魏收似乎将其看成与汉武帝时戾太子之死一样的冤案。但同时代的史书《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云:
焘(太武帝讳)至汝南瓜步,晃(景穆太子讳)私遣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云:
子焘,字佛狸代立,年号太平真君。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晃后谋杀佛狸见杀。
据以上记载,景穆太子图谋弑杀太武帝。如此则不能视此事件为冤案。《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宋纪》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六月条袭用了前引《宗爱传》的记述,《资治通鉴考异》卷五《宋纪上》元嘉二十八年六月“魏太子晃以忧卒”条下议曰:
宋《索虏传》云:“......(上引记载)”萧子显《齐书》亦云:“晃谋杀佛狸,见杀。”《宋略》曰:“焘既南侵,晃淫于内,谋欲杀焘。焘知之,归而诈死,召晃迎丧。晃至,执之,罩以铁笼,捶之三百,曳于丛棘以杀焉。”又《索虏传》云:“晃弟秦王乌奕旰与晃对掌国事,晃疾之,诉其贪暴。焘鞭之二百,遣镇枹罕。”此皆江南传闻之语。今从《后魏书》。
此处《考异》以“江南传闻之语”否定《索虏传》《魏虏传》的谋杀说,“从《后魏书》”。不过《索虏传》《魏虏传》毕竟是同时代的史著,如所周知,两传保存了很多超出《魏书》的史实。而且《考异》虽选择“从《后魏书》”,却未对《魏书》所记景穆太子死后四天的匆匆下葬以及“其戾园之悼欤”的表述有所解释。另外,景穆太子丧生的正平元年,已经统一华北的太武帝正倾全国之力南伐。前一年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九月辛卯,南伐军出征,很快于十一月壬子进至徐州彭城城下,十二月丁卯即渡过淮水,接着便攻掠淮西、淮南,该月癸未最终到达刘宋都城建康对岸的瓜步山(江苏六合东南临长江之山)并营建行宫。翌年正月丙戌元旦,也就是景穆太子逝年的正月元旦,太武帝于江岸集结诸军,在对方土地上论功行赏。而次日,正月二日丁亥,他就踏上归途,二月癸未至鲁口(河北饶阳南),景穆太子于行宫迎接,三月己亥车驾返抵京师平城(《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岡崎文夫氏《魏晋南北朝通史》曾论述此间经纬:
太武帝亲自南下,率军至建康城对岸的瓜步,伐苇造筏,示欲渡江。建康戒备森严,沿江六七百里舳舻相列,或谓以之进讨北军,无人响应,整个城市笼罩在危惧当中。然而翌年正月,太武帝从瓜步撤退北还。其理由目前难以确知。魏军于归途中恣意杀掠,丁壮者即加斩截,贯婴儿于槊上,盘舞以为戏。后世叙述蛮族之暴屡屡袭用这种描写。这场战争对北方也造成不小的打击,而南朝因此邑里萧条,史称元嘉之政衰矣。
可见,南伐军的突然撤退令人难以理解。没有史料显示北方的柔然当时存在异动;亦无史料反映南伐军内部突发混乱,比如太武帝卧病而影响到征战。《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保留了一些关于当时事态的记录,其中一段为:
(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朔,焘会于山上,并及土人。会竟,掠民户,烧邑屋而去。虏初缘江举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
据此,北魏的急速撤军也让南朝感到意外。接下来对其缘由做一推测。随着对外征伐的长期持续,人员疲敝、军粮不足等情况的确不难预料。但元旦的论功行赏正值南伐的高潮,即使真的发生以上状况,第二天便匆匆北返仍然十分诡异。这样的考虑再结合上文举出的种种材料,尽管还是不易确知详情,但能推想,留守平城的势力应该出现了某些问题,至少太武帝得到了让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情报。情报内容的真伪姑且不论,但其中应包含如先前《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所见,景穆太子意图弑父的信息。因此,无视《索虏传》《魏虏传》的记载,以其为“江南传闻之语”,对于掌握当时的政治状况来说是不适当的。易言之,综合这些记载将让我们有可能对当时的政治状况进行全面把握。
太武帝与景穆太子之争
太武帝和景穆太子之间为何产生了对立?这是上一节的考察带来的疑问。《宋书·索虏传》提到的景穆太子“私遣取诸营”,或是前揭《资治通鉴考异》引《宋略》提到的“淫于内”,尚无法查明真伪。而《宋书·索虏传》关于太武帝的南伐又有以下记载:
焘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而其士马死伤过半,国人并尤之。
引文所述内容如果可靠,则关系重大。皇帝耽于对外征伐,国人、军队因疲敝而心生不满,这完全有可能将皇太子卷入其中。不过问题还在更深处。接下来通过依次考察废佛前后北魏朝廷内部的争端,以及北魏皇帝与皇太子的关系来解答。
首先关注宫廷内部的争端。《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附恭宗纪》云:
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不可行师。恭宗有疑色。及车驾至姑臧,乃诏恭宗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人之多言,亦可恶也。故有此敕,以释汝疑。”......真君四年,恭宗从世祖讨蠕蠕,至鹿浑谷,与贼相遇,虏惶怖,部落扰乱。恭宗言于世祖曰:“今大军卒至,宜速进击,奄其不备,破之必矣。”尚书令刘洁固谏,以为尘盛贼多,出至平地,恐为所围,须军大集,然后击之可也。......世祖深恨之(未用恭宗之策),自是恭宗所言军国大事,多见纳用,遂知万机。
可见,太武帝曾对景穆太子颇为信任。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太子始总百揆,此后的政治状况对他来说却很不如意。《魏书》卷四八《高允传》云: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浩固争而遣之。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又载:
宋元嘉中,伪太子晃(景穆太子)与大臣崔氏(崔浩)、寇氏(寇谦之)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太武帝)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崔浩像
如上引文所示,景穆太子与太武帝宠臣崔浩不睦。而伴随太子总百揆,与之处在这种关系下的崔浩又提出了灭佛的计划。对于崇佛的前者,该提议无异于否定其信仰,而身居监国之位却在此事中未掌握主动权,这两点都会让景穆太子难以忍受。因此他必将尝试打破这一局面。不过我们知道,废佛还获得了太武帝的支持,此种打破也就变得非常艰险。《魏书》卷四八《高允传》载:
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曰:“......故愿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散。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恭宗不纳。
通观《魏书》涉及景穆太子的史料,其中不少都在展示其作为贤能太子的面貌,上引文是唯一一条叙述其“行为不端”及存在谤议的文字。因此这条材料的特异性引人注目,基于先前考察所揭示的景穆太子所处之状况,可以认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子的复杂动向。而且很有可能,引文的意涵不单单停留在文字表面的“行为不端”。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发生了崔浩被杀事件(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紧接着七月刘宋开始大举北伐(《宋书·索虏传》:“其年,大举北讨......”《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七年七月庚午条:“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北伐。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总统诸军”),又如前所述,太武帝于九月辛卯做出回应,启程南伐并亲临长江。
下面看北魏皇帝与皇太子关系如何。《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提到景穆太子对太武帝的上谏:
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
景穆太子尊崇佛教,上述谏言可以放在其宗教信仰的背景下来理解,而另一方面,引文也展示出他位居监国而总览朝政的政治姿态。这种姿态也可从以下史料窥见。《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附恭宗纪》云:
初,恭宗监国,曾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这则史料不载于《世祖纪》,而是被特意记入《恭宗纪》。因此该“令”应该是在景穆太子的主导下被采取、颁布的政策。据笔者另文研究,均田制、三长制的建立等现象反映了《周礼》被北魏视作国策制定的基准,而这种态势的形成正始于这段时期。反过来再结合景穆太子的崇佛以及反对随静轮宫的营造而出现的人力、财力消耗,可以认为景穆太子作为监国,或者说作为袭太武之迹的未来皇帝,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当明确的政治计划。进而我们能推断,当时太武帝和景穆太子不只在废佛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围绕统一华北以后的北魏如何继续经营,双方之间潜伏着深刻的路线对立。
回过头看,皇帝与皇太子或二号人物之间的对立格局,其实在北魏史上反复上演。因此可以说,这是贯穿北魏的结构性问题,那么根源何在?下面经由考察代表性的案例来尝试解答。早在始祖神元帝拓跋力微的时代(此皇帝号为后世追赠),已能见到北魏史上最初的皇帝与皇太子之争。该案例的梗概为:神元帝先以其子文帝沙漠汗质于曹魏,使其游学中原,在后者归国之际,诸部大人因畏于“若继国统,变易旧俗”而进谗言,遂致神元帝杀害文帝。《魏书》卷一《序纪·神元帝纪》关于此事的部分记载为:
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既而,始祖甚悔之。
此处,皇帝和皇太子或二号人物的对抗图景并未充分显露,更具意义的却是旧势力同皇权之间的倾轧。与之类似的事例在代国时期也能见到,这里仅指出其存在,接下来讨论北魏建立者道武帝时代的案例。道武帝与太子或二号人物之争主要能举出两例,一为建国功臣卫王仪的谋叛,二是清河王绍的弑逆。两个事件的细部因史料制约而有较多不明之处,但起因却很明确,即道武帝以解散诸部为象征的激进改革以及对此的反抗。紧接着这些事例出现的就是本章考察的景穆太子事件。此后,同类案例还可以举出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78)发生的皇太子谋叛,其详情笔者也曾作考察。以上这些事件里,均可以明确观察到皇帝旨在确立以及扩张皇权的行动,而皇太子或二号人物处于微妙的位置。这是因为在与皇帝发生对峙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被卷入反对势力,尽管如此,如果自己能登上帝位,他们也会走上先帝所追寻的道路。
皇帝寻求确立、扩大权力是在中国史上任何阶段都能见到的现象。然而在北魏的场合,这种渴望尤其强烈。原因在于,这是一个胡汉对立十分严峻的时代,皇帝过分支持其中一方,会带来不断分裂其权力和政权的危险性。关于从漠北时期以来,北魏皇权通过登用新人(新附臣民)以谋求其强化与扩张的问题,笔者已作揭示。然而,新人的过量任用以及对其的依赖,会招致旧人(主要为北族)的反弹,甚至带来国家瓦解的风险。反过来,对于正在急速扩张、飞跃式地吸收新人(主要为汉族)的北魏,仅重用旧人,又会造成与朝政现实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深的乖离。是故,虽然皇权的重心不时在旧人、新人之间来回切换,但其注定应从根本上将权威安放于超越胡汉对立的位置。如前章所论,太武帝抱有同胡族的一体感,同时又推行汉化政策,因而是兼具两面的矛盾体。但他作为超越胡汉对立的至高无上的皇帝,这对矛盾其实是联合统一的。实现平定华北后的太武帝,为了因应这一局势,选择摆脱过去作为胡族君主的立场,意志强烈地向着中华皇帝进取,并且试图通过采纳汉族出身的崔浩、寇谦之所推奉的新天师道来达成。自然,这也导致了崇佛的景穆太子以及北族势力的反抗。
在景穆太子之死背后,笔者认为存在上述问题。景穆太子的死,从根本上说,是由太武帝、景穆太子两者在北魏未来发展方针上的差异,和贯穿北魏史的皇权强化倾向及其反动所决定的,某种偶发事件(如前文所论,详情难以确定)充当了导火索。
而且笔者认为,曾与景穆太子对抗的崔浩的死,也跟同样的因素有关,即皇权确立的问题。下一节在整理崔浩事件研究史的基础上,指出疑问所在,进而从皇权强化的角度来探讨崔浩被杀的实态。
围绕崔浩之死
关于崔浩事件,宮崎市定氏有言:
崔浩之诛的缘由固然是国史事件,但根源在更深处。最重要的是其与鲜卑系官僚之间的暗斗。......原来崔浩等人寄心于南朝,视其为正统天子,内心深处终究把北魏当成夷狄。这种态度有意无意地渗入国史的记载,太武帝暴怒的真实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陈寅恪氏也谈到此事件的原因:
然则浩(崔浩)之被祸果以何为主因乎?依《卢玄传》所云,浩之被祸,以“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浩之贵族政治理想,其最不乐者,仅为李訢等非高门之汉族。当时汉人中得鲜卑之宠信者,无逾于浩,此类汉族之汉人,其力必不能杀浩,自不待言。故杀浩者,必为鲜卑部落酋长,可以无疑......
可见,日中代表性学者所得见解一致,说这是当前学界的定论也毫不为过。然而也有持不同立场的研究者。比如牟润孙氏认为崔浩死于其政敌,尤其是景穆太子的谋害。至于陈汉平、陈汉玉二氏,则完全否定成说,认为此事件基本不具有民族矛盾的色彩。但崔浩案的连坐者极多,远超崔氏一门,牟氏的见解与此抵触。考虑到众多的连坐者里大部分为汉人,且不能否认其中有亡命南朝者等史实,陈汉平、陈汉玉二氏的观点多有令人难以赞同之处。不过三位学者的探讨,尤其是二陈的见解,可以促使我们去深入反省过去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矛盾的成说。比如二陈指出,崔浩因直笔被杀,那与崔浩一道直书国史的高允何以得免?这就触及了以往定论的盲点。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定论,基本还是赞成崔浩事件系因民族矛盾而起。只是我认为,在定论之外,还有其他不亚于此的因素在该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而过去的研究没有看重。这个因素就是先前考察的皇权之确立,下面就来具体阐述两者的关联。
崔浩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为北魏统一华北、整备各项制度倾尽全力,堪称北魏前期第一功臣,也一贯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的“史臣曰”云: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这个事件令人难解,遂使魏收有如此之论。查当时史料,崔浩的罪状在同书同传里记载为: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
同书卷四八《高允传》载,该事件发生时,一同编纂北魏国史的高允被敕草诏,其中部分文字为:
敕允为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执允......
据此,崔浩罪在《国记》撰成之际的“犯触”。《崔浩传》又云:
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他还被扣上了“受赇”之罪,不过按照引文所记的调查方式,指控属实的概率较低。而且综合现在我们能掌握的史料,草诏的高允是这个事件里少见的刚直不羁、公平无私之人。他把自己置于险境,掷出“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之语,这让我们想见中国史官以性命守护真相的耿介之风。因而可以推断,崔浩之过正在于“犯触”,纵使“受赇”的罪状确实存在,也不足以将该事件导向如此严重的地步。
那么崔浩事件何以最终发展至如此重大?如前所述,陈汉平、陈汉玉二氏曾提出以下疑问:同崔浩一道直书国史的高允为何免于被诛?接下来尝试考察此点。据《魏书·高允传》,崔浩收监之时,直中书省的高允因其同景穆太子的交情受到保护,翌日与景穆太子一起被太武帝召见。关于三者间的问答,该传载:
帝召允谓曰:“国书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彦海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而臣多于浩。”帝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景穆太子为高允辩护)帝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罪应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不敢迷乱。”帝谓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诘,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时帝怒甚......帝曰:“无此人(高允)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允曰:“......至于书朝廷起动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为史之本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义无独殊......”
可见,与崔浩一样,高允也“犯触”,但他并未被处以死刑。而前文引用《高允传》的记载提到,高允在太武帝面前直陈,“直以犯触”不当构成死罪。因此很明显,“犯触”是崔浩事件的表面原因而非崔浩被处刑的主因。那主因为何?太武帝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其为政奉行法家之流的严酷,大臣犯法亦无所宽假(本纪)。从上引《高允传》的文字还能看出事件里太武帝的激愤之情。可以认为,他的这种个性也起了作用。事实上,其本纪就提到:
然果于诛戮,后多悔之......曰:“......崔司徒可惜......”褒贬雅意,皆此类也。
不过,有大功的重臣及其众多的血亲、姻族、朋党都被处死的主因,只从此处寻求并不妥当。而且细读太武帝赦免高允时的问答可知,太武帝的强直决定也带有政治上的判断。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关于道武帝有如下记载:
先是,有神巫诫开当有暴祸,唯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
据此,崔浩的本籍清河曾遭受北魏的残酷祸害。而如前文所述,崔浩之父崔玄伯内心怀有归阙江南的强烈愿望,笃孝的崔浩心知肚明。在被认为是由崔浩起草的著名废佛诏中有“胡妖鬼”“胡神”等表述,又传递出他的排夷思想。在执笔国史时,崔浩显露了这种意识,招致太武帝的愤怒。这一因素想必是存在的。但高允得免的理由依旧不明。从《高允传》所记问答来看,仅归因于景穆太子的辩护也是不合理的。于此笔者认为,前引文中太武帝以“直”“贞”来高度评价高允,具有重要意味。原本华北的汉族士大夫并不将国初以来的北魏视作正统的中原王朝。实现华北统一后的太武帝时代,汉族士大夫逐渐向承认北魏的方向倾斜,但依然有固守成见者,尤其在名族层中为数较多。《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载: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可见该事件中,与国史编纂无涉的华北高门也被大量族诛。而太武帝在杀崔浩三个月后就踏上了前文所说的南伐之途,根据以上的这些考察,难以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我们在探讨景穆之死时提出,皇权的确立和扩大是关乎北魏国家存立的重要问题。此处,太武帝个人确立、扩张皇权的强烈意志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一方面在华北统一的背景下借崔浩案之机严厉打击不愿承认皇权正统性的华北名族阶层,又以之为起点迈步南伐,力图向全中国夸示其作为中华皇帝的实力。崔浩是整个北魏前期历史上在政策订立、权谋术数方面罕有其匹的人才,而从这一事件中也能窥见将崔氏用作爪牙、榨干其所有价值的太武帝的非凡政治手腕。
对于崔浩事件的实态,过去的研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胡汉对立这一要因,在事件处置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太武帝却被放在次等位置。崔浩案之所以成为如此重大的事件,相比其他因素,太武帝的强烈意志更加不可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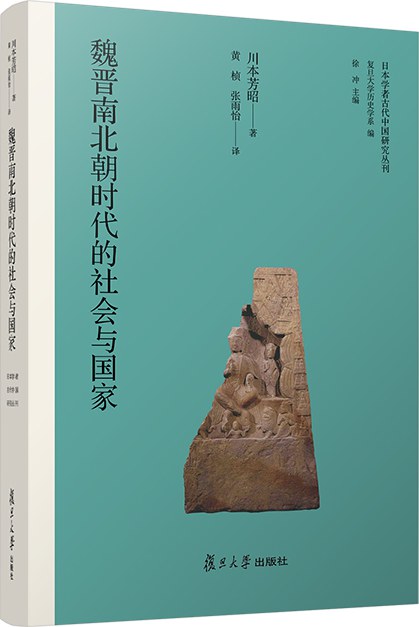
(本文摘自川本芳昭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与国家》,黄桢、张雨怡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