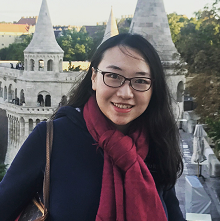出国后,我最怀念的仍然是年夜饭里家的味道|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 | 刘文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在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远离故土家人的游子,或许正在登车返乡的春运路上;也有人忙碌了一整年,想借春节长假去感受不同地域的风俗文化;还有人由于工作不便或亲人不再,选择独自过年。
新的一年就要开启,新生活也终将展开,重建秩序的当下,我们越来越能明显感受到,与年味和家味的重逢。
镜相栏目发起「疫中重逢」主题有偿作品征稿,可以是春节里的日常观察、沿途见闻或人物故事,希望在新的开端之下,记录这个不普通的新年。下文是第一篇作品,作者通过年夜饭串起各种思绪,对家乡菜肴的思念,对父母的挂念,以及疫情期间自己在异国的种种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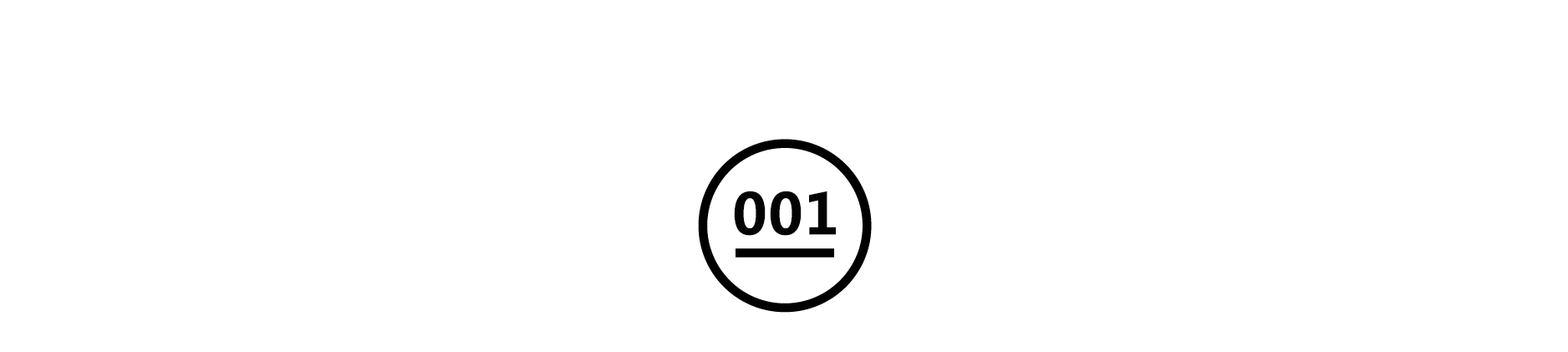
年夜饭菜单
2022年12月底,我忙着研究怎么寄布洛芬回中国,把某书软件上所有能搜索到的攻略都查了一遍,甚至还私信了几个据说能搞到处方药Paxlovid的账号,问他们要价多少,能不能保证货源,一边讨价还价,一边担心被人骗。我的饭友小钰发来微信,问我有没有想好年夜饭的菜谱。
我和小钰也是在某书上认识的,我们在华人社群并不算很壮大、中餐馆也寥寥无几的奥斯汀居住,总是在刷某书上附近的人的时候刷到对方。疫情期间,琢磨菜谱发某书成了我为数不多还能维持下去的爱好,她私信我问能不能约着一起做饭。时间长了,我就成了她想吃中餐时候打牙祭的去处。
2022年即将结束,还有几件不得不完成的工作卡在收尾的关头,但做出来的成果似乎和自己当初设定的目标有所区别。一瞬间,似乎朋友圈里所有人都得了新冠,我牵挂着家中父母的身体,特别是已经九十三岁的外婆。既要告诉他们哪些被转发了很多次的科普视频其实是错误的,哪些关于疫情的传闻其实是谣言;又要替他们在网上找哪些医院能开到Paxlovid这些可能救命的药物。当然也有争执不下的时候,我在微信里努力劝说,打出来“我也是为了你们好”这句话之后,想了想还是删掉,因为我曾经非常讨厌他们对我说这句话。
我最后还是关掉电脑上的word文档和excel表格,打开电子邮件,写下“年夜饭菜单”这几个字。这是我已经去世五年多的爷爷的习惯。他和奶奶住在上海市中心一间老旧的公寓里,客厅那颇有历史感的柜子里塞满了纸片、线头以及他去日本看我姑姑时带回来的免费餐巾纸——最上面一张被摩挲了很多遍,表面变得很滑溜的纸张上写了年夜饭菜单。他总是从七八月份就开始拟定,反复修改,从冷盘到热炒到主食到汤到甜食,洋洋洒洒写了二十几行,划去之后再添上,补充之后又要修改。冷盘是盐水鸭还是酱鸭,卤味是卤猪耳朵还是卤猪舌头,都要反复斟酌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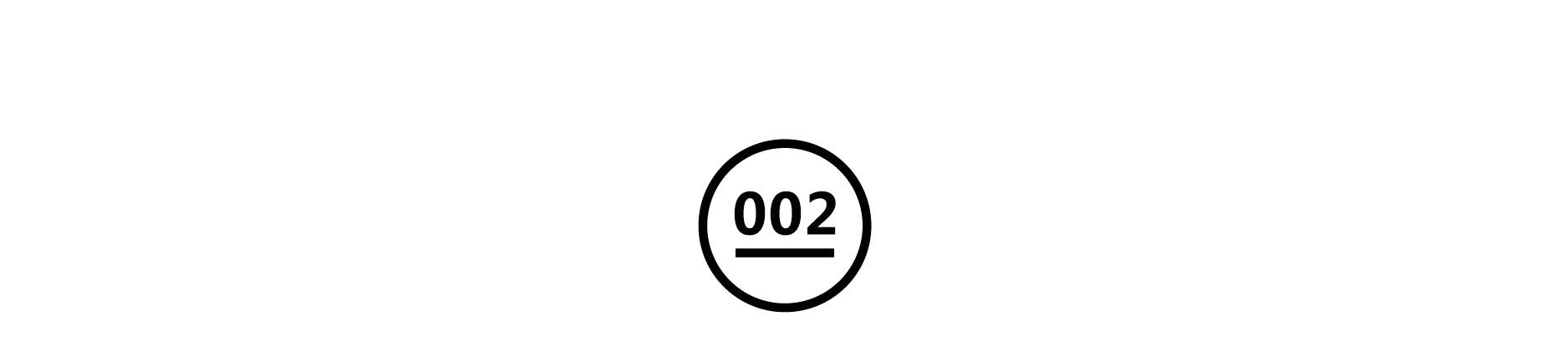
舌尖上的家
这些记忆重新浮现起来的时候,儿时的色彩、质感、声音和气味又重新出现在了眼前。
在大年夜的早上提早给外公外婆拜年,拿到厚实的红包之后,我就立刻坐火车赶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我总是按照上海话叫他们阿爷和阿娘。到的时候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阿爷家不大的客厅里已经挤满了一年也只能见这么一次的亲戚。我的两位伯伯站在走廊里一边抽烟一边用上海话聊天,两位伯母和阿娘则在狭小到连转身都困难的厨房里忙碌,阿爷作为年夜饭菜单的制定者,则像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一样站在厨房的入口处督查,时不时给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听到我们来了,伯母们一边把手在围裙上揩干净一边出来说“马上就可以吃饭了”。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阿爷制定的菜单是一项大工程,最低标准也是“八冷盘八热炒”,接下来还会有几道汤和砂锅及点心。我总是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去厨房打量,如果案板上还有生的鸡鸭鱼肉,则意味着开饭还遥遥无期,可以多吃点客厅里放的瓜子花生糖果和金币巧克力垫垫肚子。如果心灵手巧的大伯母已经开始包蛋饺了,那就离开饭不远了。我最喜欢看大伯母包蛋饺:鸡蛋加上盐和水淀粉打成蛋液,把大号长柄不锈钢汤勺在明火上烧热后,滴几滴油润滑一下汤勺,然后小心地倒入一点蛋液,旋转勺子让蛋液铺匀,接着在勺子的中心位置放入肉馅,过上几秒,赶在蛋液凝固前对折蛋皮,最后用铲子压一下边缘防止破裂。
蛋液接触到汤勺时会发出“嘶啦”一声,很多年之后,我回忆起童年时,常常会想到这轻轻的一声响,伴随着鸡蛋烧熟时有些香甜的气息,还有灶头上预备做蛋饺汤的高汤,煮沸时氤氲在空气中的水蒸气,炒菜锅里的镬气,和碗里已经切好码好的卤味发出来的诱人的酒糟味。那是回忆里又简陋又繁复,又忙乱又热闹的人间烟火气。
年夜饭准备齐全之后,阿爷把原本靠墙放的方桌推到客厅中央,在上面摆上一张巨大的圆台面。小辈们排排坐在木板床上。其他人七手八脚地摆好杯碟碗筷。大人是肯定要喝酒的,小孩子们喝雪碧、可乐、椰树牌椰汁和果粒橙。上海的冬天没有暖气,空调也是好多年后才装的,喝几口下去身体暖起来,大家脱掉厚厚的外套,才终于不会碰着旁边人的手肘。
上菜的顺序也有讲究,第一轮上的是冷菜。一定会有四喜烤麸和如意菜。四喜烤麸是烤麸、金针菇、木耳和花生米过油炒,是我父亲的最爱。如意菜的主角其实是黄豆芽,因为形状像一柄如意,所以过年的时候吃了讨个彩头。冷菜里面也是鸡鸭鱼肉样样齐全。鸡通常是白斩鸡。那段时间上海开了许多吃白斩鸡的馆子,我能够回忆起来的就有小绍兴、振鼎鸡和泰煌鸡。但哪怕馆子再多,要在除夕夜买到白斩鸡,依然要排大长队。摆在年夜饭桌上的白斩鸡鸡皮油光发亮,白嫩的肉里还掺杂着几丝嫩粉色,皮与肉之间还有一层诱人的水晶冻,蘸着用葱姜调过味的甜丝丝的酱油吃下去,肉汁四溢,是我童年时候的最爱。鸭通常是酱鸭,鱼是熏鱼,肉的话,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盆卤味,充满酒味的糟卤,搭配猪头肉、猪舌等等,鲜美入味。
至于热炒,糖醋排骨、红烧肉、红烧大排、红烧素鸡这些一定是有的,都是上海本帮菜浓油赤酱的代表,浓稠的酱汁,搭配绿绿的葱花和白芝麻,吃到嘴里甜津津的。
大人们敬上几圈酒,看一会儿电视里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每到小品的时候,大家都会放下碗筷一起看。赵本山出场的时候,整栋楼都充满哄堂大笑声。再下楼去看有钱的邻居放几轮烟花爆竹,冷风一吹,又觉得有丝丝的肚饿。再走上楼去,伯母已经端出来炸得金黄的春卷。春卷皮炸得又香又脆,边缘微焦,里面的馅是猪肉韭黄馅。蘸一点点醋,用嘴吹几下之后,迫不及待咬下一小口,“咔嚓咔嚓”地响;冬天的韭黄都特别鲜美,滚烫的汁液流到舌头上,只能张开嘴巴拿手在面前扇风,但即使这么狼狈,还是要吃完。接下来就是砂锅里煲着的海鲜汤,猪皮、鹌鹑蛋和鱼丸之外,金黄色的蛋饺是不变的主角。最后一道菜是八宝饭,内里是满满的扎实的豆沙馅,中间点缀了红丝绿丝的蜜饯,最上面再点缀一颗糖渍樱桃。分量足,味道甜,又是主菜又是甜点,每个人都至少要吃一口,同样也是讨彩头的意思。

小时候春节吃的炸春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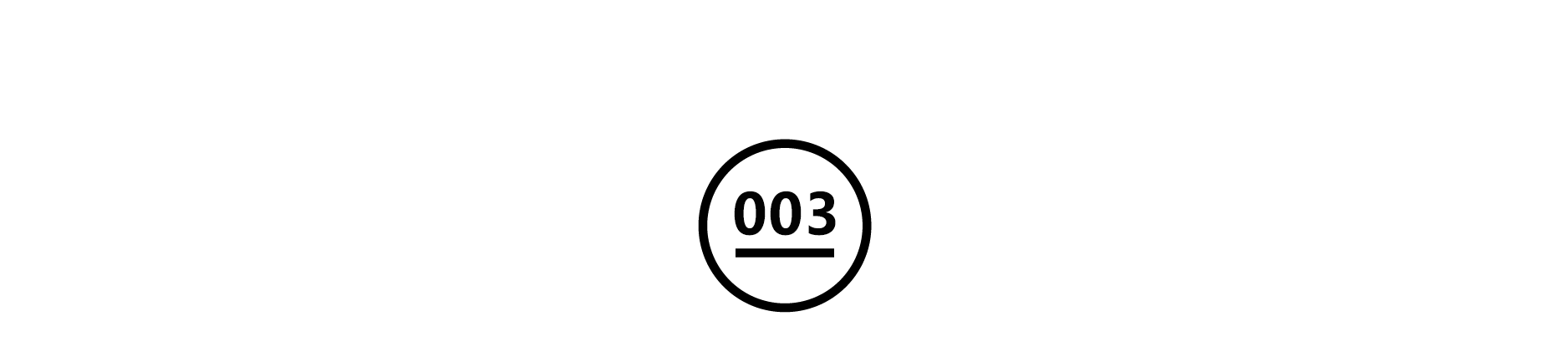
异国他乡
后来阿爷年纪大了,阿娘也去世了,在晚辈们的劝说下,阿爷终于同意到餐厅去吃年夜饭。二伯父一家认识沪上著名海鲜酒楼的主管,可以订到角落里僻静的带休息室和洗手间的豪华包厢,经理亲自来泡茶问好。桌子上的酒从便宜又辣嗓子的白酒变成了红酒和香槟,八宝饭变成了卖相精致的奶油蛋糕,浓油赤酱的红烧肉和葱烧大排变成了放在小巧的蒸笼里端上桌来的粤式小点心和做成各种图案的流沙包,海鲜煲里的猪皮鱼丸和蛋饺变成了海参和鲍鱼。旅居日本多年的小姑姑替年夜饭买单,放话让我们随便点,无论是澳洲的龙虾还是新西兰的牛排,统统端上桌来。酒过三巡,父亲脱掉我给他新买的名牌外套,露出里面穿了很多年的有个破洞的棉毛衫。
刚到美国的四五年里,我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年夜饭这个概念。理由当然有许多。过年的时候通常是学期刚开学,要忙着选课退课,和系主任讨论研究方向和毕业课题,课业进度很快,要看几十上百页的文献。工作之后,年初也总是要制定新年计划、进行年度表现考核、讨论晋升和加薪的时间,同时也是跳槽找新工作的好时机。我所学的专业和所从事的行业都是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华人并不太多,当然也不会在春节的时候放假或者聚会。

疫情得到控制后去海岛旅游
我去美国的时候已经二十六岁,这在我老家已经是早该结婚生子的年龄了。我和家人的矛盾在我出国前一两年达到顶峰,母亲会在聊起某某同学的孩子已经结婚了之后,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从小到大,我和邻居孩子都被放在一个表格里,任由各位家长进行比较,成绩很好的我一度拔得头筹,但因为在婚育上的落后,又成了旁人嗤笑的对象。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也没有稳定的恋爱对象,没有车没有房,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评价体系中,我并不算是一个成功者,但我却不甘心,因此只能跳出原本的文化和评价体系。
初到美国之后,我并没有主动找同校或者同城的中国留学生抱团,而是努力开始做我在国内时并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我和美国同学一起看橄榄球赛,买了学校橄榄球队的赛季通票,还一起攒钱飞去其他城市看季后赛。我参加了学院里组织的各种体育运动俱乐部,从打高尔夫球到拉丁舞,不一而足。周末训练之后,大家常常会到一对住在郊外别墅的兄弟家过夜。每个人都带着睡袋和零食。晚上就在地下室里打电动游戏、玩桌游、看电影。早晨和晚餐都是大家自己做,有时候是煎培根和煎鸡蛋,有时候把罐装番茄拌上牛肉糜和芝士碎,做通心粉,有时候干脆买上几种不同口味的麦片,泡牛奶吃。

疫情之后在巴黎逛菜场准备买菜做晚餐
和朋友聚会的时候,饭常常都是找便宜的地方随便对付一顿,有时候是一起买一个披萨分着吃,有时候花几美金去吃墨西哥卷饼,然后把钱都省下来去酒吧喝酒。大家轮流给所有人买shot,一起举杯喝光。等到实在囊中羞涩了,我们从酒吧出来,在路边找到一美金就能买到一罐啤酒的流动餐车,餐车老板的破旧喇叭放着上世纪的爵士乐,大家拿着啤酒罐子在月光下跳舞,女生们脱掉了高跟鞋举过头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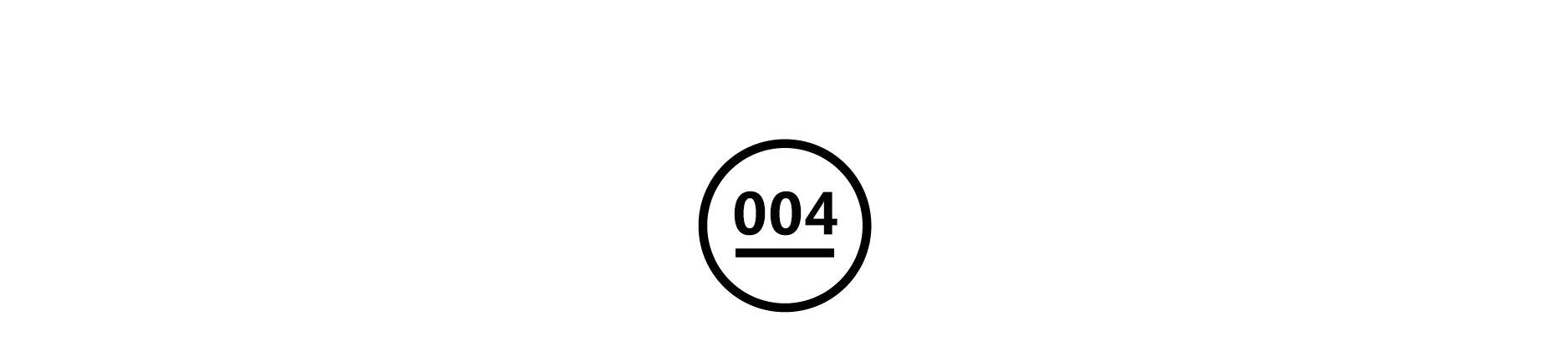
疫情之下
我当然是很享受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的,直到2020年的疫情来袭。那一年的春节,我忙着去各大超市买口罩和消毒水寄给国内的家人,还托熟悉的医生朋友捐赠给医院。其实从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我在美国的超市也见不到口罩了,但还是强迫症一样,开车出去,只要看到路边有超市或者药房,都会停车进去查看一番。我在美国的公寓里,电脑上放着国内的新闻,打开了上百个页面,全是各大媒体的报道。手机里各种家人群亲戚群朋友群读者群都不间断地有新消息,没有人知道这个病毒致死率多少,有什么药能治疗,会持续多久。国内的家人焦虑得睡不好,我也一样失眠。有一天凌晨四点,我打开YouTube想随便看点什么,突然看到了很多年前收藏过的“康熙来了”中介绍美食的视频。
那一天,我再次点开了那个视频,在多年后看到明星们七嘴八舌地介绍着卤肉饭、猪排饭、猪脚饭、牛肉面,突然获得了久违的平静。
很快,新冠疫情传播到了美国,我和先生搬到了离市中心稍远一些的房子,开始尽可能不出门,靠超市的送货app过活。我在江苏的父母与外婆也因为疫情被困在家中,由于快递服务的不通畅,连网购都很困难。好在他们原本就有囤货的习惯,家里有几十斤面粉,还有腊肉和羊腿。母亲开始研究各种能够用面粉做成的点心。她和面、剁馅、做皮冻,包出来各种口味的包子。又摆弄着面团,刷一层黄油,涂一层蛋黄,匀撒糖霜,做成各种口味的蛋糕和蛋挞。


疫情被封控在家母亲做的包子和点心
“馋不馋?”他们把午饭和晚饭的照片发到微信里问我,也顺便问我好不好。我就回答一句“好的”,或者一个竖着大拇指的表情符号。其实也算不上怎么好,但凭良心讲又不是很糟糕。我认识的人里面,有得了新冠进医院的,也有康复了之后一两个月都咳嗽气喘的,还有人失去了亲人,在众筹网站上面筹集葬礼的费用。但我和母亲从小就不是那种无话不说的关系,内心的情绪和感受也不能开口尽述。我当然也知道他们隐瞒了很多焦虑和苦闷的情绪,因为不想让我担心。后来有一次,母亲发来糖醋排骨的照片,说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了,年夜饭上面,也专门紧着这一道菜吃。我突然想,或许我也可以做一道糖醋排骨?我随口问她怎么做,她似乎特别兴奋,很快发来食谱,又发了自己做菜的视频,还不断问我做得成功吗,味道如何。
把排骨洗净之后用冷水煮开,加入葱姜和料酒去掉血腥味。在铸铁锅里倒入油和白糖,用小火炒出糖色。然后倒入用料酒、生抽和醋调制而成的酱汁,放入八角和香叶。我看着酱汁咕噜咕噜地冒着小泡,闻着肉的香味慢慢地氤氲在空气中。一顿饭做了好几个小时,但我突然获得了久违的平静。我难得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看手机,也没有不断刷新网站上和疫情相关的新闻和数据。我想到了阿爷家那间逼仄的厨房,墙壁上因为经年的烟熏火燎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家里的女眷们在里面像流水线女工一样熟练地挥动着刀和锅铲,然后一道道浓油赤酱的菜就被盛在不成套的有些还磕了边角的大海碗里端到斑驳陈旧的大圆桌上。

按照父母的食谱做的糖醋排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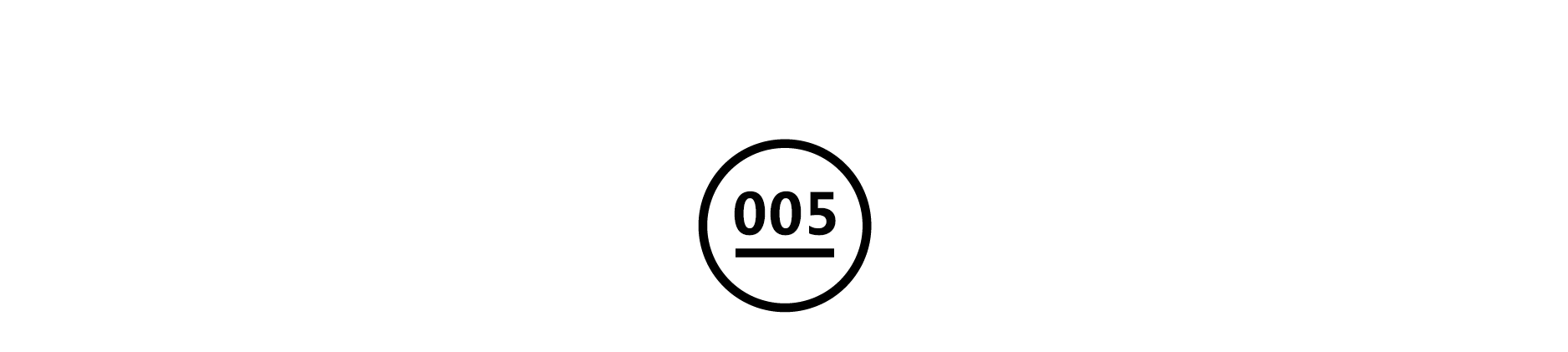
何以为「家」
那段时间,我在某书和某音上看到许多疫情期间回归家庭变成大厨的视频。原本我对这样的内容嗤之以鼻。我向来自认是新兴的独立女性,觉得女性应该从做饭洗衣服这样的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去挑战事业上的高峰,去世界的各个角落经历奇遇和冒险。我的闺蜜们也基本都是很有野心的事业女性,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吐槽那些要花费大量功夫的菜肴。为什么要花一整个白天煲汤呢?为什么要花心思去农市场上选购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呢?为什么要一顿饭做三四个菜,然后光洗菜洗碗就要耗费几个小时?吃快餐或者沙拉,然后省下时间去健身,去阅读,去旅游不好么?当我自己开始做饭之后,却觉得做饭使人平静,有点像冥想,也有点像和心理治疗师对谈:在纷繁芜杂的世界里,不要去关注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而是专注于眼前的食材该如何处理,如何调味,酸甜苦辣咸应该以哪种方式组合在一起。而做饭所带来的慰藉也是立竿见影的,不像很多其他的事情,即使努力也可能白费功夫,做出美味的菜肴,和喜欢的人一起分享着吃到肚里,这样的饱足感和满足感是实实在在能够体会到的。
过去的三年里,因为疫情,中美之间的航班减少了很多,而机票价格在许多时候都是三四万甚至八九万人民币的天价。即使买到了机票,也常常会因为核酸检测拿不到绿码或者航班因为熔断临时被取消而不能成行。再加上直到2023年1月8日之前,从美国回中国都需经历少则七天十天,多则一个多月的隔离,作为年假并不多收入也有限的打工人,回国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我和父母之间的见面机会仅限于小小的手机屏幕上的微信视频。每次聊天,讨论一下身边发生的事情,总不免会谈到许多令人沮丧的故事:熟悉的人里面,有家人得了新冠病重或者去世的,也有疫情期间被裁员或者公司倒闭的。再聊下世界新闻,也并不乐观:通胀高企、经济下行、全球疫情、战争,不一而足。对话的氛围逐渐低沉之后,我那善于调节气氛的父亲总是会让我看看他们最新做的菜,母亲则献宝一样去厨房端来各式各样的菜肴。既有我从小就喜欢吃的红烧排骨,也有他们最新开发出来的蛋黄酥这些精致的点心。我们讨论菜谱也讨论食材,他们在2022年的三、四月份和十一月份的时候,几度被封控在公寓里不能出门,没有办法去买到新鲜的春韭和太湖里的河虾,而我整个2020年直到2021年3月打完疫苗之后,都没有去过超市和餐厅。我们研究如何种植葱、香菜这些常用的调味料。他们是经历过物资真正匮乏的年代的,办法比我多,对苦难的耐受力也比我更强,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网购的食物和社区的免费蔬菜包迟迟不到,也能宠辱不惊。后来终于收到免费的蔬菜包,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们正好在准备午饭,桌子上有一盆调好的三鲜馄饨馅料,砂锅里有煲好的高汤,紫菜、虾米和鸡蛋皮码好摆在桌子上。他们拿一张馄饨皮,飞快地包好,蘸一点水封上口子,看得我口水也要滴下来。我想,虽然世界变得更加分裂,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变得更加困难,但好在口腹之欲总归还是相通的。
2021年的年夜饭,我已经可以做出葱油拌面、葱烧大排、雪里蕻竹笋炒毛豆等几道像样的上海菜。彼时,疫苗已经普及到每个城市。先生家中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已经打完了两针,一块大石头算是终于落地。我们站在厨房里,我负责给已经敲得很薄的大排裹上淀粉、蛋液和白胡椒粉,他负责将大排在热油中煎至双面微微变色,再快速放入已经热好的锅中裹上葱油味道的酱汁翻炒均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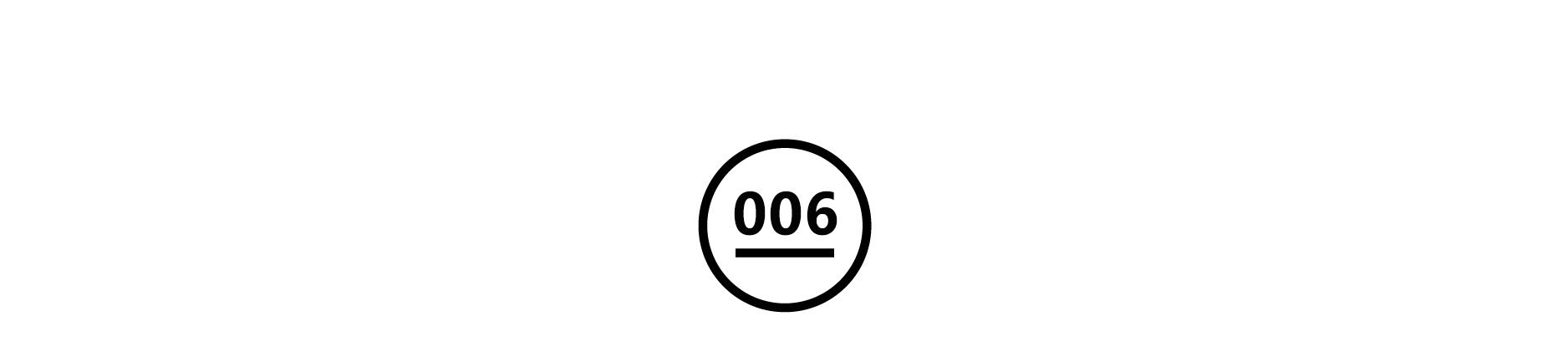
与年味重逢
2022年的年夜饭,奥密克戎的高峰逐渐过去,我终于出了一次差,也见到了在网络上已经很熟悉、但现实生活里还没交集的新同事。因为疫情两年没见的挚友飞来看我,我们吃了一次火锅,又吃了一次烧烤。像是回到了没什么钱但是又特别容易饿的大学时光。这是挚友和她的丈夫在疫情之后第一次出远门,他们穿上了两年前就买了但一直没机会穿的新衣服,光鲜亮丽地挽起袖子,在漂满红油的汤里捞牛百叶和鱼丸吃。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锃亮的皮鞋踩在雨后的小水洼里,往滋滋冒着热油的羊肉串上撒大把的辣椒粉和孜然粉。挚友和我在过去的十年里一起走过十几个国家。我们把大半工资都花在这上面,也没攒下多少钱。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不要结婚,也不要买房,而是每过几年就换一个国家住,和各种各样的人谈恋爱。等我们老了,就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她也没有想到我会有朝一日沉迷于“洗手作羹汤”之中。我们讨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轻易买到机票回国去看看已经老迈的父母。挚友买过两次机票,一次因为自己得了新冠而作罢,一次遇到航班熔断,补签了几次就错过了年假。或许要再过几个月?或许要再过一两年?谁都不能预测。我们说着说着就觉得忧愁,但食物叫人平静。

2022年春节和朋友一起吃火锅

2022年春节的烧烤
“今年的年夜饭吃腌笃鲜好吗?”我发短信给小钰。虽然腌笃鲜并不常在年夜饭上出现。这是初春最令人期待的时令菜。三月初,天气还没完全回暖,但万物已经悄然复苏,春笋也在这时候出土。对讲究要吃当季新鲜食材的外婆来说,清香脆嫩的春笋是不能错过的食材。我们家离郊区的农田很近,外婆有时候骑车去找农民买新鲜的笋,也会带上我。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油菜花还未开,柳枝刚刚垂髫,一切都是淡淡的青绿色,裹挟着微微的春风,带着薄薄的晨露,一切都充满了生机。百叶则是用我老家的特产横山桥百页,柔嫩味美,比一般的百页稍厚,可以吸饱汤汁,再加上晾了一整个冬天的咸肉,新鲜的排骨,放入几许姜片之后细火慢炖,熬出的汤雪白醇厚。冬天是我最讨厌的季节,寒冷逼仄,昼短夜长,出行又不方便。童年的时候,吃过一碗腌笃鲜,然后天气也开始变暖,日头也开始变长,出门也不用裹着围巾帽子,体育课也重新回到操场上。
今年年夜饭虽然是冬天,在美国也没地方去挖新鲜的笋,只能将就于超市里已经处理过的煮熟了的日本笋。但总觉得很契合喝一大碗腌笃鲜的心情。回国的机票终于慢慢开始降价,父母亲和外婆也至今都没感染新冠,经济虽然不如从前,但我至少也还有工作。时至今日,如果要抱怨便显得矫情,只能向前看,觉得2023年会比之前三年好一些,生活能重新焕发出一点生机来。
我告诉了父母自己要做腌笃鲜的计划,他们开始传授各种要领和心得给我。母亲从小就喜欢控制我生活的一切,而我怎么都无法符合她心目中的要求,时间长了就有了逆反心理,她给的意见一概不听。但唯有烧菜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流心得。我提早从卖中国零食的网上预订了一大只金华火腿,这只火腿终于在春节前一周漂洋过海到了我家门口。打开油汪汪的包装纸,熟悉的咸香扑鼻而来。
小钰说,要写一副春联给我作为蹭饭的礼物。“就写‘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吧!”我回复她。
别再提那思念之情,着眼当下,多吃口饭保重身体。这是多么庸俗又多么崇高的愿望啊。
欢迎继续关注「疫中重逢」专题:

海报设计:祝碧晨
投稿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投稿请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