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切斯瓦夫•米沃什依然重要?
原创 托尼·朱特 三辉图书

《灰烬与钻石》剧照
为什么切斯瓦夫•米沃什依然重要?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穆尔提丙药丸”,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凯特曼”。
文/托尼·朱特
译/何静芝
节选自《记忆小屋》
几年前,我曾赴波兰与立陶宛的边境小镇克拉斯诺格鲁达,参观经过重建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祖宅。当时,我在边境基金会主席克日什托夫•切泽夫斯基(Krzysztof Czyzewski)家借住,该基金会为见证两地冲突史而建,旨在帮助当地人重建友好关系。正值隆冬,放眼四野一片雪白,偶尔可见覆有冰雪的树木、电杆聚在一处,标出国境线。
主家兴味盎然地谈着在米沃什祖宅举办文化交流活动的计划,我却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里:70英里外的皮尔维斯基(立陶宛),是我姓阿比盖尔的父系亲人生活过并死去(有一些死在纳粹手里)的地方。1891年,我们的亲戚梅耶•伦敦就是从那附近的一个村子移民去了美国;他曾是第二个入选美国众议院的社会党人。1914年,一群无耻的纽约犹太富人和一帮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将他逐出了众议院;前者讨厌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后者则因为被他多次公开质疑自己的活动而深感受到妨碍。
对米沃什来说,克拉斯诺格鲁达——“红土”——是他的“原乡”(波兰语的原著名就是Rodzinna Europa,译为“欧洲故土”或“欧洲的家”更为妥当)。而我凝视眼前这片了无生气的雪白大地,却只能想起耶德瓦布内、卡廷和巴比亚——三处离得都不远——不禁也想到我自家的黑暗往事。克日什托夫•切泽夫斯基当然知道这一切:事实上,正是由于他,扬•格洛斯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纪录才力排众议得以在波兰出版。不过,因为诞生过波兰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此地萦回不去的悲剧气氛似乎得到了一定的消解。

扬•格洛斯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纪录指的就是这本《邻人》。作者: [美] 杨·T.格罗斯 译者: 张祝馨 出版: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米沃什,1911年生于俄属立陶宛。事实上,正像许多波兰文学家一样,从地理划分来看,他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波兰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是尚在世的波兰大师级诗人之一,出生在乌克兰;耶什•杰德罗耶茨(Jerzy Giedroyc),20世纪波兰最主要的流亡文学家,和波兰19世纪文学复兴时期的标杆人物亚当•密茨凯维奇一样,出生在白俄罗斯。尤其是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是个汇集了波兰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犹太人和其他各地区人民的大熔炉。(以赛亚•柏林和哈佛政治哲学系教授朱迪丝•施克莱都出生在附近的里加。)

切斯瓦夫•米沃什 AP Photo/Jim Palmer
米沃什在战间期的波兰共和国长大,捱过了此后的割占时期,他身为新共和国的文化大使被送往巴黎时,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1951年,他彻底投奔西方世界,并于两年后出版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被禁锢的头脑》。该书不断再版,在描绘斯大林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诱惑,或更普遍地说,在描绘权力和集权主义对整个知识界的诱惑方面,迄今还没有哪一本书比它更深刻、更经得起推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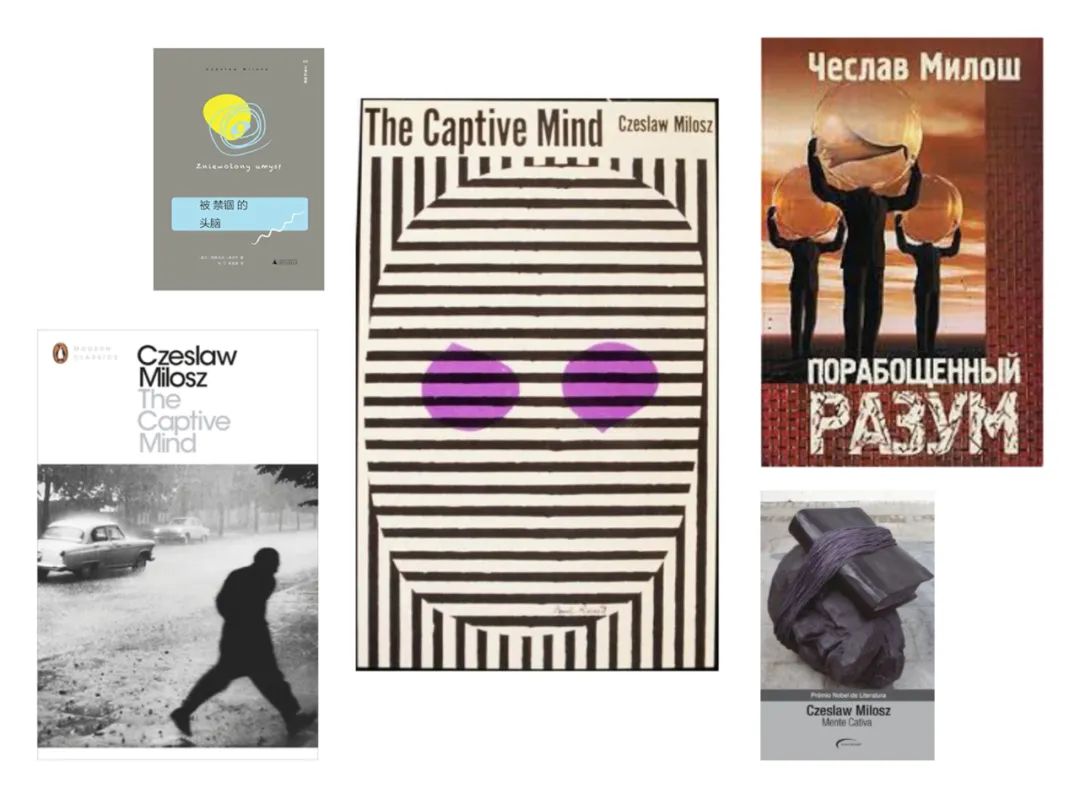
一些版本的《被禁锢的头脑》
米沃什研究了四个同代人,阐述了他们如何在自我欺骗中从自主走向服从,强调了一种被他称为知识分子对“归属感”的需求。他的研究对象中,耶日•安杰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和塔杜施•鲍罗夫斯基对英语读者或许并不陌生,前者是《灰烬与钻石》(Ashes and Diamonds)的作者(由安德烈•瓦依达改编为电影),后者就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焦灼往事写就了《毒气室往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This Way for the Ga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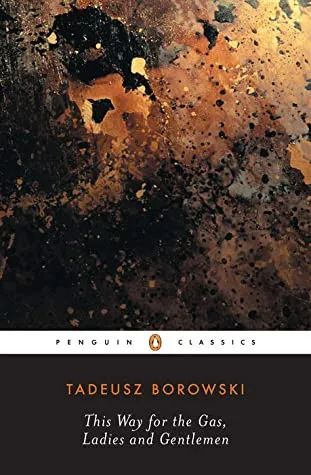
作者: Tadeusz Borowski 出版社: Penguin Classics
但《被禁锢的头脑》之所以令人难忘,却是因为以下这两个意象。一是“穆尔提丙药丸”(“Pill of Murti-Bingˮ)。这是米沃什在看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科列维奇(Stanisaw Ignacy Witkiewicz)所写的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小说《永不满足》(Insatiability,1927)时,偶尔读到的。在这个故事中,即将被一群亚洲游牧部族征服的中欧人,集体服下了一种小药丸,从此再没有了恐惧和焦虑;药丸的松弛作用,使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是愉快地接受了新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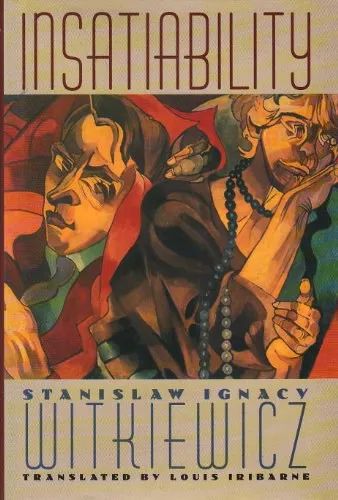
作者: 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 出版社: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二是“凯特曼”的意象。“凯特曼”这个词从阿瑟•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的《中亚的宗教与哲学》(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of Central Asia)一书中来,书中这位法国旅人记叙了在波斯国观察到的一种“表里不一”的现象。那些将“凯特曼”内化于心的人,能够在自身的言论与信仰相左的状态下生活,一边游刃有余地适应每一个新统治者的要求,一边坚信自己仍保有自由人的自主性,或至少仍保有自发选择服从他人理念和裁决的人的自主性。
用米沃什的话来说,凯特曼“解除了心理负担,滋养着意淫之梦,使四面竖起的牢墙,皆化为令人慰藉的失神幻想的机会”。写作却避不示人变成了内心自由的象征。读者迟早会理解凯特曼的,只要他们有朝一日能读到他的作品。
东欧知识分子普遍恐惧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对其艺术家和学者的漠不关心。他们说,宁与睿智的恶魔打交道,也不理睬善良的白痴。
在凯特曼和穆尔提丙药丸之间的篇幅里,米沃什还对政治同道者、盲信的理想主义者和随波逐流的犬儒主义者的心理状态做了精彩的剖析。他的文章比阿瑟•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深刻,又不似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那样逻辑艰深。我曾在多年来自己最喜欢的一门课上讲过它,这门课主要研究中、东欧散文和小说,除米沃什外,还讲到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伊沃•安德里奇、海达•科瓦丽(Heda Kovály)和保罗•果玛(Paul Goma)等作家的作品。
然而我发现,虽然昆德拉和安德里奇的小说、科瓦丽和伊芙吉尼娅•金斯伯格(Yevgenia Ginzburg)的回忆录在题材上都很陌生,美国学生却能读懂,可《被禁锢的头脑》则常让他们费解。米沃什以为他的读者凭借本能就能把握那种信徒的心理状态:那些归顺历史潮流的男女,虽然体制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他们却要向这体制看齐。1951年的当时,他会认为这种现象——无论其成因是法西斯政体还是其他政体,抑或是任何别的压迫性政治体制——谁也不陌生,当然有充分的理由。
70年代,我第一次给向往成为激进派的学生们讲这本书时,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解释为什么“被禁锢的头脑”不好。30年后,我年轻的听众们彻底一头雾水:全然不理解一个人何以将灵魂出卖给一种信念,更不要说是压迫人的信念了。到了世纪之交,我的北美学生几乎无人见过马克思主义者。为世俗信仰放下个人利益已经超出他们的想象范围。在授课之初,我所面临的挑战是解释马克思主义如何破除一个人的幻想;到今天,仅仅是说清幻想本身,就已经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代学生看不出这本书的意义何在:整件事看来毫无意义。镇压、受难、讽刺甚至宗教信仰,这些他们尚且可以领会。但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催眠呢?米沃什身后的读者们的费解,恰恰就是他曾精彩形容过的西方人和政治移民的费解:“他们不懂一个人如何付出——那些国境外的人们,他们不会明白。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换取了什么,又以何种代价才将之换来。”
也许他们真的不懂。但世间并非只有一种禁锢。就在几年前,乔治•W.布什疯狂鼓吹战争时,知识分子们不正是六神无主地纷纷用起了凯特曼吗?他们中没有几个会承认自己赞赏总统,更不要说去赞同他的世界观。于是,这些人一边与他为伍,一边坚持保留个人观点。后来,意识到大错铸成后,他们又纷纷将矛头指向行政部门的失职。实际上,他们是以凯特曼式的自我辩护,骄傲宣称“我们犯错犯得对”——这不正像是法国政治同道者们自我辩护时所说的“宁肯跟着萨特错,不愿跟着阿隆对”吗?

布什避过伊拉克记者敏达哈·扎伊迪扔的鞋(2008年12月14日)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如今,我们仍然能够听到围绕反对某些极端主义,企图重燃冷战战火的余音。但这还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精神禁锢。当代对“市场”的信仰——盲信它的必然性、进步性和历史经验——与19世纪的景况同样惨烈。倒运的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浦•斯诺登在1929年至1931年的任期中,面对经济萧条束手无策,宣称反对资本主义必然规律毫无意义,正是出于与之相同的盲信,今天的欧洲领袖为安抚“市场”,也都纷纷一头扎到财政紧缩中去。
然而“市场”——正像“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只是个抽象概念:一方面很讲道理(其论据所向披靡),一方面又无理可讲(它不容人们质疑)。它有它的忠诚信徒——和概念的创始人相比,这些信徒不过是一群庸碌之辈,只是在影响力上不逊于先人罢了;有它的支持者——尽管暗自质疑其原则主张,却继续拥护鼓吹,而没有试着另寻他法;也有它的受害者,尤其在美国,许多人都已老老实实吞下“药片”,集体颂扬市场主义的优点,尽管这些优点永远不会给他们带来丁点儿好处。
最主要的是,人民越是集体丧失另辟蹊径的想象力,就说明他们被一种意识形态束缚得越紧。我们对无节制信仰市场自由化所造成的损害都很清楚:直到最近还仍在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范围内严格执行的“华盛顿共识”——强调加强财政紧缩、私有化、低关税及宽松管制——已使百万人口失去了生计。同时,严格限制救治型药物买卖的“商业条约”,也已经导致许多地方的人均寿命出现了大幅下降。然而,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不二箴言所说的那样:“我们别无他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正是在与这相似的“舍我其谁”氛围中,出现在了它的信徒面前,且也是因为历史没有明确指出其他出路,致使苏联以外大批斯大林的拥护者变成了精神上的俘虏。然而,直至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付梓之后,西欧仍有知识分子在探讨几个很有希望的社会模型——比如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和以规范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民主变体。如今呢?除了个别凯恩斯主义者还在底层发表异见,所有人都被资本主义收编了。
米沃什认为:“东欧人很难不视美国人为小儿科,因为美国没有经历过什么足以让他们明白个人判断不过是个人思考习惯之产物的事件”。确实如此,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东欧在面对单纯的西方世界时,至今仍抱着怀疑态度。然而在面对新时代的合一运动(注:原指19世纪初,欧洲发起的一项旨在将现代基督教内各宗派和教派重新合一的运动。此处隐射所有价值观、所有主义都被“合一”,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时,西方和东方的公共言论无不自发地呈现出了同样的谄媚态度,没有哪一方是“单纯”的。像凯特曼一样,他们心中明白是非,却不愿当“出头鸟”。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共产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共同点。距离米沃什出生100年、他最重要的文字出版57年的今天,米沃什对谄媚的知识分子的指控,正前所未有地振聋发聩:“他最大的特点,便是他对自己思想的惧畏。”
本文作者 托尼·朱特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重估价值》《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作者: [美] 托尼·朱特 译者: 何静芝
出版: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列选《纽约时报书评》年度瞩目之书
◆一部映照世纪浪潮的知识分子回忆录
◆托尼·朱特最私人的回忆录,新增朱特之子关于父亲的纪念长文
本书是托尼·朱特罹患“渐冻人症”后口述的回忆录。在一个个无法动弹的寂静黑夜里,朱特以空间为线索搜索、整理了过往的记忆,筑成了一栋“记忆小屋”。他坦言,病中的写作基本上来自对记忆小屋的夜访。他有时关注小事,描写祖母的犹太料理、伦敦的绿线巴士、瑞士的小火车。有时放眼大千,论及西欧战后一代闹剧式的革命,时代的思想禁锢,以及自己对政治的观察与参与。这些文字在动人与锐利、私人性与公共性、具体发生的历史与身处其中的个体感受之间穿梭,追索的既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历程,也是20世纪的复杂历史。
编辑|艾珊珊
原标题:《被禁锢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