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勤者欢喜,善业成佛——追思霍旭初先生

克孜尔石窟——霍旭初先生长年工作的地方
2022年10月29日,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霍旭初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享年88岁。因为此前已经知道他住进医院,后来又进了重症监护室,心里有些准备。我在听闻这个消息后,马上推了一条微信:“霍旭初先生今天凌晨神升净土,他对龟兹佛教、龟兹石窟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热爱新疆文博事业,对我们的龟兹石窟题记调查研究给与最大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虽然他已功德圆满,但我们还是倍感悲痛。”当时乌鲁木齐还在封控的状态下,丧事从简。
12月16日,新疆文化和旅游厅、新疆文博院等单位联合举办“霍旭初先生追思会”,又勾起我的很多回忆。我在会上做了简要的发言,因为时间有限,未得发挥。会后将思绪整理成文,让自己的想法不要因为发言时的激动而凌乱。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所覆盖的学术领域内,龟兹学独当一面,而霍旭初先生就是龟兹学领域的中流砥柱。与敦煌、吐鲁番相比,龟兹也是一个佛教圣地,同样富有丝绸之路的城市风貌。但龟兹地处西域北道,地理范围要比敦煌、吐鲁番大得多,因此文化内涵也不一样。龟兹是小乘佛教的中心,与敦煌、吐鲁番的大乘佛教有所区别;同时当地的通行语言是龟兹语(吐火罗语B),佛教僧团也通行梵语,这和敦煌、吐鲁番以汉语为主有所不同。此外,龟兹的音乐舞蹈、音乐绘画、风土人情,也有很多特色。霍旭初先生从艺术的角度开始他的龟兹学的研究,先后主编《新疆壁画全集·克孜尔石窟》(三卷本),又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1994年7月出版了专著《龟兹艺术研究》,收录了有关龟兹石窟艺术和乐舞艺术的主要论文,表明他在龟兹学的多个方面都有所贡献。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龟兹学的主流是石窟寺研究,这一领域历来号称难治,难治的根源在于佛教问题。不同时期的洞窟是根据什么佛教思想,根据什么佛教经典,根据什么佛教粉本开凿和绘制出来的,要弄清这些问题,佛学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关键。有识于此,霍旭初先生多年来一直进行龟兹佛教的深入研究,并结合佛教思想来解说洞窟壁画,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最为丰富,先后汇集在2002年出版的《考证与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2008年的《滴泉集——龟兹佛教文化新论》、2009年的《西域佛教考论》 、2013年的《龟兹石窟佛学研究》等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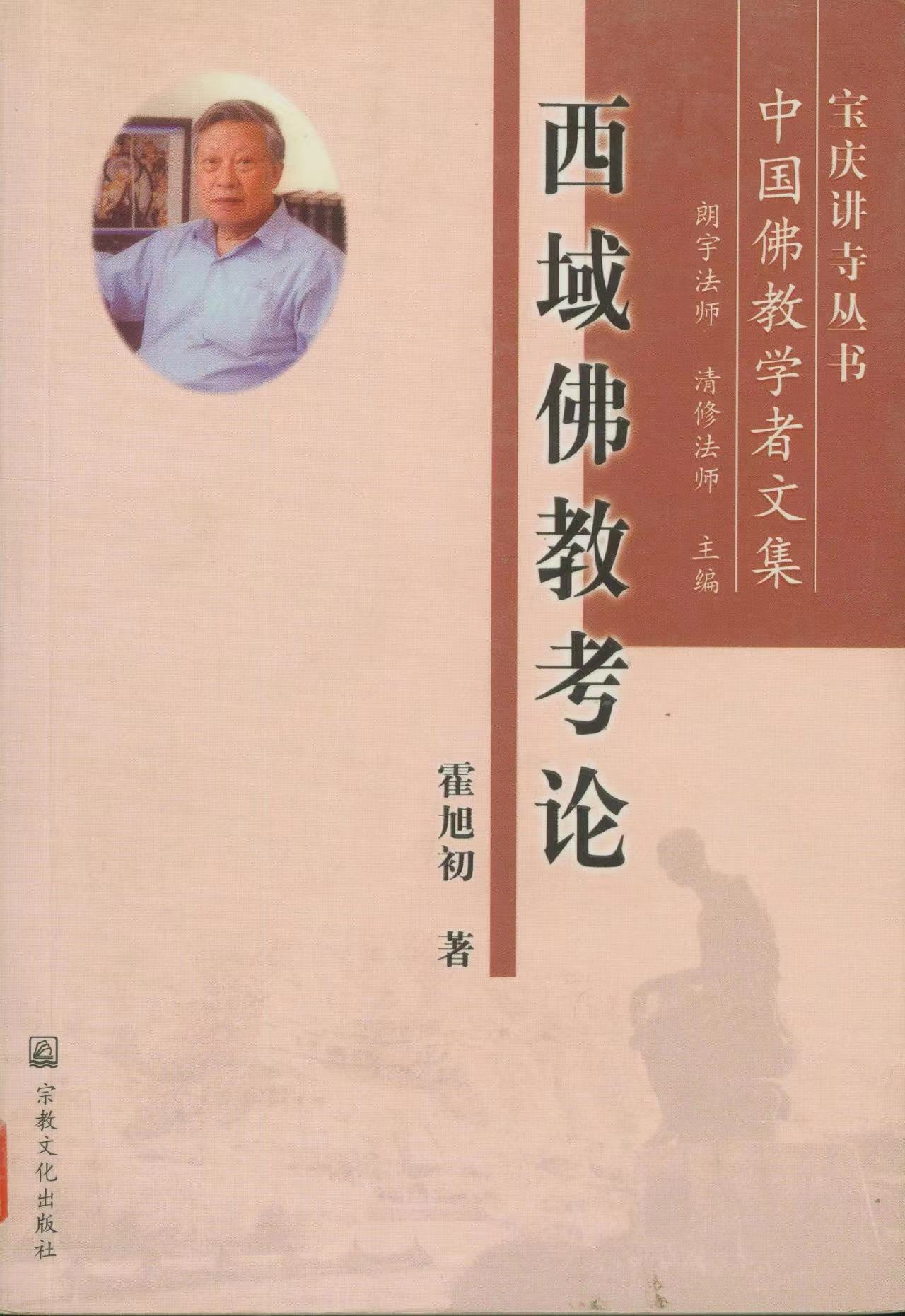

我还想说第三点,就是龟兹与敦煌、吐鲁番相比,要偏僻得多,与学术中心距离遥远,因此与外界的学术联系和合作,是推进龟兹石窟研究的一条正途。霍旭初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进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或龟兹研究院与外界的合作,不论国内的合作,还是国际的交流,他都热心支持,坦诚以待。1994年,他曾推动并主持“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把国内外许多学者汇聚到克孜尔石窟,交流学术,讨论异同。1997-1998年,又两度推动举办“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国内外一批学者前往库车,深入讨论安西大都护府和西域文明问题。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当年的选题,不能不佩服霍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远见卓识。
1998年,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雅尔迪兹来克孜尔石窟访问,受到霍旭初先生等龟兹石窟主人们的热情接待,从此开始了以赵莉为主力的合作调查流失海外龟兹壁画并复原的工作。2009年以来,我和赵莉主持的“龟兹石窟题记”项目在艰难中进行,其间获得霍先生的大力支持,应当说,没有霍先生的支持,我们的项目是无法完成的。


回想我与霍旭初先生交往,很多往事涌上心头。
2000年6月底,我们一起在敦煌莫高窟参加了“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较多时间交谈。还记得某日晚上在石室书轩门前聊天,他极力推荐他的学生彭杰考我的研究生,我当时也答应了,但不知道后来什么原因阴错阳差,彭杰一直没有能够到北大读书。我想霍先生希望有弟子能够到国内一流学校,受正规的学术训练,给龟兹地区的学术研究延续血脉。
一个月后的7月25日,我们又一起到了香港,在香港大学参加饶宗颐先生主持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我记得霍旭初先生发言介绍新发现的阿艾石窟,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关注,因为这是极为难得的龟兹石窟新发现。这个石窟为典型的唐朝汉风石窟,霍先生就此发表过数篇大文,阐发其价值和意义。
另外一次与霍先生稍长时间在一起的机会,是2002年9月去柏林开会。会前我为了争取霍先生等新疆学者能够多几位参加这次柏林的盛会,曾与德国方面反复交涉,我特别强调:新疆的学者更需要出来看看柏林的藏品。其间霍先生曾来电话,说新疆方面的官员怕柏林会是纪念德国探险队的会,将来不好说,所以向文化部申报,他担心这样一来大家都去不成了。我只能说,希望大家最后都能一起去柏林开会。好在9月8日上午,我在北京机场与霍旭初先生等新疆来的七位学者以及李崇峰会合,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 898航班于10:35起飞,当地时间14:50到阿姆斯特丹。转乘19:15的KLM 1835航班,20:35到柏林,雅尔迪兹馆长亲自来接霍先生等新疆一行人,可见她们对霍先生等的到访十分重视。我们中国学者和俄罗斯学者一起,住在洪堡大学招待所,开会地点则在达勒姆区的印度艺术博物馆,距离很远。这不是坏事,可以让我和霍先生等人有充分的交谈。9月9日上午,“重返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的百年研究”国际学术会议(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在印度艺术博物馆开幕。9月11日上午,霍旭初先生发言,讲克孜尔石窟问题;赵莉则讲德藏克孜尔壁画的原位问题,都很精彩。会议结束后,霍先生和赵莉留在柏林一段时间,仔细考察德藏龟兹石窟壁画,我因有课而随即回国。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就是在这次柏林之行中,面对大量带有龟兹语题记的壁画,我们开始有了合作整理龟兹石窟题记的想法。

2002年,荣新江先生与霍旭初先生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门前
不久以后的2003年9月,我又有机会与耿世民、霍旭初、伊弟利斯、于志勇、李崇峰、杜伟生、林世田等同行,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参加“佛陀之路:纪念大谷探险队一百周年与西域文化研究会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The Way of Buddha” 2003: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Otani Mission and the 50th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Cultures)。记得9月10日那一天的主题是“龟兹的佛教美术”,由我来主持,霍旭初先生在这个主场做了发言。
除了在外面开会,我大概每一年都要去新疆,因此有很多机会与霍先生见面并讨教。
2004年7月,在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率部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到新疆考察,住在新疆师大的宾馆中。到乌鲁木齐的第二天就去看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老师带我们参观,其间霍旭初先生也来见面。晚,朱玉麒代表新疆师大“西域文史”学科请考察队和新疆考古所、博物馆同仁餐叙,其中就有龟兹石窟研究所的霍先生和彭杰。
2005年,在霍旭初先生等人的推动下,新疆成立了龟兹学会,霍先生担任副会长。年初他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参加8月召开的龟兹学会成立大会。我原本打算参加,可是新疆考古所拟在8月中旬组团去日本佛教大学合办丹丹乌里克的专题研讨会,一定让我也去。我只能向霍先生转达歉意。我把原在台北发表的拙文《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增补改订,奉献给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2005年10月刊出,作为我的贡献。而专刊出版后,霍先生第一时间寄给我两册。
2007年年初,霍旭初先生又在推动8月底9月初的龟兹学会。他发现经办人员给我发的“2007年龟兹学学术研讨会邀请函”是错的,应该发的是“特别邀请函”,特别来电话表示歉意。我很荣幸被龟兹学会作为特邀代表邀请参加会议,所以也答应将努力准备论文,并到会学习。可惜这次会议和我原本答应过的9月初台湾的一个唐宋史的会议冲突,最终还是没有成行,有负霍先生所望。
2008年的龟兹学会的年会,霍旭初先生又是早早在做准备。我从电脑里检出一封他6月27日的来信,说到:“龟兹学会的工作人员都在忙于会议筹备,我来与您联系一些事情。您的论文全文不着急,您在会上有30分钟发言即可。我们已将您的发言安排在会议开幕式后的大会报告。开幕式除了学术会代表外,还有库车县科长以上的干部,县上要求他们听会,学习龟兹文化知识。现发去‘学术交流程序’,您有何意见,尽可提出,还可改进。我一直企盼您光临会议。”可见他对我的关爱有加。7月8日“2008年龟兹学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我忘记自己发言的题目了,但霍先生谈《龟兹佛教中的“法藏部”问题》,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法藏部在西域的流行问题,不仅涉及龟兹,也涉及于阗,我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会上,我了解到他手边缺少我编的《唐研究》,于是回京后给他补了能够找到的卷次,还有拙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他收到后立刻回信:“感谢您对龟兹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尤对我的一贯关心,十分感激。”虽为长辈,他总是这样客气相待。
2009年我们开始“龟兹石窟题记”项目之后,几乎每年都到龟兹各个石窟调查,一般在考察之后回到乌鲁木齐时,照例会到霍先生家里去做汇报。2009年5月初,我与朱玉麒一起带领婆罗谜文字释读的主力队员庆昭蓉、荻原裕敏走访了龟兹石窟研究院,签订了北大与龟兹方面的合作协议,做了初步考察,特别是借枯水期考察了亦狭克沟石窟,发现了很重要的题记。16日我们回到乌鲁木齐,龟兹学会以霍旭初先生名义设宴招待,参加者有贾应逸、张平、孟楠、牛汝极、朱玉麒、田卫疆等。饭后,我们向霍先生和贾老师汇报了龟兹考察的收获,他们两位表示大力支持,并告诉赵莉要把资料都公布给我们。然后我们又随霍先生到了他装修后的新家,宽敞明亮,很是惬意。霍先生让我们参观图书,并送副本书。赵莉要送给我的《中国新疆壁画·龟兹》和《克孜尔尕哈石窟内容总录》,我就从霍先生家里先拿走了。
2010年8月中旬,我到克孜尔参加龟兹石窟研究院建院25周年庆典,我在他们内部出版的《龟兹记忆》一书中,发表了《初访克孜尔》一文,追忆1983年第一次走访龟兹石窟的感受。与会的霍旭初先生看了非常高兴,我则送给他拙著《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请他指教。
2011年8月初,我们“龟兹石窟题记”课题组部分成员,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先生和拜城县文物局图逊江局长、库车县文物局吐尔地局长的陪同下,考察了拜城、库车、新和地区的阿艾古城、盐水沟关垒遗址、博其罕那佛寺遗址、苏巴什“西寺”、玉其吐尔遗址、科实吐尔塔、库车老城清真大寺前旧房屋拆迁后露出的唐代烽火台,还为了分析古代柘厥关位置,走访了苏巴什遗址北面的兰干村与兰干水电站。我们回到克孜尔石窟后,向霍先生汇报有关调查成果,他特别告诉我们亦狭克沟直接和盐水沟相连的重要信息。8日,龟兹研究院和我们北大中古史中心共同主办的“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大会发言,我谈“展望龟兹学:跨学科的研究”,霍旭初先生在学术研究组发言。会后我们继续考察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的洞窟题记。
我们的“题记”项目边考察,边撰写《简报》,及时把项目成果分享给学界。2012年3月2日霍旭初先生来信说到:“赐赠的《唐研究》收到。十分感激您的关怀。吐火罗文研究在您的大力推动下,已显成果,令人兴奋。需要我办的尽请吩咐,当献微薄之力。”他对我们的工作既有鼓励,又有参与。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利用我们的解读新成果,撰写论文。2013年6月下旬我去乌鲁木齐参加“隋唐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借此机会向霍旭初先生汇报吐火罗语题记简报发表情况,以及今后的安排,希望他动员新疆这边的人参与研究,写有关龟兹的文章。
2016年6月中旬,我去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丝绸之路考古历史学术研讨会,路过乌鲁木齐。我和赵莉就《龟兹石窟题记》书稿的部分章节向霍旭初先生汇报,霍先生盛赞库木吐喇第34窟榜题的解读工作,并拟在此基础上撰写文章。
2019年8月18日,我率领“敦煌与于阗”项目组结束南疆和吐鲁番的考察,回到乌鲁木齐。当晚赵莉在新疆教育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二楼,以霍旭初先生的名义宴请大家,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与霍先生见个面。当时霍先生说他心脏不好,但我看他的心态甚佳,只是显得有些老了。随后几年疫情的阻隔,让这次见面成为永诀。

2019年,荣新江先生与霍旭初先生最后的交谈
在我与霍旭初先生的交往中,得到他的帮助远远多于我对他的帮助。记得2003年我希望在《唐研究》上约不同学科的学者把克孜尔第69窟龟兹王的题记做一个综合研究,但现存图像上的题记已经模糊难辨。我向他求救,看能否找到旧照片,他回电话说自己手边也没找到,但很快就请贾应逸先生找到更早的照片,寄给我,用在了《唐研究》的图版上。
回忆与霍先生的交往,我答应的有些事情没有能够完成,感到很对不起霍先生。记得2001年初收到赵莉的来信说:“霍旭初先生和我商量,想请您写一篇关于《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书评的文章,不知您是否能挤出时间?”我没加思索就答应了,而且还问何时要?发在哪?实际上自己对于龟兹石窟说不上什么研究,翻看再三,也没敢动笔,就慢慢给敷衍过去了。2016年霍先生与赵莉、彭杰、苗利辉合著的《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霍先生有关龟兹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又让赵莉联系我,让我写一篇书评。这本来是我跟着他的思路,好好把龟兹石窟和西域佛教发展史梳理学习一遍的机会,可结果又给霍先生交了白卷,实在有愧于他的期望。
好在可以欣慰的是,我和赵莉主持的“龟兹石窟题记”项目,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最终在2020年11月结出硕果,三卷本精装彩印的《龟兹石窟题记》在上海中西书局出版,收录了龟兹各个石窟的以龟兹语为主的婆罗谜文、佉卢文、粟特文、回鹘文等胡语书写的题记七百多条,也发表了全部清晰的照片,包括现存石窟题记与探险队切割走的题记照片,附有一卷研究论文,包括霍先生有关阿艾石窟题记、库木吐喇第34窟壁画榜题的研究成果。这本书的出版,立刻获得学界的好评,已经有多篇中英文书评发表,而且获得多个奖项,包括法兰西金石美文学院的“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奖”(2021 Prix Hirayama)。我终于感到自己给龟兹石窟研究做了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没有辜负霍先生多年来的希望。

克孜尔的林荫大道
“勤者欢喜”,“善业成佛”。最后,我用这两句克孜尔石窟龟兹语的诗句,来颂扬霍旭初先生对龟兹石窟的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