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身太空浪荡儿的科幻教母,用五种世界观写作
原创 深焦艺文志 深焦艺文志

寻获与失落
The Found and the Lost
[美国] 厄休拉·勒古恩
请以你的真名呼唤我
作者:暗蓝
杂学家,译者,书评人
当女儿回到死亡世界,母亲哭泣时,即是每年的秋冬。这是真实的故事,是历史。但孩子总是会出生,孩子有她自己的故事要讲,那是非官方的,未经确认的,新的故事。
——勒古恩,《赫恩家的人们》
勒古恩是人类学家的女儿。她的作品中一个关键概念“伊库盟”(Ekumen)便是来自她的父亲A.L·克罗伯。1945年,克罗伯在一篇论文中重新发掘了希腊语单词Oikoumene,这个词的本义是“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最初指使徒教会的普世性。在克罗伯的论文中,它被用来表示人类全部历史文化的集合。而在勒古恩的“海恩系列”(Hainish Cycle)作品里,源自Oikoumene的“伊库盟”得以具象化:它是八十三个可居住行星的集合。伊库盟并不是一个“银河帝国”,相反,它所表现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用“海恩系列”最著名的作品《黑暗的左手》中主要人物金利·艾本人的话可以更好地理解何为“伊库盟”:
伊库盟在本质上不是一个政府。它是将神秘主义与政治统一起来的一种尝试,因此当然大多是失败的;但迄今为止,它的失败比它的前辈们的成功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黑暗的左手》厄休拉·勒古恩
金利·艾的身份是伊库盟的特使,他的工作是造访其他行星,劝说他们加入伊库盟。但从实际活动来看,伊库盟的特使并不像我们所习惯的“外交家”,奉国家之命纵横捭阖,撬动现实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偏转。他们往往是在观察、记录,体验异样的生活,更像是交流学者——或者人类学家。
因而你可以将以“伊库盟”为核心的“海恩系列”看做是一系列外星游记,或者不同形态文明的实验皿。在《寻获与失落》的十三个中篇故事(novella,区别于短篇小说short story和长篇小说novel)里,“海恩系列”占据七篇,第一篇《比帝国还要辽阔,还要缓慢》可谓开宗明义——既是关于“寻获与失落”这一主题,也是针对“伊库盟”概念的核心。一群格格不入者被派往遥远宇宙寻找新的生命行星,他们来到一个被森林覆盖的行星,却感受到这颗行星的恐怖与抗拒,直到一行人中具有能够感知一切情感能力的“感测者”欧斯登决心投身其中。“它的信息是抗拒。而抗拒恰恰就是我的救赎,它不具备智慧,可我有”。而他相信人类的智慧不但具有能够理解一切的能力,还可以将这一切阐释为爱,于是他最终以殖民者的身份留在了这颗行星上。相比于国内读者更熟悉的“黑暗森林”,勒古恩同样将森林看做恐怖的意象,只是她化解恐怖的方式并不是化身恐怖与其抗衡,反倒是以浪漫之爱融入其中,去想象、开启一个“比帝国还要辽阔,还要缓慢”的进程。而作为对照,在这篇小说里还有一个人未能返航——“生物学家哈费克斯,死于恐惧。”

厄休拉·勒古恩
勒古恩坚信理解的智慧与爱的力量,它们总会在“海恩系列”的实验皿中发挥关键作用。《赛格里纪事》讲女尊男卑的世界,《宽恕日》讲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族民之子》和《一名女性的解放》分别描绘少男少女如何冲破局限,成为能够自由创造价值的公民,《古乐与女奴》则进一步深化“解放”这一主题,表现了不亚于历史本身的悲怆与希望——后四篇又同属于“海恩系列”的子系列“维瑞尔与耶欧维”,前者是积重难返的“旧邦”,后者是并不完美的“新造”。通过构建这些错落分明的文明形态,勒古恩将毫无防备的个人——她的主角,以及我们读者——推入其中,令其在时间与空间的不断转译下尝试所能做到的事。重点在于,我们所能理解的一切只是局限的知识,而我们由这些知识启发而来的爱永远只是谎言的碎片。但聚合这些碎片便已经足够一时之用了——局限的善尚且保有进步之可能,终究好过囊括一切的黑暗与允许自己相信长夜难明而纵容的恶。在这一组宏大与遗憾并行的故事里,《另一个故事,或<内海渔夫>》最令人感到安慰。当志存高远的科学家遭遇意外,回到十几年前梦开始的故乡,这一次她选择了一无所成的平凡生活:
时间静静地过去,我写作,礼拜,冥想,睡觉。我在安静的水潭边醒来。
相比于“海恩系列”,勒古恩的“地海传说系列”(The Earthsea Cycle)更为有名。这个系列的核心是“古语”(Old Speech),即失落的太初之言。万事万物都有在古语中的“真名”(true name),掌握了真名便意味着掌握事物的力量,因而个人的首要任务便是求得自己的真名,而如果想要得到更多力量,则意味着需要参透他者的真名——唯有术士精通此道。
“地海传说”的主题是力量,这一点与大多数经典的奇幻作品如《魔戒》等不谋而合,毕竟人的想象大多始于对力量的渴望。在这本集子中,《寻查师》《高沼上》和《蜻蜓》三篇同属这一系列。其中《寻查师》可以看做“地海传说”的起源故事:当术士被野心家围剿,能够对抗权术之力的唯有“技术的联合”;《高沼上》是术士自身的野心所带来的危机及其解决;《蜻蜓》则描绘了“技术乌托邦”在因性别问题——人类最本质的差异——产生分裂而陷入危机,终结这一切的将是一位兼具勇气与力量的天选之女……

年轻时的厄休拉·勒古恩
因而谈论勒古恩,还是绕不开女性主义。尽管和大多数伟大作家一样,勒古恩非常排斥自己被贴上任何形式的标签,但她的创作的确带来了科幻乃至文学世界长期缺失的视角。丰功伟业、攻伐掳掠、“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往往是“第一性”不假思索的幻想选择,但勒古恩显然看到了这种辉格历史的可疑。集子中非系列的三篇《水牛城女孩,今晚相约吧》《赫恩家的人们》《失落的诸乐园》都在回应由此而来的危机。“水牛城”一篇是对经典的“帝国主义”文本《丛林故事》的反写:当男孩落入狼群,他也只会争做万兽之王;然而女孩却会哀悼死于人手的郊狼,进而可能成为弥合人与自然的桥梁;《赫恩家的人们》同样以神话中的经典形象“冥后”珀耳塞福涅的故事为基础,将她的命运赋予赫恩家的四代女性:她们是大地,但更是种子,春回大地的事业只能由哀悼与沉默者完成;《失落的诸乐园》则是两种历史观的对抗:自名为唯一乐园的,与敢于出走、探索可能的——而为破除狂热信仰提供技术支持的,仍是被“第一性”排除在外的女性。
当然在这最后一个故事里,实现拯救的是一对昔日的“青梅竹马”。也许我们可以鄙夷看到人类幼崽跑来跑去时流下喜悦泪水的路人,但对少男少女的期许绝不是“刻奇”——当他们在阴晴难料的世间互诉真名,交付彼此的力量,我们总还是有理由相信,人类仍会有美好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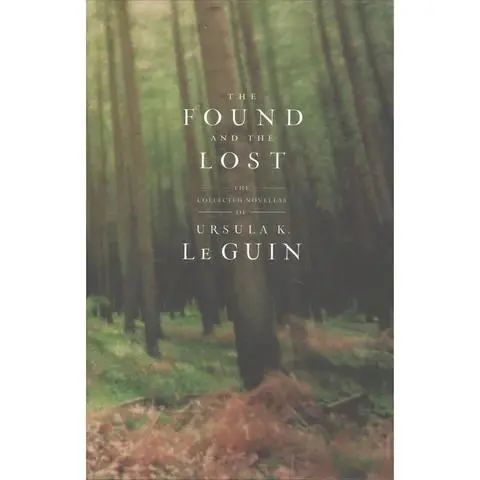
《寻获与失落》美版封面
遗憾但并不意外的是,曾以勒古恩的父亲之名命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栋教学楼日前启动了更名程序,“克罗伯大楼”被更名为“人类学与艺术实践大楼”。官方解释是作为美国西部人类学研究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一个强有力的标志,会继续唤起对美洲原住民的排斥与抹杀”(is a powerful symbol that continues to evoke exclusion and erasure for Native Americans)。然而实际上,克罗伯将人类学看做“人文主义与博物志传统的结合”,对自己的专业抱有近乎宗教的热情,渴望建立真正包容一切的人类传统。他大概是最不可能声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人。但说到底,名字不是真名,理解永远有其局限——或许勒古恩也会用自己在海恩宇宙和地海世界了解到的故事,来安慰她的父亲。
-FIN-
原标题:《化身太空浪荡儿的科幻教母,用五种世界观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