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人说|陈心想①:走出乡土时的“松绑”与“重组”
【编者按】
1948年4月,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出版《乡土中国》,是研究中国农村的经典之作。七十年过去,占中国国土面积大半的乡土如何了?
旅美学者陈心想认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民挣脱“土地”和“地缘”的束缚;知识资本的流动性让人口流动更方便;职业结构上,原来束缚在土地的农民阶层越来越少。
陈心想也指出,社会转型“松绑”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大重组”的过程,包括了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崛起;知识阶层地理分布更为集中;财富聚拢,区域差别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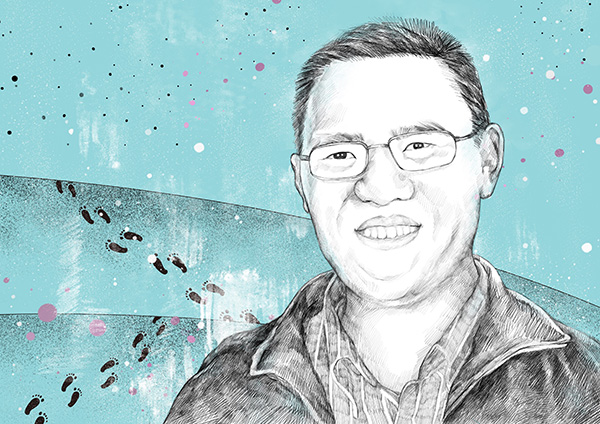
一、走出乡土:转型的“松绑”过程
1、工业化和城市化:挣脱“土地”和“地缘”上的束缚
中国社会在100多年前,尤其从鸦片战争开始,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启了中国走出乡土之路。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变迁更为快速明显。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很多的人从土地上挣脱出来了,参与到城市化提供的新的职业,这让大部分原来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村人口来到了城市,从事了一种不同于种地的行业。
2006年1月1日,中国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意义不平凡的事情。在古代,交皇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取消了“农业税”,不需要“交皇粮”了。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城镇人口超过了农业人口,科技的发展,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们的户籍制改革就让劳动力能够从土地束缚中出来后,可以流动到城市打工,从事不同的行业,虽然户籍制还没有完全开放。同时,市场经济让物品流动自由起来。人、物的自由流动,改变了原来那种“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在许多人走出乡土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发生着改变。
197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20%,2010年已经快到50%,40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发展地非常快。而且中国的城市化率,从比例上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美国2010年已经超过了80%。当然,城市化也给它带来了很多的大城市病,比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有城市的危机,所以大城市提出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北京要在2020年控制在2300万以内,上海是2500万,广州是1550万,大城市控制人口,人口就会分流到中小城市去。以上说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人的解放。
2、知识社会:知识资本的可流动性、高学历和高等教育扩招
现代社会我们说是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导资本的社会,知识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知识作为一种资本,是可以流动的。不像土地,农民在这块地上,要春夏秋冬去播种、除草、收获和储藏,只能在这块土地上流动,他不能走哪里把耕地带哪里。但知识作为资本可以流动。
我们来看看在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高等教育扩张的统计。在1990年,世界上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大约万分之三,到了二战结束时候大约万分之二十,到1990年已超过万分之一百,到2000年,超过了万分之一百六十,增长速度很快。
在世界高等教育扩招的大潮流里,看我们中国高等教育扩展的情况。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也很快,尤其是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从下图可以看出,在扩招之前大学生招收人数每年比较平稳,增幅较小,扩招后大学生增长得非常明显。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2013年中国全国社会调查数据,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上,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受高等教育是10%左右,到80后这一代就达到了34%,80后受教育程度是其前辈的三倍。高校的扩招,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因为知识资本的可流动性,给许多人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条件。


职业结构的变化分成三阶段职业地位流动(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数据,样本量9437)按照出生年代划分:1965年前出生,1965-1980年出生,1981年以及之后出生;职业地位划分成五个阶层: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
三个年龄群体中,子辈成为管理者阶层的比例——1965年前出生的人,农民子辈成为管理者阶层的比例约为2.74%,工人阶级的相比较高一些,5.88%,一般非体力劳动者的更高,8.81%,但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突然下降了,3.92%。这里可能和中国当时的社会运动有关系。管理者子辈成为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最高,11.62%。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这个群体中,子辈成为管理者阶层的比例随着父辈职业阶层的提高而提高,平缓地上升。在80后出生的人这个群体中,增长也比较平缓,管理者的子辈成为管理者的比例还是最高(7.89%),但专业技术者的子辈成为管理者的比例已经逼近(7.69%)。

再看子女成为一般非体力劳动者的比例趋势:农民阶层子女成为一般非体力劳动者的比例总体上比较小,但趋势是比例在增大,专业技术阶层和管理阶层的子女成为一般非机劳动阶层的比例较高。总体上看,各个阶层的人,不管父辈是在哪个阶层,成为中间的那个一般非体力劳动者阶层的比例都在增长,这大概是一种回归。
以上这些是“松绑”的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实际上是把人口从地缘上解放出来了;知识社会,因为知识资本具有可流动性,包括高校扩张,高学历人口越来越多,让人口流动更方便;职业结构上,原来束缚在土地的农民阶层越来越少。
二、中国社会转型新阶段:“大重组”时代
社会转型的“松绑”过程中,也有一个重新再组织的过程,包括了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崛起;知识阶层地理分布更为集中;财富聚拢,区域差别加剧。
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崛起
《2010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称长江三角洲已跻身于六大世界级城市群。2015年1月,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超越日本东京城市群,成为世界人口和面积最大的城市群。截至2017年3月底,中国已经形成了12个国家级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在吸纳资源、资本、人才上,要超过在城市群外围的城市。大城市群,不管是在政策还是地理位置上,是越来越促成资源分布不均的一个过程。从地理分布上看城市群,主要是沿海的一些城市,而中西部,没有太大的城市群,以重庆有为中心个城市群,算是沿江发展。从城市群的分布可以看到,东、西部资源、人才上的分布差距。
知识阶层地理分布更为集中
知识阶层,即高学历的人口的分布。知识阶层分为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和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Richard Florida提出过一个3T理论——Tolerance(包容)、Technology(技术)和Talent(天分)。他的3T理论强调的是人才,创意人才,受过较好高等教育的人。当以《创意阶层的崛起》闻名于学术界内外的Richard去多伦多大学就职的时候,多伦多的市长亲自来为他接风洗尘,但多伦多成千上万的市民却游行着要把他赶回去。市民认为Richard强调的是创新阶层,那更多的工人阶层怎么办?可见他的影响力。Richard在做研究的时候,和一个研究同性恋的博士讨论,他们约到咖啡馆,拿出各自的城市排名,结果两个名单的排名系数相关性非常大。我们知道,很有创意的人的性格或特点都有一些比较古怪的地方,他们所在的城市相对会比较包容。现在很多城市用政策吸引人才,但我觉得吸引人不只靠好政策这样单一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这是一个城市生态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来某个地方,他可能把家都搬过来,这会涉及到孩子的教育和整个家庭的生活和交往。这里插一个斯坦福大学老师的研究:富人移民,由于富豪很难去采访或者问卷,这位老师通过观察美国十几年的联邦税收(税收里有人的收入和地址等信息),美国每个州的税率不一样,超过多少收入会有不同的税率。一般人认为,提高税率会使富豪离开。但大数据发现,极少富豪会因为加税就移民到其他州去,因为不管是他的公司、人脉还是客户,包括他的安身立命,孩子、教育、家庭支持多方面都扎根这个地方。这个老师又用了福布斯世界排名一千的富豪做分析,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这些富豪都是在自己出生国生活的,很少在成为富豪后移民到其他国家去。即使有一些出生在比如非洲,但他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到了美国,在加州成为富豪后,基本上不可能移居到纽约,像比尔·盖茨现在还住在西雅图,乔布斯之前一直在加州。
知识人才去哪儿?有城市的综合性因素吸引,他才会来到这个地方。再说富豪移民,美国的州并不是通过降低税率把富豪吸引过来,而是提高富豪的税率。因为通常来说,富豪很少会走,用富豪的税来帮助刚毕业有创意的年轻人,培养新的富豪,在代际之间提供帮助。总体来说,哪个地方人才越多,越能吸引人才,人才都是愿意晃荡在一起的。我们看中国院士的分布,看211、985大学,在全国的分布对比,北京、上海、江苏很高。


世界不是平的,知识经济和新时代资本的发展优势和劣势则越来越不平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8年三大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12.51万亿元,占全国比重(指占地区GDP总计的比重)达到38.2%,拉动全国GDP增长4.5个百分点。关于财富的分布,可以看看中国的主要城市富豪排行:

社会意义
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原来的亲缘、血缘聚居让位给地缘、职缘,现在农村里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虽然还是原来的那种亲缘、血缘的聚居,但生产方式已经不同了。青壮年都出来打工,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在城市安家落户。甚至几年都不回家看一看,原来对村庄里的人非常熟悉,现在可能连一半的人都不认识。熟悉社会变成了半熟悉的社会。但城市的扩张,又没有重新组成新的熟悉社区,因为新社区的流动性非常大,经常是人来了又走。不像农耕文明绑在土地上的生活,太大的流动性没法形成熟悉的社区。
在大城市,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越来越大。知识、出生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智力等对个人发展和地位的影响都非常大,尤其是家庭出身,从小培养的资源不一样,到后来的发展、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也不一样,所以现在的培训班非常多。一方面说人们重视教育,其实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分层体系里,我们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教育是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
人们在空间和职业上都是在重新组合的过程,财富资本和知识资本在空间上的流动性,为这种重组提供了条件。重组的过程要求家庭和个人的价值和地位的也要重新确立。原来束缚在土地上“生于斯,死于斯”的农人所遵循的家庭和个人的价值观念,传承的传统文化观念,比如“父母在不远游”,则很难在现代情况下发挥作用了。原来价值的观念,传统的东西,需要适应的这种生活方式,进行创新。这是社会的意义。比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的传统社会里的“长老统治”,那是社会变迁缓慢的社会里靠经验和习惯的生活,年长者具有生活经验,有优势,也有权威。但是,现代社会里,流动性和知识创新都在增长的社会,“习惯是适应的障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这也是大重组的过程对社会的挑战和意义,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调整社会中对个人和家庭等的价值和文化观念。
教育意义
知识对社会地位有决定提升作用。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好多比较发达的国家对教育都非常重视。政府会出台一些政策做要求,比如一个学期不能缺课多少,对老师也有一些指标上的要求。教育成了知识社会的核心制度,因为无论是对个人成长、家庭幸福,还是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是关键因素。教育也成了各国“竞赛”的场域,比如美国现在很关注数学成绩的排名,他们很焦虑这个排名,科技发展需要数学,而中国、新加坡或者东南亚的学生的数学成绩很好,他们还会去取经,反映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教育制度还有一个功能是传播知识、传道授业。现代教育制度让知识的分布不再像前现代社会:知识和教育为一小部分人所垄断。现代社会让知识的分布更为广泛。和财产分布做比较,一般来说,财产分布和知识分布相关性很大,较富足的地带,比较重视教育。另一个是知识的获取。比如来到上海大学读书,背后有个人的不停努力、家庭的支持,还有这个地区对教育的重视。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乡最高领导说投资什么都不能投资教育,理由是学生毕业后还得回到这里,还得给他们发工资,那些不回来的,在外边出力又不给我出力。这种观念怎么能发展教育?所以说谁能获取教育,如何获取教育,这个机制里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还有现代的知识社会,受过教育的人,要学会如何学习,并能够保持终身学习。
文化意义
中国走出乡土的城市化和信息化是一次穿越式社会转型,文化价值观需要重建。为什么叫穿越式社会转型?拿美国社会进行比较,1920年代,美国和我们的乡土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而且也出现了打工潮,在1900年到1920年代,男性一般出去打工,女性在家带孩子,和我们现在的留守妇女差不多,就像我们走出乡村,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美国乡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也就是农业机械化时代,开启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大规模人口走出乡土。90年代遇到信息革命。而美国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的社会转型,我们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几乎从美国的二十世纪初穿越到二十世纪末。1929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石油革命汽车制造业拯救了美国的就业和发展。因为汽车发展需要造路,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还有造加油站、配套的修车站,一系列设施,就把乡村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就业。所以当时美国人口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它通过这种方式把人从农村解放出来,到城市谋取职位。二战的爆发也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从1920年代到1950年,美国人养的马和骡子数量迅速降低,从2500万头减少到800万头,因为不需要这些畜力了。
中国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差别在于我们进入信息化、城市化社会和走出农耕农业文明几乎是同步的,而美国大约是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所以说我们是压缩式的转型,经济、人才、社会大重组。重组后,我们原来依靠的伦理责任和相应的权利,以及这种传统文化下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组合方式下,已经不能再发挥基础性的力量。举个例子像养老,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提到,一个人到老年的时候会排序,和差序格局一样,如果他有自己的子女,他会让自己的子女养老,如果没有子女,他会让哥哥弟弟的孩子来负责养老,从亲到疏从大到小整个排序,是一种伦理的责任。但在现在,如果他的侄子跑到几千里外去工作,按照排序的话,他应该由侄子来负责养老,但实际上不可能让他回来养老了,而且现在也有养老新的政策。文化的观念、伦理的责任和力量在减弱,而新的法治化的重新建构的文化作为开始形成一种基础力量,比如新的养老院和养老金文化。
另外,在大重组中,不确定性和竞争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社会人的焦虑也比较强。我觉得,在下一步的大重组过程中,应该找到一个向相反的方向,“和”“合”文化将显示出力量,“和”指的是和谐和秩序,另一个“合”指的是合作互助,不能再那么强调竞争。大重组的社会也是制度创新的沃土,可以期待“和合”新文化:“各成其美,成人之美,美美与共,欣欣向荣。”
(作者陈心想系美国密西西比州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走出乡土 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等。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经作者审订)
------------------
社会学人说,是澎湃新闻·请讲的常设栏目,以社会学者第一人称,从社会学视角观察中国,解释中国,发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