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只兔子:我的八年,麦克白的一生 | 三明治
原创 勿心 三明治

麦克白的右耳上缠了几圈绷带,放着留置针。绷带是紫红色的,上面有一颗颗可爱的红心。兽医先往留置针里注入水,然后拿起另一支针筒,缓缓地往麦克白的耳朵里推入药剂。麦克白的毛发随着心跳一起一伏,几秒种后就静止了。
安乐死结束后,兽医轻柔地把麦克白用白浴巾包了起来,留下护士和我们沟通遗体处理事宜。护士让我们不用着急,因为他们会将麦克白在冷冻柜里保留七天。
我不想让麦克白在一个陌生的冷冻柜里冰冻七天,我还想让孩子们见一见他的遗体,和他说再见。护士说,我们可以把麦克白带回家,但是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我们家的冰箱里堆积着全家的食物,想来是放不下麦克白了。对不起,麦克白,我不能接你回家了。

2014年1月,纽约飘着雪,Ethan Hawke主演的话剧《麦克白》在林肯中心公演。那时我还单身,大学毕业一年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想养一只宠物作伴。我没时间照顾狗,对猫又没有什么感情,就想养一只毛茸茸的兔子。看完演出没几天,我领养了一只黑白色的混种狮子兔。他脸周围的一圈毛特别长,灰调里带着一丝血光。如果光线直射到他的眼睛里,他的眼珠会反射出邪恶的酒红色,我把他取名为“麦克白”。
我是在纽约布朗克斯的一家领养中心遇见麦克白的,当时他还叫爱丽丝,是一只一岁半的成年公兔。工作人员把他从笼子里放出来和我互动,他便抱着我的手臂不肯放。我以为他喜欢我,后来才知道这只是未绝育公兔的生理反应。绝育后,麦克白失去了繁殖欲,我才发现他一点也不喜欢抱我,也不喜欢被我抱。我只要一伸出双手,他就会蹦出一米远。
兔子后肢很发达,抱的时候如果不稳,他们会在挣扎中受伤。我看了好多视频,研究如何安全地抱兔子,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抱起麦克白。其实,我如果能坚定地一把箍住他,他反而会更有安全感,但我就是生怕弄伤他。这八年里,我可能只抱过麦克白五次。最后一次抱他,是在安乐死执行前,老公让我抱着他拍点照片。他轻得很,像一团围巾。这一次,他一点都没有挣扎,非常平静地躺在我的臂弯里。
领养麦克白的时候我和一个室友住在泽西城一栋老房子的三楼。公寓大概只有三十几平米,房间很小。厅倒是很大,我买了一米五高的铁围栏,把半个厅分给了麦克白,里面有他的厕所、牧草、玩的纸箱。我还把粉红色床单折了三折,铺在地上当作他的垫子。我常常骄傲地告诉朋友,麦克白是一只会上厕所的兔子。他的大便像一粒粒小版麦丽素,硬硬的,新鲜的时候还会散发出青草香。
没几天,麦克白就能辨认出自己的名字了。听到我喊他,他会蹦到离我不远的地方,左闻闻、右嗅嗅。确认是我后,他会再蹦一小步,用湿漉漉的小鼻子顶一顶我的手,示意我摸他。舒服的时候,他会咯吱咯吱地磨牙,表示他很幸福。
有一次,他突然蹦得好高,把后腿都甩了出去,像是抽风一样。我吓了一跳,赶紧查了查兔子的行为说明。原来,他们非常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蹦跶,像在跳舞一样。麦克白喜欢在宽敞柔软的地方飞奔,边跑边跳,但是他又会突然冷静下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默默地磨牙。
熟悉了我家的结构以后,麦克白就开始四处探索。他总是钻到床底下,卡在我的两个大型行李箱中间,用爪子轻轻地划过木质地板,“唰”地一声,把整个身体拉成半米长,成为一具“狮身兔面像”。再悠闲一点的时候,他会把整个身体侧躺在地上,眼睛半睁半闭,两只前爪和两只后爪都慵懒地伸往一边,像一个毛绒玩具。
一旦周围有什么声响,他又会缩回毛球状。要是外面的声音烦到他了,他还会猛蹬一下后腿,发出“咚”的跺脚声——没听过的人绝对想象不到兔子跺脚能这么大声。好笑的是,如果把他四脚朝天放在地上,他会突然“冻结”,这是兔子的装死技能。可惜,一边装死,屎还是会紧张得一颗一颗往外跳,一下子就破了防。
麦克白领回来没几个月,就发生了一个事故。有一天,我在切莴笋,麦克白闻到香味就蹦了过来,用后脚站着讨吃的,我便切了一厘米的莴笋尖尖给他吃。到了晚上,他躲在自己的纸箱子里不出来。我走到近处,推了推他,他也不肯动。我仔细一听,发现他的磨牙声和平时不一样,好像是牙齿在打冷战。由于兔子是一种“猎物”,他们的身体很脆弱,一旦肠胃出问题,很有可能突然就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吃的那截莴笋堵住了肠道,让他不能再进食了。整个晚上,我不停地去推搡麦克白,想让他动。我烧了热水,倒在密封盒里,再用毛巾包好,放在他旁边。他牙齿打颤的时候我就轻轻按摩他的肚子。我轻轻地和他说话,让他快快好起来。
到了深夜,麦克白还是没有进食,也没有排泄。我很害怕失去麦克白,如果再这么下去,我早上一定要带他去兽医院急救了。我开了很多个手机闹钟,让自己每半个小时醒一次,查看他的状况。凌晨四点,麦克白突然就吃了一根我喂的牧草!我多喂了他几根,又推他在厅里跑了几步。半小时后,他好像突然清醒了,知道要蹦回窝里吃草了。当我闻到他带有青草香的大便味时,终于放心了。
我关注了很多兔子主人的社交媒体,学习各种各样的兔子习性。兔子每天需要三四个小时的玩耍时间,我便给麦克白添置了很多“装备”。我买了供他钻的隧道,还有叼着会发出声音的木质玩具。我在回收的纸箱上裁出大小不一的洞,作为他的“城堡”,再把牧草塞进纸筒里,让他边吃边玩。慢慢地,麦克白好像知道自己也是这个家的主人了。他会跳到我的床上,趴在我的作业边,或者偷喝我杯子里的水。有时候,他还会像小狗一样,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就趴到围栏上迎接我。

后来,我结婚了,领养了一只猫,生了一个孩子,搬来了香港,生了第二个孩子,麦克白始终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只不过,我们有了更多的家人。
我们的猫叫作铁豹,名字也是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是个反派。他被领养的时候就叫这个名字了,毛发的颜色又和麦克白一样,我觉得他俩特别有缘。我本身不太喜欢猫,但是老公提出养猫的时候,我也表示了同意。而且,铁豹和一般的猫不太一样,他特别温顺,很亲近人,我觉得他可以和麦克白和平共处。不过,他有点嫉妒麦克白的存在,每次我蹲下身摸麦克白的时候,无论铁豹在哪里,都会冲过来顶我的手,让我改摸他。偶尔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铁豹也会伸出利爪,挠一下麦克白屁股上的毛,吓唬他。如果我打开围栏,铁豹还会征用麦克白的厕所,演绎“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戏码。
我们刚来香港的时候,在客厅里铺了一个爬行垫,让大儿子玩。有时候,我会让麦克白从围栏里出来,和他一起玩。麦克白也很喜欢这个软垫,经常在上面奔跑起来。大儿子想要追上麦克白,就跟在他身后飞快地爬。当他快要扑到麦克白时,麦克白又会弹开,逗得大儿子咯咯直笑。
香港的房子人均面积很小,我们只好在客厅里匀出一个一平米的角落,让麦克白住在那里。请了家庭佣工以后,她每周都会负责给麦克白清理居住空间,放入足够的牧草,我只需要每天喂他一勺兔粮就可以了。后来,生活变得忙碌,我连兔粮都交给工人喂了。
由于麦克白在香港的活动面积更小了,兽医建议我尽量少给他吃蔬菜和水果。我偶尔做菜的时候,会切一小截胡萝卜或芹菜给他吃,大儿子有时候也会帮我喂。有一次,我买了一些兔子点心给麦克白吃。点心的形状有点像我们早餐吃的谷物,是一粒一粒小小的环形饼干。大儿子拿了一粒,想要喂给麦克白吃。可是,大儿子的手指太小了,麦克白分不清是点心还是手指,猛得一下就咬了下去。大儿子痛得大叫,想要扯出手指,麦克白却紧紧咬着不放。我只好拍打麦克白,让他松口,跳到旁边去。大儿子的小手指被咬破了一块皮,鲜血直流。我很担心孩子们再被咬到,不太敢让他们喂麦克白了。随着麦克白的年龄增长,他也需要减少牧草以外的饮食,我就不太再喂他了。
小儿子出生后,我们家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孩子们一会大哭,一会到处跑,一会尖叫,吓得家里的两只宠物都躲到了角落里。我似乎不再主动照顾麦克白,而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亲子活动的道具。偶尔给他梳毛的时候,孩子们会围过来,想要摸他。可是,麦克白很快就可以辨认出孩子的手,变得很警惕,不一会儿就跳走了。
我常常教孩子们,接触动物的时候动作不能太快,可以先叫他们的名字,看看他们的反应,再轻轻伸手去摸。孩子们常常在围栏旁边大叫:“麦克白,过来这里!麦克白!”但是麦克白却卧倒在一边,不理他们。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把两只宠物放在了心上,出门的时候会和他们一一说再见。如果有人问他们爱谁,他们把一个一个家庭成员认真地数一遍:“妈妈,爸爸,工人姐姐,麦克白和铁豹!”
在孩子们入睡后,我和老公常常聊起两个宠物的年龄。我们不会每年庆祝宠物的生日,所以每次都不记得他俩到底几岁,需要从头开始再算一遍:“我领养麦克白的时候他一岁半,我们还没认识,所以是2014年。现在是2022年,他九岁半了……”工作苦恼时,我和老公总是很羡慕麦克白和铁豹“躺平”的样子,想要和他们交换灵魂。
后来,家里越来越拥挤了,每次我老公准备用电脑时,椅子总是会撞到麦克白的围栏,乒乒乓乓几声,才能坐下。麦克白很生气,每天半夜都会在他的身后跺脚示威。今年年初,老公又在麦克白围栏里支了一根铁柱子,用来挂自行车。不知道麦克白是不是感觉到了来自上空的压迫感,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我每年都带麦克白体检,他一直都没生过什么大病。我开玩笑说,单身的时候,我一年只要做一次体检;现在,我要做五次——包括两个儿子、两只宠物和我自己的体检。
麦克白来香港的时候已经五岁了,其实当时就已经步入了兔子的晚年生活。也许是他年纪大的缘故,每一次给他体检,医生总要提一些小问题。一开始,医生说他的大便形状不均匀,让我减少兔粮的投喂。后来,医生又说他毛太长了,需要每天梳毛,防止他自己吃进去太多兔毛。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把医生说的话当回事,只是偶尔想起来的时候,才给麦克白梳一次毛。这几年,他的毛发好像越来越乱,也越来越没有光泽了。连他自己似乎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形象,不那么频繁地舔毛了。
两年前的一次检查中,麦克白的脚跟磨损很严重。医生把他的后脚掌提起来给我看,果然都快被磨秃了。有个位置磨得特别红,似乎都磨出了一个水泡。兔子完全不会为自己发声,如果医生不检查,我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在忍着痛。回家后,我给麦克白的小空间铺上了软垫,他的脚跟也慢慢好了。
去年,医生又发现麦克白的皮肤开始有皮屑出现,怀疑是牧草自带的寄生虫。医生问我,麦克白最近有没有经常挠痒痒。我说,好像没有。其实,我自己都不确定,因为我太少关注麦克白了。给麦克白用了几次药后,皮肤问题仍然存在,但是也没有恶化,所以医生让我不用担心。
今年四月,我发现麦克白眼周的毛黏在了一起,梳也梳不开。医生告诉我,这是他泪管堵塞导致的,然后帮他冲洗了眼睛,剪掉了眼周黏在一起的毛。医生让我继续观察,如果还有类似情况,再带他来复查。六月时,我觉得他新长出的毛还是会黏在一起,便想再带他做检查,但始终没有排上日程。
每次体检时,医生总是会给麦克白例行称重。上一次,医生平淡地说了一句:“他的体重又下降了。”我点点头,说麦克白的食量好像小了,但其他方面还很正常。当时,医生并没有再追问下去,也没有说需要做更详细的检查。现在想来,那是不是就是他生病的征兆呢?如果我再警惕一点,是不是可以提早发现他的肿瘤呢?
如果我早些发现他的肿瘤,我会选择让他动手术吗?也许也不会。我当时就知道,宠物兔的平均寿命是8-10岁,麦克白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很多宠物到了年迈的时候,各种器官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生命老去的自然现象。我不是个忌讳死亡的人,麦克白死前我经常和朋友提起他,说他应该活不久了。我希望自己能够平静地尊崇自然规律。我经常给大儿子讲,蝴蝶会死、蚂蚁会死、鱼会死、鸟会死,我会告诉他不同动物的死亡过程,给他解释一种生物是如何依赖于另一种生物的死亡而生存的。

我以为我早就做好了麦克白即将死去的心理准备,但是,他的死还是让我感觉如此突然。
我努力回忆麦克白死前的样子,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他像平时一样,喜欢安安静静地侧躺,被我和老公戏称为“佛系养生兔”。他“躺平”的样子让我觉得很放松,很有安全感,好像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悲伤和疼痛。
七月中旬,我的大儿子做了一个小手术,我住在医院照顾他。第三天傍晚,大儿子得到出院批准。我急忙办理出院手续,赶在晚饭时回到了家。一到家,孩子们忙着玩,我开始嘱咐工人接下来几天照顾大儿子的细节。说完后,我瘫坐在沙发上,准备吃完饭好好睡一觉。
开饭时,我走向餐桌,瞥了一眼麦克白。正要坐下时,我又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趴在了围栏的正中心。我的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抢先一步,猛地拉开围栏,大叫了一声:“麦克白!”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吓得跳起来,还是直直地趴在那里,只有耳朵微微颤抖了一下。
我蹲在麦克白旁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大叫他的名字。我瞪着他的毛发安静了几秒,发现他还在呼吸,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可是,他完全没有动,好像四肢无力似地趴着。我又开始大叫,发出了恐惧的呜咽声。麦克白,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他仍旧趴着不动。
我拿来了梳子,轻柔地给他梳毛,眼泪滴在他的毛发里。老公一看情况不对,连忙打电话联系兽医。由于已经过了办公时间,老公只好给几个紧急号码留言,默默地等待回复。我轻轻地托起麦克白的上半身,他完全任我摆布。老公这才发现,麦克白的左腿已经肿成了一个大毛球。
终于,老公联系上了一家24小时开门的珍奇异兽兽医院,约到了晚上十点的时间。我很想马上带着麦克白冲去医院,可是大儿子才刚出院,小儿子三天没有见到我了,而当时正好是他们的睡觉时间。我还是决定留在家里,陪孩子们睡着后,再带麦克白去医院。
虽然我当时大声哭嚎,两个孩子却冷静得很。小儿子看到我很伤心,过来安慰我说:“妈妈,那我们买一个新的好不好?买一个一模一样的?”
到了兽医院后,麦克白立即被转移到了一个氧气箱里。根据初步诊断,麦克白左腿的肿瘤很大,也许好几个内脏已经衰竭了,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诊。兽医问我们是要继续检查,还是当场执行安乐死。老公问兽医,检查后治愈的几率大概有多少?兽医说,小于百分之五十。我有一点犹豫,不知道这场检查还“值不值得”。老公却觉得,麦克白在氧气箱里的眼神还散发着生存的渴望,还是先看一下检查结果再说。
兽医把我们交给了一个护士,让他给我们详细讲解检查的风险。拍X光时,麦克白需要保持一个特别的姿势。如果他自己无法保持,就需要接受镇定剂注射,失去知觉。讲解完,护士给我们递来一张风险同意书,让我们签名接受检查时有可能遇到的所有风险。同意书有一条选项,问我们如果麦克白遭遇紧急状况,需不需要急救,小字中标注了我们需要额外支付的急救费用和急救有可能带来的死亡风险。老公想都没想,选择了“需要急救”,我却拦住了他。
“不用了吧。如果麦克白撑不下去,就让他去吧。”我轻声说道。我不想让麦克白死,但是我也不想成为阻挡他死亡的人,让他承受更多的痛苦。
等待检查结果需要两个小时,我和老公没有回家,在兽医院附近散了会步。我们聊起了死亡。我们都觉得,如果是我们俩身患绝症,得在清醒的时候坦然地接受安乐死。麦克白的年龄已经相当于一个百岁老人了,如果治愈的几率很低,我们真的要逼迫他继续承受痛苦吗?
那一晚的月亮又圆又大,像是在邀请我们上去作客。“我们就和孩子们说,麦克白搬到月亮上去住了吧。”我提议道。老公笑道:“是啊,麦克白忙着去做月饼了。”

第二天一早,大儿子问我麦克白的去向,我照着昨天和老公商量的方案告诉了他。大儿子眼睛一眨一眨的,没有说什么。过了好一阵,他嘟囔道:“可是我想麦克白。”
我仔细翻看兽医院给我的宠物殡葬传单,又在网上搜索了几家,一时间觉得眼花缭乱。宠物的主人可以选择请法师做法,或者在小教堂里举办音乐追悼会,还可以自己去按火葬开火的按钮。有的殡葬公司可以做宠物纪念脚印,甚至能收集宠物口腔内的粘膜细胞,制作成DNA项链。普通的骨灰不宜保存,所以主人可以选择将骨灰转化为晶石,价格上万。
我告诉自己,麦克白死后花的钱并不是花在了他身上,只是我自私地想给自己提供一种安慰。大学时,我上过一门生物行为学的课,教授常常说,人类喜欢给动物的生老病死赋予情感。这些情感,动物本身是没有的,是我们定义了何为残酷、何为可怜。我决定省略其他的殡葬仪式,只需要简易火葬服务。我还定制了一条镶入麦克白骨灰的星空球项链,这样,他身体的一部分就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了。
几天后,殡葬公司给我发了麦克白火葬的视频。工作人员一边拍,一边轻轻抚摸着麦克白。“麦克白,不要怕,没事的,乖乖的。你的主人很爱你,有缘再相会,拜拜啦!”说完,他在麦克白的身上放了一束蓝色的绣球花,关上了盒子,打开了火闸。
大儿子在我的手机里翻到了这个视频,看了好几遍,又沉默了。等他再抬头的时候,他的嘴角向下一歪,嘤嘤哭了起来。当时离麦克白去世已经过了好几天,我很惊讶他会因为这个视频突然感到悲伤。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了火,知道火是危险的东西,终于明白麦克白被烧了以后就不存在了。我搂住儿子,告诉他,这就是麦克白的火箭,他已经到达月球了。

麦克白死后,我们反而更常在家里提到他了。
睡前,孩子们喜欢趴在窗口看月亮,找麦克白的影子。夜晚孩子们害怕怪兽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麦克白现在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保护着他们。大儿子翻出了许久不玩的兔子娃娃,叫它麦克白,介绍给来我们家的客人认识。
老公还以麦克白的名义注册了个邮箱,装作自己是麦克白,给孩子们写信。孩子们想麦克白的时候,老公就会帮他们把想说的话写成邮件。
7月15日
老公附上了麦克白火葬前躺在绣球花旁的照片
“大家好!我到达月球啦。耶!这是我的照片,我在去月球的漫长旅途中打了个瞌睡。记得要吃我给你们做的月饼哦!”
7月21日
“我爱你,麦克白。我想你。”
麦克白走后,我们把他生活的那个一平米的角落清空了,老公突然不习惯椅子可以一路退后的感觉了。我一直以为,老公和麦克白没什么深厚的感情,他却主动印了几张麦克白生前的照片,放在了桌子上。孩子们入睡后,我们常常围着铁豹抚摸他,给他吃更多猫粮,好像想弥补与麦克白错过的时光。
有麦克白陪伴的这八年里,我度过了人生中很多重要的阶段。最重要的是,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我有了一个家,有很多人依赖我。领养麦克白的时候,我孤身一人在国外生活,是麦克白让我感觉到,有一个生命需要我。现在,我不需要麦克白也能有这种感觉了,也许麦克白也觉得自己完成了使命吧。
在老公印出来的照片里,有一张我们在美国时带麦克白去公园的照片。他身上绑着牵引绳,脑袋上顶着一片枯叶,眼睛里泛着光。翻着麦克白的老照片,让我们也回顾了一遍这几年发生的事:老公帮麦克白剪毛、剪指甲,我们一起带麦克白去做体检,我们还把两个宠物装进了空运专用箱,让他们在香港和我们汇合。养宠物让我俩预演了一遍当父母的感受,麦克白和铁豹是我们最先拥有的两个孩子。我们都觉得,我们暂时应该没有心力再养新的宠物了。等到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会住在哪里,会养些什么其他的动物呢?
开学后,我和大儿子经常在上学的路上看到尚未消失的白月亮。我问儿子,看不看得见月亮上的麦克白,他说看不到。从他的语气里,我无法辨认他相不相信麦克白住在月亮上,也许他自己也半信半疑的。可能他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便开始仔细观察地面上的一切生命,麻雀、八哥、蜗牛、蚂蚁,被台风吹断的树、雨后新开的野花。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一只蜗牛抛弃了自己的壳,缓慢地向灌木丛里爬去。我告诉儿子,它的壳应该坏了,它就跑了,也许很快就会被鸟吃掉了。儿子问我:“为什么它会被鸟吃掉呢?”我告诉他,这些昆虫的寿命本来就是很短的,很多鸟都需要靠吃虫子来生存,如果鸟看到它,就会把它吃了。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踩死蚂蚁,蝴蝶的翅膀被雨打烂就活不久了。那棵被台风吹断的树,也在一天一天枯死。
两周前,我和老公选了个晴朗的天气去爬山,将麦克白的骨灰撒在了海洋公园对面的一个小山坡上。刚撒完,我的脚边就飞出一只花蝴蝶,蝴蝶的翅膀上有一道亮蓝色的花纹,特别夺目。我开玩笑说,麦克白难道也化蝶了?紧接着又来了两只老鹰,在我们的头顶盘旋。蝴蝶和老鹰知道我在这片土地上刚刚洒下了另一只动物的骨灰吗?
登到山顶时,我们又看到了更多的蝴蝶,这是我第一次在香港看到这么多色彩各异的蝴蝶。其中有几只嫩黄色的蝴蝶,特别好看。它们仿佛在空气中跳着芭蕾,你追我赶,在玩一个只有它们明白的游戏。我突然想到了麦克白高兴时蹦跳的样子,也像这几只蝴蝶一样自由、活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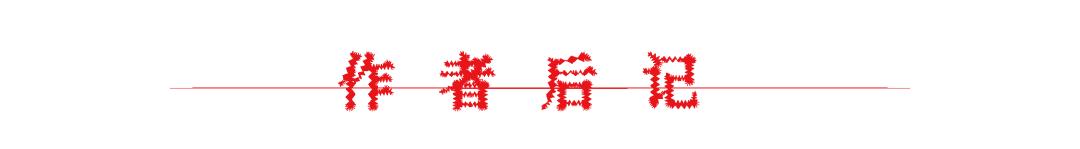
很多朋友听说麦克白过世的消息,都安慰我说,至少他在世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爱。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周转于孩子和工作之间,偶尔才俯下身给他梳毛。他过世的前几个月,我一直想带他去兽医院复查,却因为自己暑假的安排连连推迟检查时间。
我和心理医生聊起了麦克白的死亡,说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在自己窝里休息,但又在我愿意抚摸他的时候,热情地与我亲近。心理医生说,听起来他是你心目中完美的家人啊,不会对你大声说话,不会在你需要集中精力的时候来打扰你,也从来不会离开你。
回头想来,麦克白连死亡都选了一个不为难我的日子。他死在了我不用上班的暑假,死在了儿子手术出院后,死在了我深夜要倒时差上的培训课开始之前。7月14日,正好是我没有任何安排的日子。他温柔地选择了这一天,让我有充裕的时间安排他的后事。
麦克白的死亡是我成年后经历的第一次死亡,也让我目睹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接受死亡概念的过程。平时说宠物是家人的时候总是有点煽情,麦克白的死亡却让我真实体会到了与家人永别的心情。同时,我也观察到了我们全家应对死亡的不同方式。虽然我很容易落泪,但是我总是以非常科学、理性的逻辑来做与麦克白死亡相关的决定。我的老公平时看似对麦克白感情不深,却为麦克白做了很多浪漫的事。大儿子心里默默难受,小儿子仍然不理解死亡,只想换个新的。通过麦克白的死,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了解自己了吧。
*这篇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原标题:《纪念一只兔子:我的八年,麦克白的一生 | 三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