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中国与17世纪世界的危机
谕户部等衙门:朕念比年兵事未息,供亿孔殷,加以水旱频仍,小民艰食,地方官不行抚绥,遂致流离载道。普天率土,系命朕躬,如此艰苦,不忍闻见,朕为之寝食不遑。拯济安全,时不容缓。户部等衙门凡有钱粮职掌者,即将见今贮库银两实在数目,作速查明来看。特谕。
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二十三日
明朝(1368-1644)的衰落和清朝政权(1616-1911)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最浓墨重彩、最惊心动魄的朝代更替。尽管满人于1644年突然占领北京,但明朝皇帝自缢于紫禁城外后才6个星期便开始发生的明清更替,却并非一场突发的政变。无论是从我们今天超然的视角来看,还是从当时明朝遗民与清朝占领者各自的利益出发,这一改变肯定显现了它是一段较长过程的一部分:17世纪商业的经济衰败,明朝秩序的社会崩溃以及清朝统治的政治强化。
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讲,明代晚期中国与世界货币体制的联系已是相当明了的事情。由于在支付平衡上持续出现偏向中国商品与企业的失调,白银从世界各地流向中国的世界经济体中。“早在欧洲人全面了解整体世界之前,地球就已经被划分为或多或少的中心和一体化的区域,也就是被划分为相互依存的几个世界经济圈。”17世纪初,在东亚经济圈,中国大概平均每年从日本进口33000-48000公斤的白银,甚至有更多的钱币从这个经济圈之外流入“欧洲金钱的坟墓”。
17世纪,中国通过与西班牙治殖民地菲律宾的贸易,成为美洲白银的主要接收国,好年景时可以接收二三百万比索(57500-86250公斤)。一些史学者曾经说这种从美洲欧属殖民地国流通到中国的钱币只不过是一种从属性的顺差贸易。然而,我们仍然认为东亚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经济圈,一个自我的世界,有其核心与外围,尽管没有与其相应的欧洲世界经济那样的海外领地和殖民国。中国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吸取了西班牙在美洲开采银矿之出产的20%之多,白银以帆船装载直接穿越太平洋,经马尼拉运送到广东、福建和浙江,换取丝绸与瓷器。1597年,这是墨西哥白银出口的一个大年,帆船从阿卡普克运送了345000公斤白银到中国。这些白银比明帝国半个世纪所产总量还要多。其他美洲银锭则通过在布哈拉(Bukhara)的中亚贸易间接到达中国。于是,新大陆开采出来的贵金属50%流通到了中国。将这个数字与日本输出的白银数量相结合,17世纪前30年每年到达中国的钱币总量至少有250万-265万公斤,很有可能会更多。
尽管时间尚早,但那时中国的经济已是后来发生在17世纪2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那场沉重打击了以塞维尔为中心的欧洲交易系统的经济大萧条的一大靶子。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大萧条之前,每年在马尼拉待命的中国船只有41艘之多,而到162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6艘。由于中国与中亚的贸易关系同时削弱,来自新大陆的白银供给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的流通量又一次大增,马尼拉帆船继续从西班牙殖民地运来白银,澳门人把日本白银带到了广东,还有更多的钱币从果阿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到了澳门。然而,紧接着,17世纪30年代初到17世纪40年代末,这一流通又一次,甚至是更严重地被打断,而此时恰恰是中国的长江下游高度商业化的地区经济越加依赖扩大货币数量以对抗通货膨胀的时候。
1634年腓力四世采取措施严格限制阿卡普克(Acapulco)出口的商船;1639-1640年之间的冬季,很多在马尼拉的中国商人被西班牙人和当地人屠杀;1640年日本中断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1641年马六甲落入连接果阿与澳门的荷兰人之手。中国的白银进口急速下滑。
对中国的铜-银货币制的经久影响之一,很可能是晚明持续恶化的铜钱币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使得长江下游三角洲这样人口密集地区的谷物价格上涨,城镇人口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17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食品涨价的同时,其他物资的价格下降了。1635年到1640年之间白银运输的急剧缩减所产生的即刻冲击,对那一地区靠养蚕为生的居民尤为严重。蚕丝国际贸易萎缩,导致白银进口进一步衰落,浙江北部杭州这类养蚕丝织地区的经济变得越加萧条。

清朝时期街头的苦力
与此同时,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人口剧增(1400年到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口从6500万增长到1亿5000万多)之后,气候与疾病开始显恶。1626-1640年间,反常的恶劣气候突然袭击中国,蒙德极小期(或者叫做路易十四小冰期)开始的那几年,地球上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极度干旱之后紧接着是反复的洪水泛滥,而上个世纪修筑的主堤溃破又使洪水灾情进一步恶化。在这同一时期,频繁的饥荒伴随着蝗虫与天花的瘟疫,产生了饥民,饿殍遍地。其结果就是明朝末年人口异常减少。有学者甚至说,1585年到1645年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40%之多。总之,与全球经济萧条那几年巧合,中国出现了非同一般的人口下降:“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与西方的进步与退化几乎同一节奏,似乎所有的人类都在原初宇宙命运的掌控之中,相比之下,好像人类历史的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了。”这种普遍的人口减少让史学家相信,中国卷入了那场覆盖整个地中海的17世纪的危机。
在晚明很多经历了通货膨胀潮流的人们看来,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困难主要归因于不断增长的经济货币化。当时的士绅普遍抱怨商业化并高度赞扬一两个世纪前那种较简单的生活,那时候,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较少卷入市场关系。例如,一份17世纪早期的地方志对照了弘治时期(1488-1505)平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那时候可耕地充足,住房空闲,山林葱郁,村庄平和,路不拾遗;随着嘉靖年间(1522-1566)的社会混乱,财富频繁易手,价格飞腾,贫富分化,市场条件变化无常。这本地方志强调,到了1600年,情况越发糟糕:“百户之中有一个是富裕户,十户却有九户贫穷。穷人无法反抗富人,以至于跟常理相反,少数控制了多数。银钱与铜钱似乎可以管天管地。”
现代史学家普遍将晚明的经济困境归因于影响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崩溃。明初实行的是自我维持管理方式,税收由百姓中的收税人收集供应,军费由各地世袭的军户消化,徭役由苦力或世袭永久注册在案的匠户提供,这些都依赖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注册和分配程序的能力。经济的货币化,国都迁往北京,远离了长江下游三角洲重要的谷物产地,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的程序来贯彻理想化的自保性人口单位,这些都导致了崩溃。
从行政部门体制可以看到,在新经济影响的压力下旧的国家金融体制的腐朽。例如,在明初,当时唯一的国都在南京,行政部门加上皇帝的男性亲属都靠皇帝的薪俸生活,薪俸折成大米按石发放。国都北迁之后,俸禄的发放转换成其他形式:起初是纸币,后改为布匹,最后是银子。兑换的比例按照当时谷物的价格换算。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谷物价格时涨时跌,而银子的薪俸相应保持常数。到1629年,给京城文官和男性皇族(单单在北京就有四万人)的补贴总和只有15万两或更少,占全国总预算的1%。谋取私利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虽然因低薪而引起的贪污腐败是中国历史上重复发生的事情,在明朝末期却显得特别严重。各品位的官员通过挪用公款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谋求额外收入。1643年,崇祯皇帝(1627-1644年在位)决定检验军队配给制度的可靠性,并且秘密查访,看兵部四万两的军饷有多少可以真正摊派到辽东。他的御史报告说军饷一文也没有发放到目的地,在途中就消失了。
当然,这是传统史学所下的定论:道德堕落的统治者将失去对当政王朝的统治权力。但是,在这件个案中,即使很难衡量出皇权在抵抗上文分析的全球性经济萧条时施政恶劣所带来的相应代价,但毫无疑问,统治者个人的奢侈嗜好还是间接地增加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尤其受谴责的是万历皇帝(1572-1620年在位),他多次挪用政府资金建筑皇宫,公私款项混淆,还允许他的供应商经常在所有开支中拿20%的回扣,不论他们是否已有其他的“撇油”。但尽管他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万历皇帝也只是明朝需要支撑紫禁城内庞大的个人机构的很多皇帝中的一个。到17世纪,北京的皇宫里有3000宫女,近20000宦官。一部分的宦官要照顾皇后与皇妃,但这只是宦官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作为皇帝的御用仆人,他们管理着由十二监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皇朝税务机关与政府仓库,负责政府的盐业专卖,垄断铜矿,征收皇家房地产的租金(一时曾占有全国房产的七分之一及京师周围八个区的几乎所有土地),监督御林军守卫京师,并且组成了秘密特务机构(让人胆战心惊的东厂),这个机构完全拥有逮捕、拷打的权力,处死的人甚至比正规的大理寺还要多。

万历皇帝
作为皇帝的权势极大的左膀右臂,宦官机构吸引了众多的宦官,超出了自己所能稳固支持的能力。在宫里有数不清的贪污、受宠及其他机会。太监主事的局面终于在明朝末期因为它给朝廷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而告结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明朝末期,宦官们经常作为皇帝的征税人在正常赋税额之上擅自追加巨额的额外商税,进入私人腰包,而他们自己却逃税。尽管1618年后开征紧急土地税,户部仍然有幸得到2100万两银子的70%收入,部分来自国库的皇帝的小金库,却并不那么如意。发生在1643年的一件逸闻,恰当地,或许有些戏剧性地说明了王朝的税收枯竭问题。
那一年的秋天,据说崇祯皇帝想要检查他的珍宝库的一些账目,被唤来的看门人,诺诺地一遍遍地假装找不着开门的钥匙。库房终于打开之后,皇帝看到,除了一个小小的红盒子,里面装有几张褪了色的收据,库房已经是空空如也。宦官除了对公共财政是一个明显负担,对于公众来讲,他们还象征了将晚明几乎所有的皇帝与外部及行政相隔离的障碍。由于一直扮演内宫与外界的中间人,太监很快就承当起向皇上转达大臣奏折,然后起草皇上御旨和法令的角色。如此一来,皇帝就无须直接处理日常行政。而在明朝初年,像太祖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位)和成祖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都曾经使用他们的私人亲信以增加对政府的个人控制,宦官势力的增大导致明朝末期统治者实际上失去了对行政机构的权力与权威。有的皇帝完全取消了召见一般大臣的做法,成为将他们与外界隔离的首辅大学士或太监手中操纵的傀儡。1469年到1497年之间的皇帝没有出席过一次朝会。在16世纪,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只与他们的各部尚书见过一次面而已。结果,官员们因从未见过他们的皇上——藏在深宫大内的影子,于是对皇帝任何行动的确切性一概失去信心。由于深知个人好恶可以左右每一件事情,他们便与太监私下勾结,或者在他们自己中间结成非正式(也便非法)政治帮派,以促成决策通过。通过科举制度进行政治庇护的做法更加深了这种倾轧,以至于到17世纪30年代,中央机构被深刻的不协调所撕裂,最终导致了像东林党学士与太监魏忠贤党羽集团之间的政治清洗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相对没那么重要的问题也被这种倾轧所煽动,其结果往往成为一个僵局,而不能形成决定。
在这样的条件下,帝国的社会支柱经济和政治开始解体。到了崇祯时期(1628-1644),穷人与饥民涌入城市,试图以乞讨或偷窃养活自己,华中的整个农村地区完全变成赤地千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穷人心中的愤怒在增长,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震惊于这几年穷富之间一直增长的相互仇恨,正如那时一首唱给老天爷的民歌:
老天爷,
你老得耳朵聋来眼睛瞎。
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那杀人放火的享荣华;
那吃斋念佛的把饥荒闹。
下来吧,老天爷,你咋能那么高?
你咋能那么高?下来到地下。
1640-1641年间河南大饥荒之后,几十万义愤填膺的穷苦农民开始聚集在李自成这样的造反领袖的旗帜之下,这些领袖已经开始拥抱自己做皇帝的野心。

明代荒年志碑刻拓片局部
公共服务也同时崩溃。1629年,政府的邮政系统为减轻开支而削减了30%,但结果却是交通的瘫痪。由于许多驿站被荒废掉,帝国血脉梗阻,1630年之后,各省的官员都不能确定他们的奏折是否能够到达京师。在17世纪30年代,私人通常取代了公共管理,像防火、灌溉、赈灾,甚至地方法律与秩序。在这些活动的管理方面,公私的界限向来不是泾渭分明,但现在认真负责的地方官只有自掏腰包雇用私人武装,地方士绅训练自己的乡兵以自卫。
大门口的敌人可以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就是大明的一个士兵。1636年,左良玉将军的30000士兵说是为了平定张献忠的叛乱而进入河北,当地百姓却不得不逃到山上的断崖,以免自己的妻子受辱,也好保全自己的性命。后来,1642年到1643年间,左将军反叛了自己的皇上,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江南居民怕他更甚于怕暴乱。是为皇帝而战还是与暴乱者为伍决定了他是否倒戈,左良玉这类部队反映出一种无控制的武装化的普遍模式。稳定的社会结构似乎让位于流动性的军事藩侯,而军事藩侯最终推翻了这个早就对各种社会力量失控且受其牵制的统治王朝。
从最终战胜崇祯皇帝并使其丧失了后裔的清朝统治者角度看,统治中原的大业远在1644年前,或许在1618年东北的抚顺被攻陷就开始了。满族最后的征服还要花上三分之二个世纪来完成——以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1681年成功收服三藩,1683年成功战胜台湾的郑家政权而告结束。清朝统治的政治巩固也因此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从与明帝国发展并进的准备期开始,到满人在北京对承续的明朝体系做调整的实验期,再到最终产生“汉”“满”微妙混合的统治模式——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但满人与汉人各自都得接受的清朝政权现实。
对这一兴起、调整、完成之政治进程至关重要的,是那些在满族朝着儒家王朝发展中与其合作的汉族人。在不同时期,这些汉人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而且他们的社会背景也与那接二连三的征服相符:那些早期就住在满洲的汉人,他们在努尔哈赤兴起之时就采用了贵族部落的满族人身份;一些人在辽东军事诸侯控制东北几省后组成了一支新的自己的精英汉人旗;北方的汉族乡绅以帮助多尔衮接管北京的中央政府为交换,而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江南士绅为促进以行政而非屠城和战斗的方式征服南方,接受了绥靖御史的角色。大概除了第一种情况,很多支持清廷的汉人仍然对满族人心存芥蒂,而满族人对他们也持暧昧态度。
没有汉族官员的合作,满族皇帝们便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幕僚。但他们也知道,沿袭汉人朝廷制为帝王,他们会因为迅速而轻易地变得太汉化而失去自己人的忠诚与爱戴。因此,在他们感激汉人合作者教他们如何以儒家之道统治这个帝国的同时,有些满族统治者也鄙视那些变节者,藐视他们的利害观,责备他们的道德妥协。就像摄政王多尔衮(1643-1650年摄政)所说:“崇祯皇帝尚可。惟其武将虚功冒赏,文官贪赃枉法。此其所以丧国。”
但是,正因为这种解释明朝灭亡的判断对于汉人官员是可以接受的,儒家的政治调和因而超越了种族差异,适应了各阶级的共同利益。正如17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向法国和欧洲的专制主义状态妥协以解决国内的社会不安定那样,在臭名昭著的1661年江南税案之后,拥有土地的汉族精英与满族皇室达成一致,同意制约士绅免税特权和满族军事特权,以支持稳定的政府统治。
然而,这种双方调和的代价就是随之产生的道德不安。明朝遗民放弃了绚丽的道德英雄主义,清朝的汉人集团则得到了真正的机会实行政治改革,他们确实稳固了中央政府,这是崇祯朝廷中自以为是的学士们从未做到的。通过有效地“救民于水火”,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以儒家身份而立命,然而,这些合作者也丧失了一定的思想独立和道德承诺,道德哲人成了学术型的翰林学士,政治领袖变成了官僚长官。合作带来的精神不安甚至在一些汉人官员中引发了对温和改革更大的热情,他们是清朝早期就归顺的最懂得利害关系的那些人。就是这些人能够通过清醒地将其满族主子在北京继承的明代制度合理化,来缓和自己投身敌方统治者所带来的道德焦虑。方案一个接一个出笼——改进的地籍测量和税收方法,新的更有效率的官僚交通形式,功能性地区分了水利管理,特别设计了管辖京师周围几省的地方控制机制。这些措施使清朝政权以非同寻常的速度重建了中央政府。政治稳定不仅伴随甚至是加速了经济的恢复,表现在促进区域间物资流通、鼓励贮存的白银投入流通、稳定谷价等方面。
中国的政治及其所治理的社会就这样从17世纪的危机中得到了恢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都要来得快。
1661年,江南一些市镇的人口恢复到了16世纪的水平。1644-1645年间,苏州和杭州的织布机曾全部被毁,但最迟到1659年纺织业已重新恢复。1686年,在实现以前明代的粮长配额和实行被称为“买丝招匠”的经营体制后,两方面都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1688年,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也恢复了。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人已经可以吃得和17世纪20年代以前一样好,华北迅速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富农阶层。在1683-1712年间,耕地增长了23%,达到1626年耕地总量的93%。1770年,已开垦的土地增长到9.5亿亩(约5800万公顷),1650年是6亿亩(约3700万公顷)。1661-1685年间,赋税提高了13.3%,盐业专卖的收入增长了43.7%。到1685年,进入政府国库的田赋、盐款和综合税收实际有2900万两。又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三番。
自然,随着清朝早期经济生产力的恢复,市场上也出现部分的紧缩,这是白银流通量减少的结果。17世纪60年代末,流通中的白银量竟然每年减少200万两,这个现象一是因为对抗台湾的郑氏政权而封锁了海岸线,二是因为帝国财政在囤积银锭。在康熙早期,日用品价格下跌主要是需要用现金购买谷物、肉类和衣物,在江南,每石稻米的价格从三两银子跌到了半两。当然,价格下跌也可能反映了生产的恢复,但是,财政储备在平定三藩的战争时期的花费,以及1684-1685年海禁解除,使更多的白银进入流通,物价和日常用品的流通都随之相应上涨了。
如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演变,一如它在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那样被认为是目的论式的进步,那么,用危机理论家的话讲,清代早期政治与经济的恢复可能只是对明末灾祸的“假性解决”。其发展模式无法为旧的主权提供基本的替代,尽管王朝秩序的恢复的确让人有古代政治制度历久弥新的感觉,这种制度成为欧洲专制主义者羡慕的对象,他们可能错误判读了其最终的财富与势力。满族王室建立在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奠定的稳固的制度基础之上,上层建筑的恐怖部分被遮蔽在炫目的文化盛装之下。将近两个世纪之后,当中国的疆界扩大到明朝治下的几乎两倍时,已没有严重的国内对手和真正的境外对手能够挑战满族人对全国的统治。但是,清朝盛世时的“泛满化”却含有一种适得其反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所在地已经从地中海移到了北海,由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大战争都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参战者之间,这些国家都被迫进行军事技术革新,并使独裁治理体系合理化。
而中国因为缺乏能够与之竞争的对手,并没有面临迫切的改进军事技术的需要,它当时仅需征服相对落后的亚洲内陆诸民族,控制哥萨克的冒险,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主权而已。更有甚者,虽然18世纪成立的军机处代表了帝国政府最高层次的权力集中,雍正时期(1723-1735)的财政改革——这可能向清政府提供了在后来与西方斗争时所需要的、更有效地向其百姓征税的手段——仅持续了几年。1753-1908年之间的田赋从白银5.5亿两增加到了10.2亿两,而同一时期全国县级税收从平均每亩0.0942两降到0.0706两。甚至将海关收入包括在内之后,19世纪末中央政府的年收入不足全国生产总量的6%,这个数字在那时是非同寻常地低。
这种相对无弹性的税收制度的持续状况,不仅是因为早些时候清朝帝国未遇到足以迫使它进行体系改革的对手,还因为清朝初期非常成功地通过利用相当先进但仍然非常传统的制度与技术而恢复了政治安定。权力的高度集中没有经过彻底合理化。王室的权威得以增大,而行政机构的自主性被减弱。1835年,托克维尔对中国仍然充满哲学家倾慕式的想象,他写道:
旅行家告诉我们,中国人有宁静没有快乐,有工业没有进步,有稳定没有力量,有物质秩序没有公共道德。有这些,社会发展得不错,却从来没有很好过。我想象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时,他们会发现这是世界上最优良的集中管理的典范。
终于以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欧洲人发现,清帝国的治理并没有托克维尔认为的那么好。权力依然高度集中,而管理范畴的边缘却与行政机构的决策中心失去了联系。更糟糕的是,整个系统已经僵硬,失却了清朝统治初期所具有的韧性。正是这份满族人在17世纪重建了帝国秩序的成功,使中国在19世纪终于进入世界历史的新阶段时,很难做出其他制度性的选择。在这一时期中,那些把分离的世界经济相连接起来的遥远而往往不太明显的维系,已被更直接更快速的政治联系所取代,从而制造出一个在欧洲帝国主义庇护之下的单一性全球体制。
17世纪中国的危机发生在东亚的世界经济圈内,是气候和疾病等全球性因素影响的结果,进而间接地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西洋weltwirtschaft(世界经济)相连。与这一危机准确关联的因素仍需探究,甚至还有一种可能:中国如此迅速地从1650年的全球危机中复苏,从而为18世纪早期通过茶叶和丝绸贸易实现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契机。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中国自己也萎靡不振了。尤其是1759年之后,清朝似乎控制了自己的贸易港口,才决定发展自己的世界帝国,而没有正式承认正在进入由大英帝国控制的茶叶和鸦片的三角性世界贸易中去。在自己的疆界之内,人口增长之后通过开垦森林、拓荒造田,从而完全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中国国内的经济繁荣了。虽然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种内在的增长与中华帝国外部的世界经济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很明显,为维持顺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设计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御1800年之后在西方兴起的工业诸国。中国从17世纪世界危机中的复苏之迅速是惊人的。200年之后,中国惊异地发现自己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欲用完全自主的方式来复苏,尚需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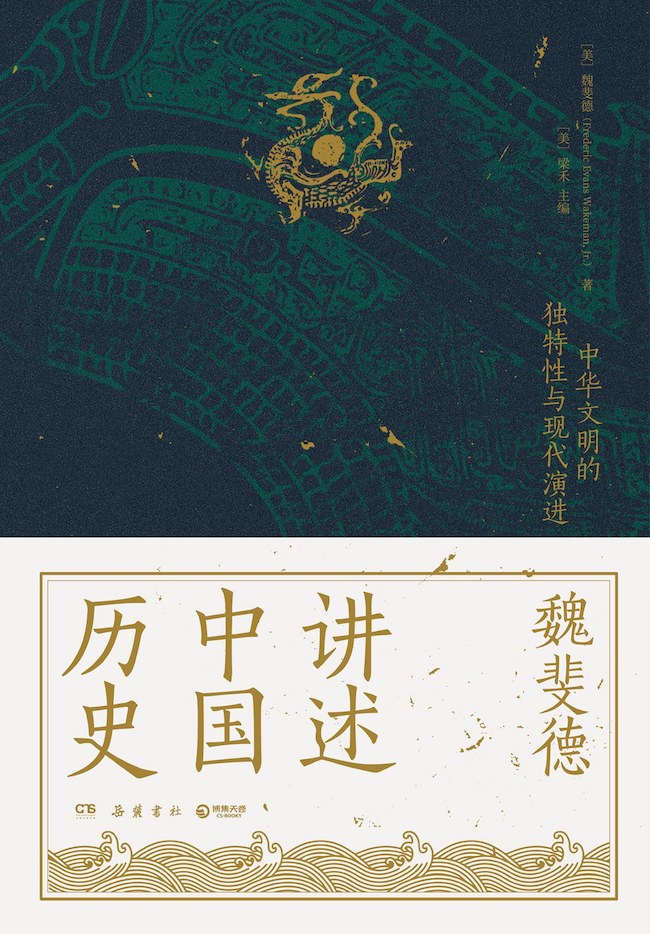
(本文摘自《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现代演进》,岳麓书社,2022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