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编译 | 英国殖民主义的漫长阴影
邪恶的帝国?英国殖民主义的漫长阴影
编者按:
来自普利策奖获奖历史学家埃尔金斯:对大英帝国的尖锐研究,探究了该国在整个二十世纪普遍使用暴力的情况,并追踪了这些做法如何在全球各地的殖民地被输出、修改和制度化。
卡洛琳•埃尔金斯揭示了一种进化的和种族化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通过不懈地部署暴力来确保和维护国家的帝国利益。她概述了暴力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如何植根于维多利亚时代对惩罚不听话的土著的呼吁,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形式如何变得越来越系统化。她明确指出,当英国无法再维持对其挑起和实施的暴力的控制时,它就从帝国中退缩,销毁和隐藏其政策和做法的罪证。
《暴力的遗产》借鉴了十多年来在四大洲的研究,将英国政治分歧的所有方面都牵涉到帝国暴力的产生、执行和掩盖中。通过证明暴力是支撑英国帝国和国家在国内的帝国身份的最突出因素,埃尔金斯颠覆了长期以来的神话,并对帝国在塑造当今世界的作用提出了新的看法。
作者简介:
Lauren Benton,耶鲁大学
文献来源:
Lauren Benton (2022). Evil Empires? The long shadow of British Colonialism. Foreign Affairs.

Lauren Benton
大多数欧洲帝国可能已经在20世纪解体,但它们的遗产仍然存在。
任何后帝国时代国家能否真正从其践踏弱国人民政治意愿的历史中解脱出来?答案的一方面在于,这些帝国曾经的恶行是有限的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即不公正和有组织暴力的结构性趋势。另一方面在于,表面上崇尚法治、自诩的自由主义帝国,与纵容滥用武力和认为国家行为不受惩罚的非自由主义帝国之间,究竟有没有实质性区别。
历史学家埃尔金斯的新书《暴力的遗产》提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答案。在埃尔金斯看来,大英帝国的"自由帝国主义"是一个矛盾的说法。英国政府声称,传播良好的治理和英国法律下的平等保护是其帝国的明确目标,但对于一个执迷于系统性、在国家指挥下使用武力的帝国,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主义。埃尔金斯写道: "暴力不仅仅是大英帝国的助产士,它是英国统治结构和制度的顽疾。"她对大英帝国的暴力的揭露令人不寒而栗。从十八世纪印度东印度公司的扩张到二十世纪肯尼亚对茅茅起义的残酷镇压,大英帝国统治的可怕后果的例子层出不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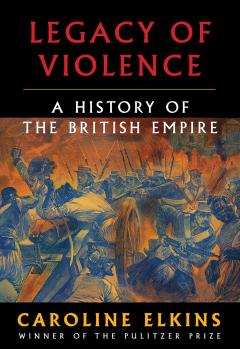
历史学家埃尔金斯的新书《暴力的遗产》扉页
埃尔金斯展示了大英帝国法律如何为暴力提供便利,以及镇压的做法如何在大英帝国内流传。在她急于揭开帝国的黑暗面时,她很少注意到法律也成为弱势群体的资源和反帝国运动的战场的方式。埃尔金斯还将大英帝国描绘成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连贯一致。她正确地纠正了苏格兰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和哲学家奈杰尔·比格的观点,即大英帝国的遗产具有绝对的积极意义。但埃尔金斯的结论也并不令人满意,她把大英帝国描绘成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力量。这个结论会造成不愉快的扭曲。特别是它导致了在大英帝国的所谓自由帝国主义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比较,夸大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
帝国的血腥代价
埃尔金斯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英国暴行的世界之旅。现代英帝国的丑闻都在这里。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发明了集中营,把20万非洲黑人和南非白人,包括大量非战斗人员,关进残酷的南非集中营。接着是对爱尔兰的残忍报复。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遭到残酷镇压:英国军队依据戒严法处决了15名爱尔兰人,逮捕了至少1500名平民。
1919年,印度阿姆利则发生惨案,英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抗议者开枪,造成至少400人死亡,1500人受伤。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人对巴勒斯坦实施暴力管制,从而引发对20世纪30年代阿拉伯起义的全面镇压。20世纪50年代,大英帝国练就的这些手段在肯尼亚茅茅起义中发挥了毁灭性作用,英国人用逮捕、拘留和酷刑镇压了这场运动,约9万肯尼亚人惨遭杀戮、伤害或虐待,16万人被关进集中营。

19世纪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同时加冕为印度女皇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份大英帝国暴行实录。她认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暴力事件是由贪婪的国家机器策划和运作的,这台国家机器醉心于监视、镇压和军国主义。人和思想的流动将这些做法带到了帝国各地,而暴力征服的政策有助于统一政治和文化上不同的殖民地。同时,戒严法和其他紧急措施将国家的暴力定义为必要的并予以支持。
埃尔金斯有效地追踪了官员们如何在大英帝国各地流动,带来新的镇压策略。例如,图德少将在1920年招募了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在爱尔兰建立了一支准军事部队,然后在巴勒斯坦运用他可怕的专业知识。特加特在1920年代作为加尔各答的警察局长镇压了印度民族主义,然后在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监督建造了一个由强化警察局和边境围栏组成的群岛。杰拉尔德•坦普勒将军将酷刑和镇压方法从巴勒斯坦带到了马来亚,阿瑟•杨上校在马来亚完善了警务战术,然后将他学到的东西应用到肯尼亚。军事情报官员弗兰克•基特森,埃尔金斯写道: "他在肯尼亚、马来亚、塞浦路斯、阿曼和亚丁等地跳来跳去,然后在北爱尔兰升至将军级别。"
该书的一个重点是它坚持将爱尔兰作为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埃尔金斯指出,爱尔兰拥有"模糊的地位",它在形式上属于英国,但在"涉及到法治和公民自由的问题"时却处于英国之外。她表明,爱尔兰既是帝国暴力新方法的试验场,也是应用其他地方开发的残酷技术的地方。
用于控制大英帝国热点地区的严厉做法也在国内出现。帝国的战时紧急权力在英国被用来镇压异议,如1939年通过的立法授权不经审判拘留被指控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英国公民。战后英国为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定位所做的努力激发了关于移民和公民权的排他性国内政策。1962年和1971年的议会立法反映了在英国社会中激增的种族主义,并改变了生活在非白人为主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人的公民身份。
书末讲述了英国政府为了隐藏帝国暴力记录的努力。2009年,五名在茅茅起义后被监禁和折磨的肯尼亚人就他们在拘留期间的痛苦向英国政府提起诉讼。2011年,英国政府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即随着二十世纪一个又一个殖民地获得独立,英国政府偷偷拿走了大量的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国家在肯尼亚和帝国其他地区指挥暴力的恐怖。尽管埃尔金斯在她的《帝国的清算》一书中被批评为夸大了英国人使用的严酷手段。出土的秘密文件证明她是对的。
法律与秩序
2012年法院对茅茅起义原告有利的判决标志着本书中英国法律作为国家暴力镇压的掩护之外的一个罕见时刻。该书强调了法律运作的方式,使帝国权力合法化。埃尔金斯说明,戒严令和其他紧急措施再出现允许暂停对帝国臣民的基本保护,如人身保护令。
其他历史学家,包括埃尔金斯引用的几位历史学家,以前曾追踪过戒严法如何在大英帝国打开暴力镇压的闸门。然而,这些历史也显示,戒严令的宣布引发了关于帝国宪法的广泛争论。帝国的批评者一再敦促限制法律如何被用来促进殖民地精英的利益和释放任意的权力。埃尔金斯将这段有据可查的关于帝国的法律和正义的争论历史推到一边,转而对定期中止权利进行简单化的描述。
她用“合法的违法”来描述“特殊的、国家主导的暴力”。埃尔金斯在这里和德国法学家施密特的观点,以及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观点一致。后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例外状态"释放出原始的国家权力,然后逐渐成为规范。她从这一角度分析了“特殊”时刻或“合法性危机”,在这些时候,帝国的极端暴力被法律认可,然后成为惯例。
合法的非法这个标签不太可能坚持下去,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口号。在强调特殊的暴力时,埃尔金斯设法反对她的核心论点,即大英帝国的暴力是常规和系统的。有时她似乎意识到了这种紧张。她认识到,戒严令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模式,即帝国的法律权力被授予地方官员、殖民精英和军事指挥官。这种结构超越了特殊时刻,增加了极端暴力的机会。然而,埃尔金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特殊主义的语言。
但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大英帝国的法律史。历史学家记录了大量普通人利用法律和法律语言维护自身权利和倡导司法公正的例子。利用法律和自由主义言论挑战或改变帝国统治,可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自由主义的困惑
当埃尔金斯试图衡量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影响时,问题就更复杂了。尽管这个词出现在整本书中,但埃尔金斯并没有准确地定义它。她提到了许多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即帝国是一种致力于良好治理的文明力量。她还指出,虽然经典的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大英帝国则是通过征服或其他手段形成了未经同意的统治。她还将政府作为对暴力的制约的自由主义理想与帝国中作为政府官方政策的暴力现实进行了对比。
在对大英帝国的自由主义进行毫不妥协的攻击时,埃尔金斯不得不压制其历史的复杂性。她从十八世纪末孟加拉第一任总督黑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因在印度的腐败而被弹劾和宣告无罪开始。保守派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领导了这次起诉,在埃尔金斯的叙述中,他作为帝国问责制的失败者出现。然而,伯克并不是改革者。他想通过让东印度公司更坚定地服从于议会,特别是上议院,来控制它的权力,是帝国克制的一个奇怪的海报。埃尔金斯还忽略了黑斯廷斯辩护的一一个关键方面:他在印度承认印度教和穆斯林法律并限制东印度公司的管辖权的努力。埃尔金斯对黑斯廷斯审判的处理,其弱点并不是她把反派和英雄的角色搞错了。而是这种分配过度简化了这些法律斗争,忽略了自由主义和帝国之间的模糊性。
埃尔金斯在追溯1865年莫兰特湾起义后牙买加镇压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辩论时,被迫偏离了自由主义者与帝国暴力共谋的直接故事。总督爱德华•艾尔(Edward Eyre)下令逮捕威廉戈登,他是殖民政府的知名批评家。戈登在岛上一个没有戒严的地方被逮捕,然后被运到莫兰特湾,在那里他被军事法庭审判,被定罪并被绞死。在伦敦,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努力调和帝国的不平等和不均衡的司法与他们对一个致力于保护所有公民和臣民的政府的愿景。
埃尔金斯在此停顿下来,观察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埃尔金斯来说,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为限制权力提供有效的指导。它只是为大英帝国的暴力披上了改革的外衣。她写道,当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在巴勒斯坦达到"成熟"状态时,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在"法治的无花果叶下"运作。
出现的帝国国家的形象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全面的力量。当故事发展到帝国的终结时,这种描述就会出现偏差,因为埃尔金斯没有为帝国的消亡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她追踪了战后几十年大英帝国各地的反帝国运动,强调暴力运动而非非暴力运动,但与英国压倒性的镇压力量相比,它们的影响显得微不足道。她写道,最后,当"镇压中心无法维持"时,大英帝国就自我折叠起来了。
叙述中的不一致,最终暴露了埃尔金斯所说的"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概念的缺陷。帝国是一个冲突的场所,自由主义在其中发挥了不一致的作用。
与此同时,官方暴力也越来越协调,但也越来越少。在镇压反对派和叛乱方面,它并不完全有效。正如成功的反帝国运动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帝国的暴力并不是一种全面的力量,它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假象。
不自由的帝国
埃尔金斯将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描绘成一个巨无霸,使她非常接近于称大英帝国为法西斯主义。埃尔金斯反复引用当代观察家将英帝国主义者与纳粹相提并论。
埃尔金斯更进一步,暗示了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不明确的直接联系。在结束语中,她写道: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大英帝国和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相似之处部分是由于纳粹官员借用了英帝国的法律和做法"。我努力寻找这一证据。除了对《我的奋斗》的选择性解读,强调阿道夫•希特勒对帝国的羡慕之外,证据似乎主要包括埃尔金斯的主张,即德国向东方的帝国扩张代表了对自由帝国主义的适应,因为它抹杀了被征服政体的主权。
埃尔金斯引用了历史学家马佐尔的观点,他有说服力地认为德国是一个帝国国家。但与马佐尔不同的是,埃尔金斯在没有分析纳粹德国的具体机构和做法的情况下就使用了帝国的标签。这种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她没有带来什么证据来支持她的说法,即德国在"吞并主权国家进入纳粹帝国并发动种族灭绝行为"时重新利用了英帝国的策略。
这种说法以影射取代了历史。在二十世纪的大英帝国,合法的、由国家指导的暴力是系统性的,这一有据可依的主要观点在埃尔金斯专注于提升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在万神殿中的地位时被忽略。这个议程具有煽动性,但作为对帝国及其遗产的仔细评估,它是失败的。这个项目需要调查英帝国主义更广泛的制度影响,并分析一个长达几个世纪的全球秩序,其中帝国是主导性的政治实体。
大英帝国的官方暴力值得仔细研究,而埃尔金斯为揭露其隐藏的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镜头也可能是扭曲的。正如德国在20世纪40年代所展示的。自由主义的帝国观既培养了帝国的暴力,也批判了帝国的暴力。他们并不拥有理解国家直接暴行的独特钥匙。
读者当然应该听从埃尔金斯的呼吁,揭开帝国历史中的暴力逻辑和模式。他们也应该跟随她的推动,询问帝国的暴力是如何并继续"系统化、制定和理解"的。但他们不应该局限于她。
唐世平教授签名书籍
《众人皆吾师》、《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与《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
编译 | 黄 勇
审核 | 林陌声
终审 | 李致宪
©Political理论志
前沿追踪/理论方法/专家评论
ID: ThePoliticalReview
原标题:《顶刊编译 | 邪恶的帝国?英国殖民主义的漫长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