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付东:《东京物语》是一部最不小津风格的电影,却成为他的巅峰之作 | 纯粹电影

小津安二郎
新锐导演陈雨的最新译著——法国《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十三个小津》已经完稿。现特推出本书中对最伟大的日本电影之一——小津安二郎《东京物语》的解读。
东京物语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法)让-米歇尔·付东/著 陈雨/译

《东京物语》 剧照
《东京物语》无疑是小津安二郎的巅峰之作,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部。西方观众正是通过这部电影发现了小津。
影片在电视上频频转播,是激发评论,对大师进行注解的源泉之作。《东京物语》实在精彩,至今,它的艺术地位仍然巍然屹立,不曾撼动。但令人吊诡的是,当提及小津安二郎最具代表性,可以完美浓缩导演精神的作品时,普遍认为不是这部,而是《晚春》。可能大家对1953年的日本电影辨识度不高,加上《东京物语》让人颇感不适的叙事手段及事件之间的连接方式:一切都随着可预知的结局发展——母亲去世,父亲陷入孤独,舆情观念的影响,儿女缺失陪伴父母的时光,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但最终无法成为对其评判的艺术标准。纵观故事的进展(甚至在完全了解结局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窥得导演叙事手法的创造力与丰富性。比如影片中诸多有趣的小事件在互相影响、互相生长,让人快速察觉到在小津的叙事逻辑里,对大量敏感性符号和情境运用的尝试,同时成功地遏制了让事件不陷入过于扁平和含蓄化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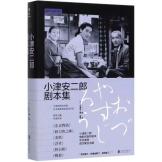
小津安二郎剧本集
作者: [日] 小津安二郎 著 吴菲 译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品公司
出版时间: 2020-04
在影片的推进中,观众逐渐了解这个家庭结构的组成:三个儿子(幼子已战亡),两个女儿和年轻的遗孀——儿媳法子(而演员原节子,也经常被赋予这个名字)。我们发现所有成员住所的异地化使得家庭关系亦显得支离破碎。父母和小女儿徐岙居住于广岛地区的尾道;二儿子在大阪;而其他三位则定居东京。这时我们可以理解小津严谨叙事的含义,他对于场景以及电影情节的陈述可以做得如水晶一般透彻,这样的创作方式支配着他所有的作品。《东京物语》让我们无法阻止去想象,在这样一个拥有众多直系或旁系小辈成员的家庭中,将会撞见多少意外。
小津不是肥皂剧作者,更不是书写梁上君子或流浪汉题材的作家。若是从叙事上讲,或许更接近于简单而直接的短篇小说作者——不排除他作品的深度及细腻度。顺其“以小博大”的电影手腕,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就可以从这种类似短小的俳句中看到一个极致放大的气象。悖论在于,《东京物语》当时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上映时被发掘,其叙事风格也被接纳,但其实在25年后,我们才发现这恰恰是一部最不“小津风格”的电影。

小津安二郎
当然,这并不影响《东京物语》来自多种路径的不同美感,它似乎可以将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所强调的“小津流”萃取到极致——偏向于表现人物及其所处的情境,和基于整体剧情推演中的场景更替。如果说此片的结构与大多数作品中紧凑的戏剧主线不太一样,比如拿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17部故事片作比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之外的作品中找到此种形式主题外扩的迹象。诸如场景的变化——坐旅游巴士的东京之旅;老夫妇去一家本应让人放松的温泉浴场,却遭遇弦歌不辍者的午夜惊扰;父亲和他的老友们酒栈群酗的荒诞戏——貌似不存在绝对的关联,堪比小津的那些 “空 ”画面,在影片中着实起到了点缀作用。它们不哗众取宠,不定义章节,和很多著名的空镜头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含义,但贡献了一派完全开放的演绎,在影片中扮演了相当于“呼吸”的重要角色。这些镜头引发了很多评论——让我们回顾一下德勒兹的总结,他罗列了诸如施拉德(Schrader)的“停滞”,诺尔·伯奇(Noël Burch)的“空镜头”(pillow shots),里奇(Richie)的“静物”。诺尔则针对这个分析补充道:“问题在于,这些分类是否真正存在差别”,但德勒兹可能还是太急于总结这个问题,他武断地认为,这应该只介于 “静物 ”和 “风景 ”之间的区别。

小津安二郎全日记
作者: [日] 小津安二郎 著 周以量 译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02
我们似乎远未达到可以理性看待相关电影画面丰富性的程度,这些画面存在于它们自身的质地和光芒当中,我们也并不一定非要强加一个常规性的理由,至少它们超越了我们眼中的象征意义。传统的石质灯笼切向工厂烟囱的镜头,意味着古老的过去和现代工业的并存,折射出小津无法穷尽的艺术匠心和造型能力。他精心构图,一些画面带有明显的抽象化意图,由再简单不过甚而是平庸的物件构成(譬如,晾衣架等)。有几个看似常规的构图,则跃跃欲试传递一种完美的自洽意味(比如在屏幕的左边,有一大块黑色的多边形屋顶,右面则呈现完美水平的山脊线,突显了祖母和孙子的侧面轮廓)。同样,从上述提及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精确地解读出,老人扮演现代都市游客,暗示了他们是时代和城市化进程的局外人,与本应是度假名胜的场所格格不入,或者说,善良、智慧、富有爱心的笠智众已今非昔比。他似乎绝缘了每个个体身上原来可以激活的,那些感官的或诗意的一切。

《东京物语》 剧照
电影对子女及他们行为的塑造方式绝不简单。片尾,父亲说在东京时幼子的媳妇对他们的照顾是最为周到的,与此番在母亲去世时的情形适成反差。事实上,亲生长子和长女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下已经极其所能。父母对子女的处境不免抱有一些幻想,不请自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或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伦理上,父母也有权利居住在子女的家里——是否真的就理所当然呢?无论如何,小津并不这样认为,他选择没有直接谴责子女们,而是成功地将寒酸的儿科医生(儿子)和美发厅的经营者(女儿)塑造成不怎么热心的形象。他们不应该包揽所有的过错,其真实的困境似乎也值得被考虑。小津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插入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启示,在这些人物中,社会学和心理学互相交织,他们看起来既不值得收获赞赏,也不见得招致唾弃。问题聚焦于平山的父母是否应该享受到更多的孝道?然而,真正意义上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代人之间的沟壑已经越拉越扩大,比如“从东京到尾道有很长的路要走”,多个画面不断提醒我们,父母居住的城市尾道并不是碰巧位于瀨戶市的内海,而是处于日本群岛的主要岛屿之间。当首都东京作为日新月异、现代化并且深受西方影响的地方以电影片名出现时,远离东京的传统意义上的家乡,其实隐喻了这个国家永恒的“心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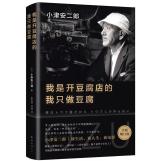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作者: [日] 小津安二郎 著 陈宝莲 译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13-06
影片中有多个画面交待了平山家族的过去并不如何优渥,尤其是祖上的表现,可谓不堪。因此,这部电影否认了“以前更好”之类的想当然的反面假设,这个“以前”,意味着战火频仍,而且,战争对他们的幼子施以极刑,即法子的丈夫。我们来回顾一个令人震惊的镜头,妻子去世后,当笠智众被(几乎)整个家庭包围时,他的脸似乎脱离了身体而触碰到了即刻将其吞噬的孤独,甚至触及到了死亡,开启了一种与怀念某个从未存在过的时代完全不同性质的张力,一种理想化的家庭社区中,关于爱与团结的幻想。这个镜头不动声色地掀起了影片的高潮,是所有不连贯的细碎事件的汇聚点。

《东京物语》 剧照
两位炙手可热的演员——笠智众和原节子贡献了精湛的演技,他们在场景和调性的不断更迭中揭示了影片的立意。从情节剧到悲喜剧,从准纪录片过渡到戏剧的风格,促成了影片的质地肌理的丰富让人啧啧称赞。在严肃呆板的老鳏夫和洋溢笑容且富有活力的年轻寡妇之间,影片对立的不是过去和现在,甚至不是传统和现代、旧与新,而是一种异常抽象、异常本质的概念:即我们所说的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法子守护着她和亡夫的记忆,同时就职于一家美国跨国公司(普利司通轮胎)的日本子公司,并负责为她的哥哥和姐姐的生计辩护,理解他们所必须直面的义务。这位原则坚定的年轻女子——一句话,她有绝对的意识,有不甘心自己被束缚的坦诚——她可以放任各种可能性,偶发事件,日常生活,稍纵即逝的美好,日复一日的不堪,萦绕在自己的生活周围。至于笠智众,或许还有小津本人,必定会给她一个再婚的建议——法子招待婆婆的那晚,婆婆也完全语重心长地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东京物语》以死亡作为标记的结局,无疑是悲伤的,但它绝不是人们所述说的那样一种悲哀。在时间流逝的岁月长河中,铭刻死亡,每个人的行为和动作都在其中循环,就像铺满片尾明亮的画面里的那些船儿,向着内海而行,乘风破浪,人生,亦如自然的真实面容,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小津安二郎周游
作者: [日] 田中真澄 著 周以量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05

小津安二郎(1903年12月12日-1963年12月12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日本电影导演、编剧。1923年,进入松竹公司蒲田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助手;1927年,拍摄了电影处女作《忏悔之刃》,这是其唯一的古装片;1933年,编导了剧情片《心血来潮》,该片被日本《电影旬报》选为年度最佳电影;1936年,编导了首部有声电影《独生子》;1949年,拍摄了剧情片《晚春》,该片被日本《电影旬报》选为年度十佳影片第一位,并入选日本电影名片200部;1951年,执导并参与创作了剧情片《麦秋》,该片被日本《电影旬报》选为年度十佳影片第一位,并入选日本电影名片200部;1953年,执导了家庭伦理电影《东京物语》,影片获第1届伦敦国际电影节萨瑟兰奖;1958年,第一次尝试采用彩色胶卷,拍摄了《彼岸花》,因此获得艺术祭文部大臣赏及紫绶褒章;1959年,获日本艺术院赏;1961年,因拍摄《秋日和》而获得第8届亚太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962年,执导了剧情片《秋刀鱼之味》,该片获选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佳影片;1963年被选为艺术学院会员,是电影导演首次获此荣誉。
原标题:《米歇尔·付东:《东京物语》是一部最不小津风格的电影,却成为他的巅峰之作 | 纯粹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