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宏丨《晚明佛教考——从僧俗互动的视野展开》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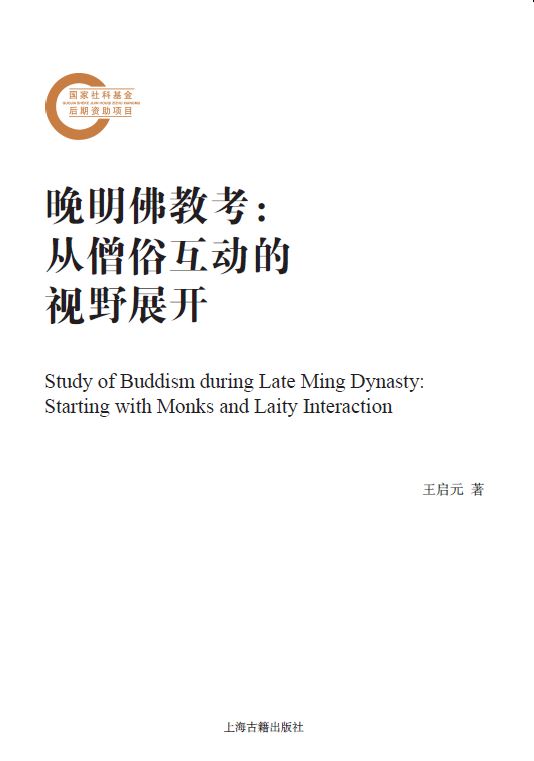
《晚明佛教考——从僧俗互动的视野展开》,王启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版
佛教在晚明社会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样一个富含意味的话题,当然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相比较明代中期的沉寂,“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①],并且涌现义学精湛的高僧大德以及士大夫居士群体,而“三教合一”思潮日益渗透民间,一切确有风生水起之色。这些现象背后,或即具有某种晚明佛教复兴的指向性;同时也让我们感到,这恐怕并非拘限于佛教史自身可作完全解答。王启元博士的新作《晚明佛教考——从僧俗互动的视野展开》,在我看来正是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这部新作是启元在2012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明僧侣的政治生活、世俗交游及其文学表现》基础上大幅改订而成,曾获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整个修改过程,前后经历十年的时光——那恰好是其学术上获得成长的关键阶段,也成为大陆佛教史相关研究视域及学风递变的一个见证。两种著作在结构上虽皆由三个块面构成,讨论的专题、关注的重心却已有所转移与充扩。
启元撰写博士论文的立足点,在于运用文学文化史的观念与方法,拓展近世文学研究的界域,探究晚明僧侣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如何参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活动,并为文学创作的审美表现作出独特的贡献。就当时来说,如何落实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要求和旨趣,同时也正好补近世佛教文学之弱,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故其阐论重心显然落在晚明僧侣的文学表现一侧,要在藉明代佛教史之研究成果,将僧侣在世俗社会之作为,置于整个晚明文化发展之大格局中,探索僧侣文学之重兴与政治社会及士大夫阶级交往等多重因素的关系,特别是于万历以来呈现高潮的诗僧创作,清理出如何由早期较为强烈的世道功用,转向后期诗禅交融的审美境界这一内在演进脉络,而恰与该时期佛教中兴、法界昌盛的进程相印合。

冯梦祯《快雪堂日记校注》
启元毕业后,即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他的相关研究,联系导师为文化史、宗教学等领域的大家李天纲教授。在天纲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出站工作报告《近世佛教源流下的晚明佛教复兴》。显然,此际的研究重心已转向近世佛教史,尤其是试图将佛教在近世社会的演进与万历以来佛教复兴的现象贯通起来解释,新作中的思路于此际已渐次形成,要处理的是相对阔大背景下更为复杂的生态及机制,也就是说,依据如许理和“三种佛教”理论、任继愈“佛教势力三个层次”所提供的分层阐说框架,考察政治、权力与信仰、学术、社会经济等相互摩荡的运行架构及态势。与此同时,他又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兼职,在接待众多来访的优秀学者的工作中,获得他们有益的指点和帮助,也因此打开了海外汉学的视野,这使得他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上有不少积累和训练,拓展了不少新关注的面向。
全面修订后的三编,上编集中讨论晚明佛教与其时宫廷政治的关系,通过聚焦慈圣李太后奉佛及礼事高僧、崇祯帝在本土释道与外来天主教之间的选择、憨山德清乙未之狱、紫柏真可“妖书案”等事件,在重新厘清各自原委、经过,并试图揭示更为隐秘的动机的同时,抉发隐伏在信仰生活背后与晚明党争密切相关的诸多政治、宗教势力较量的暗脉。中编围绕“方册藏”的刊刻事业,展示高僧与奉佛士大夫之间的互动,尤以密藏道开与冯梦祯两位重要助力者为例,呈现僧界与精英士大夫错综复杂的局面,究明世俗社会中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在刻经事业中的作用,以及此一事件对后世造成的长远影响。下编则是探讨晚明佛教的多种成色及其表现:如士大夫居士身上体现的本土宗教对佛教信仰的影响,文学艺术与佛教的联系,藏传佛教对汉地的影响及其本土化吸收等,仍是以不同的个案,展示这个时代信仰生活的多元特征。

憨山德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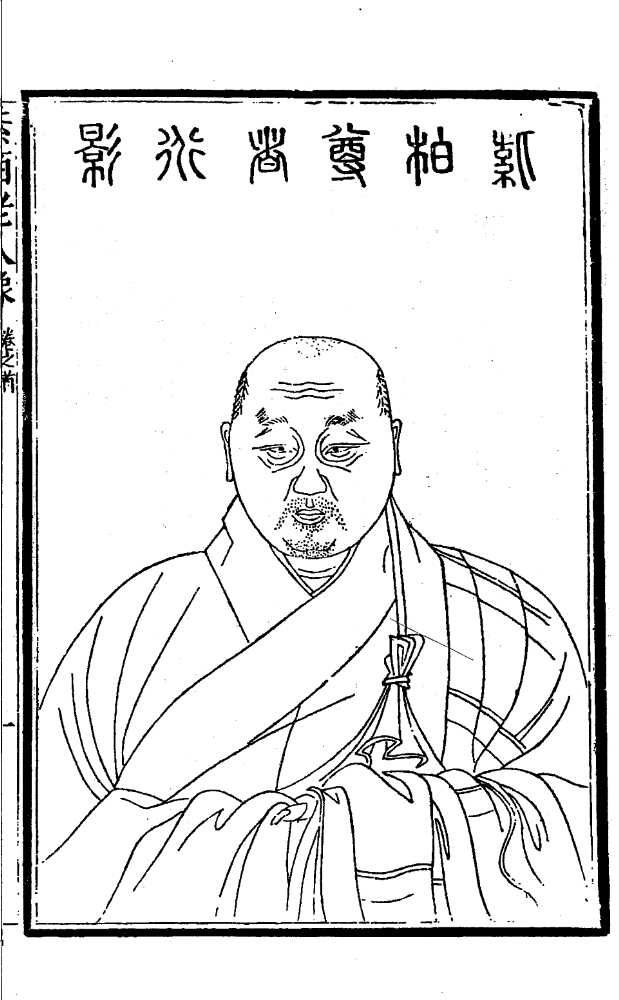
紫柏真可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新作中,因为要选取有新的开掘空间或重释价值的例证,作者并不纠结于整个叙述构架是否有严密的统一性,毋宁说,它更像是一种散点透视,透过宫廷帝后、僧团、士大夫群体交织的人际网络,分别就各自的立场、视角及其互动,探寻触发、推展晚明佛教复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尽可能还原整个过程中各结构性要素如何相互作用,它们在实际碰撞、交流中与目标之间形成怎样的张力。于是,各章节的叙写受问题的引导,总体上仍构成一有机的大事件。整个结构可以说是一种互文式的,事件与事件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材料与材料之间,各有其内在关联,依靠这种多棱镜似的相互观照,完成整个图景的复原。
启元在试图做好这一大事件叙述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将其中的细部展示给读者。他不仅注重利用尚未被充分关注的僧侣及士大夫居士的尺牍、日记诸史料,乃至碑刻图像资料等,通过细致的排比、对读,去做一些解蔽的工作,甄辨不易发现的事实;而且尝试用心体会其中的曲笔,以一种特别的敏感,构建对该问题可能的阐释。当然,当史料并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时,他的探考也审慎地暂付阙如,留待今后再解。对于明清佛教研究而言,所存史料的浩若烟海,与所受关注的程度往往不相匹配,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全方位地捜辑并举证材料仍是征实还原现场的必要手段,如启元曾自述,他运用愈益琐细的尺牍、日记中相关记载,即旨在“尝试挑战或纠正之前研究中普遍根据僧人自述等单一史料所建立的佛教史话语权”[②]。而在另一方面,面对那些被忽视、被误读的材料与语境,史学批判的重要性日显,更加让人感到在近世佛教史研究中解构或去蔽的紧迫性,也因而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新的叙事方式,启元同样将之视作是自己学术上精进的凭据。
关于“四高僧与佛教史建构”,是启元在全面修订中新设的一个话题,可看作是学术经典化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四大高僧谱系之成立、变迁,显示他们在晚明至清盛期被接受的动态过程,是僧侣与精英士大夫之间双向对话与形塑的结果。正因为此一谱系构建几乎就是晚明佛教史的缩影,牵动着这个时代纤细而多极的神经,故其复杂的程度自亦难以言状。我在读《陈眉公先生全集》时,曾看到这样一则材料:崇祯七年(1634)冬至后,华亭居士薛正平(字更生)携《庆历六道人像》入山访眉公。此所谓庆历,乃隆庆、万历之省称,据陈继儒所记,六道人分别为遍融、达观、云栖、憨山、雪浪、卓吾李和尚[③]。其时六人皆已作古,而同被列像供奉,深感或许是认识崇祯间四高僧谱系是否成形及其以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构成类群的重要线索之一。薛氏晚年以字行,从觉浪道盛学参禅。其卒,钱谦益为撰墓志,称“少为儒,长为侠,老归释氏”[④]。鉴于我掌握的其他材料相当有限,难以对此作出有效的解释,故特将所见奉呈于此,就教于启元,以求获致更为圆满的结论。

陈继儒像
忝为启元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承嘱略书数语。说来惭愧,我在启元所关注的领域并没有什么研究,无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商讨意见,但却很高兴看到他转益多师,不断挑战自我。近年来,启元在近世佛教史领域探研乐此不疲,积储日富,气象日新,有不少充满激情、追求高远的研究计划,期待他不懈努力,砥砺前行,弘而胜其重,毅而致其远,争取更大的成就。
壬寅夏于抱朴守拙斋
[①]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三《士大夫之禅悦及出家》,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页。
[②] 《从五台山到径山:密藏道开与嘉兴藏初期经场成立论考》,《法鼓佛学学报》第20期。
[③] 《题薛更生卷》,《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五十一,明崇祯间陈氏家刻本。
[④] 《薛更生墓志铭》,《有学集》卷三十一,《四部丛刊》景清康熙三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