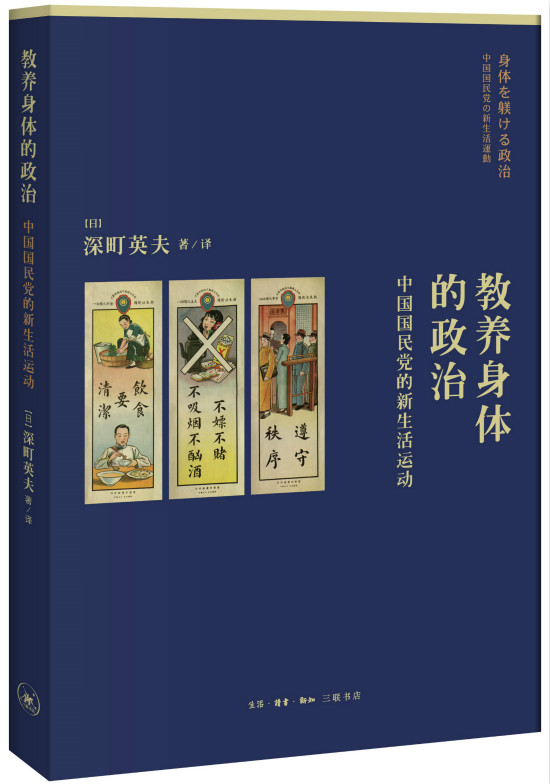“扣好钮扣,勿吐痰”: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
扣好钮扣,勿吐痰!
1934年2月至3月期间,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江西省南昌市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对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做出了如下描述:
比方说,江西的中学生,现在虽然大多数都比较好了一点,但是我去年初来的时候所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
你看吃饭的时候,不要说一切食物、食具零乱、污秽,而且吃的时候,有的将身体靠着墙壁或门板上来吃,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地下,有的站在门外。吃完以后,菜汤饭屑弄得狼藉满地,甚至使人家不敢进身。……再讲普通一般中国人的穿衣,十个有九个是钮扣不扣齐的,帽子歪戴的。还有对于自己身体不仅不知洗澡,甚至连脸也不洗的。……再讲住房子,普通一般中国人,没有几个知道住房子是怎么住的,尤其是中国人住洋房,笑话更多。就是洒扫,也只知扫除房子中间一块,至于屋角或门后,就不堪言状,堆满垃圾,布满尘土,甚至一年半载,没有人去过问,听他发臭、生微菌。试问如此住宅,安得不发生疾疫?还有一般人随便吐痰,到处解手。
为了改善中国人的这种日常生活习惯,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2月21日正式成立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他的心腹邓文仪任主任干事,由邓文仪起草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以“规矩、清洁”两项为目标,还规定了《新生活须知》95条。这些围绕日常生活中各项行为的极其具体、广泛、细小的一系列规定,就是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内容。

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在江西省进行第五次“剿共”战,试图歼灭共产党在该省南部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九一八事变已过去约两年半,东北四省已成为沦陷区。而经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直至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统治结束为止,新生活运动共持续了十五年之久(虽其性质和内容有所变化)。对此,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个既简单又根本性的疑问——面临如此深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何故发动并持续了这种略带肤浅、琐碎之嫌的启蒙运动?而且,它何以发展成为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此时,整个民族是否忽然患上了集体性神经质或洁癖症?抑或此运动只不过是独裁政党发动的强迫性群众动员而已?简而言之,国民党政权何故且如何企图介入、干预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胡适的质疑
对于蒋介石发动的这场不可思议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虽出现了不少赞同的文章,但也有一些表示否定态度的言论。例如,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最全面的、最深刻的批判。他赞扬蒋介石的人格说:“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烟卷。”但是,对新生活运动本身,他毫不客气地加以批判。
他的第一个论点是生活礼仪的改良不能解决国民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写道:
《须知》小册子上的九十六〔五〕条,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做到了这九十六〔五〕样,也不过是学会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人样子。我们现在所以要提倡这些人样子,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里还有许多人不够这种人样子。九十六〔五〕件,件件俱全,也只够得上一个人的本分。
第二个论点是生活习惯的改良应该是教育运动,不是政治运动。
把一些生活常识编到小学教科书里去,用一些生活常识做学校考绩的标准,用政府力量举办公众卫生,用警察的力量禁止一些妨害公安与公共卫生的行为,官吏公仆用一些生活标准来互相戒约,这些是政府所能做的。此外便都是家庭教育与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了。……若靠一般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摸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可以增加虚伪而已。
第三个论点是中国经济水准过低,缺乏倡导提高道德的物质条件。
父母教儿女背着篮子,拿着铁签,到处向拉〔垃〕圾堆里去寻一块半块不曾烧完的煤球,或一片半片极污秽的破布。……大学学生——甚至于大学教授——假期回家,往往到处托人弄火车免票,他们毫不觉得这样因私事而用公家的免票就是贪污的行为。凡此种种,都是因为生活太穷,眼光只看小钱,看不见道德。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
胡适的议论可简述为三点,即:(1)在国难当中,(2)即便开展政治秀,(3)也不能靠文明礼貌吃饭。这些论点几乎把新生活运动所包含的所有问题都分析得淋漓尽致。虽然如此,新生活运动如上所述扩大到全国,并持续了十五年之久。胡适对这场运动所持有的诧异和疑虑后来并未得到解决,甚至遗留至今。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是时代的必然
国民党政权在与共产党进行内战之际,开始实施宪政,蒋介石于1948年5月20日就任总统,但显见败势已明,遂于翌年1月21日下野,在浙江省奉化老家静观局势变化。当渐近2月19日新生活运动15周年之际,黄仁霖向蒋介石询问了有关运动的前景问题,蒋回答说:“目前暂时把新生活运动的一切活动停止办理。” 2月12日,蒋介石听取了黄仁霖的“接收美援此次到台之武器数量以及军费之报告”,上述的对话或许就发生在此时。对于正在准备撤至台湾的蒋介石而言,新生活运动的使命已经结束。此时运动本身已处于低潮,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机关报《新运导报》第15年第2期,即自上一期后,间隔了半年之久才于1948年10月31日发行,但此后似乎停刊。
新生活运动于1943年2月19日发起后,旋即以星火燎原之势扩展至全国各地,并将蒋介石推举到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即使在中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亦未曾中断,但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之际,随着蒋介石的下野,运动默默地拉下了帷幕。
笔者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是时代的必然。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原为最强烈地认同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而不是特定的区域、阶级或传统文化的革命精英集团,企图通过党国体制(party-stateregime),即作为前卫革命政党单独地掌握权力,并将其组织浸透于各个阶层,由此成为国家、社会之间唯一的媒介,进而由政府驯化人民,普及认同民族共和国的观念,简言之,即创造出近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然而,国民党通过国民革命掌握全国政权以后,蒋介石采取了“重军轻党”的方针,使得孙中山的体制构想,即由革命政党指导国家及社会,逐渐趋于形式化。
虽然如此,国民党的统治正统性使其自认为该党是创造近代国民的典范,是故正如模仿自己而创造出人类的上帝一样,始终不能放弃创造国民的责任。尤其是蒋介石,为了对抗正在威胁中国独立和统一的日本,企图以曾在日本接受过“身体的教养”的自己为模范,将中国人民改造成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国民。但是,与主要通过军队、学校等集体生活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公共意识的欧美、日本(及其殖民地)不同,中国采取的全民皆兵及国民教育的制度非常落后,因此仅能通过由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身体的教养”,于是发起、推动了新生活运动。
赞同、参加这场运动的人物中不仅有邓文仪、杨永泰、黄仁霖等蒋介石的心腹,亦有与蒋介石同样怀有近代化志向的汪精卫、阎锡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以及曾毅等民间知识份子与牧恩民等西洋传教士,蒋介石由此作为“教主”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但是,尽管新生活运动主要在城市实行,对于提倡、强调与传统观念不同的近代性身体观、社会观的由上而下的启蒙/监视,一般人民却往往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应对,导致了这场运动的戏剧化和空洞化。总之,正是为了对付国难,才须要普及文明礼貌--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从而创造出近代国民,为此所采取的方法即使是注定将以失败告终的尝试,但除了发动政治秀般的群众运动之外,国民党政权毫无其他方法。
新生活运动发动后不久,日本人就浅薄地认为这是一场排日策谋,于是动员曾让蒋介石羡慕不已、并非常畏惧的绝对性国家能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得国民党政权在未能创造出近代国民之前被迫卷入近代总体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筹集当前所需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抚慰”在战火中受伤的中国人民之身体的活动在新生活运动中所占的比例则日益上升。
妇女起初是被期待成为在家庭中将孩子“教养”成为近代国民的角色,但宋美龄等提倡男女应平等地参与社会,在其倡导下,妇女逐渐转化成作为“抗战建国”的劳动力被动员的对象,新生活运动则推动了托儿所的开设。此时,为了“抚慰”作为盾牌而受伤的下层民众的身体,国民党政权开展了徐维廉首倡的“伤兵之友”运动;对于成为中国救世主的驻华美军,黄仁霖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则积极进行了各种接待工作;这两种活动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中美两国军人所受到的待遇差距之大清楚地反应着国民党政权的苦恼,即在未能成功地完成近代国家军队编制的状况下,不得不依靠比敌军更为强大的盟军,唯此才能获得抗战的胜利。
总之,国民党政权虽然确实未能成功地创造出近代国民国家,但勉强保住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尽管如此,天意和民意对其还是过于刻薄。正如唆使亚当和夏娃使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可耻之物的蛇成为人们诅咒、厌恶、畏惧的对象那样,在与至今尚未形成的想像上的“中国国民”进行比较的状况下,对中国人民的身体进行蔑视、否定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权终究被人民大众唾弃、排斥,最后被迫撤离大陆。与此相反,另一个前卫革命政党因以提倡代表占中国人民最大多数之特定阶级的现实利益为正统性原理,成功地策动、利用了社会内部的竞争关系,从而取代了国民党的统治。

中国人是爱迪生吗?
然而,对1949年以后相隔于台湾海峡相互对峙的国共两党政权而言,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近代国民这个课题仍然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由日本殖民地转为中华民国一个省份的台湾,于1947年8月21日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日益激烈的国共内战中,作为动员工作的一环推进了这场运动。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1952年1月1日发动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其内容中有“社会改造运动”、“文化改造运动”,即开展了民族精神教育和清洁运动等。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1966年11月12日发起,并于翌年7月28日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其主要活动为颂扬传统文化和孙中山思想。《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第6项规定云:“积极推行新生活运动,使国民生活在固有文化四维八德薰陶之下,走上现代化与合理化,同时政府应积极研究制定完整之礼乐与礼仪,使中外人士均能体认我为礼义之邦。”。1968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国民生活须知》99项,其大半酷似30多年前的《新生活须知》。
当时大陆正在进行着否定传统思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以继承中华文明为己任,以此主张自己的正统性。这种以传统文化作为国民统合的精神依据,正是继承了新生活运动的源流。但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具体成果、影响并不明确,蒋介石亦终究未能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于1975年4月5日逝世,其后这场运动似乎不了了之。对于曾受到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并成为自己离世之处的台湾之社会及人民,不知蒋介石晚年持有何种看法。
在大陆,出于对美国可能会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恐怖,共产党政权于1952年7月10日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党中央及国务院于1958年2月12日指示驱除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等“四害”。“文化大革命”之后,1981年2月25日开始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倡“五讲四美”的运动。进入21世纪以后,2003年非典(SARS)蔓延时,仿佛新生活运动复活一般,详细地指摘了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在纪律、卫生上所特有的“陋习”。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际,北京市政府规定每月11日为“自觉排队日”,并对随地吐痰的行为进行了批判。2010年举办世博会之前,上海市政府呼吁居民不要穿着睡衣出门,其是与非引起了争论。而2012年的流行语就是“中国式过马路”。
这些运动和言论的成果及影响虽不易评价,但60多年来反复指出同样的问题此一事实本身即意味着近代性身体观和社会观在中国社会的普及是何等之难!那么,在新生活运动发起8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难道仍未成功地实现近代化吗?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近代国民的目的确实不能说是已经完全实现了。最近爱国主义时有暴力形态的表现,这种现象表明出来的与其说是民族意识的强烈性,不如说是公共意识的薄弱性。虽然如此,在此期间中国经过多重磨难不断发展,毫无疑问现在已成为对全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军事、经济超级大国。与先进诸国的事例比较起来,中国的这种近代化过程该如何理解呢?
“近代化”的概念很难定义,但在非西方世界(至少在东亚),它似乎可以说是随着国民国家的自我建成或被列强殖民化(或双方并行)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具体而言(尤其是前者),为了对抗列强维持独立和统一,须要加强社会编制(普及教育、振兴产业等),由此必须尽量增加从社会上筹措的人力、物力资源。与此同时,对于原来仅为征发赋税及维持治安之对象的人民,促其转化成为主动致力国家发展的“国民”,为此须要逐渐进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近代国民的这种尝试,是试图培养出既勤勉又健康的士兵和工人,并以此提高国民国家之军事、经济潜力的社会编制之一环。
若将这种“身体的教养”或近代化过程本身单纯地描绘成是充满希望的或是暗淡无光的,均过于片面。应该认为这既是启蒙、改良,同时又是监视、控制,正如章炳麟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的“善恶并进,苦乐并进”那样,是善恶苦乐与时代并进的过程。“身体的教养”确实具有个人服从国家的含义,不过前近代社会中的个人亦并非独立于血缘、地缘、宗教等规范而能享受到自由的个体。从长远来看,近代国民的创造促进了对个人的尊重,即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而已确立了参政权和社会权的先进国家成功地建立了尊重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法治社会,此亦为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极其耐人寻味的是中国虽然在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国民的过程中辗转迂回,但却成功地加强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并提高了国际地位。换言之,21世纪的中国并未按照先进诸国曾经走过的近代化路程行进,而是作为特异的“后近代(post-modern)”超级大国,即以富强为目的的国家高于个人的方式,正在崛起。……正如“中国模式”及“北京共识”等概念所示,中国是否要树立新的“近代化”榜样?
若将中国的这种“近代化”过程与同样受到西方列强冲击后开始推进近代化的日本经验比较起来,笔者不得不想起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众所周知,爱迪生少年时期不能适应学校的教育,但长大后却成为了著名的发明家,由此显示出曾将其排斥的教育之缺陷。若将日本人比喻成为略微凡庸的优等学生,即未对“近代”这本教科书之内容是否妥当产生任何质疑,就开始了有时甚至比西方先进各国的学长们更加认真的学习,从而实现了近代化,那么,中国人则仿佛是具有天才气质的劣等学生,即由于其所具有的强烈个性而未能适应学校的功课。
中国终究是通过其爱迪生般的独创性的成功迫使人们改写陈旧的“近代”教科书呢?还是现在的发展方式在不久的将来失去其有效性,不得以重新接受“近代”的补习呢?――此一问题尚未得出答案。
(本文节选自深町英夫著《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