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开卷|带着审美眼光,美术史家的“海外旅行”
萨德瓦尔德[1900—1974]曾说:真正的翻译是一种本质上带有否定性的活动,译者努力抹灭巴别塔计划失败后人类语言的淆乱。美术史译作若能清晰而完整地传递原作的意思,那它就和原作一样好。倘若它再能让读者带着很大的愉悦和美感去阅读,那它也许能成为著作,译者也许能成为经典作家。艺术理论可以傅雷先生翻译丹纳的《艺术哲学》为例,它的语言之美可能已超过原文。
近期,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乔治·罗丽的著作《中国画的原理》,这是“海外中国艺术史译丛”的系列第一册。该书试图阐释中国文化特征并分析其在绘画原理中的表现。《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译丛主编、艺术史学者范景中教授撰写的丛书总序。

《中国画的原理》 [美]乔治·罗丽 著 刘晶晶 译 海外中国艺术史译丛01 | 范景中 主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中国画的原理》内页
20世纪80年代初,洪再新先生和我经常讨论中国美术史的一些问题。记得有一次向他建议,是否抽暇写一部中国美术史学史的著作,准备工作可以从外国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文献开始,因为海外起步得早。我当时正关注西方美术史的学术史,在想象中,若把中外都周览一过,让美术史来一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参酌,或许中国美术史的格局和境界都会大变;而忽于道术的精微、群言的得失,必然盲入歧途。这也是1984年《艺术的故事》的译稿搁浅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无人审稿,我便借机为之编写笺注、推阐其义的原因。那时,正好朱季海先生发表《朗润园读画记》(1984),谈到喜龙仁、施派泽、罗樾和高居翰等西方学者,也提出“希望有更多的人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以为当前中国画的创新作一铺路石”。洪再新与朱先生为忘年好友,受到鼓舞,即欣然把目光投向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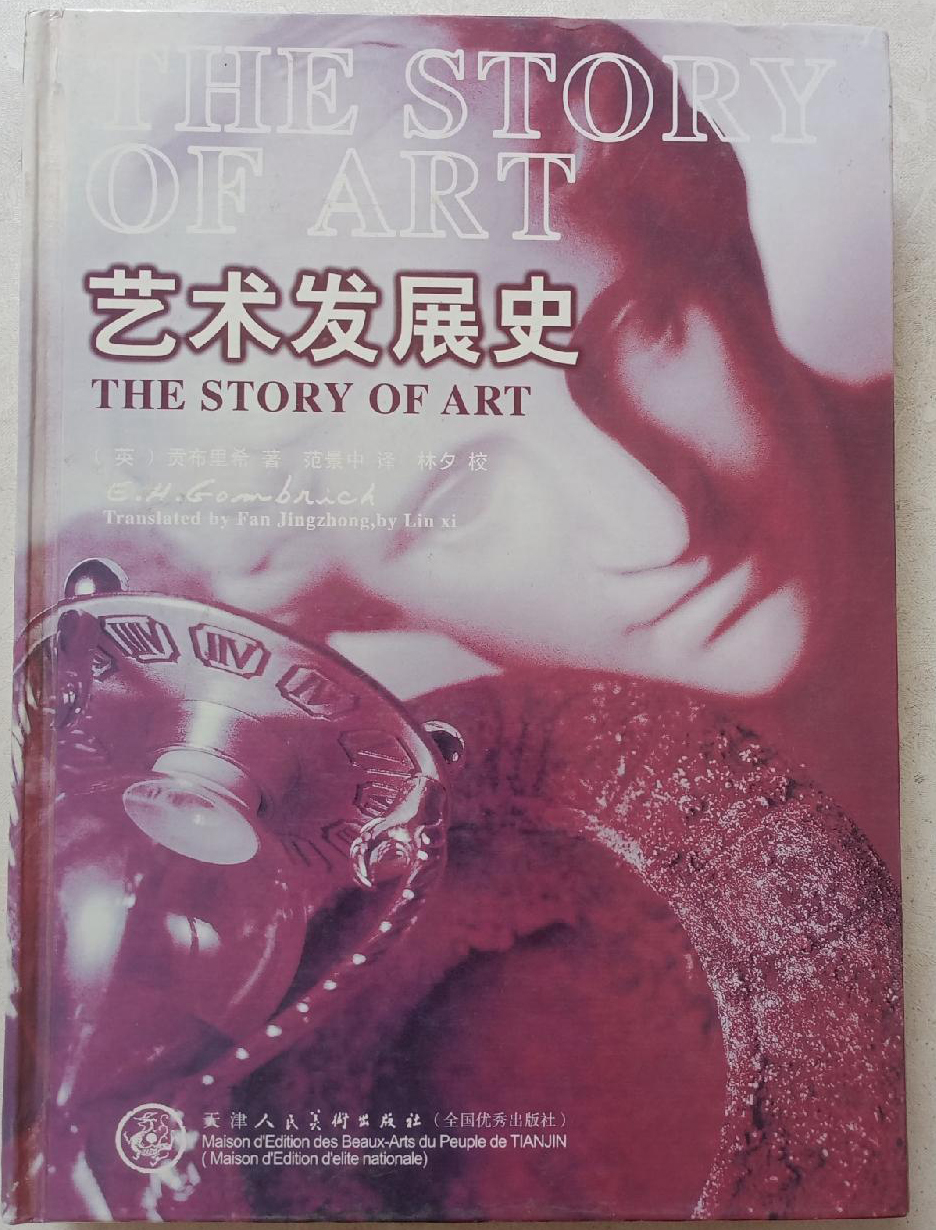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年,洪再新先生努力的第一项成果完成,书名为《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这是第一部有系统地以编史的模式展示海外中国画研究发展的著作,它以评介式的翻译文集方式出版。为什么选择译文的方式,道理很简单,在海外中国美术史已纳入大学教育中的人文学科,而在中国,它只是一门附属。中央美术学院虽然率先一步,但很快也停足了,所以我们有必要让中国的学者了解海外的工作。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翻译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论著已蔚然大观,重要的学者像喜龙仁、方闻、高居翰等人的著作都有成套的译本,上海书画出版社还推出了十几种日本学者的著述。在这种翻译成果丰硕且颇有越界之势的情况下,我们是仍然继续,还是把它限制在某种范围,防止它对我们构成威胁,或者干脆停止翻译?对于这个问题,虽然言人人殊,但也许把它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进行考察更为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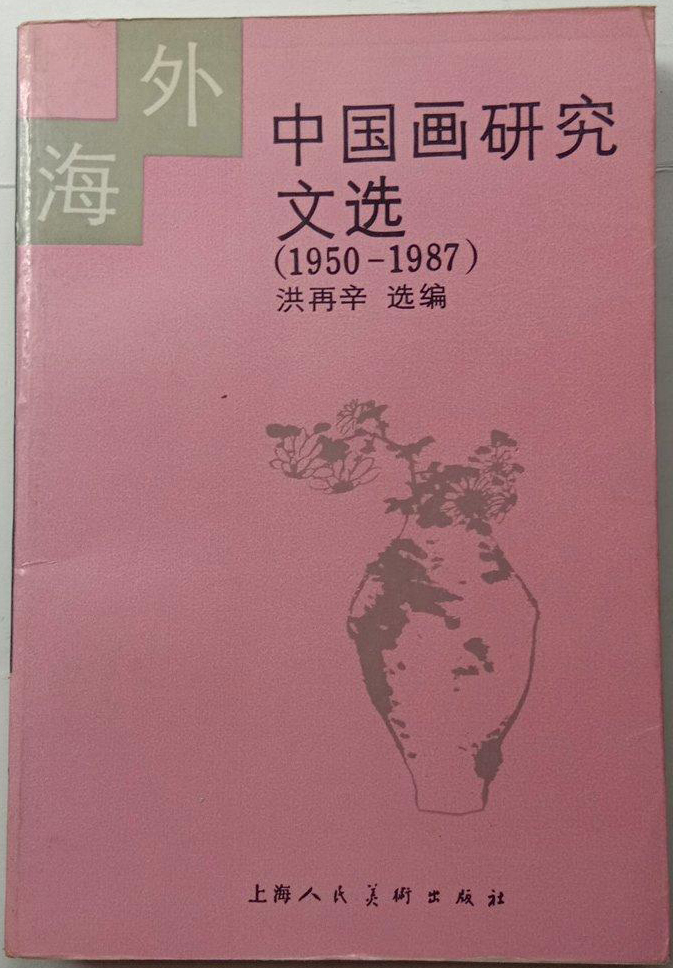
洪再新《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
一个多世纪以来,翻译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从某种意义上,是以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方式,倚重翻译来接受他者,进行不断扩展的,因此,我们是经历过翻译冲动的民族,并且深刻地印证了歌德的一句名言:一门语言的文化的力量不是推拒他者,而是将之吞噬。我们的语言在经历了持续的培植、发展和活跃之后,也一如席勒所说,从“隐藏的深处[die verborgenen Tiefen]”,迸发出重生的活力,获得了形而上的发现。
翻译能成为一种历史的力量显现在文化中,但它往往不是靠一二本译作,而是靠一批译作来催生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像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古典时代之间的深刻联系,就是通过一波翻译古典著作的运动展现的。法国的古典主义与古罗马文学的联系也是如此。我们今日的中国美术史即是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一次翻译的热潮才形成今天的面貌。我们翻译外来的著作,不只是获取有益的信息,而是在互化互生中让强健的灵魂随之流动[Interinanimates two soules/The abler soule which thence doth flow]。因此,有时表面看来过时的信息,甚至错误的信息,在某种语境中,也会让人有意外的惊奇。杨思梁先生告诉我们,即使像一部出版于1908年的英国学者宾雍[Laurence Binyon,1869—1943]的《远东绘画史》[Painting in the Far East]那样陈旧的书,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艺术理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大名鼎鼎的批评家罗杰·弗莱正是阅读宾雍的著作,汲取“六法”的理论,才为其理论赋予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空谷之音,让西方世界认识到不仅塞尚的画中流动着气韵,即使“波蒂切利,在本质上也是一位中国艺术家。他依靠线性韵律来组织构图,而且其韵律具有一流中国画所展示的那种流畅,那种优雅轻松”。借用气韵生动的观念,弗莱还覙缕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一连串的画家。

宾雍 《远东绘画史》
宾雍的故事还不算完。杜姆[Thomas Leslie Dume]在博士论文《叶芝的阅读》[Yeats: A Survey of his Reading,1950]中讲道,《远东绘画史》也把爱尔兰诗人叶芝带入大英博物馆,带入中国艺术,并化进他的诗歌创作,我们熟悉的吟咏艺术意蕴的名篇《天青石雕》[Lapis Lazuli]就足供佳例。
另一位主攻美术史的东方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对我们来说已然是位陈旧的人物,但不要忘记他对波士顿中国艺术收藏所作的奠基性贡献,也不要忘了他对中国书写的兴趣所留下的遗作《中国书写文字之为诗歌媒介》[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那部书激荡起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灵性,促使他翻译了名为《华夏集》[Cathay,1915]的中国古诗。有意思的是庞德不懂中文,更不要说中国古诗,但他通过观察中国文字而改变了自己的语言感觉,并为英美现代诗歌的节奏定下格局。又一位精通中文,也研究中国绘画题诗和印章、在大英博物馆供职的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看到庞德翻译的《长干行》,涌起兴致,也迻译为英文。第一句“妾发初覆额”,庞德的文字为:While 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韦利给出的是:Soon after I wore my hair covering my forehead;评者认为前者更精确,更有意象;而著名的不妥之句At fourteen I married My Lord you,却恰好表达了不知礼节的孩子的特有口气,一副灿然的天真;一痕传神之笔,韦利却没有抓住。庞德善于吸收中国文化的姿色与体态,即使错了,也给人启迪。这让我们想起中国美术史中的类似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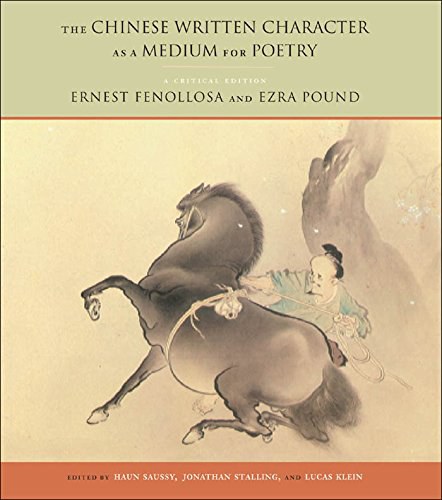
费诺罗萨《中国书写文字之为诗歌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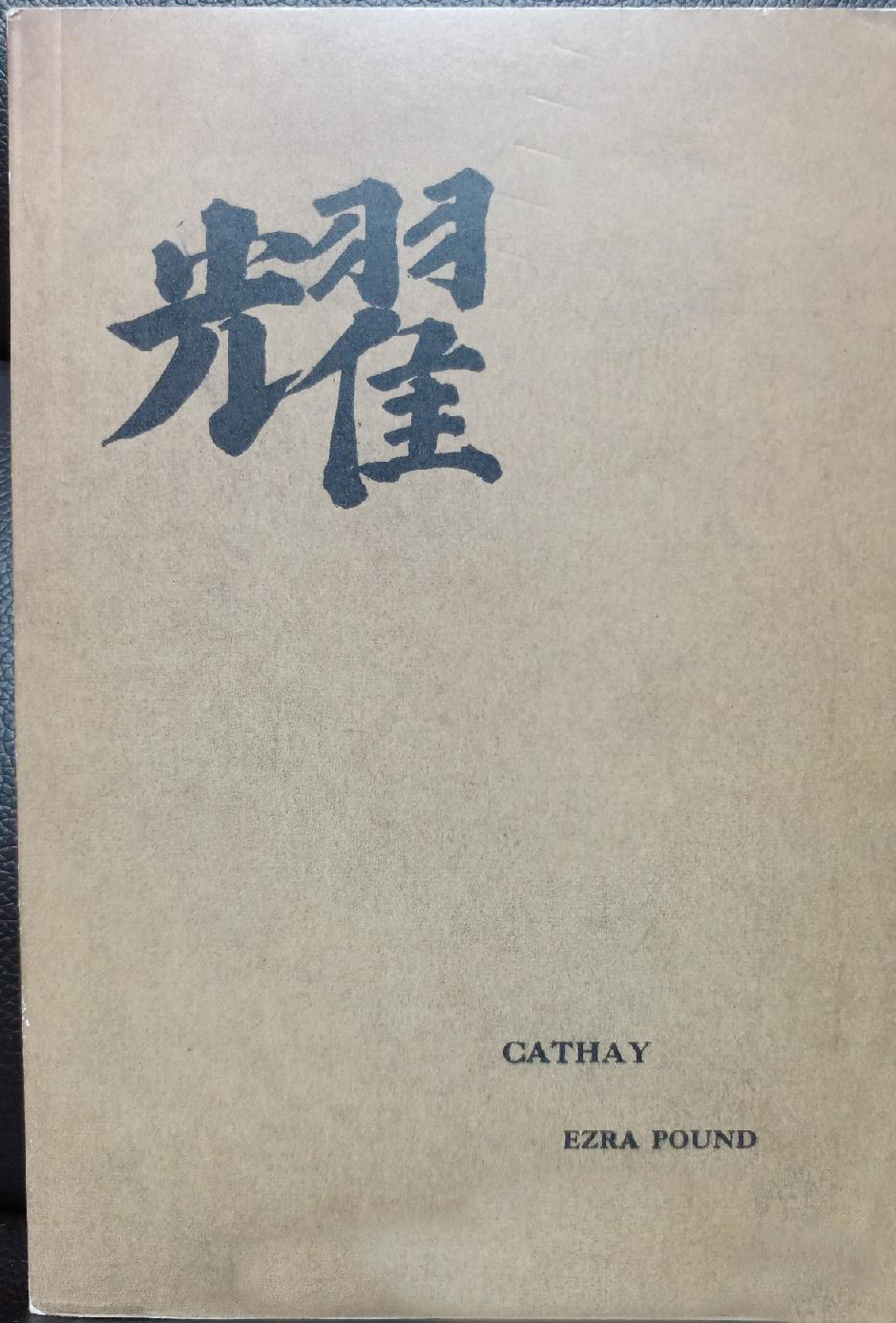
《华夏集》
高居翰先生的《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是我非常敬佩的一部杰作,第三章讨论吴彬、西洋影响及北宋山水的复兴中有一个假设:晚明的一些画家因看到西方绘画而改变画风,其中吴彬是一位受影响既深且早的画家。具体说就是,吴彬1570年到南京,直到17世纪20年代去世为止,主要往来于南京与北京两地,故有机缘与传教士接触,极有可能观赏过利玛窦1601年献呈万历皇帝的油画与图画书,例如1579年出版的《全球史事舆图》[Teatrum Orbis Terrarum],它们影响了吴彬的风格取向。高先生批评那种认为吴彬是对真景描写的观点:
纵使到了今日,中国学者仍坚持吴彬画境之奇,乃是源自于他在福建或四川之所见,而无法归诸为画家心灵想象的飞跃。

高居翰《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
我同意吴彬不是对真景写生,但也怀疑高先生的假设,即吴彬看到西洋画后才发展出一种奇异的风格,因为我曾看过吴彬画于1570年之前的一幅长卷,所绘的景象奇特反常,那时他不可能见到西洋画。不过,即使高先生的假设经不起反驳,却依然含有丰富的洞见,是一个有瑕疵的生气盎然的假设。它不只引起我们对吴彬的重视,还让我们重新看待园林图、没骨法和凹凸画等,尤其是北宋山水画复兴的大问题,让我们以崭新的眼光重新看待那一段历史。
《气势撼人》不仅敏于思,而且精于言。读这部书常常让我想到翻译的问题,想到不同的语言之网如何捕捉画面中对象的问题。下面引用王嘉骥诸位先生的译文并参照原文稍稍修改,看一看高居翰先生对王蒙《青卞隐居图》的描述:
《青卞隐居图》以底部河岸边的几排树展开近景,然后在画面上方以远山峰峦为结。较为宁静的山径围绕着无限扩展的中景部分,同时,却又似乎涵摄不住其中因动态形体[dynamic forms]间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所产生的一股股骚动的力量。中景的部分被压缩,成为一垂直平面[vertical plane],排除了此中蕴藏深度[depth]暗示的可能性,使得中景和近、远景之间无法连成整体,这样一来,却创造出了强烈的空间多义性[spatial ambivalence]……它汲取了郭熙传统中的强烈而且带戏剧性的光影[light and shadow],以及土石造型上的有力动感……画中表现主义的张力[expressionist tension]不仅抵制了现实实景的形貌,同时也与较正统的仿董源风格或郭熙传统的追随者们所可能表现的山石的含蓄且理想化的图像[ideal images],形成了一种拉锯关系。
这种描述方式,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在写作中也会采用,几乎忘记了它是翻译的语言。而老派的学者显然更习惯下面的描述:
此图水墨山水,满幅淋漓,山顶多作矾头,皴法披麻而兼解索,苔点加以破墨长点,更为新奇,此乃自开生面者。其间山势嶾嶙,林木交错,一人曳杖步于山径。画左山林深处结庐数间,堂内一人倚床抱膝而坐,甚得幽致,此乃隐居之所也。按叔明作画,多宗董巨,有时追宗右丞,界画法卫贤。此图全用巨然法,其荒率峭逸,而又超乎巨师之外。(《墨缘汇观》)
两种描述《青卞隐居图》的文字都出自专门之家,却创造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人们很难想象这是面对同一幅画的观感。第一种描述标出外文的地方都是外来的概念,至于矾头、破墨和皴法之类则是西方根本不存在的术语。这让我们认识到,不同的语言之间,可以互相引导,互相启迪,在对方的映照下,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语言的可能与局限,意识到语言中存在的处处空白,从而理解了自身语言的运作方式。
对于美术史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其中还含蓄着一种翻译中的翻译。高居翰先生在写那段话时,他显然面临着一种任务,即把事物变成名称、把画面变成陈述;这种“变成”的过程即是翻译,而且是一种艰难的翻译;因为我们不仅要用颗粒状的分立的词语把连续的画面表达为语言,还要形容其笔墨和色彩,揭示出画面上实际见不到的风格和气韵;而语言主要处理的却是共相和概念,词汇表明的也是性质和类别;实际上,语言之网是一张漏鱼之网,它会让我们处处捉襟见肘,逼迫我们去追逐词语;不过,这也正是一件幸事,否则语言会有无穷的词汇,我们也就很难学会了。陆士龙云:“虽随手之妙,良难以词谕。”这是美术史家天天都能感受到的。
不知不觉,我们已进入了语言哲学的边缘,趁着未被形而上的迷雾牢笼,还是赶紧返回翻译的领域。从事所谓学术的人都知道翻译学有一个假设,那就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用一句夸大的短语所表达的,“翻译生发了所有的科学”;简言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不仅仅是信息传递,它还对学科的构建发挥作用。在美术界,最明显的事例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术译丛》所引入的观念,例如图式、赞助人、艺格敷词、形式分析和图像学等,它们对中国美术史的构建作用已不言而喻。然而,当时引入的最重要的观念,也许是“普通知识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General Knowledge]”的观念。正是这种传统面临着世界性的衰退,所以,翻译显得尤为重要。

《美术译丛》
翻译对于一个民族语言的塑造,大概德国最典型了,德文的诞生就是同路德的《圣经》翻译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歌德深刻地思考了翻译的价值。他将之放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大背景去看待,他的信念是:“艺术和科学,跟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物一样,都属于整个世界。只有在跟同时代人自由和全面地交流思想时,在经常向我们所继承的遗产请教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得到不断的发展。”(《箴言与沉思》页448)他本人不但翻译了不少世界名著,而且也关注美术史的作品,翻译了《切利尼自传》[Leben des Benvenuto Cellini,1797],这是我们至今还经常述及的。正是艰辛的翻译实践,让他对不可译的困难怀有惊人的洞察:“翻译者必须触及不可译;只有那一时刻,他才能对别的民族和别的语言有所领悟。”(《箴言与沉思》页479)人们不仅无须回避不可译,而且要尊重它,因为那正是一种语言的价值和品格。他提出的三种翻译,尽管扎根于更深刻的理论,但是或许能够有助于我们美术史的翻译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第一种翻译让我们熟悉外国文化,它将外语内容通过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方式呈现。这种翻译最好采用平实的散文语体。这样翻译的外语作品,可以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几乎不会意识到这股在我们周围流淌的崭新而令人振奋的感觉。
第二种翻译通过替换来获取。译者吸收外语作品的内容,并用自身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构成一种新的作品以替换原作。外来的内容用本土的形式取而代之。译者不惜代价,要让异域的种子在自己的土壤中结出果实。
第三种是最高的、最终的翻译模式,它力求实现译文和原文的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意味着新的文本“并不替代原文,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发挥原文的作用[so dass eins nicht anstatt des andern, sondern an der Stelle des andern gelten solle]”。它要求译者放弃自身文化的独创性,由此催生出一种崭新的“第三恩典[tertium datum]”。这样的翻译会遭到大众的反对,但它仍是最高贵的翻译。
如果把歌德的三种翻译与严复的信、达、雅做一番比较,说不定能从自身的翻译作品中反观出许多以往看不到的珍珠。翻译史上有一些现象可供我们参稽。文艺复兴也是一场翻译的运动,按照西蒙斯[John Addingdon Symonds,1840—1893]的说法,整个罗马成了将希腊文译为拉丁文的工场。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是第一位这样的译者,他是同时能够满足希腊文原著和拉丁文译著两方面要求的人,但他显然不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为满足,而是有悬绝于常人的更高远的志向,他把《伊利亚特》(IX222-603)中的三篇讲演译成演说风格的拉丁文,还在文中为荷马献诗一首。他翻译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让普鲁塔克从此名扬天下。他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原著散文中的韵律,也重新发现了古代拉丁文中的多重结构[numerosa structura], 这对于人文主义者模仿西塞罗式的拉丁文至关重要。另一位晚生半个多世纪的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1454—1494],十七岁即写希腊文诗歌,他自豪地将其翻译的诗体《伊利亚特》(四卷)命名为《青年荷马》[Homericus juvenis],显然,他也是以经典作家自居的。
科拉尔多[Collardeau]在18世纪末曾提出这么一个主张:“要说翻译有什么价值,那就是它可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完善原文,让原文更美,并赋予其一种属于我们民族的气息,将这棵异国的植物移植过来。”换言之,一个好的翻译会让作品重生。
《鲁拜集》是波斯哲人奥玛·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31]所写的诗集,几个世纪都默默无闻,1857年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把它译为英文,不但《鲁拜集》成了名作,菲氏的译作也成了英诗中的明珠。莎士比亚戏剧由于有了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尽管后译者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要想读莎翁,似乎仍以朱氏的译本为经典之作;不看译本,只要想想朱生豪投入的生命就令人震惊,他像是博尔赫斯笔下的梅纳尔:“殚精竭虑、焚膏继晷地用一种外语复制一部早已有之的书。草稿的数量越来越多;他顽强地修订,撕毁了成千上万张稿纸”[Pierre Menard, Author of the Quixote, 1939]。艺术理论可以傅雷先生翻译丹纳的《艺术哲学》为例,它的语言之美可能已超过原文,因为哈斯克尔教授告诉我们,丹纳的语言不是那么卓拔。它们虽是翻译,却似乎像是一种神圣的婚礼:菲氏翻译《鲁拜集》成为真正的《鲁拜集》,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成为真正的莎士比亚,傅雷翻译《艺术哲学》成为真正的《艺术哲学》;它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似乎堪与原作相埒,成为不朽之作,哪怕之后再有重译,也只能在婚礼中做个伴郎或伴娘;身为译作却是文学史或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译作,是成为著作的译作,而不是单纯作为文献或介绍性文本存在的谦卑译作。
萨德瓦尔德[W. Schadewaldt,1900—1974]曾说:真正的翻译是一种本质上带有否定性的活动,译者努力抹灭巴别塔计划失败后人类语言的淆乱。美术史译作若能清晰而完整地传递原作的意思,那它就和原作一样好。倘若它再能让读者带着很大的愉悦和美感去阅读,那它也许能成为著作,译者也许能成为经典作家。至于我们的领域现在是否有或将来可能有此种译作和译者,只有耐心地等待时间淘洗出的答案了。1603年弗洛里奥[John Florio,1553—1625]翻译的蒙田文集出版,卷端有一首丹尼尔[Samuel Daniel,1562—1619]写的序诗:
It being the portion of a happie Pen,
Not to b’invassal’d to one Monarchie,
But dwells with all the better world of men
Whose spirits are all of one communitie.
Whom neither Ocean, Desarts, Rockes nor Sands,
Can keepe from th’intertraffique of the minde,
But that it vents her treasure in all lands,
And doth a most secure commercement finde.
Wrap Excellencie up never so much,
In Hierogliphicques, Ciphers, Caracters,
And let her speake never so strange a speach,
Her Genius yet finds apt decipherers…
诗的大意说:
要让笔杆欢快起来,就不应受专断的牢笼,而应与天下更高尚的具有大同精神的人同在。海洋、沙漠、岩石都阻挡不了心灵的交通,她要在各地撒遍精神的珠玑。永远不要用密码字符将人类的精华包裹,也不要使用古怪的语言,而是让她的天才得到恰当的转述。
它点出了翻译的人文价值,这就是不受晦涩之物干扰和破坏的世界性的伟大的精神交流。歌德欢呼这种精神交流,因此他对翻译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翻译活动无论有多么不足,但它仍然是世界交换市场上的一项最重要、最值得尊重的活动。《古兰经》说真主为每个民族都派遣了一位使用他们语言的先知。所以,每一个译者都是他的民族的先知。”
帕兹 [Octavio Paz,1914—1998]说: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个人感觉,都浸没在翻译的世界中,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对其他世界的翻译,对其他体系的翻译[Our age, our personal sensibilities, are immersed in the world of translation or, more precisely, in a world which is itself a translation of other worlds, of other systems]。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或因寄所托,或受命译写,而美术史家整装到海外旅行,带着审美的眼光,盘桓在他国的花园,采集美丽的花朵,把它奉献给自己的祖国,让异域的花朵也来装饰我们的文明。这也许就是美术史著作翻译的意义了。
202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