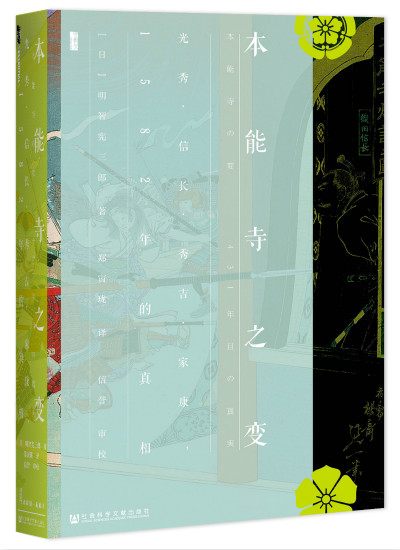明智光秀后人:丰臣秀吉是本能寺之变种种“定论”的始作俑者
胜利者散布的伪造事实
天正十年(一五八二)六月二日的早晨,京都本能寺被明智光秀的军队包围了。经过短暂的战斗后,本能寺陷入了一片火海,在那火焰中,未能实现统一全国之梦的织田信长结束了他四十九岁的人生。紧接着光秀军攻击了信长嫡子织田信忠所据守的二条御所,信忠最终也自杀身亡,至此光秀取得了“本能寺之变”的胜利。
可是,仅仅十一日后的六月十三日,光秀在山崎合战中败给羽柴秀吉,在朝着居城近江(今滋贺县)坂本城逃亡的途中丢掉了性命——这就是本能寺之变及其后的山崎合战的梗概。
以上内容是确定的事实。而作为所谓的历史常识,每个人都知道不少有关此事的各种传闻。
比如,信长屡屡苛待光秀,光秀因此产生怨恨而谋反,在吟咏的“如今正是好时机,土岐五月统天下”中宣告了夺取天下的决心;光秀独自策划了谋反,临事发前向重臣们表明心迹,发出“敌在本能寺”的号令后率军前往本能寺;羽柴秀吉在备中高松城之战中得知信长被杀,他号啕痛哭,为报君恩,决意复仇;等等。
但是,这一切都是创作的故事。它们只不过是在被称为军记物的故事中被创作出来的情节罢了,而这些故事创作于本能寺之变后数十年的江户时代。
那么,为什么在本能寺之变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创作出来的军记物里全都写着相似的内容呢?难道真的是因为它们更接近真相么?
其实它们都是“被当作真相而散布”的故事而已。某个人在本能寺之变发生的四个月后,对外正式宣称:本能寺之变因明智光秀对信长的怨恨以及他夺取天下的野心而起,且为光秀的单独犯罪。在不像现今这样拥有自由媒体的时代,若有人用强权散布“这就是真相”的话,那就会成为“事实”。
而军记物又在此基础上各种添油加醋、夸大其词。
比如“光秀因为被取消了在安土城中招待德川家康的宴席负责人的资格而怨恨信长”;“光秀遭信长留难而被打,所以怨恨信长”;“接到剥夺自己重要领地的命令从而怨恨信长”;“光秀的母亲因信长的责任遭到杀害,故而产生怨恨”——该说法就这样不断丰满起来了。
时至今日,还有人从各种方面推测光秀被信长讨厌的原因或是光秀怨恨信长的原因,继续添油加醋。在这之中,居然出现了光秀由于近视眼而眼神凶恶,所以被信长讨厌云云等新说法。这样一来,事情就成了只要饶有趣味,便怎么解释都行了。

秀吉的政治宣传书《惟任退治记》
那么,首先将这些说法当作“事实”传播的人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羽柴秀吉,也就是之后的丰臣秀吉。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情几乎无人知晓。
如今正是好时机,土岐五月统天下。
这句连歌作为光秀表明谋反心迹的证据广为人知。它是本能寺之变三天前,在光秀居城丹波龟山附近的爱宕山举行的名为“爱宕百韵”的连歌会的发句,也就是连歌的首句。那么,为什么这句连歌能如此广为人知呢?现在,若有重大事件发生,各家新闻媒体会同时对相关的事情进行调查,相关信息一下子就传播开了。而在当时是没有这类媒体的,照理说事件的相关消息不可能广泛传播。可是唯独“光秀所作之句”,连同光秀在其中的寓意都一并广为人知。促成此事的就是《惟任退治记》一书。
《惟任退治记》是在本能寺之变仅四个月后的天正十年(一五八二)十月,羽柴秀吉命其雇用的御伽众大村由己所写的二十页左右的短篇著作,书中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本能寺之变的始末,即所谓的事件报告书。御伽众乃是陪伴主君谈话的近侍,而大村由己则因其文采获得器重,担任类似现代宣传部官员的角色。“惟任”是朝廷赐给光秀的姓氏,如书名所示,这正是一部讲述在山崎合战中秀吉消灭光秀的宣传书。此书是在事件发生后,最早问世的交代本能寺之变始末的著作,也是秀吉针对本能寺之变发布的官方公告。
通过这本书,秀吉将“本能寺之变是光秀单独犯案,其谋反动机出自私怨,以及光秀早已怀有夺取天下的野心”变成了本能寺之变的官方定调。
为了证明光秀心怀夺取天下的野心,秀吉所出示的证据便是“光秀所咏的发句”。《惟任退治记》里是如此记载的:
光秀发句云。
ときは今あめかしたしる五月かな
今思惟之,则诚谋反之先兆也。何人兼悟之哉。
(光秀在发句里说道:“如今正是好时机,土岐五月统天下。”现在回想起来,这根本就是谋反的先兆,可当时又有谁明白呢?)
光秀的句子按字面来解释的话,意为“梅雨淅沥下不停,便知时逢五月天”,也就是吟咏梅雨情景之句。可是秀吉在《惟任退治记》里,没有把此句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而是把“时”作“土岐”,“雨下”作“天下”,“知道”作“统治”,写道:到如今才明白,此句所含真意为“已经到了由土岐家的我(指光秀)来统治天下的五月”。
可是,被认为是光秀发句的连歌并不只有这一版本。
事实上流传下来的《爱宕百韵》的抄本有数十种,其中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抄本里,“下しる”的部分被写作“下なる”流传下来。以下便是该句:
時は今あめが下なる五月かな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今在雨下,时逢五月天”。
光秀所咏的句子如果是“あめが下なる”的话,按照字面意思就是“在雨的下面”,就读不出像《惟任退治记》里所说的“已经到了由土岐家的我来统治天下的五月”的意思了。
那么,光秀原本所咏的到底是哪一句?如果摒除成见,重新考虑四百多年来都被当作定论的“统治天下”一说,又会怎样呢?
从结论来说,毫无疑问光秀咏的是“雨下”,即咏“梅雨下不停的五月”之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惟任退治记》的“统治天下的五月”之说里有决定性的矛盾。
让我们假想一下,如果确实如《惟任退治记》所说,光秀咏的是“已经到了由土岐家的我来统治天下的五月”,那么本能寺之变是几月发生的呢?本能寺之变于六月二日发生——不是五月,而是六月。
既然本能寺发生在六月,那么“已经到了由土岐家的我来统治天下的五月”的这种解释,在月份上就合不来。这乍看只是很微小的问题,可是在历史搜查里不能放过一点差错,这和现代的警方搜查是一个道理。
由于《爱宕百韵》是为祈求战争胜利而作的连歌,并且将供奉于爱宕神社前,因此绝不会有如此随便的祈愿。故而这应该被视为硬生生地改写句子后所产生的矛盾。

被窜改的《爱宕百韵》
很明显,秀吉为了让光秀看起来怀有夺取天下的野心,命令大村由己在《惟任退治记》里将连歌改写成了“统治天下”。如此推理的依据不仅是月份的矛盾,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光秀咏的确实是“雨下”。
那就是“爱宕百韵”连歌会的日期。秀吉窜改的不仅是“天下”,还有“爱宕百韵”连歌会的“日期”。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抄本等众多版本都记载着“爱宕百韵”连歌会的举行日期为五月二十四日,可是《惟任退治记》里写的是五月二十八日。
正是历史搜查让我着眼于这种日期的不同,因为我认为那个改动之中隐藏着某种目的。一直以来,相关研究从未着眼于此并继续向下挖掘,因为它们是“研究”而不是“搜查”。
历史搜查的结果是:为了尽量掩饰“夺取天下是在六月(本能寺之变发生在六月二日),而不是五月”这种谁都会发现的矛盾,秀吉故意将“爱宕百韵”连歌会举办的日期延至二十八日。若是保留“五月二十四日”的话,谁都看得出月份不合。但改成二十八日的话,感觉就大大不同了。也就是说,天正十年这一年的五月只有二十九天,改成“二十八日”的话,就能以“离六月仅差两天”而敷衍过去。
这一改动出色地发挥了预想的效果,这正能证明——窜改日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推理成立。这样一来,月份不合这种简单的矛盾就不会被人指出了,并且这种伪装历经四百多年都不曾被识破,甚至至今通用。谁都彻底相信了光秀咏的是“统治天下”。
这一说法之所以会被如此深信,与信长家臣太田牛一在《信长公记》一书中的记述有关。在当时的书籍中,这部书被认为是可信度最高的一级史料。而《信长公记》里也写着“光秀在五月二十八日,吟咏了五月统天下之句”,这和奉秀吉之命所写的《惟任退治记》里的内容一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信长公记》是将信长的家臣太田牛一每次写下的类似日记的原稿搜集整理、编纂而成的著作。乍看与报纸上新闻的写法相似,但它和军记物在记录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书中既没有歌颂信长的文章,也完全没有诽谤光秀的记述。所以,可以认定《信长公记》正是可信度最高的一级史料。
可是,对于不同的记述对象,其可信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并不能因为它是一级史料,就认为其所有记述的可信度都是第一级的,实际使用时也有必要评估每条记述的可信度。
太田牛一是信长身边的家臣,所以许多有关信长周边的信息,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或是通过可靠渠道取得的,当然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包括广为人知的本能寺之变中信长死前的情况——由于是牛一直接听到了在场人员的讲述,所以可信。可是有关信长周边以外的信息,则是他不知从何处听来的传闻,其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爱宕百韵”连歌会的消息就属此类。
遭到窜改的铁证
难道就没有秀吉窜改日期的铁证么?作为历史搜查,有必要确认更切实的证据。在“爱宕百韵”连歌会上,除了光秀,同席的还有著名连歌宗师绍巴,以及他的弟子等十人左右。如果能找到其中某人于二十八日身在别处的记录的话,那在场证明就站不住脚了。
可是,在光秀及绍巴等人经常参加的堺市商人——天王寺屋屋(津田)宗及的茶会记录以及与光秀有深交的公家日记等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光秀等人在二十八日的活动记录。当我正想放弃时,忽然发现了一件事——有另一个可以让在场证明不成立的证据。推论顺利的话,也许能证明《惟任退治记》中所谓光秀在五月二十八日作歌是不可能的,而二十四日的话就可以。
那就是当日的天气。
所谓连歌,就是按照被称为“式目”的一种规则,参与者一人一句衔接作歌的一种诗歌形式。百韵是五、七、五的上句和七、七的下句交替吟咏,把它们连成五十组共一百句。当中有很多必须遵守的规矩,其中一个就是“发句(即首句)必须领会当场的风雅情趣而作”。
光秀的发句咏的是“雨下”,这是光秀领会眼前爱宕山之雨景的情趣所作。也就是说,那天爱宕山上肯定下了雨。如果二十四日有雨,而二十八日没有下雨的话,就能证明秀吉窜改了日期。这是一种极为科学的证明方式。
于是,我便去调查是否存在记载了当时天气的史料。幸运的是,有人在日记里记载了天气。其中一人便是在爱宕山附近的京都居住的公家山科言经——他确实是一丝不苟地记录了每一天的天气。
看了他的日记《言经卿记》,便能发现二十四日的天气写的是“晴阴、下未”。“晴阴”是“时而晴天、时而阴天”的意思,那“下未”又是什么意思呢?古语辞典里也没有相关记载。
从《言经卿记》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的记述可知,“下未”既不是晴天也不是大雨或小雨。因为这段时间的日记里有使用“天晴”、“大雨”、“小雨”等词。为了确认意义不同于这些天气表述的“下未”的意思,我还试着调查了其他人写的日记。
那就是位于京都以南约四十公里的奈良兴福寺多闻院的院主英俊写的《多闻院日记》,以及当时所处京都以东约一百二十公里的三河(今爱知县)冈崎附近的深沟城的松平家忠所写的《家忠日记》。这两人都只记录下雨天。将《言经卿记》中写着“下未”的四天与这两人的日记对比,就可得知“下未”便是“下雨”,既非大雨也非小雨,意味着“普通的雨”。
于是,便能从《言经卿记》的记载得知存在疑点的二十四日,京都时而晴,时而阴,后下雨。爱宕山在京都市中心西北方向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比比叡山还高,海拔超过九百米。即使现在也要先从京都站起搭五十多分钟的大巴,再沿陡峭的参拜道路步行三小时才能最终到达山顶的神社。京都市内“下雨”的话,在西边山地的爱宕山肯定比京都市内还要早下雨。毋庸置疑,五月二十四日爱宕山下了梅雨。
另一方面,《惟任退治记》里所宣称的二十八日的天气又如何呢?
参考《言经卿记》,从五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六日都是下雨,而到二十七日雨停,然后二十八日的天气是“天霁”。“霁”即“晴”,也就是说二十八日的天气是“晴”。
二十八日的《多闻院日记》和《家忠日记》里都没写天气。因为这两人都有只记雨天的习惯,所以至少可知“天气不是下雨”。所以可以认为,二十八日近畿、中部地区是大范围的晴天。
这样一来就证明了《爱宕百韵》确确实实遭到了窜改。被所有人毫不怀疑地相信了四百多年的“如今正是好时机,土岐五月统天下”这句连歌,是秀吉为了极力宣传光秀怀有夺取天下的野心而故意将其中的词句和日期窜改的结果,以上就是这一伪造行为的证据。

宣传书里包含的秀吉的意图
秀吉正当化的不仅是“野心说”,他更通过《惟任退治记》说光秀“企图密谋叛变。但是,这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出于多年来的反意”,将其说成从很久之前就怀有谋反之心。然后,书中还让信长留下“所谓以怨报恩,也并非史无前例”的遗言,造成一种信长自己也认为光秀的谋反是出于怨恨的印象。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怨恨说”的源头。
但是,《惟任退治记》中所谓的“怨恨”是毫无根据的。那不过是秀吉对于光秀的心理活动所给出的一种专断的解释。不论光秀是否在很久之前就怀有谋反之心,或是他是否怨恨信长,还是他是否在《爱宕百韵》的发句中蕴含了夺取天下的决心,这些都只不过是秀吉的片面之词。
所谓的信长遗言原本就很可疑。实际上,可信度很高的太田牛一所作《信长公记》里就写着完全不同的内容。
秀吉有必须强行这么下结论的动机。整件事情不过是他把对自己有利和自己要鼓吹的内容写进《惟任退治记》里而已。传说秀吉曾几次命令作者大村由己向亲王和公家朗读此书。秀吉利用《惟任退治记》完完全全地创造了世间对本能寺之变的普遍认识。
有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秀吉本人和他流传至今的形象是不同的。即便他是信长忠诚的家臣,本来也并不曾仰慕过信长。通过分析《惟任退治记》的记述,就必定能明白事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通读《惟任退治记》后我注意到,里面完全没有体现他崇拜、仰慕信长的记述。更甚者,秀吉本人与传说中被信长偏爱的形象也相差很远。
在此书开头描写信长在安土城的荣华境况的部分,记述了信长每晚耽于享乐的事。该书还写道,在本能寺之变的当晚,信长如往日一般沉溺于美色,甚至他在遭遇袭击丧命前,把那些女人“一个一个地刺死了”。原文是这样的:
将军倾春光秋月乎,翫给红紫粉黛,悉皆指杀,御殿手自悬火,被召御腹毕矣。
[此时将军(信长),把春花秋月时赏玩的粉黛佳人们全部一一刺死,然后亲自点燃大殿,便切腹了。]
然而,太田牛一在《信长公记》里写道,信长当时说“女子勿在此受苦,速速出逃”,下令让女人们逃跑。因为牛一的记录肯定是直接取材自从本能寺逃出来的女性处的,所以不会有错。信长即使面临自己的死亡,也依然有关怀他人的胸襟。
可是,秀吉很明显出于某种目的而掩饰了这段事实。他宣扬信长是淫乱残忍之人,而光秀则因怨恨、野心等私人理由发动了谋反,而其他武将与此事盖无关系。这就是本能寺之变事后处理的最后举措。秀吉让所有的武将都相信他从而集合到他麾下。他做出了如此宣言,并制订了夺取政权的计划。而历史也证明了秀吉依据此计划成功地篡夺了织田家政权。
依照秀吉的政治意图而如此写就的宣传书,以及本能寺之变所谓定论即源于本书这一重要事实至今仍遭到忽视。由此可见,有关本能寺之变的研究从根本上就是歪曲的。
(本文摘自明智宪三郎著、郑寅珑译《本能寺之变——光秀·信长·秀吉·家康,1582年的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作者系明智光秀之子於寉丸的子孙。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