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到MAUSS:反功利主义运动的前世今生
在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与法国的政治有关。媒体精英正联合起来,试着用美国式的无脑评论家取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成功。更重要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变得更与政治相关了。1995年法国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意味着法国成为了第一个确定反对以“美国模式”作为经济体系的国家,他们拒绝使自己的福利国家解体。自此之后,美国的媒体几乎屏蔽了来自法国的文化新闻,法国立刻成为了愚蠢的国家,正徒劳地躲避历史的潮流。
当然,这种说法本身很难迷惑那些读过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美国人。美国学者寄希望于从法国获得的是一种智识上的高潮,是参与奇特、激进想法的能力——比如展现西方对真实和人性之间的内在暴力这类东西。但是这种能力不能指向任何政治行动,或者通常不能带有任何行动的责任。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几乎被政治精英和99%的普通民众忽略的阶级是有可能这么想的。换句话说,虽然美国媒体将法国展现为一个愚蠢的国家,但是美国学者则在法国思想家中挑选看起来符合他们要求的人。
因此,你从未听说过今天法国一些最有趣的学者的名字。其中一派学者致力于系统性地攻击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他们的名字显得有些冗长: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简称MAUSS。这一派人是从20世纪初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那里得到的灵感。莫斯最著名的作品,《礼物》(1925年),可能是有史以来对经济理论背后的假设最漂亮的批评。在“自由市场”正作为人性自然的且必然的产物灌输到每个人的大脑中时,莫斯的作品可能是与此关系最密切的。莫斯展示出,不仅是大部分的非西方社会,大部分现代西方社会也不遵循任何类似市场的原则。对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敬重法国的美国学者看起来正处于无话可说的时候,MAUSS的学者们已经在攻击它的基础。
莫斯的思想

介绍一下背景。1872年马塞尔·莫斯出生在法国孚日山脉的一个东正教犹太人家庭。他的舅舅,埃米尔·涂尔干,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涂尔干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聪慧的年轻助手,在这些人当中,莫斯被指定去研究宗教。但是,这个圈子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击碎了:许多人死在了战壕里,包括涂尔干的儿子,涂尔干本人也因为悲伤而在不久后去世了。只剩下莫斯重新捡起地上的残片。
但是,所有的记录都表明,莫斯并没有被认真地看作一个继承人。尽管他十分博学(他至少懂得十几种语言,包括梵语、毛利语以及古阿拉伯语),但是他始终缺乏成为一位大教授的气质。他曾经是一名业余拳击手,身体健壮,始终带着一种开玩笑似的、略显愚蠢的态度。他是那种总是在思考十几个出色的想法,却从不建设伟大的哲学体系的人。他一生都用在写作至少五本书上(有关祈祷,有关民族主义,有关金钱的起源,等等),却没能完成任何一本。不过,他仍然成功地训练了新一代的社会学家,基本上开创了法国的人类学,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极其具有创新性的文章,每一篇几乎都独自创立了一套新的社会理论。
莫斯也是一个革命者。自从他还是一个学生开始,他就经常为左翼媒体贡献文字。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法国合作社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巴黎创立了一个消费者合作社,并且协助运营这个合作社很多年。他经常被派去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社运动接触(因此他在革命之后在俄罗斯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是,莫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与欧文和蒲鲁东的传统更相近。
“经济”是社会中必要存在的吗?
莫斯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首先,几乎所有“经济科学”有关经济史方面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积极推动自由市场的人所作的普遍假设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驱动人们的根本力量是最大化自己的乐趣、舒适和物质财富(他们的“效用”)的愿望,所以一切有意义的人类互动都可以用市场的语言来分析。在标准的说法中,最开始出现的是物物交换。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人们必须以一物易一物。由于这样做非常不方便,他们最终发明了金钱,以此作为交换的通用媒介。其他交换技术的发明(信用、银行、股市)仅仅就是上述内容在逻辑上的延伸。
莫斯很快就指出,问题在于,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一个物物交换的社会真实存在过。事实上,人类学家发现,在许多社会中,经济生活完全基于不同的原则,大部分东西都以礼物的形式不断流动——几乎所有我们会称为“经济的”行为都是伪装出来的,它们是基于纯粹的慷慨以及对准确计算交易主体和交易货物的拒斥。这样的“礼物经济”有时可能会变得非常具有竞争性,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与现在的我们截然相反:人们并不比较谁的积累最多,而给予最多的人才是胜者。在一些臭名昭著的案例中——比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夸扣特尔人——这会导致戏剧性的慷慨程度竞赛,雄心壮志的酋长会通过散发数以千计的银制手链,哈德逊湾毛毯和胜家缝纫机来试着超越其他人。他们因此甚至会破坏自己的财产——将祖传宝物沉入大海,将成堆的财富点燃,并且挑战其他酋长也做出相同的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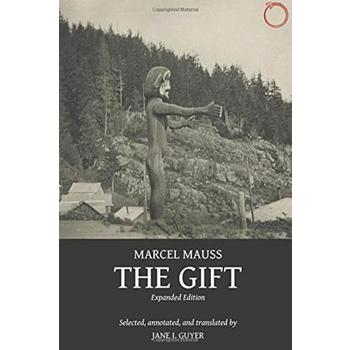
所有这些行为可能看起来都非常古怪。但是就像莫斯所问的:事实上,这到底有多另类?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中,赠礼的行为不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为什么当一个人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件礼物(一杯饮料,一次晚宴邀请,一次称赞)的时候,这个人会觉得有义务以相应的形式回馈?为什么一个慷慨举动的受益者如果不能回馈,就会觉得矮人一截?这些难道不是普遍的人类感受,不知为何在我们的社会中不被重视,却是很多其他社会经济体系的基础?以及,难道这个截然不同的冲动和道德标准的存在——甚至在我们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也有——不能为另一种视野,一种政策所产生的吸引力,提供真正的基础?莫斯的感受显然是这样的。
莫斯的分析在很多角度上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异化和物化的理论有明显的相似性。在大致同一时代,像卢卡奇这样的人物正在发展这些理论。莫斯认为,在礼物经济当中,交换不具有资本主义市场中非人(impersonal)的特点:事实上,即使是具有很高价值的物品发生了交换,真正有关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交换是为了创造友谊,或者缓解争斗,或者履行义务,只是有时凑巧是为了使具有价值的物品发生流动。因此,所有的东西都具有人格,甚至土地也是如此:在礼物经济中,最著名的财富——祖传的项链、武器、羽毛斗篷——都似乎发展出了各自的个性。
在市场经济中,情况正好完全倒转过来。交易被看作仅仅是用于获取有用的东西的途径,买家与卖家的人格,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是完全无关的。因此,所有的东西,即使是人,也开始被当作物品对待。(在这一思路下,考虑“商品和服务”这一表述)莫斯生活的年代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守着经济决定论的底线,然而莫斯认为在过去没有市场的社会中——同时也暗示,在未来任何一个具有人性的社会中——“经济”作为一个只关心财富分配、只遵循自身非人逻辑的自主行动领域,将根本不会存在。
莫斯始终不确定自己实践性的结论是什么。俄国的经验说服了莫斯,在现代社会买卖不能被简单地废除,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市场精神却可以弃置。劳动可以公社化,有效的社会保障可以得到保证,新的一种精神可以建立起来:按照这种精神,任何积累财富的唯一理由就是将它们赠予他人。结果会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它以“公开赠予的喜悦,在艺术上慷慨花销的愉悦感,公开或私人宴席上款待他人的乐趣”为最高的价值。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里面有些东西看起来非常的天真,但是与75年前相比,莫斯的核心洞见与当下的关系无疑更密切了。今天,经济“科学”已经事实上成为了现代神圣的宗教。至少对于MAUSS的创建者来说是这样的。

莫斯主义左派:市场逻辑最激进的反抗者
MAUSS的想法开始于1980年。这个计划据说源于法国社会学家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和瑞士人类学家杰哈德·贝斯德(Gérald Berthoud)的一次午餐对话中。他们刚刚参加了一个历时几天的跨学科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礼物。他们在阅读了会议论文之后,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参会的学者意识到赠礼的一个重要动机可能是,比如说慷慨,或者说对另一个人幸福的真正关怀。事实上,会议上的学者们都假设“礼物”并不真的存在:只要足够深入任何人类行动的背后,你总能发现某种自私的、精确计算的策略。更加奇怪的是,他们假设这种自私策略总是、并且必然是事情背后的真相,它比任何可能与之交织的其他动机都更接近于真实。这好像就是说,如果要显得科学,显得“客观”,那么就必须完全变得自利。为什么?
迦耶最终将此归罪于基督教。古代罗马仍然保存着一些对贵族式慷慨的理想。手握重权的罗马人建造了公共公园,树立了纪念碑,并且竞相赞助最宏大的娱乐节目。但是罗马的慷慨也很显然是以伤害为目的的:他们最喜爱的习惯之一就是在人们面前撒下金银,然后观看他们在泥土里为了争夺财富而搏斗。显然,早期的基督教徒有关慈善的观念,是对这些令人厌恶的习惯作出的直接反应。真正的慈善不基于任何建立权威、或获得好处的欲望,或者不应该有任何利己的动机。甚至可以说,如果给予者从这一行为中获得了任何东西,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赠予。
但是这就带来了无尽的问题,因为很难想象一种对于给予者来说完全无益的赠予行为。即使是一个完全无私的行为,也能让人在上帝面前得分。因此一种探索每个行为背后的动机的习惯就建立起来了,这种探索就是为了找出行为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背后的利己动机,然后假设这种利己动机才是真正重要的。在现代社会理论中,人们也能看到这种探索在不断地被重复。经济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都同意,如果一个人从慷慨的行为中获得某种乐趣,那么它就不那么慷慨了。他们不能互相同意的只是其中的道德内涵。为了对抗这种非常逆向的逻辑,莫斯强调了赠予的“乐趣”和“喜悦”: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并不假设在我们称为的自利(他注意到,自利这个词甚至都不能翻译到大部分的人类语言中)与关心他人之间存在任何矛盾。传统意义上的礼物的整个目的,就是同时为了自利,也为了关心他人。
无论如何,这些就是最早让一小群跨学科的法国籍或说法语的学者[阿兰·迦耶,贝斯德,阿马特·因泽尔(Ahmet Insel),塞尔吉·拉托什(Serge Latouche),波琳·泰伊布(Pauline Taieb)]聚集在一起的原因,而之后他们就形成了MAUSS。事实上,这个小组最开始是作为一份期刊开始的,叫作《MAUSS评论》(Revue du MAUSS)。这是一份非常小的期刊,粗糙地印制在质量很差的纸张上,其中文章的作者既把它看作严肃的学术期刊,也把它看作某种圈内的玩笑,因为它是一个当时尚不存在的宏大世界性运动的旗帜性刊物。迦耶写了许多宣言,因泽尔写了未来反对功利主义协定的幻想。经济学的文章与俄国小说家的选段夹杂在一起。但是慢慢地,这一运动开始出现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MAUSS变成了一个可观的学者网络:从社会学家到人类学家到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从欧洲到北非再到中东。他们的想法刊登在三种不同的期刊上,还有一套出色的丛书(都是用法语写的),同时有年会提供支持。
自从1995年罢工以及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之后,莫斯自己的著作在法国开始经历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复兴,他的传记和他的政治文字得到了出版。同时,MAUSS小组自身变得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1997年,迦耶发布了一张单页,题为“一个新左人士的30个论点”,MAUSS小组开始将他们的年会用于特定的政策问题研究。例如,对于那些要求法国采取“美国模式”并使自己的福利国家解体的无尽呼吁,他们的回应是开始传播一个原先由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提出的经济想法:全民基本收入。改革福利政策的真正方法不是开始去除社会保障,而是重新理解一个概念:国家对其公民的亏欠究竟是什么?他们说,让我们舍弃福利和失业保障。但是,让我们创造一个体系,保证每一个法国公民都有相同的基本收入(例如,20000美金,由政府直接提供),其他的就由他们自己获取。
很难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莫斯主义左派,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简单看作是极其富有激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并不真正对社会的激进转变有兴趣。例如,迦耶的“30个论点”同意莫斯的看法,即承认某种形式的市场必然会存在——但是就像他一样,这份宣言期待着废除资本主义。这里资本主义指的是将金融利润本身看作目的。不过,在另一个层面上,莫斯主义对市场逻辑的攻击比现在知识领域中的任何想法都更加根本,更加激进。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这或许就是为何事实上莫斯主义者的作品几乎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说这也是下述现象背后的原因:美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是最疯狂的激进主义者的人,愿意解构除了贪欲和自私之外其他几乎一切概念,却不知道如何对待莫斯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