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瑜再评《死屋》︱反思一篇惨遭退稿的书评
大约两年前,笔者在《上海书评》发表文章(《流放西伯利亚,所禁锢的与重生的》)评述了英国历史学家丹尼斯·比尔所著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以下简称《死屋》)。
这本书是2017年度坎迪尔历史学奖的获奖作品。坎迪尔历史学奖堪称历史学界的诺贝尔奖,能获得此奖对于每一个历史学家而言都是莫大的荣耀。笔者在阅读《死屋》时完全是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照英文版读了好几遍,做了好几万字的读书笔记,书评写出来后自己也很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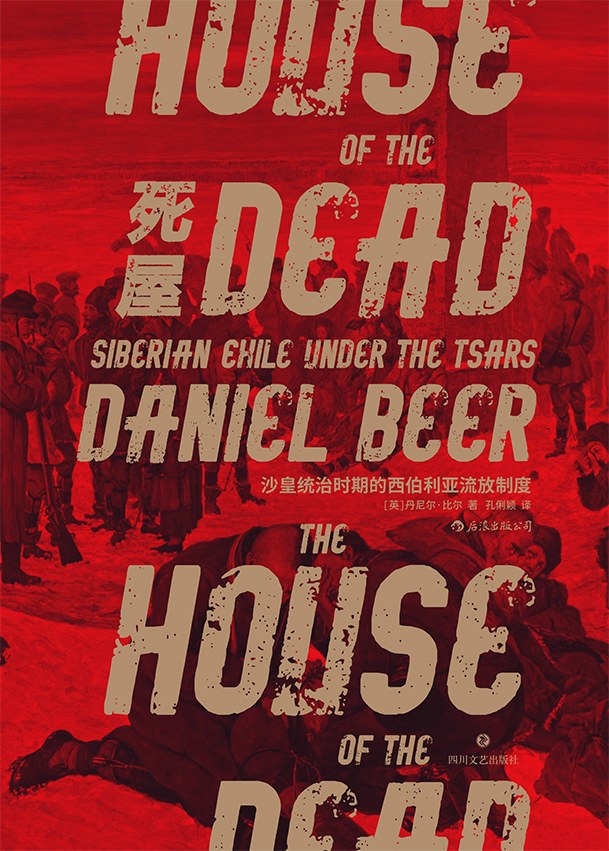
《死屋 : 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英]丹尼尔·比尔著,孔俐颖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528页,88.00元
《死屋》在中国和西方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遗憾的是,笔者并未发现这本书的俄文版。后来,我把书评翻译成俄文又补充了大概三分之一的内容投给了俄罗斯某著名学术期刊,我希望俄方能组织译者将这本书翻译、推荐给俄罗斯读者。但是书评经编辑部审核后,惨遭退稿。两位俄罗斯编辑给出的理由非常充分,让人无从辩驳。在此,想与读者分享这段被退稿的经历以及我的反思。
《死屋》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之处
《死屋》这本书令读者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对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描写。近两百年来,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把十二月党人的故事给神话了,认为十二月党人是俄罗斯贵族高贵精神的一种符号和象征;同样被神话的,还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认为她们为了爱情毫不犹豫地放弃一切,追随丈夫,共赴西伯利亚。事实上,这次起义是非常鲁莽和轻率的,也并非所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都表现出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他们的妻子在追随丈夫去西伯利亚这件事上也并不都是因为爱情和浪漫主义因素。
但他们是在西伯利亚出现的第一批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的上层社会人士。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经营农场、建立孤儿院和学校以帮助当地民众,这些都令当地民众受益,十二月党人让欧洲知识阶层在西伯利亚站稳了脚跟。当初的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开始落到了实地。
他们尽管被流放于环境极端恶劣的西伯利亚,但仍然不忘初衷,用一位被流放的军官尼古拉·别利亚耶夫的话说: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时期“是一段美妙的道德、智力、宗教和哲学的学习时间”。先是赤塔,后来是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成了沙皇俄国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最有活力的文化中心,作家兼外交官谢苗·列切帕诺夫在1834年调查了十二月党人的团体,他在日记上写道:“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可以称得上一个拥有一百二十名学者或教授的学院或大学。”
所以,笔者在前一篇书评中提到:“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并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重生。”我认为十二月党人应是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的俄罗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十二月党人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支持者描绘的那种道德质朴、无法安抚的革命牺牲者。但他们在流放地的生活确实给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和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美德的振奋故事。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公民活动——他们的园艺、他们的教学工作、他们的民族志研究——表达着他们对公益的热情追求。十二月党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偶像。他们的民主理想和爱国理想成了新一代激进分子——民粹主义者甚至列宁主义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死屋》还提到西伯利亚的特殊环境对革命者的精神影响。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政治流放犯越发敏感、孤僻与多疑,彼此之间互相猜疑和争吵。这些心理问题成为日后布尔什维克党派别林立的原因之一。丹尼斯·比尔认为西伯利亚的暴力文化,是联系布尔什维克党与十九世纪俄国政治激进派的重要纽带。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和西方学者而言确实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来自俄罗斯学者的专业评价
给我审稿的两位俄罗斯编辑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但他们对《死屋》的评价并不高,甚至非常负面。
首先,《死屋》作为一本研究沙皇俄国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获奖史学作品居然没有学术史,不符合学术专著的基本规范。其中所涉及的关于十二月党人的研究,一百多年来在俄罗斯史学界所出版的专著和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几乎每个细节都有研究。许多俄罗斯的历史学家把一生都投入到了十二月党人研究上,而在丹尼斯·比尔的专著中对俄罗斯同行所做出的贡献只字未提。《死屋》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俄罗斯学术界早已是常识性问题。丹尼斯·比尔就好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发明家突然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发明了自行车一样,可笑之极。
其次,如果《死屋》的定位是一本学术专著,那么它的问题意识和思辨性显然不够,全书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文字,就像是一个普通俄罗斯本科生写的拙劣蹩脚的学年论文,而且更加枯燥冗长;如果《死屋》的定位是一本史学科普读物,那么丹尼斯·比尔的许多结论非常武断而又缺乏依据。例如,丹尼斯·比尔认为西伯利亚的暴力文化是联系布尔什维克党与十九世纪俄国政治激进派的重要纽带。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来自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贵族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本身是很有教养的。而当他们流放至西伯利亚时,受当地暴力文化的影响,自己也变得野蛮暴力,当他们后来投身革命时,又把这种来自西伯利亚的暴力文化传统带到了革命事业当中。作者似乎想证明布尔什维克党在建立政权之后的暴力统治模式来源于当初党的领导人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沙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奴制的国家。这种野蛮专横的家长制作风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当中。对于这个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而言,他们可以随意殴打农奴并强奸女奴。军队服役的贵族,殴打士兵是家常便饭,士兵因殴打致死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农村妇女因为贫困而从事卖淫活动更是普遍性的。这种暴力文化并非西伯利亚所特有,而是遍布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贵族、平民还是农奴都深受这种暴力文化的影响。
笔者是认同这种观点的,这让我想到了伊凡雷帝时代的《治家格言》是这么描述俄罗斯人的教子之道的:“……在儿子小的时候要经常揍他,那么他长大后就会很乖,就能给你的精神宁静。揍男孩子不会有什么坏处,因为用棍子打不会打死他,只会让他更健康,当你揍他的时候,也就拯救了他的灵魂,如果你爱你的儿子,那就经常揍他,将来你会以此感到庆幸的。……”《治家格言》也特别强调了丈夫对妻子也应经常体罚,以利驾驭。但体罚须讲究分寸:“不宜殴打头部或心脏以下的部位,不宜用棍棒或铁器。最好用鞭子抽。首先,丈夫应将妻子引到避人耳目之处,脱去她的衬衫,以免撕破;然后捆绑双手,以便有条不紊的打到适当时候为止。另外,还应对她软语慰藉,以免影响将来的夫妻关系。”
此外,俄罗斯学者指出了《死屋》中的一些非常严重的硬伤。例如:
1、丹尼斯·比尔在书中引用了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名句 “年轻的头脑无事可做,成年的淘气鬼也借此作乐”来证明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密谋的轻视,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尽管《叶夫盖尼·奥涅金》出版于1833年,但诗人描写的却是1810年至1820年之间的事情,这比十二月党人起义至少早了十年。事实上普希金写过许多讴歌十二月党人的诗歌,例如俄罗斯和中国读者都耳熟能详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因此,以这几句诗文来证明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密谋的轻视并不合逻辑。
2、书中提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当天,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谢尔盖·特鲁别斯科伊并未出现在广场上。尽管丹尼斯·比尔在这里加了注释,但这在俄罗斯的学术界是争议性很大的问题,并没有定论,直接这么描述至少是不严谨的。
3、历史上,玛丽亚·沃尔康斯卡娅嫁给谢尔盖·沃尔康斯基公爵时是十九至二十岁,这在俄罗斯学术界是一个常识问题,并非书中所写的十七岁。
4、丹尼斯·比尔在提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愿意追随丈夫奔赴西伯利亚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她们受到了拜伦式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事实上关于“婚姻誓言的神圣性”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存在于俄罗斯,与拜伦的小说和英国式的浪漫主义文学无关。
5、丹尼斯·比尔在书中提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伊尔库茨克市政建筑(包括歌剧院、博物馆和美术馆)都与十二月党人的文化影响有关。事实上并非如此,伊尔库茨克至今都没有任何一座歌剧院,那里只有音乐剧院和戏剧院,还是后来在苏联时代建立的,与十二月党人并无任何关联。
最后,俄罗斯编辑告诉我,尽管《死屋》获得了坎迪尔史学大奖,但这本书无论是作为严肃的史学专著还是轻松的科普读物都称不上是一部优秀作品。也许它很符合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口味,但出版社是不会考虑引进翻译的,而我的书评也绝不可能在任何一家俄罗斯的权威期刊发表。
退稿之反思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想从以下两方面谈谈自己的感受。
首先,关于《死屋》中所存在的常识方面的硬伤。笔者认为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下笔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就会闹大笑话。研究别国史的专家学者在给本国读者传播知识的过程中似乎掌握着很大的“权力”,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膜,大多数读者是不具备考据这些细节的能力的,然而一旦成果发表,白纸黑字的,在相当长时间段内就有形塑他人认知的决定性力量。正如世俗权力不可滥用一样,学者更要用良知、理性和严谨来对待笔下的权力。
其次,《死屋》在西方和中国学术界都大受好评,已经证明了这本书的价值。然而该书在俄罗斯遭遇冷落也是有原因的,这体现了历史学家对他国历史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外国人研究别国史和本国学者的差异。以中国史研究为例,像史景迁、费正清和孔飞力这些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他们的许多研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也许是常识性的,并不值得太过惊喜,但对于国外读者而言就很有价值,而中国顶级学者的研究在本国人看来很有价值,而对于国外读者而言却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这就是文化差异性。
中国史学界对于这种文化差异性总体而言是很宽容的。我们的史学前辈是这么教育我们的,当我们读到一些外国人写的中国史专著时,也许会觉得很普通很平庸,但只要这些书能在西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那就证明它们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为什么这些书会在国外大受欢迎?为什么我们认为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会让老外感兴趣?作者是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让老外觉得耳目一新的?
实际上这些的背后,反映的都是国外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好的历史写作首先要基于好的问题意识,而由于现实处境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的人,即便是面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也会有着不一样的问题意识。问题的结构通常也就决定着答案的结构,通过对不同问题意识——从而是不同的答案结构——的了解,反过来可以充实我们理解历史的意义空间。因此,把西方汉学家的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仍然是很有意义的事。同理,俄罗斯学术界把西方和中国的“俄学家”的著作翻译介绍给俄罗斯读者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只可惜,目前俄罗斯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许多俄罗斯学者是可以用英文在西方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的,而以往俄罗斯学术界却很少将西方和中国的“俄学家”的著作翻译成俄文介绍给本国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也许以后情况会有所改变。
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我希望俄罗斯学术界今后能与西方和中国的“俄学家”进行更频繁和更深入的交流,这对于三方都有好处。只有以开放的心态,不断进行有益的国际学术交流,相互取长补短,这种文化差异性才会越来越小。
我相信,最优秀的学术著作一定是具有某种跨越国界和文化的普适性的,而这应该是学者们毕生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