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儿童“纯真”背后:美国佛州家长教育权利法案与文化战争
编者按:今年3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签署了佛罗里达州家长教育权利法案,通常被称为“不要说同性恋”(Don't Say Gay)法案。该法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迪士尼公司也在员工的压力下对该法案表示抗议。然而,该法案的支持者采取了令人惊讶的策略,即为该法案的反对者贴上“恋童癖”的标签。在这种肮脏的诽谤背后,是保守派尝试通过提出“保护儿童的纯真”再次发动文化战争的愿景。2021年的统计显示,全美基督徒与无宗教信仰者的比例仅为2:1,相较于2007年5:1的比例,基督教的影响力与受众似乎正在逐步减弱。因此,家长教育权利法案也被视作保守派的又一次反扑。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作者迈克尔·布朗斯基(Michael Bronski)是哈佛大学女性、性别和性行为研究领域的媒体实践和行动主义教授。
今年3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签署了佛罗里达州家长教育权利法案,通常被称为“不要说同性恋”(Don't Say Gay)法案。尽管该法案没有使用“同性恋”一词,但其禁止公立学校在幼儿园至三年级展开任何关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课堂教学”。法案还以非常模糊的语言,禁止在所有年级进行任何不适合学生的年龄或发展的、关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教学。截至4月中旬,全美十多个州的立法机构已经起草了类似的法案,其中一些法案甚至更为严厉。
“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支持者选择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策略,将该法案的反对者与恋童癖画上等号。德桑蒂斯发言人克里斯蒂娜·普肖(Christina Pushaw)在推特上写道:“自由派人士不准确地称之为‘不要说同性恋’的法案,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反儿童色诱法’(Anti-Grooming Bill)。”普肖的发言表达了公开的同性恋恐惧症,她暗示同性恋者会“培养”或“招募”儿童成为同性恋,以便他们与儿童发生性关系。她接着表示:“如果你反对‘反儿童色诱法’,你可能就是诱奸者,或者至少你不谴责诱奸4到8岁儿童的行为。如果你选择沉默,那么你就是帮凶”。当迪士尼公司在员工的压力下站出来反对佛罗里达州的法案时,特朗普支持者、阴谋论者坎迪斯·欧文(Candace Owen)在推特上写道:“诱奸儿童者和恋童癖现在已经公开承认他们对你们的孩子抱有隐秘计划。这就是迪士尼的末日。”

当地时间2021年9月3日,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
“不要说同性恋”法案,以及其他一系列旨在“保护”儿童的措施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些措施包括将有关种族和性的书籍从公共和学校图书馆中移除、阻止“1619计划”和批判种族理论的教学,以及对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提出“婴儿是不是种族主义者”的质询。它们与其他州的一些法案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得克萨斯州的法案禁止为变性青年提供医疗服务,该法案将“同意接受护理的父母”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归为虐待儿童者,同时将其作为“父母要求解除对孩子监护权”以及从父母身边带走孩子的理由。这些事件都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观念和法律基础之上,基于这些观念和法律基础,出现了例如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禁止TA们使用与自己性别相符的卫生间等措施。这一切是在全面攻击生殖权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包括试图将销售和使用堕胎药物定罪,将帮助妇女堕胎定为犯罪,以及计划废除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等等。这一切都是在保护“所有人类中最无辜的人:未出生的孩子”的说辞下进行的。
这种与“保护儿童”法律的泛滥,与宗教右派长期以来的文化战争策略相一致。在二战结束后的75年里,渐进式的改革浪潮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包括民权、女性主义、移民改革、环保主义、社会正义和LGBTQ平等都迎来了进步。但现在,这些进步都遇到了阻力。保守派和传统派对这些变化做出了疯狂的反击,怀揣着盲目的愿景,试图恢复理想化的过去。
“不要说同性恋”法案与该模式保持一致,并在很多方面遵循了上个世纪类似法律的模板。事实上,某些法案直接复制了那些模板:20世纪80年代,在“石墙”事件之后,美国同性恋权利得到了提升;宗教保守派曾试图通过相同的法律以限制同性恋权利,并在某些情况下获得了成功。通过理解“不要说同性恋”法案如何与当下反对进步的历史相契合,我们就能发现它是保守派对于“儿童的纯真、纯洁、社会控制”的长期迷恋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不要说同性恋”法案,以及更广泛的对“反色诱”的热衷,是为“基督徒对于罪恶和危险的陈旧恐惧”赋予了新的面孔,并通过循环使用中世纪反犹太主义的血祭诽谤来重申这一点。只不过保守派使用了LGBTQ群体代替犹太人来构成对儿童的威胁。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公众对高调的暴力性犯罪的愤怒助长了全国对性犯罪浪潮的恐慌。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并不存在性犯罪“浪潮”。然而,各种各样的国家状况:大萧条的巨大压力,越来越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和更生动的摄影报道),从农村地区到城市的青年人口流动,同性恋文化和反主流文化的日益普及,为政客们提供了机会。他们号称会以严厉的法律来“保护”公众(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从而迎合选民。
这些新法律受到了医学论述的支持,并且结合了相对较新的“科学”:犯罪学。一种全新的性犯罪者类别出现了,即无法控制“性犯罪”冲动的犯罪者。1947年,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写道:“增长最快的犯罪类型是堕落的性犯罪者……如果野兽冲出马戏团的笼子,那么整个城市将被立即动员起来。但是堕落的人类,比野兽更野蛮,却被允许在美国随意游荡。”所谓的性心理变态法律就是答案。根据这些新的法律,被理解为无法改造的性心理变态者可以被无限期拘留在精神病院或医疗机构内。在1937年至1967年期间,全美超过半数州和华盛顿特区通过了性心理变态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根据这些法律,只要性心理变态者被判断为有可能犯罪,他们甚至会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被拘留。
引起恐慌的主要犯罪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袭击,或者至少应该是这样。1947年震惊全国的黑色大丽花谋杀案,导致了第一个性罪犯登记制度的建立。但实际上,性心理变态者的法律经常被用来针对从事自愿同性活动的同性恋男子,这在战后成为了常态,同性恋男子常常被描绘成捕食年轻男孩的罪犯。
二十年后,随着LGBTQ法律改革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主要是在城市和县颁布反歧视条例),另一种法律策略出现了。这种新的法律策略声称,其规定不是关于歧视,甚至不是关于犯罪本身,而是关于保护儿童的纯真。安妮塔·布莱恩特(Anita Bryant)是该策略臭名昭著的拥护者,她还算成功的歌唱事业,帮助她找到了一份佛罗里达州柑橘委员会(Florida Citrus Commission)发言人的工作。1977年,迈阿密戴德郡通过了一项反歧视法,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布莱恩特带头发起了一场宗教性的讨伐活动,要求废除这项法律,理由是它将允许同性恋在该郡的公立学校任教。布莱恩特成为了 “拯救我们的孩子”(Save Our Children)联盟的名义领袖。组织成员是新兴宗教右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和老杰里·法尔维尔(Jerry Falwell, Sr.),布莱恩特通过将同性恋描绘成儿童掠食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当时还没有出现“诱奸者”(groomer)这个词,但布莱恩特坚持认为“同性恋者不能繁殖,所以他们必须进行招募”,这激发了人们的支持。在她1978年出版的《不惜一切代价》(At Any Cost)一书中,她写道:“这些人真正想要的,隐藏在晦涩的法律短语背后的,是能够向我们的孩子提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合法权利……我将领导一场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讨伐行动来阻止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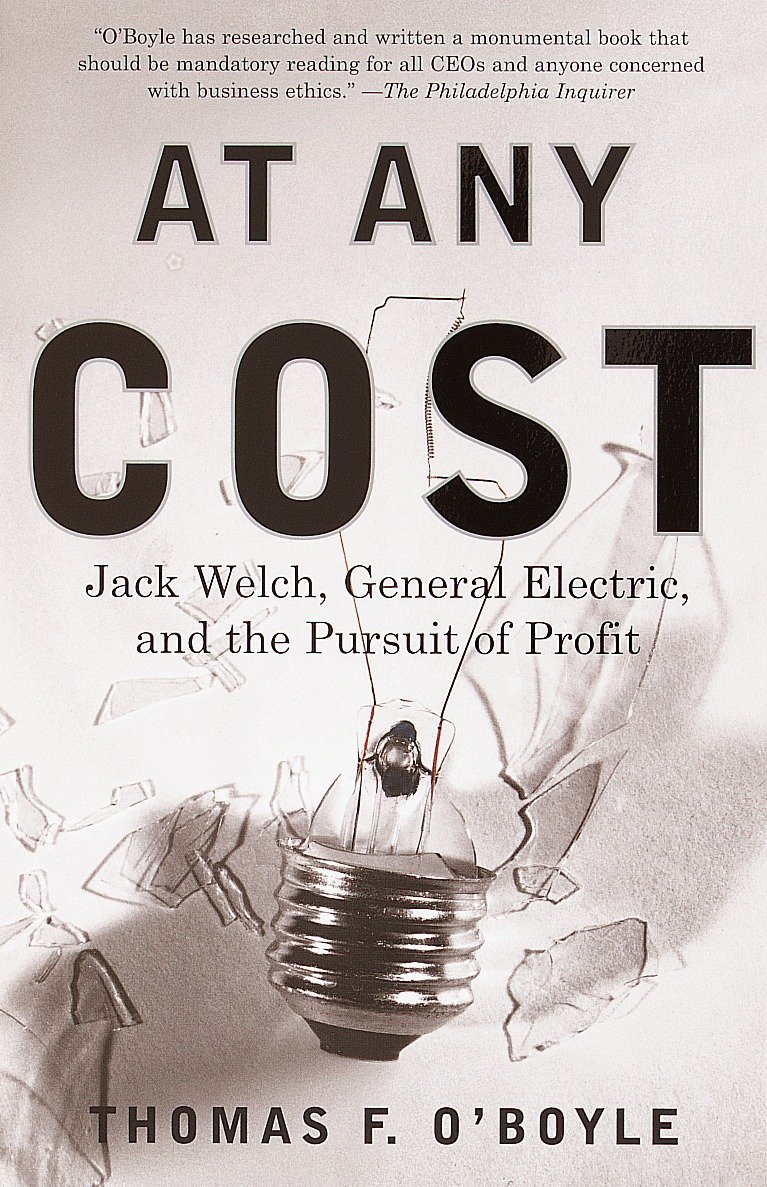
《不惜一切代价》
“拯救我们的孩子”组织的努力获得了成效,迈阿密戴德郡的反歧视法被废除了;禁止男女同性恋者收养孩子的法律也被批准。在这次成功之后,全国各地的其他多项反歧视法律也受到了挑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遭到废除。“拯救我们的孩子”组织还帮助推动了加州1978年的第六号提案(也被称为布里格斯提案,以提出该提案的州参议员约翰·布里格斯为名)。虽然该倡议最终失败了,但它提议禁止男女同性恋者在加州学校系统中任教,并规定学校必须解雇那些被发现“鼓励”儿童成为同性恋者的人,这显然是“不要说同性恋”法律的灵感来源。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强烈反对导致人们努力使在医疗、保险、住房、工作,甚至在公共场所对同性恋的歧视合法化。这种反弹还包括一套更广泛的法律,俗称“禁止同性恋法”:禁止在课堂上讨论LGBT问题,有时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禁止展开讨论,并且禁止了像同性恋与异性恋联盟等团体。这些法律也经常要求学校进行各种各样的“传统家庭”教育,比如在性教育课程中,在同性性行为和艾滋病之间画上等号。到1995年,已有16个州通过了这样的法律,而“不要说同性恋”法案明显受到了这些法律的影响。那时,“诱奸者”这个词也被认为是将同性恋男子与恋童癖联系起来的蔑称。
自“拯救我们的孩子”和“禁止同性恋法”的时代以来,美国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法律权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高法院基本拆除了反LGBTQ歧视的支柱,最高法院在2003年“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使同性行为去罪化;在2015年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中使同性婚姻合法化;并在2020年裁定,雇主因员工的性取向或性别而解雇员工的行为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
在取得这些法律成果的同时,美国社会发生了更为巨大的文化转变。许多私立学校和部分公立学校纷纷开始悬挂彩虹旗。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和瑞秋·麦道(Rachel Maddow)等新闻广播员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是一位同性恋父亲。杰森·柯林斯(Jason Collins)是一名出柜的职业篮球运动员。许多大公司开始刊登同性伴侣广告。同性恋角色也出现在许多主流电视节目中,甚至迪士尼频道也在针对中小学儿童观众的节目中设置了同性恋角色。2021年,公共宗教研究所的调查发现:76%的受访者支持LGBTQ权利。
但是,反击通常是由对过去的强烈怀念,以及同样重要的“对未来的深刻偏执”所推动的。“保护”儿童的想法首先是对“想象中的过去纯真”的强烈追求,因此,它与实际的儿童没有任何关系。今天,无论是主流还是边缘的美国右派,都习惯于将其对失去控制的偏执转化为儿童保护主义的语言。但它的直接前身,则热衷于将其目的更明显地暴露出来,它不是以保护儿童为框架,而是以边境为框架。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围绕着“让美国再次伟大”与想象中的“强奸犯和毒贩涌入边境”共同展开,这令人震惊。
这种偏执与保护主义的范式在过去五年中转变为对“保护儿童”的关注,但其根源仍然是父权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它与QAnon的信念(现在大多数共和党人都赞同这一阴谋论)有着同样的根源,即民主党的精英正在经营一个全球的儿童性贩卖网络。在对首位获得最高法院任命的黑人女性凯坦吉·布朗·杰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的拷问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大男子主义民族主义。在她的任命听证会上,她被问及对恋童癖者是否会表现得“软弱”。她给出的答案都无法令提问者满意:当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给投票支持杰克森的三名共和党参议员贴上“亲恋童癖”的标签时,这一切就再明显不过了。问题不在于杰克森如何做出裁决,而在于她是谁。
一个有影响力的右翼基督教民族主义分支,已经选择将其政治框架设定为一场关于纯真概念的神学斗争,而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与有关童年、性以及最终的救赎或诅咒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对于那些被这种政治影响的人与许多主流保守派而言,在整个美国推行《圣经》价值观是一项优先任务。这些问题可能是迂腐的,甚至是超越地方性的:忘了同性婚姻吧,我们谈论的是数学教科书、学区反歧视政策、小镇的图书馆里有什么书,但这里的总体论述是关于神学的,战场则像宇宙一般巨大。
4月中旬,当多个争议爆发时,福音派阴谋论者富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写道:“基督徒需要祈祷并投票给最符合圣经价值观的候选人。堕胎、性取向和性别等问题正被前所未有地政治化,但最终,这些都是《圣经》明确指出的道德问题。”格雷厄姆是正确的:所有这些文化战争都试图将圣经价值观的特定观点嫁接到国家身上。他们表现出对人类堕落和被逐出伊甸园的痴迷。这些关于纯真堕落的观念(总是与性和罪恶联系在一起)是保守的基督教将儿童概念化的根源。这种神学范式则是这些法条竞合(overlapping laws)、阴谋论和边缘思想的核心。
在伊甸园神话中,亚当和夏娃在一条蛇的引诱下吃下了智慧树的禁果,直接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结果,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注定要生活在有关自己身体的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耻之中。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却不感到羞耻”,但在他们不顺从后,“二人就睁开了双眼,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亚当和夏娃的罪(在基督教神学中,这就是人类的“原罪”),不仅仅是不顺从的罪,更体现在性的方面。由此,西方文化继承了关于罪、顺从与不顺从和性的观念,并且将它们视作彼此密不可分的问题。正如十六世纪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写的那样:“人类的本性不仅不是善良的,而且产生了各种恶,它不可能是消极的……人的内心充满了邪欲。”

从结构上讲,关于堕落的神话构成了怀旧观念的基础,即童年应该与世界隔绝,被视作一个纯真无邪的领域。这反过来又形成了关于成年人应该如何教育和对待儿童的观念,以及成年人对儿童机构的态度。但它也使得许多成年人对自己的童年感到遗憾,他们最终失去了童年的纯真,并对那些不认同“童年等于纯真幻想的人”感到愤怒。孩子们自己也很容易落入这样的误区:他们是神学上的不确定因素,处于性发育前的“纯真”状态,但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也处于“多方面的反常”(polymorphic perverse),因此不断地处于犯下严重罪行的边缘。在西方的想象中,这导致了堂吉诃德式的强烈焦虑和对儿童的矛盾心理。孩子通常被称为“小天使”或“小恶魔”、“快乐和负担”。如果孩子们不离开伊甸园(他们必然在性发育后离开),他们就是未来的希望。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服从。
从比喻意义上讲,成年之旅就是被逐出伊甸园的过程。因此,(成年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或延长儿童的天真。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智慧树的果实而遭到驱逐,因此保护儿童的最好方法是强迫他们保持无知。某些人内心深处的天堂般的童年神话正在助长这些令人绝望的法律。我们现在看到了“保护”儿童免受当前“禁果”影响的措施:禁止他们去了解性、性别和种族。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措施所要保护的不是真正的“儿童”,而是国家。这种将儿童与国家合二为一的想象力在言辞中显而易见。在最近于奥罗尔罗伯茨大学举行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会议上,鹰山教会的高级执行牧师吉恩·贝利(Gene Bailey)宣称:
在这个房间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说,“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善良与邪恶的对立。如果你不愿意为了“觉醒的议程”而置你的国家于不顾,那么你就必须反抗……他们想要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把你们的孩子从家庭中带走。他们想教育你的孩子。他们想从你身边夺走你的孩子。他们不想让你们做任何与基督教相关的事情,不想让你们为正确的事情、为真理挺身而出。
童年纯真的丧失与政治和文化的丧失交织在一起:父母对教育控制权的丧失;2020年选举的丧失;异性恋规范的丧失;传统性别角色的丧失;白人在美国身份的中心地位的丧失;基督教在美国生活内中心地位的丧失——甚至对一些人而言,这种丧失自内战以来就已存在。这场公开的、政治性的基督教大潮让人想起第三次大觉醒,它带来了新一轮的圣经原教旨主义、禁酒令、严格的性道德,以及1925年的斯科普斯审判(其背后是围绕猴子和人类的进化论争论),该审判维护了田纳西州学校的针对进化论的教学禁令。这也让人想起葛培理(福音派阴谋论者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的父亲)的早期基督教复兴主义浪潮,以及他在拒绝新政进步主义推动下举行的巨大集会。这两者都离不开精心策划的道德恐慌,试图向白人选民灌输对失去控制权的恐惧......而他们希望控制的对象包括:无信仰者、不道德者、无神论者、犹太人、移民、社会主义者、黑人、同性恋等。
最近一连串的法律正试图召唤新的敌人或将过去的敌人重新包装:觉醒主义者;批判性种族理论家;变性的大学运动员;东海岸的精英们,他们在背后操控着一切,为每个人戴上面具。除了其中很多触及传统的反犹太主义陈词滥调(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最近声称“犹太银行家”为达尔文主义提供资金),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幻想大多围绕着教育和财富展开——精英们已经渗透到公立学校,并正在推广非基督教、非美国的思想,例如批判性种族理论、接受LGBTQ人群,以及颠覆传统意义上的性别。重要的是,佛罗里达州的法案向公众宣传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家长对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内容发表意见的权利”。换句话说,该法案同时反对了精英与同性恋。
当然,基督教右翼对公共教育的痴迷并不新鲜。正如凯瑟琳·斯图尔特(Katherine Stewart)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指出的:
反对公共教育是美国宗教权利基因中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这场运动不仅仅围绕着堕胎政治展开……更围绕着国税局威胁取消教会领导的“种族隔离学院”免税地位的愤怒。1979年,老杰里·法尔韦尔(Jerry Falwell)表示,他希望有一天公立学校不复存在,教会将再次接管这些学校,并由基督徒来管理他们。
但是,如果这些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那么是何种变化导致了这些法律和政策的突然爆发?在世俗主义和传统保守宗教之间的斗争中,后者正处于全面失败的状态。2021年,皮尤调查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30%的美国人现在声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目前,美国基督徒的数量仍然是无宗教信仰人数的2倍;但在2007年,这一比例是5比1。宗教保守派觉得国家(更准确地说,是文明)的未来岌岌可危。因此,为了保住他们的控制权,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再难以理解。
人们的当务之急,是更好地理解支撑这场文化战争背后的不安全心理。但我们已经看到这场反LGBTQ的恐慌如何迎合了人们对世界现状的恐惧。为了避免被忽视,“同性恋者是不是恋童癖”再次成为公众随意讨论的热点问题。这种倒退让人感到痛心,坦率地说这一切是超现实的,且令人震惊。
同志们并不缺少支持,这并非什么安慰。基督徒指责异教徒、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虐待、调戏和杀害儿童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经常被指控在仪式上杀害基督徒的孩子、用他们的血做无酵饼,这被称作血祭诽谤。虚构的受害者:林肯的小休,诺里奇的威廉,特伦特的西蒙,甚至被封为圣人,以激起大屠杀的热情。指责同性恋者“引诱”儿童成为同性恋者或质疑他们的性别,这相当于现代的血腥诽谤,即猥亵诽谤。这也是实施针对同性恋者的“性心理变态法”,以及安妮塔·布莱恩特的“拯救我们的孩子”运动的核心。稍有新意的是,现在当政客们指责学区或教师诱导儿童时,他们想到:即使是教育儿童认识同性恋者的存在,也等同于恋童癖的行为。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让同性恋者完全隐身。“引诱”与其说是诱导,不如说是提供关于世界上无限变化的性和性别身份的知识。它已经成为心理学版本的“禁果”,教育者面对着被逐出伊甸园的风险。在这种新的理解下,即使是迪士尼公司也可以成为一个“引诱者”(这肯定会对其他公司产生寒蝉效应,在它们决定是否发声之前,要先观察迪士尼的情况)。
其中的问题从来不是保护儿童,如果政客们真的希望保护儿童,他们就会禁止枪支,强制学校提供免费午餐;但他们现在要做的是推广儿童纯真的理念。就是为什么迪士尼的“背叛”让法案的支持者如此恼火的原因。毕竟,迪士尼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赚钱的品牌之一,是因为它抓住了人们对童年纯真、魔法和奇迹的一种特殊怀念。它自称是一个“魔法王国”,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然而,即使是魔法王国也必须与时俱进。迪士尼在他们的节目中引入LGBTQ角色并非是某种社会正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年轻观众的期望。这也许是右派如此愤怒的真正原因。许多人认为,迪士尼呼吁废除佛罗里达州的“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行为是对他们纯真理念的隐喻性谴责。再加上最近迪士尼节目中公开的同性恋角色,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象征行为与商业表现,表明了对于LGBTQ人群的展现和接受是社会和文化的必然之举,且不会消失。
人们必须明白,尽管宗教右派一直在谈论保护儿童,但他们实际上害怕(也许甚至憎恨)儿童可能成为的人。儿童从纯真中坠落,不仅预示着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失败,而且预示着基督教民族主义政治灭亡的可能性。儿童就是未来。如果无宗教信仰人群的比例继续增加,右派有理由对自己的孩子感到恐惧。因为孩子们有无穷的想象力和成长潜力,他们恰恰代表了对传统文化价值观不可避免的、甚至不可逆转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