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不停丨无需抢菜的时日,人们在江南跟着味蕾寻蔬旅行
原创 Miya 故乡与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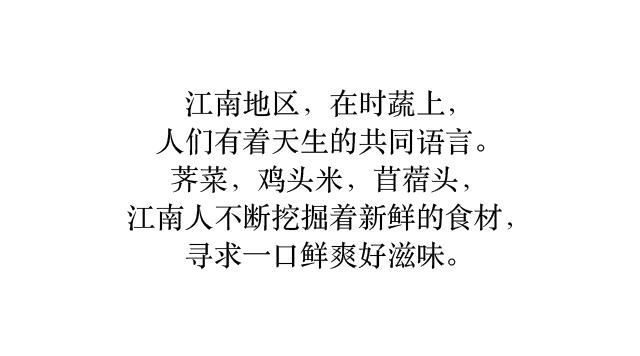

疫情之下“抢菜”成为一些城市人的心结,餐桌上的时令蔬菜仿佛一个衡量日常如常的指标。野生野长的蔬菜在自然之中肆意成长,江南人胃也没闲着,用特定的娴熟技法,诠释新鲜爽脆好滋味。我们跟随作者重温春夏的江南之旅,希望这些关于蔬菜的文化讲究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韵味。徽州二美、宁波三臭、七头一脑、水八仙、旱八仙……一座座温婉江南水乡,食之精髓在颗颗时令鲜蔬里显现。
——编者按
江南一带,但凡相去几里路,便换了一种乡音。但在时蔬之道上,无论皖南苏北,城里乡下,生就有一门共通的语言。1924年春,身在北京的周作人听妻子说叨,西单市场有荠菜在卖,一时感怀,便有了那篇流传甚广的《故乡的野菜》。不同于北方将荠菜剁馅儿包饺子,浙东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周先生开篇即言,“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字里行间,多少又透着点言不由衷。
浙东之外,周先生居住过六年的南京,也奉荠菜为至味。荠菜常见于地头田间,不少小区附近也有,小小的叶子紧巴着地皮,不打眼,但生命力极强,有水和土地就会生长,已经在江南一带的餐桌上存续了数千年。即使去乡已久,这门味觉语言不会生疏。南京话里,有“七头一脑不输春”的说法,荠菜头便是这“七头一脑”之一。“七头”是枸杞头、马兰头、荠菜头、香椿头、苜蓿头、豌豆头和小蒜头的统称,“脑”则指一味菊花脑。苏南的苏州人,苏北的扬州人,时常觉得南京人在美食上少一窍,但说起蔬食,却都噤了声。南京人食蔬已自成一套话语体系,除了“七头一脑”,还有和水八仙对照而来的“旱八仙”(荠菜、枸杞头、马兰头、苜宿头、香椿头、马齿苋、蒌蒿、鹅儿肠),旱八仙加上地皮菜、茭白等,即是“金陵十三菜”。


春雨过后,南京城的野菜齐齐冒头。©小红书:A lonely waiting
每年春日,一两声钝钝的春雷后,就是数场春雨,漫山间疯长的除了林间春笋,就是这各类杂七杂八的芽头新叶,争先恐后地往视线里钻。猫了一冬的南京人,伺机出动,挎着竹篮,拿着小铲子小锄头,奔向城市近郊或者山间野外,开始一场浩浩荡荡的全民挖野菜活动。南京当地的媒体为方便市民,还曾出过几版南京挖野菜地图。新一期的图谱显示,荠菜主要分布在江心洲、玄武湖和护城河边,香椿头在狮子山、丁山、武定门城墙段,马兰头在莫愁湖公园一带,菊花脑则集中在江心洲附近。旧时光里,老人会教授晚辈如何分辨野菜,什么时候更嫩,怎样做风味更足,如今放眼全国,这些代际间的食物经验日渐消逝,反而在江南一带,还留存有一丝旧风。

明末清初的李渔曾说过“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
江南素有食素传统,堪称明末清初“生活美学家”的李渔,早在变身“蟹仙”前,就已明了食蔬的要义。“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尤其这种春时嫩蔬,有“园种蔬菜所缺少的清香”,烹饪上宜化繁为简,清炒或凉拌为上策。荠菜焯过,碎切,和香干细丁同拌,略加油盐抟成宝塔形,临吃再推倒。马兰头也素净,采回来清水冲洗过,再温水汆烫,和着切得细长细长的干丝,滴些麻油和薄盐足够,再加其他,就有画蛇添足之嫌。


左图:白酒烹制的酒香草头。
右图:雪菜炒年糕。
苜宿头味道寡淡,倒不嫌戏多,常用酒来加持,无论佐以黄酒素炒的酒香草头,或者酒烧的河豚或鳜鱼,都有种以小博大的劲儿。历史上,苜宿头由张骞从西域引进,是一带一路的古物,如今常见于路边田野,因开有金黄色的小花,讨个口彩,又得了金花菜之名。苜宿头根茎极短,一般都是采个嫩头,掐出那尖尖上的三片绿叶入菜。第一次在餐桌上见到,是在本帮菜馆里,一层苜宿头打底,上面堆着数节肥肠,那是本帮菜里的名菜草头圈子。上海话里称苜蓿头为草头,那标致的肥肠即为圈子,酱油、黄酒、黄酒焖烧后,放在煸炒后的草头上即成,江湖传闻里拥趸不少,杜月笙就是其中之一,黑帮头子配草头圈子,倒也相得益彰。
“七头一脑”中的最后一味菊花脑,就是菊花的嫩叶子,别地欣赏不来,南京人却爱极,单独成列也要把它加入这名目里。也不精烹细作,洗净后,放在水中烫一下,再打个蛋,融成一碗金玉交错的蛋花汤,快手之余,还有一股清凉醒脑之味。南京的蔬菜,虽名目繁多,却没有门户之见,讲的就是个口缘。
江南的菜场,面目也是格外眉清目秀些,每次出差趁有闲暇,便会去住处附近的菜场转转。与笋打的照面最多,春笋、雷笋、冬笋,每次去总会偶遇一二。其次就是菱角、茭白之类,概因来时多在天气舒爽的夏秋时节,正赶上这些水生植物新市。江南多山水,山不高,水却盛,水生水养的时蔬也多。不同于北方人养植物的悉心,居于环山抱水间的江南人,感受更多的则是植物养人。文雅的苏州人把“鸡头米,茨菇,藕,菱角,茭白,莼菜,荸荠”列为水八仙,这一口水灵,可以一直从金秋吃到初冬。

江南的菜场,笋的种类繁多,雷笋、春笋、冬笋等。
“阿要买南荡鸡头肉!”苏州老城里,常见吆喝,长一声,短一声,经人指点,终于得以破译,说的是水八仙榜首的鸡头米,也就是大众更为熟知的芡实。芡实多长在池塘湖沼中,以南荡的最佳,糯且清香,远超别地产的“北芡”。南荡,更具体一点,是至苏州城南葑门外的湖荡,湖面清波涟漪,养育着无数野物。芡实硕大的圆叶漂在水面,形似石榴的果实长在水里,哼哧哼哧采上岸,水淋淋沉甸甸的,还带着泥。洗净后,敲开枣栗色的硬壳,才见玉珠似的小粒籽米。新鲜鸡头米可入菜,与虾仁、菱角肉同炒,更常见的还是煮来做甜羹,六分水,四分米,再添点当季桂花,苏州小吃的百年流变里,这一味鸡头米羹仍牢牢占据茶社桌席间的主角。


平江路历史街区,在狮林寺巷附近,狮林寺巷中,藏着许多苏式私房菜馆。©小红书:一只拍照的依琳
水生水长的时鲜,更不等人。鲜有二义,一来自季节更替,越时令越鲜,另一则是从采收到入盘,间隔越短越佳。刚采收的鸡头米当天就要剥出,不然容易沤坏,苏州人的耐性、巧手以及对吃的较劲,在一味鸡头米上展露无遗。每次在街巷里见人一边吴侬软语地话着家常,一边手速飞快地剥着鸡头米,就会心生感慨,江南人哪,为了这张嘴真是不怕麻烦。收了一茬鸡头米后,下一拨便是种水芹。苏州博物馆对面的狮林寺巷里,一派藏龙卧虎,匿着不少苏式私房菜馆。其中之一以“老板娘永远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在本地老饕中闻名,好在菜式地道,到店必点水芹炒香干,通常吃完的白瓷碟里,只剩一汪黄中带绿的油。

苏州小店的水芹香干。
水芹一般生于低湿地,茎杆中空,一身轻盈,入菜颇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秋后的水芹茎白牙黄,接近根部的白嫩一段尤其脆嫩,常和熏制的百香干同炒。每次去到江南地界,一路上就开始盘算吃什么,马兰头炒香干、腌笃鲜、酒香金花菜、大蒜茨菰肉皮,往往眼大胃小,最后多以一道水芹香干结尾。莼鲈之思的典故里,久居洛阳为官的苏州人张瀚一见西风起,便念起故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最后干脆舍官回乡,换个“人生适意”。从这个层面来说,水芹就是我的“莼鲈”,非江南人,为了这味,这些年没少往那里跑。
江南时蔬之丰,一在土生,二于水长,三则为腌食。深秋之后,腌菜便多了起来。江南菜系里,苏帮菜、杭帮菜、本帮菜、淮扬菜,各个独占一方,谁也不服谁,表面的杂芜下,实则也潜在统一秩序:鲜咸合一,无论什么菜系的厨师,都会把新鲜与腌制的食材放在一起烹制,比如本帮菜的腌笃鲜,或是杭帮菜里雪菜炒冬笋的炒二冬。


左图:雪菜又称为“雪里蕻”,是一味百搭的食材。
右图:家常菜笋衣烧肉。
秋冬腌菜里,数雪菜最百搭。雪菜又称“雪里蕻”,用芥菜的茎叶发酵制成。上海的小菜场,常见刚从大瓮里捞出来的雪里蕻,青绿色的脆口,黄绿色的味足。雪里蕻和瘦肉做浇头,就是一碗上海小囡魂牵梦萦的雪菜肉丝面,和冬笋肉片炒后下面条里用,就是杭州人的片儿汆。入汤也美味。上世纪 30 年代的北平饭馆,有道“马先生汤”闻名京城,用的是白菜、嫩笋、豆腐做主料,配以雪里蕻等二十余种佐料烧制而成。此汤的发明者—当时某位马姓教育家后来一语道破天机 :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蕻为要品。
绍兴重“霉”,霉豆腐、霉千张、霉笋,还有一味霉干菜。霉干菜是将芥菜腌制后晒干而成,颜色比雪里蕻深上不少,常用来做梅干菜烧肉,或者入馅做饼、包包子。宁波食臭,臭冬瓜、臭菜心、臭苋菜梗组成了“宁波三臭”。老卤发酵好的苋菜梗,皮色青绿,内部却已絮化成果冻状,吃的是里面的汁水和嫩的菜茎,与徽州地区的“徽州二美”(臭鳜鱼、毛豆腐)一个理儿,都是先有怪臭,后觉鲜爽。
徽州二美、宁波三臭、七头一脑、水八仙、旱八仙,都明目张胆地显露着一种丰富。这丰富不仅是江南这片富饶之乡的佐证,也昭示着这片土地上的人对食物的包容与智慧。国内不少地方,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但江南一带,城市和乡野距离很近,从绍兴城里到城外,一路可见晾晒的笋干,乡里人自己挖笋自己晒,城里人就买笋自己晒。晒笋是旧日传统,也是今时情趣。旧的秩序消散了些,又有新的秩序建立,传统和现代,城里和乡间,还有一根银线牵引着。四季流转,那些野生野长的时蔬不闲着,江南人的好胃口也闲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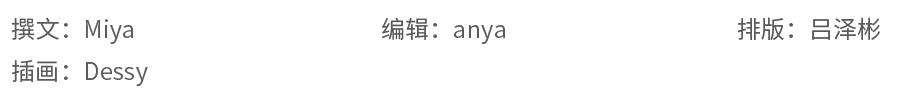
原标题:《步履不停丨无需抢菜的时日,人们在江南跟着味蕾寻蔬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