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铺到舞厅,成都的悠闲都在细节里
说到成都,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什么?
茶铺会是一个选项。在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者王笛看来,“一个城市中,公共空间——特别是那些和城市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就是一个城市性格的展示。茶铺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吸引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而且茶铺又是如此紧密地与街头联系在一起”。
也有人会想到舞厅。生于河南,曾在青岛、北京求学,2005年开始到成都生活的城市与生活方式研究者张丰写道:“舞厅逃避光亮,它的精髓在于黑暗,而不是光明。对那些顾客来说,它也是逃避现实的地方,他们不会在这里谈梦想,谈感情,甚至连谈论起自己都要小心翼翼。”
从茶铺到舞厅,展示的是成都这座城市的民间性。
王笛的《那间街角的茶铺》与张丰的《成都的细节》,是我近来所读的两本关于成都的著作。

《那间街角的茶铺》
作者:王笛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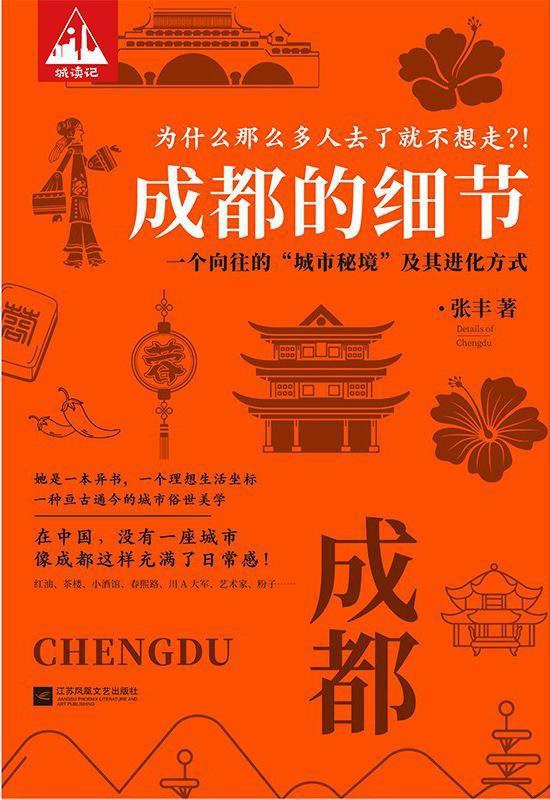
《成都的细节》
作者:张丰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两本书所记录的年代和方式都不相同。《那间街角的茶铺》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展示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成都的细节》则从自然景观、饮食习俗、历史与当下等不同时空维度来解读成都,铺陈这座城市的河流、城池、街道、饮食、男女、酒吧、书店……
两本书都采用了微观角度,以成都的细节为切入点。当然,王笛笔下的成都茶铺,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同于当下,即使茶铺依然被视为成都文化的代表。
王笛所强调的微观史,是将历史放到显微镜下,放大来看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他试图在那些波澜不惊的叙述中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正如书中所言:“历史学家要为百姓写史,哪怕是凡夫俗子每天坐茶铺的‘毫无意义’的日常行为,也远胜于一代枭雄所谱写的横尸遍野的血泪史。”
从晚清到1949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动荡中,但成都茶铺却始终稳定发展。尤其是抗战时期,成都作为大后方,迁入大量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工厂,人口急剧增加,茶铺更是成为日常生活、社交和经济活动的空间。
基于茶铺的公共空间属性,王笛很自然地将茶铺与西方的咖啡馆进行了比较。《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写道,茶馆“犹如伊斯兰和早期近代欧洲城市的咖啡馆,人们去那里并不是寻求保持隐私,而是享受无拘束的闲聊”。“与欧洲近代早期和美国的咖啡馆、酒店和酒吧间一样,成都茶铺的社会功能远远超出了仅仅作为休闲场所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成都茶铺所扮演的社会、文化角色比西方类似的空间更为复杂。它们不仅是人们休闲、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是工作的场所和地方政治的舞台。”
茶铺之所以更为复杂,是因为西方的咖啡馆与成都茶铺虽然有着相同的社交功能,但喝咖啡这件事,显然不能从早喝到晚,喝完了得再买。酒吧的情况也类似,喝完一杯就得另外再买。茶铺却不同,买一碗茶就能从早喝到晚,哪怕喝到茶汤变成白开水。
同时,咖啡馆的内部相对单一,茶铺却可为许多人提供生计。旧时成都茶铺里,有人理发、有人掏耳朵、有人擦鞋、有人算命、有人卖小吃……各种行当都可以将茶铺作为自己小生意的载体。
晚清民国时期的茶铺,人们喜欢在里面谈论政治。许多政治组织也将茶铺作为开展活动的据点,比如反清的袍哥会等。王笛写道:“在过去的50年里,他们所光顾的茶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坐茶馆生活习惯,竟一直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特性较量的‘战场’。他们每天到茶馆吃茶,竟然就是拿起‘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弱者的反抗’。这也即是说,弱小而手无寸铁的茶馆经理人、堂倌和茶客们,在这50年的反复鏖战中,任凭茶碗中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他们犹如冲锋陷阵的勇士,为茶馆和日常文化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如书中所言,“一个城市中,公共空间——特别是那些和城市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就是一个城市性格的展示。茶铺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吸引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而且茶铺又是如此紧密地与街头联系在一起”。茶铺就是这样,以一个小小空间折射出大社会。但很显然,如今的成都茶馆,呈现的面貌与王笛笔下的旧时茶铺大不相同。
在成都已经定居17年的张丰,以观察者的视角将目光投射于现实。在来到成都之前,张丰的生活基本在校园中度过,成都可算是他城市生活的开始。在他看来,成都有着中国城市里最好的市民生活,市民精神也发育得很好。作为一个聚集大量外来人口的大城市,成都保存了真正的本土生活特色,相对缓慢的生活节奏也有利于给生活留白,压力相对较小,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
《成都的细节》以河流为开篇。在张丰笔下,对水的态度决定了城市的性格,有河的地方就有生活。也正是在河流的滋养之下,在一座座桥梁的串联之下,人们游走于茶馆、苍蝇馆子、酒吧和舞厅,还有全国最多的书店。虽然春熙路、宽窄巷子、太古里和玉林名声在外,但或平民或热闹或时尚的它们,都是这座城市里的一角。严格来说,成都是一个没有中心点的城市。
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城市往往更为宜居。没有中心,固然在城建方面没那么“好看”,但却会让城市每个区域都能形成自己的中心,也让人们可以拥有更理想的生活半径。成都之外,东莞也是一个例子。
有趣的是,这样的城市也往往有着极大的包容性。《成都的细节》中写道,与很多地方不同,谈及祖上在哪里这个问题,成都人往往会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这是因为“大部分老成都,其实也都老不到哪里去。每一个成都名人的家世,似乎都很清楚。比如,巴金,祖上是浙江嘉兴,他到上海打拼后,还专门去嘉兴拜访同宗族的长辈。李劼人,祖籍湖北黄陂,八世祖李述明在清初逃荒到四川,是“湖广填四川”大军的一员;流沙河,祖籍在江苏泰兴;“大地主”刘文彩,祖籍在安徽,也是湖光填四川时来的。”
所谓“湖广填四川”,其实是一个泛指,是指政府引导和推动的外省人移民四川的行为,尤其是清代初年的几十年。湖南、湖北、江苏、江西乃至山西等地,都有不少人迁来。现在的“老成都”,就是指的这一批。
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成都的细节》提到了洛带古镇的三座会馆——湖广会馆、广东会馆和江西会馆。张丰写道:“在乾隆十年左右,成都周边兴起了一股兴建会馆和祠堂的潮流,人们富裕了之后,有余力进行文化建设,首先想到的就是‘不忘祖先’。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流行文化’,它说明,一些家族和同乡会拥有话语权的人(一定是老人),开始感受到某种危机:子孙身上来自原籍的气质,似乎越来越少,必须强化一些仪式,来让他们不要忘了自己是哪里来的。反过来思考,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会馆的密集出现,恰恰说明到了乾隆十年前后,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已经让来自各地的移民产生了新的认同,大家都普遍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那就是‘成都人’。”
书中继而写道:“在成都历史上,外来者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建造成都城的张若,建造都江堰的李冰,开办官学的文翁,都是外地人。诸葛亮和刘备带来大量外地人家的孩子,而在唐代,很多人像杜甫一样,追随唐明皇的脚步到成都避难。这种融合一直都在持续,清初几十年的移民,也不是最后一波,到了1930年代,随着抗战爆发,很多人从沿海迁到四川,1949年后,也有很多外地人参加‘三线建设’来到这里。”
这使得成都人没有特别需要捍卫的地方历史记忆,也让城市更具包容性。反过来说,当外地人来到成都,似乎也更容易适应,甚至沉迷其中。
茶馆仍然是成都细节中不可绕过的一部分。人们在此喝茶、闲聊、听戏、打麻将,享受午后时光,诠释着成都的“慢”。
而在张丰记录的当下成都,舞厅显得更有趣一些。他写道:“二环内外,舞厅和星巴克,这是两个世界。舞厅通常是在二环内,这里是地理意义上的市中心,经济意义上的老城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和别的城市一样,成都也经历了迅速的扩张,从二环往外,大多是新开发的商业楼盘。这里的人们,住着电梯公寓,每月交着房租,她们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时空。”
同时,“舞厅不像茶馆那样,被视为这个城市生活的灵魂。但是,舞厅也是深深地扎根于这个城市的现实之中,在别的城市,并没有这种形态的舞厅,即便是有,也是转瞬即逝。这和成都人的性格有关,‘耍’一直是成都人推崇的生活,谈恋爱也变成了‘耍朋友’。比‘耍’更过分的是‘晃’,‘晃’有贬义,但是仍然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舞厅是一群人“晃”的地方,也是另一群人的谋生之地。这也是一个小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但最终“每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舞女,顾客,服务生,保安,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没有谁强调秩序,但是却都遵循着某种秩序。”
书中写道,在成都,洞洞舞厅大概有三十年的历史。它最早的形态,是90年代的交谊舞,后来因为有人在废弃的防空洞里办舞厅,就被称为“洞洞舞”。它是茶馆、酒吧、KTV、舞厅的某种奇怪混合。这两年自媒体繁荣,写洞洞舞厅的公号不少,对这样的“灰色地带”,人们没必要大惊小怪。它在成都存在这么久,逐渐成为一个城市特色。
无论茶铺还是舞厅,所体现的都是市井性,这也是成都这座城市的底色。
当然,一直以来,成都因为它的“慵懒”引来不少批评,比如“少不入川”这句老话便是例证。
《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就写道,晚清民国时期的成都人就因为爱喝茶招致批评。比如 1938年,就有一篇名为《成都是“例外”吗?》的文章。作者从海外归来,“怀着热烈的愿望来看视十年前自己所居住过的古城。最初我以为这个城市该有一点不同了,该进步一点了,然而我失了望。时间尽管不停地跑走,而这个城市是被时代所抛弃了。”“一小部分的人还没有醒过来……他们仍然像平时一样怎么去讲求饮食和服装,怎样才可以不费体力和脑力来消磨去一天又一天——甚至一辈子的时间。”
在当时许多精英看来,混在茶铺是对时间与金钱的浪费。王笛认为,这也是当时西化生活方式与成都传统生活方式之争,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生活方式之争。但实际上,不同阶层和群体对时间和金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每天辛苦劳作的下层劳工、小作坊工人、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公共场所的小商贩来说,茶铺是他们辛苦后难得的闲暇时光。
1942年发表于《华西晚报》的《谈成都人吃茶》,指出吃茶是成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身并不轻视它,也不重视它。唯有经别人发现后,就认为了不得了”,其实“吃一碗茶也是穷人最后一条路”。
教育家舒新城则在《蜀游心影》中这样为成都人的“悠闲”辩护:“所谓耗费金钱实在是很少的事。‘虚耗时间’几个字,在这里是很少有人道及的,你又何必替他们白着急。”
成都的细节,就藏在这样的争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