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若薇: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
辽朝科举始于何时?
关于辽朝开始实行科举的时间,在《辽史》中有这样两条明确记载:《景宗纪》保宁八年(976)十二月戊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圣宗纪》统和六年(988),“是岁,诏开贡举”。
大概正是根据了上面两条材料,出于元人之手的《辽史》卷一○三《文学传》“序”这样写道:“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蒐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这段议论旨在综述有辽一代的“礼文之事”,其中《辽史》的撰修者们已明确地说,“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即辽朝科举制度兴起于景宗、圣宗时期。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学者厉鹗曾在《易水志》上发现有这样的记载:易州在保宁九年(977)有进士魏璟,统和二年(984)有进士魏上达,统和五年有进士魏元贞。于是,厉鹗编撰《辽史拾遗》时,在卷一六《补选举志》中加了这样一段按语:“史称景宗保宁八年诏复南京礼部贡院,圣宗统和六年诏开贡举。而保宁九年至统和五年,十年之中易州已有进士三人,又出一姓,皆在未开贡举之前。岂景宗诏复贡院之后,南京已设科而未及他处耶?惜不可考矣!”厉鹗这段话,明显是对《辽史》关于“开贡举”时间的记载表示疑问,不过他遗憾地认为这一问题“不可考矣”。厉鹗提出的疑问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乃至于今天的学者,仍大都不以辽朝开贡举在景圣时期为疑。
厉鹗所发现的易州进士的事例,已是对《辽史》所云开贡举于景圣间的一个有力反驳,那么,辽朝究竟于何时开始实行科举的呢?这并非是件“不可考”的事。

辽代壁画
在统和六年“诏开贡举”之前、保宁八年“诏复南京礼部贡院”之后这段时间里,易州已有三名进士,而比这时间更早,即在保宁八年之前,辽朝已实行科举的史料亦可以找到。
保留下来的辽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撰刻于应历十五年(965),其碑末署“前乡贡进士郑熙书”。应历十五年前,这里既已有“乡贡进士”称号,可为已有举行进士科举之证。但这个碑虽然是应历年间所刻,而这个乡贡进士郑熙却不一定就是经辽朝科举所录取的。郑熙所生活的幽州地区划入辽国版图是在会同元年(938),到应历十五年有二十七年的时间,这就不能排除郑熙是中原后唐政权统治下幽州地区乡贡进士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既然如此,就还应举出更有说服力的史料。这种史料在《辽史》中也是可以找见的:卷七九《室昉传》载,室昉为南京(幽州)人,“幼谨厚笃学,不出外户二十年,虽里人莫识,其精如此。会同初,登进士第”。会同元年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正式将幽云十六州地割献给辽。《室昉传》此处明言辽国年号“会同”,显然,室昉所登,应为辽国的进士第。这就说明,会同初年,当幽云十六州地入辽之后,辽朝就在幽云地区沿袭其旧来的科举制度了。
来自宋人的记载,也可以对这一事实做出说明。北宋人田况在他所写的《儒林公议》(卷下)中说:“契丹既有幽、蓟、雁门以北,亦开举选,以收士人。”而在元人所修的《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中也载,宋琪为幽州蓟人,“少好学,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岁开贡部,琪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侍读,时天福六年也”。寿安王后来即位为辽穆宗,天福六年即辽会同四年(941)。上述这些记载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辽朝在会同年间已开科举这一事实。再考虑一下这些应科举的人,都出自幽蓟地区。这就更可确证:辽朝在得到幽云十六州大片汉地之后,便在这一地区继续实行了中原封建王朝所实施过的科举制度。
基于这样的事实,再看《辽史》上的记载,就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保宁八年“诏复南京礼部贡院”一事,有可能出于下面的某一原因。一,保宁八年之前,因为辽国仅仅是在局部地区——幽云十六州之地实行科举,故只由这一地区的地方官掌管,并没有像中原政权那样,设置一个隶属礼部掌管全国科举考试的机构——贡院。经过了近四十年局部地区实行科举的实践,根据需要,到保宁八年,辽政府才决定正式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以便在全国实行科举制度;二,在幽云地区实行科举时,南京曾设有贡院,但并未作为常设机构,而是或置或废,至保宁八年正式恢复设立,并作为常设机构。
关于统和六年所谓“诏开贡举”一事。在统和六年之前,幽云地区已是“岁开贡部”,即每年都行科举,且就在统和五年,易州还有魏元贞为进士,那么,就绝不能把这条材料理解为是在停止了多年之后,才又于此年重开贡举的。它只能从别的方面说明辽朝在贡举制度上起了变化。仔细分析比较统和六年诏令下达之前与诏令下达之后辽朝科举实施的情况便可以看出,圣宗皇帝正式下诏开贡举,是指从这一年开始,辽国就不限于在幽云地区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对汉人实行科举制度。本文下面对辽朝应试对象所由来地区的考察,也可对此做进一步的证实。
《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太平十年(1030)七月壬午条云:“诏来岁行贡举法。”这条记载说明,辽朝在全国实行科举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制定或完善了“贡举法”,并决定从太平十一年开始颁行这一贡举法。我们不会据此认为辽国于太平十一年才实行科举,正如不应以统和六年“诏开贡举”一语就认为辽国科举始行于统和六年一样。
辽朝科举应试之对象
宋人路振于统和二十六年(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使辽国,回宋后所作《乘轺录》记载说,辽国“岁开贡举,以登汉民之俊秀者”。从《辽史》记载的历年登科者姓名中也可以看出,辽朝科举的主要对象是汉人。
自圣宗统和六年诏开贡举之后,辽朝五京各地区都有汉人应举并登科。兹将见于文献及石刻明确记载的出自某京道的进士简列如下。
南京道:统和十四年进士张俭,开泰五年进士杜防,太平十一年进士杨绩,重熙五年进士刘伸、赵徽,重熙七年进士王观,咸雍中进士牛温舒,乾统间进士韩企先,等等,知其姓名并确为出自南京道者已有三十余人。
中京道:中京道兴中县人姚景行重熙五年中进士,中京人窦景庸清宁年间中进士,中京道建州永霸县人张孝杰重熙二十四年中进士,等等。出土的辽代墓志中也有中京道人进士登科的记载,如大康二年撰刻的《王敦裕墓志铭》记,中京道建州人王敦裕曾中进士;《孟有孚墓志铭》记,中都人孟有孚于咸雍九年登科;等等。
上京道: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八《费县令郭明府墓碑》云,辽上京临潢府长泰县之汉人郭愿诚曾中辽进士;《遗山先生文集》卷二九《显武将军吴君阡表》云,辽上京道长春州人吴昊曾于咸雍十年进士登科;等等。

契丹还猎图
东京道:东京道人马人望于咸雍中“第进士”,东京道显州人曹勇义曾为辽进士,等等。
西京道:《史洵直墓志铭》记载,西京道儒州人史洵直于清宁八年登进士第;《大同府志》记载,辽末大同有边贯道为状元;等等。
上述材料证实,辽朝的科举制度自统和六年之后便面向全国各地区的汉人(统和六年之前,找不到一例幽云地区以外之汉人应举者)。不仅如此,辽朝的科举制度同样适用于“一依汉法”治理的渤海人。例如,《契丹国志》卷一○“天庆八年”条载:“有杨朴者,辽东铁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进士第,累官校书郎。”《辽史》卷一○五《大公鼎传》亦载,居住于中京的渤海人大公鼎是咸雍十年的进士,等等。这说明,在辽朝,渤海人与汉人一样可以参加科举。
契丹统治者奉行的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蕃汉不同治”的治国政策,对于契丹族以及辽国境内的北方其他部族人民,采取的是与汉族和渤海人民截然不同的统治政策和制度。科举制度作为“汉制”,只是用以对待汉人的,因此,辽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绝对不允许契丹族以及北方其他部族人涉足科举场中。但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与汉族的杂居和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契丹族以及北方其他部族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从而仰慕和崇尚汉族文明,于是,契丹族的某些文人冲破陈规,径自参加了汉族文人们引以为荣的科举考试。《辽史》卷八九《耶律蒲鲁传》载,横帐季父房的耶律蒲鲁,“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但由于当时契丹统治者依然严禁契丹人参加科举,所以,在耶律蒲鲁举进士第之后,“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耶律蒲鲁之父)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但是,这种不许契丹人“就科目”的禁令可能没有再维持多久,因为它已阻挡不住契丹及北方部族人崇尚、学习汉文化而希图获取科举功名的大势了。有例为证:辽末率众西迁中亚、建立了西辽国的耶律大石是契丹皇族,他就曾在天庆五年(1115)登进士第。再举一个北方其他族人参加科举的事例,证明辽后期对科举政策(即对应试者民族成分的规定)的改变。《郑恪墓志铭》记载:
君讳恪,世为白霫北原人。......君少敏达,博学世俗事,通契丹语,识小简字。生二十九年,以属文举进士,中第三甲。......生子六人,三男三女。长企望,次企荣,皆隶进士业。
白霫,与奚族毗邻,居中京以北地区,是与契丹族习俗相近的一个游猎民族。《郑恪墓志铭》记载,白霫人郑恪卒于大安六年(1090),寿五十七。据此上推,可知他生于1033年。而二十九岁时进士登科,时为清宁八年(1062)。这就说明,至少在辽道宗朝,白霫族人参加科举不但为法律所允许,且已非偶然之事(郑恪的两个儿子亦“皆隶进士业”)。由于辽统治者对白霫是采取与契丹族基本同样的“国制”来治理的,所以,白霫人可以参加科举,无疑又提供了一个间接证明,即至少到了道宗朝,包括契丹族在内的北方各族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中记载了金世宗对臣下说的一段话:
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辽后期契丹族人所参加的科举考试,是与汉人同样的科目,并未另立契丹字科。
辽朝前期在幽云地区实行科举,每年取士的数目尚无从考究。圣宗统和六年对全国汉人普遍实行科举后,至统和二十二年,即宋辽澶渊之盟前,辽国几乎是每年开科取士一次,但每次所取进士一般仅一二名,最多不超过六人。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取士标准过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应举者数量并不太多。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辽前期尚武轻文的风气。澶渊之盟后,随着宋辽战争的减少,军备防御的松弛,辽国的经济文化得以迅速繁荣发展,于是社会风气转变,由崇武转趋于尚文,科举取士之数便日见增多。到兴宗朝中期,一次取士已达六七十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应试人数之增多。正因为如此,辽廷开始采取了对应试者加以限制的措施:兴宗重熙十九年(1050)六月壬申,“诏医卜、屠贩、奴隶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这一诏令恰从反面说明,当时社会上各阶层的各色人物都有参加科举应试的,他们以科举作为进身、提高或改变社会地位的一个途径,这是科举在辽代政治、社会上作用增大的反映,致使统治者对科举一事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专门颁布了限制应举人员的诏令。科举制度继续实行和发展,到了道宗、天祚帝朝,取士常常一次多达百数十人。天祚帝乾统五年(1105)十一月戊戌,颁布禁令:“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这又把商贾之家排斥在可以应举的范围之外了。
考试科目
《契丹国志》卷二三《试士科制》云:“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这说明,辽朝的科举主要分诗赋和经义两科,而在圣宗时期,则是分作词赋和法律两科的。但这一说法也不甚准确。因为圣宗朝以后,辽国仍有律学科考试。《窦景庸女赐紫比丘尼造经记》中有“乡贡律学张贞吉”的字样。窦景庸为道宗朝人,必其时仍有“律学”一科,故有所谓“乡贡律学”存在。《涿州志》又载,王吉甫,涿州人,天庆二年(1112)试律学第一。天庆为辽天祚帝年号。这说明直到辽末,仍有“律学”一科。但“颇用唐进士法取人”4的辽朝,与唐朝相似,一直是重进士科,即诗赋、词赋科考试的。《辽史》中未用只字记录其他科目考试之情况,已足见其轻视态度,而迄今所能见到的其他文献和石刻材料上有关明经及律学等科情况的文字,亦寥若晨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仅据《辽史》诸《纪》中所记,圣宗统和六年以后(包括辽末耶律淳在燕京建立的北辽政权),辽朝放进士五十五次,总计人数达二千三百三十八人。进士科(亦即诗赋或词赋科)在辽朝备受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史籍中留有一些辽朝进士科考试诗赋的题目。如《辽史》卷一八《兴宗纪》载,重熙五年(1036)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辽史》卷五七《仪卫志》载“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老学庵笔记》卷七载“仁宗皇帝庆历中尝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八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会六符知贡举,乃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而以‘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为韵”。因为辽国地偏北方,且为游牧的契丹族统治者所建,故其封建文化程度与科举水平同中原相比,自然要略逊一筹。这曾引起宋人的嘲讽。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载:“吕正献公以翰林学士馆伴北使,使颇桀黠,语屡及朝廷故事。公摘契丹隐密询之曰:‘北朝尝试进士,出圣心独悟赋。赋无出处,何也?’使人愕然语塞。”吕正献公即吕公著,他以辽朝科举考试题目无经典根据为话柄,反唇相讥,大挫辽使傲慢之气,足证辽朝使臣的文化水平尚难与宋比。
辽朝模仿中原科举制度,也开设过制科,即于常科之外,皇帝临时定立科目以试士人。《辽史》上明确记载的制举有三次,均为“贤良科”。道宗咸雍六年(1070)五月甲寅,“设贤良科。诏应是科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咸雍十年(1074)六月丙子,道宗“御永定殿,策贤良”。天祚帝乾统二年(1102)闰六月庚申,“策贤良”。
此外,史书上还有制举登科者的记载。《辽史》卷一○四《刘辉传》载,刘辉于大康五年(1079)第进士之后,“诏以贤良对策。辉言多中时病,擢史馆修撰”。《金史》卷七五《虞仲文传》记载,虞仲文在辽后期曾“第进士,累仕州县,以廉能称。举贤良方正,对策优等,擢起居郎,史馆修撰”。根据时间推算,刘辉与虞仲文所参加的,大约都是天祚帝乾统二年的那次制科。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群中壁画
科举在辽朝的地位和影响
“辽以用武立国”,本不以“礼文之事”为重。所以,辽前期,特别是只在幽云地区实行的科举制,并不被统治阶级看重,也不以此作为选拔汉人官僚的主要途径。因此,当时的科举制度对辽国社会没有起到什么重要影响,就连实行科举的幽云地区的汉族士大夫也不以应举为要务。除室昉外,《辽史》上记载的辽前期担任重要官僚的幽云地区的汉人,均不是以科举之途入仕的。如,应州人邢抱朴及其弟邢抱质,在景宗、圣宗朝,皆“以儒术显”。邢抱朴官至南院枢密使,邢抱质亦官至侍中,然他们都未曾参加科举。南京人马得臣,在景宗、圣宗朝亦为显官,史称他“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于诗”,但亦非科举出身。
辽后期,随着崇尚中原文明的风气日盛,科举对辽国社会,包括契丹族人在内,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契丹统治阶级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制度,并积极利用这一制度来作为加强巩固其政权的工具。这有以下事实可以为证。
第一,辽朝对进士科中第者待遇优厚,表现在朝廷礼仪上,专门制有“进士接见仪”“进士赐等甲敕仪”“进士赐章服仪”等。进士登科者,将由朝廷在皇帝行宫为他们举行一系列礼仪。《辽史》卷五三《礼志》对这些礼仪做了详细记载。但是,这些礼仪并不是辽朝实行科举制度伊始,也不是统和六年“诏开贡举”后制定并实行的,这些礼仪是随着辽后期统治阶级对科举制度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才制定并固定下来的。《辽史》卷八○《张俭传》载,张俭,“统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调云州幕官。故事,车驾经行,长吏当有所献。圣宗猎云中,节度使进曰:‘臣境无他产,惟幕僚张俭,一代之宝,愿以为献。’......召见,容止朴野,访及世务,占奏三十余事”。张俭于统和十四年(996)举进士第一,且是年只放进士三人。倘若当时已有“进士接见仪”及其他礼仪,圣宗皇帝一定已见过张俭。然而不然,圣宗在猎云中时才初次见到“容止朴野”的张俭。这足以说明,辽朝那些对待进士的礼仪是后来才出现的。
第二,科举的实施,使一般汉族以此为目标,竞相教习,以求登第。从出土的石刻中就见到不少有关汉族人自小“习进士业”“学进士业”,然后“应进士举”的内容。受这种浓厚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辽朝中后期,就连契丹族的皇帝、后妃以至于一般贵族也都积极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化,崇尚诗文,喜好儒术,等等,具备了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例如,《辽史》记载,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兴宗“好儒术,通音律”。道宗懿德皇后、天祚帝文妃也都留有艺术价值很高的诗词。《秦晋国妃墓志铭》载,秦晋国妃为景宗的外孙女,她“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汉文化在契丹族的普及和提高,促使契丹族文人涌向科场。终于,禁限被冲破,契丹族人也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这正是科举制度对辽朝社会影响甚大的极好说明。
第三,辽国入仕之途有多种。对于契丹贵族,有世选制度;对于汉族,则有因袭中原政权制度的荫补等制度。特别是汉族的一些世家大族,如所谓韩、刘、马、赵四大家族,基本上都是靠荫补而世代做官。重熙六年(1037)撰刻的《韩橁墓志铭》就记载韩氏一门靠荫补而做官的情况。韩氏家族中,韩德让被“赐姓耶律氏,属籍于宗室”,其余“戚属族人,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而韩橁本人也是靠“袭世禄”而做官的。荫补之盛,是《金史》卷五一《选举志》“序”中说的辽朝“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金史》上的这段议论是统括有辽一代情况而言的,仔细分析起来,辽后期与前期状况是大相径庭的。辽圣宗朝以后的汉人重要官僚,大都是进士出身,而南面最高官署——南枢密院,从长官到下面的院吏,几乎都由进士出身者担当。由于受这种科举取士的强烈冲击,世有荫补特权的汉族显贵家族也开始不以荫补得官为满足,而以获取科场之名为荣耀了。《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记载,韩氏家族的韩企先在辽后期就参加了科举,并中进士第。《金史》卷七八《刘筈传》记载,刘筈幼时以荫隶门官职,他却不就,而“去从学”,后被耶律淳建立的北辽政权赐进士第。《王师儒墓志铭》载,辽道宗朝为宰相的王师儒,其父亲和他都以进士登科而得官。王师儒的儿子王德孙承恩荫被授率府副率、门祗候,但仍“应进士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第四,辽末,耶律淳在燕京建北辽,耶律淳死后,由其妻德妃摄政。这个政权首尾维持统治不过九个月的时间,政治无所更张,而面临着宋、金大兵压境的险恶局势,竟曾两次放进士:耶律淳放进士一十九人,德妃放进士百八人。北辽政权的这种举动,一方面是用以稳定燕京地区的人心,拉拢燕京地区士大夫对北辽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证明,科举在辽政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即使在国难当头之际,仍把科举作为不可或缺的大事来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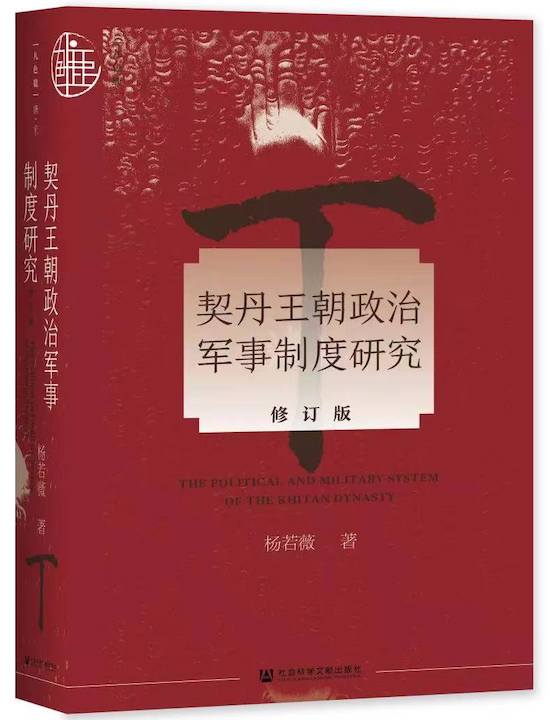
(本文摘自杨若薇著《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