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禾丨翻译也是战场——语言之间的对等与全球关系的不对等
原创 刘禾 三联学术通讯
本文是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Lydia H. Liu)与埃及期刊Alif特邀访谈人James St. André在2016年期间通过电子邮件完成的一次访谈。刘禾教授曾长期致力于研究全球文明中的各种观念、理论、话语及其表现形式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渗透与变迁。在本次访谈中,刘禾教授对翻译的核心作用,对衍指符号(supersigns)、对等逻辑(logic of equivalency)、性别(gender)和普世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历程与相关思考。
人物介绍

刘禾 学者,作家。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全球史、新翻译理论、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等,曾获美国古根海姆学术大奖。英文专著有The Freudian Robot (2011),The Clash of Empires (2004年),Translingual Practice(1995年)等。中文专著有《语际书写》(1997年),《跨语际实践》(2002年),《帝国的话语政治》(2014年),《六个字母的解法》(2014年)等。
James St. André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

翻译也是战场
语言之间的对等与全球关系的不对等
*本文原载于Alif: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etics, no. 38(2018)
原标题“The Battleground of Translation: Making Equal in a Global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苏诗毅 译
刘禾 校订
André:您有一本著作题为《交换的符码》(Tokens of Exchange),而Alif本期特刊征稿始于这点声明,“本刊的出发点……是,知识是被‘生产’的,甚于其是被‘发现’的”以及“翻译是生产和传播各种形式知识的一个核心机制”,因此我想先请教您,在关于翻译与知识的讨论中,您对自己所用术语抱持的观点。从传统上看,在例如科学史与技术史这样的领域,研究者一说起翻译,往往说的是知识的传输(transmission)或专业技术(expertise)的传递(transfer)。而在近来的论文征集中,编辑们则慎重地采用了两个颇为不同的术语——生产(production)和流通(circulation);在一次私人对话中,Mona Baker亦提及了一个可能的选择——构建(construction)和创造(creation)。
在我所编辑的一本书的引语里(《通过翻译用隐喻思考》,Thinking through Translation with Metaphors,2010),我曾论述:Lakoff与Johnson关于语言学的著作和Black与Ortony关于科学史的著作应该警示我们,隐喻(metaphors)有办法(并也经常这样)令我们在界定(conceptualize)翻译的方式上预先取向,甚或先入为主。您认为,您迄今为止所用的术语,在多大程度上界定了翻译与知识研究的可能界限?对于以下选项,即交往(communicative)的模式(传输)、运送(transportative)的模式(传递)、商业的模式(传播/交换)、工业的模式(生产)和宗教的模式(创作——如果我们将圣经故事里的创造世界视为原初文本,正如我们今天思考英文里的creation[创造]一词那样),您认为哪一种最有益?以及,您如何看待您自己所采用的一些术语——尤其是“跨语际实践”和“交换的符码”——正在介入设想翻译之角色的过程中,不仅在中国或东亚,还在更普遍的意义上?
刘禾:回想自己讨论过的有关翻译的议题,我几乎从不使用“传输”或“传递”这些词汇,除非把它们当作批评的对象。我比较倾向于使用“生产”和“流通”,事实上,为了分析全球流通中的翻译实践,我特意将“流通”一词放入《交换的符码》(1999年)一书的副标题中。
您提起了科学史与技术史,并将它们视为典范,而在这些领域,知识或专业技术常被视为可传输或可传递的,这很有意思。我们几乎到处都碰见这样的术语,不是吗?这究竟是因为人们将这个过程本身看做是隐喻意义上翻译,还是因为翻译的操作不得不依赖于“传输”或“传递”的隐喻呢?常被提及的英文词translation的拉丁语词根translatio,意为“转带”(carrying over)或“传递”(圣物),它其实已经体现了这种隐喻的双重性(metaphorical doubling)。不过,如果不去纠缠“翻译”这个词本身,如果有些语言碰巧不属于拉丁语词源,那我们仅从拉丁语的词源出发去规定“翻译”的概念(concept of translation),这个做法有效吗?
接下来的疑难是,即使我们把目光转向非欧语言,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经由翻译又一次在词源上陷入一场徒劳的语义操练?当我们借由非欧语言探讨“翻译”的概念时,我们目力所及的东西有可能是自己早已熟悉、早已被人翻译过的“镜像”之物,不是吗?最后一点,在多重语言语域(multiple linguistic registers)下的语义操练,它能够穷尽“翻译”这个概念的含义吗?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我们首先要在“概念”和“词语”之间维持哲学上的区分。
我觉得您提出的问题包含着相互交缠的一系列议题:翻译,知识,隐喻等。能不能先挨个陈述,再整体处理它们,这对我而言或许会容易一些。我想,您的问题的针对性,与其说是术语,不如说是颇为普遍的一种概念之间移动的不定性(slippage);这种移动的不定性导致了一系列相互交缠且都很有意思的问题。即便概念移动的不定性和必然性广泛存在着,我还是建议我们进行一场思想实验,我们的思想实验的出发点是把翻译作为历史规定的概念来对待,检视在既定的话语传统(discursive traditions)中,翻译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界限在哪里,例如人们对“可译”与“不可译”的纠缠等等,翻译理论及其实践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类话语传统。我们的思想实验是不是也适用于翻译的概念变动性(conceptual mobility)、多样性以及与其他概念的交缠不休?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任何概念都不可能单独存在,或者独立于特定的话语传统存在。我们只能在具体的话语传统中对概念进行辨别。
回到《交换的符码》,这本书我编写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1999年)。我在书的序文中写到,在翻译的概念中,可译与不可译的规定常常是被移了位的抗争——被移位到形而上学的话语中去了。其实,真实的抗争发生在历史上存在的语言之间,抗争的焦点在于语言和语言的“意义价值”之间有没有交互关系(reciprocity)。我在这本书中主要提出如下问题:首先,不同文化之间的历史遭遇(包括征服)是如何在它们的语言之间生产或抗拒“意义价值”之间的交互关系?(请注意,此处“生产”[produce]和“抗拒”[contest]两词是在福柯的知识生产的意义上,而不是工业生产的意义上使用的。)其次,当主导全球交换的不平等形式是“意义价值”交换的物质框架时,我们如何思考语词之间的所谓对等性?
近些年,我对这些思考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集中在对等逻辑对语词的驾驭上。无论如何,“X=Y”的逻辑对于翻译的概念不可或缺,同样的逻辑也控制着隐喻的内在结构。不过,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语词之间的对等逻辑如何一边造就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一边又隐藏这种关系?其手法恰恰在于依靠翻译,让不同语言的语义之间发生“对等”,但语义“对等”的背后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起我在过去的著作中提出的问题更棘手一些,不过我可以尝试着回答。毕竟,人们永远在把不同事物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进行翻译。假如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我们可以对比较行为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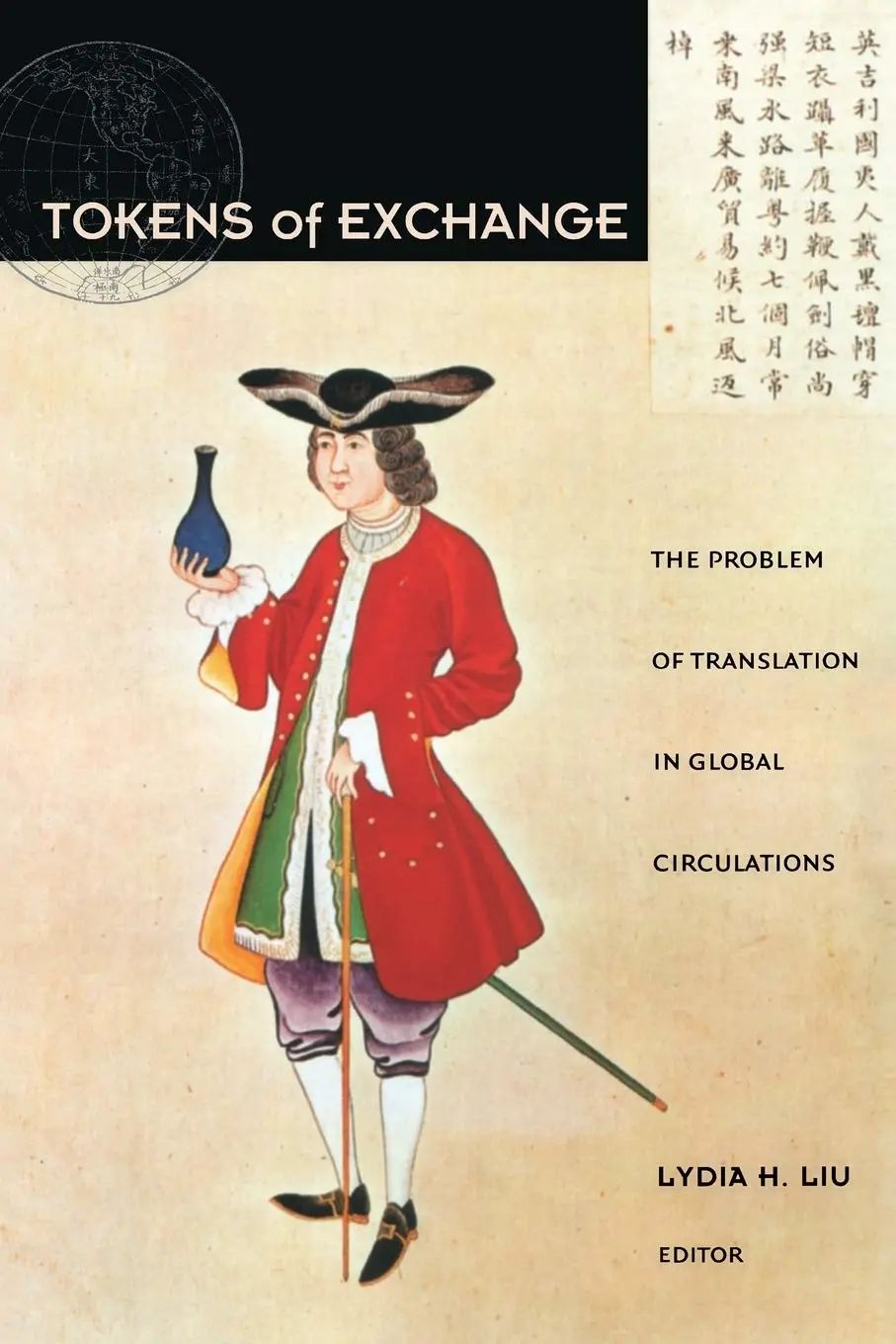
▲ Tokens of Exchange(1999)封面
无论如何,我一直认为,对翻译研究富有创见的参与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因为翻译之难并非仅是语言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或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事,它还跨越其他的学科和领域。例如,就像我在《弗氏人偶》(The Freudian Robot,2010)一书中已经展示的那样,在分子生物学里,已被用于界定DNA与RNA生物化学过程的“翻译”这一概念广泛存在,这似乎不成问题,但从未被充分的理论化。存在于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手头的那种隐喻的变动性,大大超出了人们对翻译的概念进行清晰辨别的能力,更不要说提出一个分析跨学科下翻译理念的话语行为的方法了。简而言之,在这场讨论中,还有比翻译中的语言的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之忧更加利害攸关的东西——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多条战线上争斗(包括翻译的战线),由此这一利害只会有增无减。
但是理论创新的路还很长,就目前来讲,翻译研究的路上有很多障碍,包括我们脑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些有关翻译的联想,例如词语传递(verbal transfer)、信息交往(communication),以及不同语言之间是可通约还是不可通约的,等等。其中,我们来看您在问题中提到的两个阻碍:(1)翻译的交往模式;(2)神学的模式——即您所说的翻译的“宗教模式”。
这些模式的误区在哪里?第一种模式把语言视为一种交往工具,它暗示了一种工具主义的、扭曲的和贫瘠的语言观。第二种模式则坚持语义在翻译中的充足性,就好像不同语言间的语义满足或语义缺席——无论是福是祸——是翻译中唯一可能发生的事情。许多年来,翻译研究的领域在极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这些模式的阴影中。在这里,有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说法以旧充新,反复出现,毫无新意。坦白说,我认为这一类模式智趣贫瘠,非常令人失望。在《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1995)和《帝国的话语政治》(The Clash of Empires,2014)这两部著作中,以及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翻译也是事件”(The Eventfulness of Translation,2014)中,我曾在哲学、语言学、神学、文化人类学的层面上,批判了这些模式将以逻各斯为中心作为前提的顽固性。同样,我们也看到在翻译理论的交往模式与神学模式中,以逻各斯为中心的预设今天仍与我们如影随形;它们由来已久地专注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专注于翻译的传递与传输功能,这就是翻译研究构建的话语传统。
André:您的回答引出了我在提出下个问题前想先简要回应的几个有趣议题。首先,我明确同意您“在当今世界我们不应允许我们对概念的使用方式被词源所规定”这一点,尤其是我们正在讨论的“翻译”这一术语。更甚者是,我们还需留意词源背景,以便能够看到它何时何地在我们对术语的使用上产生影响。在刚刚写完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论述:“翻译”一词的词源学根源和它在不同语言里的大致对等词汇,以及许多更为普遍的关于翻译的隐喻,都使我们产生将翻译看作孤立的行为甚于合作的过程这种预先取向。它只是一个例子。我认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用法造成的负担,通过许多方式压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长期保持警惕。您后面对交往模式和神学模式的评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您关于对等的问题(“语词之间的对等逻辑如何一边造就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一边又隐藏这种关系?”),对于许多人而言,也是十分吸引人的,是对翻译概念的基础要素的再度思考。尽管近来的一些翻译研究工作争论“我们需要超越对等”,我不确定这类尝试是否已很成功——除了在需要改写和再创造的有限的地方;一旦我们开始恰切地谈论翻译,对等便总会以各种方式存在。
您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福柯式的,因为谈及不平等难免让人想起权力议题,与之相关的讨论当然在后殖民(postcolonial)的面向上对翻译有重要贡献。从理论上说,在谈及人、语言和文化时,一个人应有能力在实践中而不是从价值判断上谈及不平等——这一概念似乎总是在涉及这类议题时变得交缠难分。因此,“那些最初的字典和比较性语法的编者是谁”这一问题便至关重要。关于这一点,中国的情况是:最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和稍晚些的商人与新教传教士在着手此事时,便始于以自身语言为尺度、以汉语言为规制对象的假设——后者常常显得有所“缺陷”。我是就杜赫德(Du Halde)和其他用中文写作的早期作家的情况来讨论这一现象的:无论这些作家如何将汉语言比照欧洲语言,几乎总是把两者之间的差异落在汉语言的某种“缺乏”上,比如语音的“缺乏”,时态的“缺乏”,语法的“缺乏”,“现代”术语的“缺乏”等(请见《翻译中国》[Translating China])。
回到您将跨语际实践之概念表述成一种“摆脱对等的尝试”这一愿望上,您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您在这方面的介入已经成功了?换句话说,您认为,作为一个领域的翻译研究已经接受那些理念了吗?并且(或者),对于其他人“超越对等”的尝试——我们似乎能间或听闻这样的说法,您怎么看?如果说“对等逻辑使不平等的结构既成为可能又被隐藏”,那么这意味存在着抗拒这种“摆脱”(或“超越”)的既得利益者,或者存在着对这种理念分散而隐微的抗拒吗?
刘禾:感谢您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让我有机会进一步展开一些在翻译的实践与理论中都更加关乎利害的话题,其在翻译的时空事件性(temporal-spatial eventness)和其对所涉语言不可逆转的影响中都更具意义。在进入主要观点之前,我应该坦承,我对翻译研究本身并不热衷,也并不特别感兴趣。事实上,如果翻译没有以其强大的伦理、社会、政治力量强迫我注意,或者——怎么说——如果翻译不是从语言直接指向社会或政治生活的精神来源,它或许根本不会引起我的关注。比如我多次提到的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双语条约的例子,它恰恰说明翻译的时空事件性及其对语言不可逆转的影响。我猜想,在奥斯曼帝国与英帝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但不懂阿拉伯语这一点,阻碍了我与世界的这个地区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建立富有意义的联系。我别无选择,就只能把我所能举的例子限定在东亚,希望其他学者能够建立进一步的联系。
在英国殖民征服亚洲的进程中,相较而言,“谁是蛮夷?”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明确的,但是未必。它充斥着认识上的断裂与困难,一部分困境源自发声主体之地位的“逆转性”(reversibility)——在我们熟知的文明等级的话语之中,这使得遭遇者几乎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他者之镜(mirror of the other)看待自己。在实际的遭遇中,这一逆转导致“蛮夷”的意义加倍动荡,最终使认知之镜(mirror of recognition)遭到粉碎,竟然在东亚语言中生出诸如“英夷”(English barbarian)这样的事物。这恰恰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中的真实事情。
重温签订于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我们必然在第51款中看到这么一条,它写道: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It is agreed that, henceforward, the character “i”(夷[barbarian]), shall not be applied to the Government or subjects of Her Britannic Majesty in any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 issu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ither in the Capital or in the Provinces.)
我用斜体字强调上文中的一行字,因为这行字正是在英文版原文中的书写形式。这是一条三重符号链:罗马字母“i”转录了该汉字的语音或发音,而书写字形“夷”则与其英文对等语义——即括号内的“barbarian”——并置在一起。表音的罗马字母,表形的汉字,被括号括起来的英文词,这三者究竟哪一个是原文,哪一个是译文?

▲ 《天津条约》第51款
答案似乎在该条约的第50款给出了。为了防止歧义,英国当局预防性地在“夷”字禁令前插入了第50款,便有: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书详细较对无讹,亦照此例。
(It is understood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any difference of meaning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ext, the English Government will hold the sense as expressed in the English text to be the correct sense. This provision is to apply to the Treaty now negotiated, the Chinese text of which has been carefully corrected by the English original.)
最后一行的斜体字强调的是,第51款条约中的汉字“夷”必须经由英文翻译,“详细较对无讹”,成为法定的语义。
那么何者是原文,何者又是译文?而译方如何使自己与另一方相区别?倘若《天津条约》第51款中的英文词“barbarian”(夷)是准备用以匡正一切译文的原文,可是它在文中也同时仍是汉字“夷”的译文,这不是有点奇怪吗?因为它规定英文词既为原文,又是译文,继而形成一个令汉字“夷”无处可逃的彻底的语义闭环。我们必须向这一闭环发起的不是诸如“‘夷’的含义到底是不是‘barbarian’”这种问题(它有得选择吗?),而是这两个术语之间的那种语义对等,最初是如何建立的,以及为什么建立的。
在导向鸦片战争的一系列事件中,英国官员最早声称中国人称外国人为“barbarian”(蛮夷)——尽管我们很确定满族人和(其他)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只是在自己的话语中把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称作“i”(夷)。英国人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翻译和亲耳听到“barbarian”这个词而掌握“夷”的含义的。清朝官员并没有为英国人的自卑心理感到得意,而是对“夷”这个字眼竟冒犯了对方感到费解,他们试图让英国人相信这个词并不是其自认为的意思。这场争论绝非无谓的小事,因为《天津条约》第51款颁布的条律禁令是所谓的“中国人的排外心理”的来源,这个故事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流传至今。
条律禁令中用括号括起来的英文词“barbarian”确保了中英《天津条约》中“夷”字翻译的语义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一双语(双边)条约迫使清朝官员服从英文原文的权威地位,领受“夷”乃至任何其他中文词的“正确”含义。然而,事实证明,“夷”的英文意义绝非唯一,因为在获得权威的过程开始运作之前,必有一种先前的“原意”为新的意义所消解或废黜。在鸦片战争爆发的一百多年前,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大部分官方文件中曾将汉字“夷”对等于另一个英文词“foreign”(外国),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当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15—1823年编纂并出版英华双语《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时,收录了这一词义。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foreign的词义忽然变得不合用,而被barbarian取代。
在《帝国的话语政治》(2004年)一书的研究中,我记录了汉字“夷”在英文翻译中从foreign到barbarian的变化,当时曾发明了一个新概念来分析外文的语义是如何通过翻译在本国语言中出现的,我使用的新概念是“衍指符号”。“衍指符号”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跨语际研究的一个部分,我已为之努力了二十多年,为的是摆脱可译性或不可译性等问题的纠缠。这不意味着词义对等的问题从此在我的研究中消失,恰恰相反,从衍指符号的角度来看,词义对等在翻译中的位置和功能成了一个更值得谈讨的问题。
让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衍指符号是什么意思:在任何已知的语言中,衍指符号指的不是现有的语词,而是异语言的意指链(heterolinguistic signifying chain);通过翻译,它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域,就像“i”(夷[barbarian])的情况。在我对双语条约签订谈判的研究中,我发现这个概念卓有效用,因为它抛下对不同语言之间的语义对等的形而上学的预设,使分析者得以通过翻译的动态过程,找到异语言基本要素的联结,因为这一过程总是隐而不显。我们看到《天津条约》第51款正是通过授权这样一个衍指符号来施行针对汉字“夷”的禁令,尽管这一衍指符号从无此意:其糅合了一组图式的混杂物(graphic concoctions),即转录了“夷”之发音的“i”+作为原文的“夷”+英文“barbarian”。作为其成功的证据,该禁令自此将“夷”字逐出了语义的流通链。这个汉字已被埋葬,不再是汉语鲜活的一部分;它是个死词,一如人们在字典或档案中看到的过时词汇那样。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天津条约》第51款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肯定还有其他的翻译例子更多地体现出和谐关系,而非胁迫。不错,我也相信世界和平,但我更明白战争与和平相隔并不遥远。如果对等的逻辑确实存在,且无法被驱除,那么再多几个例子,或者再少几个例子,并不会撼动这个逻辑本身的效力。所以接下来,我具体分析一下什么是对等逻辑,主要集中在三个要点上。
首先,我们不妨把对等逻辑作为先验的概念范畴来对待。当每个翻译者开始着手翻译工作时,其实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根据对等的逻辑——即甲语言中的X与乙语言中的Y对等还是不对等——来支配自己在翻译中所面对的不同语言。即使有人声称翻译不可能,那么这个断言也是事先接受了对等逻辑的前提才能作出。一直以来,我在自己的书里试图提出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对等逻辑是一种先验范畴,它在反复的无休止运动中制造事物和事物间的对等或不对等,并由此引出所谓的“同一”和“差异”。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等或者不对等的语义,而是说当人们在翻译中判断什么是可译的,什么是不可译的,他们其实是受到了这个逻辑的驱动。

▲ 《天津条约》签订之场景
简言之,人们面对语言系统之间的多样性,需要知道什么是可通约的、什么是不可通约的,往往习惯于把一切都归因于存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同与异,而我上述论述则与此相反:假如我们不在语言和语言之间做比较或者翻译,假如我们没有根据对等逻辑进行比较或者翻译,那么语言之间的同一和差异怎么能辨别出来?
这就引出我的下一个主要论点:对等逻辑的显现要么有标记,要么没有标记。在数学中,这个逻辑总是以数学家发明的奇异符号为标志。在数学中,真正重要的符号不是数值,而是等式、函数和其他运作符号。当数学家说,X和Y在实数的集合上处于对等关系时,他们在说什么?或者不妨进一步追问,数学家在做什么?他们其实在操纵“=”,“<”,“≤”这一类的符号。这些小小的符号之所以没人敢冒犯,就因为它们规定了各类的对等关系,也是这些对等符号才让X和Y之间发生了关系。出于同一理由,只有在这些小小符号上建立起来的对等(或不对等)的关系中,X和Y的数值才能被思考。这些对等符号进入符号系统后,就成为数学中的对等逻辑。
数学思维的严谨在言语或语词翻译中自然不是必需的,因此,对等符号必然要被隐抑,除了某些语言中的系词,这要另说。虽然语言中的对等符号被隐抑,但对等逻辑的支配却一如既往。我把它称为不带标记的对等逻辑,它让翻译者获得操纵词语意义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比如发明衍指符号等等,我在前面分析过这种方式。
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对等逻辑不仅在数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它还扩展到认知活动的诸多领域。回到翻译的话题,所有的翻译都是在甲语言和乙语言之间展开的,两者之间的可通约性一直是翻译者追求的目标。然而,这里的困难是,翻译者无法先验地从语言学出发,去判断两个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达到语义上充足对应(adequatio);也不可能从语言内部找到用以标记对等逻辑的明确符号。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的意图不是要重谈形而上学的老命题,或者重提神学上的疑难,甚至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纯粹语言(reine Sprache)的幻想再说一遍。恕我直言,这些途径恐怕都不足以帮助我们解决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最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语义的所在有关,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当人们通过“语义”把不同语言纳入某种可通约的关系之中时,这个语义的奇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我之所以对本雅明及其他西方翻译理论家的论述不满意,是因为他们对“语义”(sense)进行思考时,事先排除了“无意义”(nonsense)的存在,而其实“意义”和“无意义”两者相互依存。很多人在翻译的过程中,其所作所为就是尽量地把那些“无意义”的干扰从文本中赶出去,这种做法很普遍,流行于世,随处可见,几乎接近于偏执。即使在胡言乱语中,人们也试图捕捉“意义”。这里的警示是,我们在进行翻译的理论工作时,不能不对理性思维所受到的心理限制有所警惕。
由于这次采访篇幅有限,因此我就不在这方面议论太多。我在《弗氏人偶》一书中专门开辟了一章,详细地讨论意义和无意义的问题(第3章,“心灵机器的有意义与无意义”[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Psychic Machine],第99—152页),其中提到,弗洛伊德(Freud)、拉康(Lacan)和德勒兹(Deleuze)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宁愿冒险也要探索“意义”中的“无意义”的思想家。回到我说的语词翻译中的对等逻辑,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翻译者总要被语言之间的对等是存在还是缺失这些问题所困扰。
为进一步展开这个议题,我想说的是,不带标记的对等逻辑也同样支配着隐喻的结构——这是您的研究领域——正如它也支配着所有试图在翻译中思考语言的人一样。隐喻是在两个事物之间建立可通约的关系,并不需要给出明确的标记来担保对等关系的实现。比如英语动词open的隐喻用法,当我说“开启一个讨论”时,这里的动词“开启”(open)并不要求像“开启窗户”这一句子中的“开启”(open)那样做同样的动作。虽然这两个“开启”之间没有对等关系的明确标记,但隐喻的功能就是将一个句子的陈述投射到另一个句子陈述上,让两者相似或对等,乃至合二为一。它靠的是诗意的想象力,想象力将一些被虚构出来的对等事物结合在一起,而不必像数学家那样依赖外在的对等符号进行推理和建立。它常常导致X=Y的多样性融合于隐喻之中,而语言本身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隐喻系统,因此不可能不产生诗歌。
出于这个原因,隐喻的丰富性值得另行讨论,可能远远超出了我在这次采访中所能触及的范围。毕竟人类的语言可以达到修辞、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隐喻,以及转喻联想(metonymic associations)等方面的无限的可能性。我想强调一下,在隐喻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但不带标记的对等逻辑,这是很吸引我的东西。或许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X=Y的多样性在翻译中的无休止形变。
这就说到了我提到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它与以创造性的方式实践翻译的可能性有关——这种方式能够对抗语义对等的“专横”,而产生新含义的多样性。翻译工作总是很困难。我自己就做过翻译,很清楚这个工作多么耗时耗力,尤其是诗歌翻译。在面对不可译的困难时,人们通常总是被上述的对等逻辑所驱动,以为翻译的困难来自于找不到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对等词汇,奇怪的是,人们总能找到其他办法把所谓不可译的词句翻译过来。
André:这便引出一个相关问题,即汉语中的女性主义话语的翻译(创作)。我希望您能谈谈这个领域,因为我认为这会引起许多Alif读者的兴趣。具体而言,您如何描述汉语中关于性别的话语创作?以及,从(“堕落的资产阶级的”)西方翻译过来的作为概念的女性主义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在阿拉伯语世界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刘禾:这个问题很好。举个例子,我和Rebecca Karl教授、Dorothy Ko教授曾合作翻译和编辑过一本书,叫《中国女性主义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2013)。我们必须小心处理在英语世界人人熟知的gender范畴,因为把“性别”范畴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很容易落入概念陷阱。我们的翻译工作不得不变成理论创新——在翻译中,我们开始从中文概念的角度向英文性别理论中的woman、gender和其他女性主义的概念发问。
这本书翻译的晚清女性主义的作者包括何震(笔名何殷震),何震是晚清无政府女性主义刊物《天义报》(1907—1908)的创始人和主编。现代人最熟悉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口号是gender equality,其标准中译是“男女平等”。它指的是在法律地位、受教育的机会、投票权、社会福利等多方面的“男女平等”。然而,从翻译晚清文献一开始,我们就受困于一个问题:如何翻译何殷震笔下的“男女”一词?是不是能草率地把它译成man and woman?或译成gender(性别)?甚至译成male/female(男/女)以及其他人们熟知的一些英文概念。我们发现这个翻译上的难题,反过来激发我们在性别话语上把一种跨语际实践推向理论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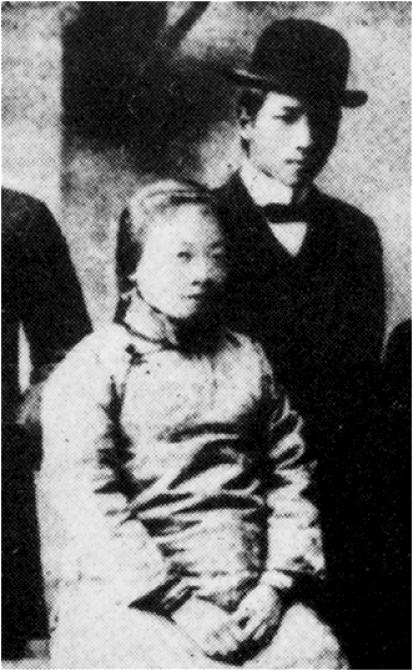
▲ 何震,中国近代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当时的思考是:假如把“男女”翻译成英语的gender,它可能推动何震的思想被纳入全球20世纪女性主义的理论话语,也就是英语世界所熟悉的理论话语,但这种做法也会让我们落入概念的陷阱之中。另一个选择就是将“男女”逐字翻译,比如man and woman或者male/female,但结果同样不令我们满意,因为逐字翻译和何震的理论倾向正好违背,因为她其实把“男女”视为单一的整体概念,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何震认为,“男女”的概念机制渗透于父权统治的基础,尤其在抽象的概括和等级的区分上。这种抽象的概括和等级的区分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而不限于社会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我们最后决定让“男女”的翻译服从于不同语境,获得宽松的语义变动性,译词有时用gender,有时用man and woman或male/female,有时甚至使用拼音nannü。这一决定基于如下理解:我们的困难并不完全在于英语和汉语之间是否存在对等语义,而在于分析范畴的跨语际流动——不论这些范畴是否能成功地穿越诸不同语言及其概念的网格。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力图让“男女”的分析范畴在汉英两语中同时获得意义。为了保持阐释的开放性,我们不去一味地追问英文的gender概念在非西方语言中能不能找到对应的语义,这个问题是偏颇的。反过来说,追问中文的“男女”这一范畴是否存在于英语中也同样于事无益。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语言的不可通约性,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何震的“男女”范畴放在比较的框架中去理解,由此不仅诘问它在汉语中的用法,还要同时诘问英语世界中gender这个理论范畴。
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过程:其一,它要求我们关注“男女”的范畴在汉语和何震的写作中的理论和历史价效。这涉及到对晚清时代发明的跨语际新词和衍指符号的考量;在那个时代,外来语言正在引发尚待转入其现代形式的汉语的转化(如您所知,这一转化的规模是我1995年的《跨语际实践》一书研究的重点)。我们在翻译“男女”的分析范畴和其他关键概念时所面临的困难,其实和何震那代人的经验完全相合——她们当时不得不面对大量涌入汉语的新词和新语法,大都是来自日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等外国语言。
除了跨语际的认识论方面的鸿沟,我们还尽量避免把思想上的难题简约为或置换为汉英之间的语义的不可通约,甚至把它简化为中国如何受西方影响的问题。面对运动不定的语义斜坡,我们还面临着第二个挑战,即如何不让英语的概念如gender以偷梁换柱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翻译实践,成为隐藏在背后的终极参照物。为了避免这种事发生,我们不直接在汉语和英语之间创造唯一的对等词,而是由“男女”和“gender”共同打开一个空间,发生理论共鸣。这种做法适用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其他范畴,也就是通过全球语言的多样性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我们认为,承认在全球范围的女性主义理论的语言衍生和话语多样性,就是让不同的分析范畴相互竞争,以凸显每个术语的局限性,以及它在历史中与其他语言之间形成的纽带。
这里结论就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gender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其自身必须在比较的光照下重新评估,这也包括Joan W. Scott在“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用的范畴”(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1986)中的开创性研究。我们要进一步问,一个有用的分析历史的范畴,它本身能不能超越历史?何震的“男女”概念,可以激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直接参与女性主义传统的跨语际实践,重新思考作为分析范畴的性别概念。
André:当构造活动通过在诸语言之一中发明一个新的符号推进时——要么是通过借取(borrowing),要么是通过转借(calquing);对等语汇的构造本质也许最为明显。我正在思考“关系“这一词汇,它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知识领域进入英语(先是人类学,然后是商业研究)。在商业研究中,采用这个词可能单纯只是一种风尚;但在人类学中,有证据表明用它重新思考亲属关系的中心性对该学科有益。因此,很高兴您将我关于性别的问题引入中国,并在各处谈论英文翻译中的“男女”;这一举动提醒我们,尽管“gender”作为英语的概念范畴,且今天对我们而言很自然,但它事实上出现在20世纪一场英裔美国女性主义的独特的历史与社会运动中。
进入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刚刚读了您关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和人权的文章(2014年),我想知道,您在这次采访中对对等逻辑的讨论,将如何与那篇文章中对普世主义的讨论相结合;尤其是考虑到,即便您早些时候曾提到《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起草委员会的中国成员张彭春未能为概念“仁”找到一个可行的对等词汇(张彭春给出的译文是“two-man mindedness”,您给出的译文是“the plural human”),但您仍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对宣言的成功抱持乐观态度。回到您的“衍指符号”概念,我想知道,“人权”是否是一个与负面例子“夷”字相反的正面例子?
刘禾:我很愿意借用普世主义来总结我们的采访。普世主义的变迁是我那篇题为"普世主义的阴影:关于人权不为人知的故事,1948年"(Shadows of Universalism: The Untold Story of Human Rights Around 1948)的文章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围绕战后最著名的文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DHR)的多语言制定过程,分析战后的普世主义政治。最初写这篇文章时,翻译不是我的中心着眼点,但我确实思考了它如何揭示普世的条件。
人权的价值被许多人拥护和质疑,其普世主义特征几乎总是与文化相对论、特殊性等相提并论。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人权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批评者称人权为“西方价值观”时,他们通过求援于其诸对立面,一致采取反普世主义的立场。我们怎么才能在制定《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分析人权的普世性,同时避免不自觉地陷入某种概念的陷阱呢?这是我在研究1946—1950年的联合国档案时给自己提出的根本问题。
我在档案中还发现了什么?别的不说,我还发现,在《世界人权宣言》和构成《国际人权法案》(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的两个重要公约的制定过程中,普世主义是一种信念,它促成了理念和文本跨越不同语言与多重哲学传统的话语流动性。除此之外,这项研究还使语义的多样性运转起来,并使它们向不确定的(多半还是政治上的)未来敞开。
外交官张彭春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像其他核心成员引起那么多的关注。事实上,他是起草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共同主持工作。他的巨大贡献远远超过将儒家概念引入《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款,他把“仁”的概念译成英文two-man mindedness,而不是通常的benevolence。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张彭春的译词意指复数意义上的人(the plural human则是我的英译),由此对抗以个人为人权的根基(依据许慎《说文解字》以来的诠释,“仁”字从“人”从“二”)。无论如何,我们也许要读了中文版的《世界人权宣言》,才能了解张彭春是怎样翻译孟子的概念。我这么说,并非因为宣言第一款中的英文翻译“conscience”不是一个好的对等词,而是因为翻译本身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普世性如何受到相互博弈中的不同哲学和不同语言的制约。

▲ 张彭春,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
《世界人权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
我的论点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从一开始就涉及到多重语言和多重哲学的传统,因此,将其奉为或贬为“西方的文献”毫无意义。容我说,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即《世界人权宣言》是由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其他国家代表联合制定的联合国文件,因而将其称为“西方的文献”是个大错误。在《圣经》翻译之外,《世界人权宣言》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被翻译得最多的文本,目前有500种语言的译本,包括手语。这些语言都对这一文件的普世化作出了贡献,反过来,每个译本也都承载着这一文本跨越自身语言,参与历史和哲学之联结的庞大语言网络。出于这个原因,我总是建议我的学生用尽其所掌握的不同语言来阅读《世界人权宣言》,这可以让他们再度领略在1946—1948年间《世界人权宣言》制定过程中,联合国代表如何在博弈和斗争中达到普世性的唯一方法。
事实上,张彭春和第三世界代表为《世界人权宣言》引入了斗争中的普世性。他们在联合国辩论中对普世主义的肯定,也是对为殖民诡辩的文化相对论和特殊性的拒绝。我在文章中也对联合国在1950年11月纽约Lake Success举行的第三委员会的会议作了分析,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普世主义是这些斗争者努力坚持的立场,他们的对立面恰恰就是文化相对论。当时,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提议通过一项殖民条款,以文化相对论为由将那些“尚未实现自治的人群”(根据“文明的神圣信托”对被殖民的“野蛮人”的委婉称呼)排除在人权适用的范围之外。
张彭春在大会上的发言表明,文化相对论可以追溯到殖民历史中的经典的文明等级论,其将所有社会分为文明、半文明、蒙昧和野蛮。他申明,这种文明论使欧洲帝国的扩张和殖民统治获得合法性,但在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后,它再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了。于是,张彭春呼吁联合国为未来重新构想新的普世的道德基础,取代经典的文明等级论。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坚持,人权的普世主义第一次挫败了欧美的文化相对论。
您提到“人权”与负面例子“夷”字的故事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正面的例子。难道您会不同意,当比利时和殖民列强努力将所谓的“野蛮人”和“半野蛮人”社会排除在人权的适用范围之外时,“人权”的故事和“夷”字的故事两者就已经密不可分了吗?其连接点就是欧美的文明等级论。这是我在文章中所强调的人权的话语结构的历史关节点。当然,人权的普世主义总有被工具化的危险——就像自20世纪70年代卡特政府以来所做的那样,它有可能堕落为美国的“文明标准”。这个危险很真实,它会使包括张彭春在内的那些宣言缔造者的道德愿景淡出。所以我对人权的话语其实不那么乐观,但我确信——用我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就是“这个普世文本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能否获得意义,将取决于我们自己和后来者”;其他被翻译的文本也享有同样的命运。
原标题:《专访刘禾丨翻译也是战场——语言之间的对等与全球关系的不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