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都山里内观,我十天不说话 | 三明治
原创 林瞳 三明治 收录于话题 #短故事学院 239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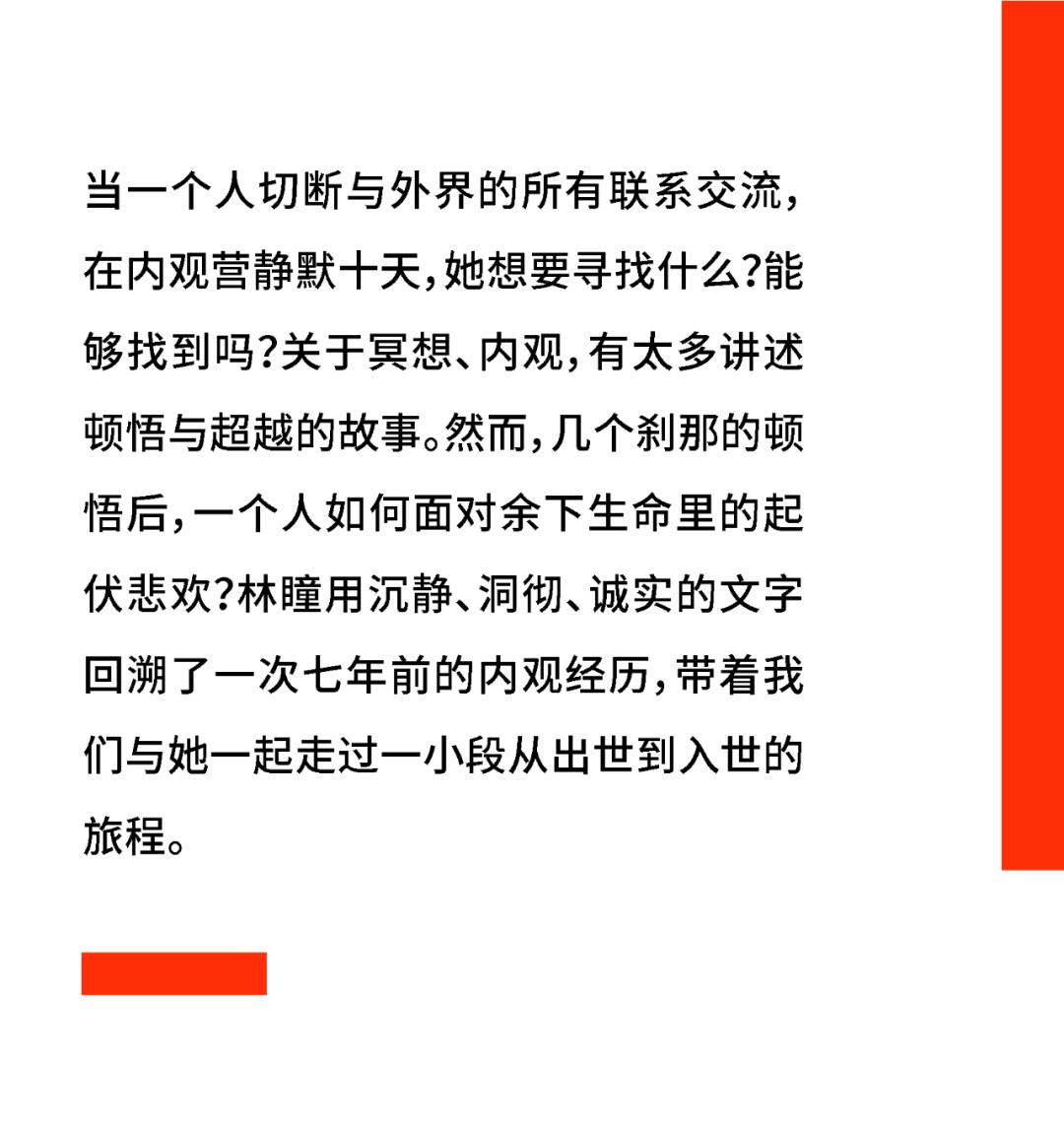
作者|林瞳
编辑|恕行
新干线列车驶入京都车站的那天,九月底的京都不再闷热难耐。与乌丸中央出口遥遥相望的京都塔巍然伫立于千年古都之上厚重的云层间。阴天,很适合这座城市的气质。
逐渐地我发现,我喜欢的城市,伦敦、京都、西雅图皆阴郁得令人发愁。那几年我独独钟爱京都,一年会在那里呆上二十来天。我也像个门外汉,一人穿梭于黑白灰相间的街弄巷衢。相较于满遍古城的佛寺古刹,在这座仿昔日长安城排列整齐的格子城市里,我偏心贯穿京都流动的水。鸭川的粼粼波光、潺潺流水,千年不变。
这一次的旅途,我琢磨了大半年。即使我再清楚不过,出走的目的仅是为了在京都葱郁的山与冷冽的水之间,老老实实地坐着。我决意上山,安于在群山环绕的内观冥想中心生活十天。这期间,必须严格遵循中心制定的神圣沉默的规矩,交付出身上所有的电子产品,与外界彻底隔绝;舍弃语言、文字、视觉所有向外索求的感官刺激,不说话,不阅读,不写一个字。每日清晨四点起早,在打坐垫上盘坐十个小时,直至太阳下山。
盛传内观冥想法是悉达多王子赖以证悟的修行法门,两千五百年来一脉相传,1969年起由印度商人葛印卡于世界各地弘扬广大。葛印卡相信,他传授的内观禅修法没有宗教派系,任何人皆能受益。
内观,顾名思义,即向内察看,如实观察。经由葛印卡与其弟子的引导,从细微地观察一呼一吸开始,逐渐安住心念,进而觉知不断变化的身与心的真实本质。
如同这座城市驯服我的野性的方式,我企图制伏我脑海中喋喋不休、狂妄奔放如猿猴般的心绪。我不能肯定,亦不能保证我能如期完成。打从第一天起,我即抱持着坚持不下去大不了走人的心理准备。生命里,生活中,满是强人所难的无奈,我不愿意处处勉强自己。一如面对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家族丑事,我选择随时离去,宁愿让时间长河做我的审判者。

由新干线列车换乘山阴本线动车,在园部站换33号站台的JR巴士。中心提前发送的邮件里指示参与者抵达桧山站,在巴士站停车场边上乘坐前往中心的专车小巴。拉扯着接下来十天需要的大行李箱,一路上我吃力地在中心发送的英文交通指示与手机地图上的汉字间转换,犹如我再熟悉不过的生存方式,总是在两个文化间吃力地拉扯与转换。Where are you from? Boston. No, no, 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 你从哪里来?波士顿,我答。不不,你究竟来自哪里?他们总是追问。
一坐上小巴,众人仿佛做好了不再说话的准备,七八个人没人开口。我打量车上其他学员,大多是三十岁上下样似白领的日本男女。他们是京都本地人吗?我禁不住猜测。我喜欢京都人,他们冷漠擅保持距离,他们高傲沉重,背负着守护千年古都建筑的重责大任。不同于我的家乡人,来自亚热地带岛屿的人们过于热情,他们窥探我的隐私,想知道我结婚了吗?薪水多少?父母是做什么的?我总是在他们提及父母这个话题时打上嘴。我喜爱京都因为她悠远深沉的历史,却无法诚实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历史。
坐落于群山间的内观中心是一幢日式老木屋,屋内屋外角落四隅贴满日文与英文的指示牌,食堂、宿舍、澡堂、打坐室、工作人员办公室,用餐时间、休息时间、上课时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皆清楚地标示,暗喻着毫无开口发问的必要。所有你必须知道的已在你面前,其余你也不需要知道。
在报到登记处,签署同意书与提供紧急联络人信息后,工作人员在一张纸上用原子笔敲了敲重要课程规章:
十天内,全体学员必须保持神圣的静默,包含身体、言语及意念的静默。禁止与其他学员之间有任何形式的沟通,不管是言语、手势、手语、写字等等都不允许。内观的训练基础是戒律(道德的行为)。而戒律是发展心的专注力的基础,经由内观的修习达到内心的净化。所有参加内观课程的学员在课程期间都必须严格遵守下列五戒:不杀害任何生命、不偷盗、不淫(禁绝所有的性行为)、不说谎、戒除所有烟酒毒品。
随后,工作人员发放每人一个小布袋,放入身上所有的电子设备,标示好名字,储藏进箱子里后上锁,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毫无犹豫地,我交出了手机与平板,却在挣扎片刻后决定保留我的Kindle电子书。打从第一天起,我即逾矩,违反了戒律。那时,我正开始读一美国女人嫁给不丹男人后,移居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 不丹的回忆录。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又或者我害怕被剥夺所有关于我的象征。
那几年,我阅读大量现代悉达多的故事,一个个平凡人出走的真人真事。回忆录的情节与转折千篇一律:某某某曾经功成名就,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却在经历一次重大变故后(大多是婚姻破碎、或毫无预警地面临裁员) 开始思考人生意义,于是毅然决然放下一切,出走到印度(此处可替换成其他贫困国家或地区,但印度似乎颇得人心)。历经磨难与无数次深层灵魂考验,最终领悟生命真相与自我价值,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THE END。
我向往现代悉达多的经历,如同我渴望明白两千五百年前29岁的悉达多王子离开皇宫,舍弃富贵选择苦行的决定。那时,31岁的我,害怕已经迟了。流浪六年后,日食仅一麻一麦,忍受饥饿、历经磨难,出身王公贵族的悉达多于35岁在菩提树下顿悟。究竟是旅途上的大苦与大难成就了王子,又或,我们强烈渴求的智慧与平静,不需远行,不用多难,此时此刻已在我们的坐垫之上。所有你必须知道的已在你面前,其余你也不需要知道。
小时候读过一则令人发笑的故事,记忆深刻。有个人买了七个大饼,吃了一个不饱足,吃了三个也不行,吃了六个还不饱,直到吃第七个大饼时,才吃了一半他已经觉得很饱了。他懊恼地说,早知道第七个大饼就能吃饱,就不枉吃前面六个了!在追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担心我是那愚昧无知的人,只想吃第七个大饼,自作聪明地以为我只需安静地坐着即能顿悟,永保快乐。
日式木屋里的环境与设备整洁朴素,按照性别六个人被分配到一间放满上下床铺的小房间。用过简单的日式晚餐后(咖哩、糙米饭、腌渍梅子、味增汤,我即将发现每一天的午餐菜色一模一样,而接下来9天的晚餐只提供了水果与柠檬水),约莫晚间9点,老木屋周边的林地已然夜色深重万籁俱寂,很快我们也熄灯就寝。我在自己的睡袋里翻来覆去,木板床硬得让我睡不着,我也为即将展开的内观体验兴奋不已。

即便造访京都数次,我对清晨四点京都野外的萧瑟淡薄仍感陌生。天还未亮,又湿又冷,我易犯过敏的鼻子立刻难受得抽动了起来。早餐有煮熟的生燕麦片或家乐氏麦片搭配牛奶的选择。在沉默之间大伙用完早餐,休息片刻后按照指示牌上的时间表依序步入打坐室。同样地,按照性别,男人在左边区域,女人在右边,随机选定坐垫即可坐下盘腿。我环顾四周,约略地数数,大约一百人左右,男女数量平均各五十。打坐室的前方坐着一白人男士,目测约六十来岁,头顶两侧所剩不多的毛发已白。直到最后一天我才知道,来自美国的约翰已定居日本三十余年,能说流利的日语,主持京都内观中心十年之久。
我选择了屋内中央的软垫后坐下,模仿大部分人佯装对打坐这回事熟稔自信。敲钟后,众人坐定,一百多人的大堂里,安静地好似空无一人。约翰开始播放葛印卡大师用难以辨认的语言唱诵无法理解的咒语录音(后来我得知那是古老的语言- 巴利语)。我讶异地发现,好几人能完整地跟着老师唱诵这世界上已无人使用的古印度语言。
接下来所有的指示皆由约翰播放葛印卡大师的录音档,以大师需费心理解、厚重的印度口音指导学员进行内观法的修炼。如坊间大部分的静坐教学,第一阶段、前三天的练习并不陌生。一把低沉平静的声音,交替着日本语的翻译,邀请我们放松全身,专注于自己的呼吸。那声音说,请将注意力放在鼻子与上唇间的倒三角区域,观察外界气息进入鼻孔时一丁点冷冽搔痒的感觉,随着气息缓缓地进入鼻腔内逐渐温暖起来,横隔膜扩展,能量充盈肺部、直至全身。
仿佛带领众人学习一样全新技能一般,大师接着说,接下来,感受你的横隔膜收缩下沉,气息缓慢细长地由鼻子离开你的身体。如果你愿意,他诚挚地邀请你,细微地体验、察觉每一个呼吸接触肌肤的感觉。接着,不需多加思考,再次把注意力集中于呼吸之上。大师说,今天一整天,十个小时,你只需要做这一件事。保持不走神,察觉每一个呼吸。
一整天,十个小时,只做一件事,呼吸。
痛苦从那个时刻开始。
新鲜感很快褪去,我对呼吸的热情仅仅只延续了三个呼吸。在一呼一吸之间,我开始想,午餐该不会还是日式咖哩,我没那么喜欢咖哩。味增汤是不是偷工减料,未免也太清淡了。隔壁坐垫上的日本女人还戴了假睫毛来打坐,表现给谁看呢?下课的时候我还是去外面晒晒太阳,整日坐着也不好。该不会要吃十天的咖哩吧,腌渍梅子也只有日本人吃得习惯。她的假睫毛应该会一天天掉落,十天后就所剩无几了,看她还怎么得意。希望午餐不要是咖哩。
应该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吧。我环顾四周,完了,没有时钟,我也没带表,早知道应该带表。其他人看起来很投入,而我在想什么呢?我应该要观察呼吸,察觉气体进入鼻内,冰与火产生撞击的那一刻。希望午餐不要是咖哩,但毕竟全程免费,也不好要求。这下气息要离开鼻子了,感受它感受它,为什么要感受它?究竟要感受什么?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午餐会是什么?我明明在日本,到底坐在这里干嘛呢?前男友G就住在大坂,从京都过去也就半个小时,出关后我要不要联系他?我到底是不是他最难忘怀的女友?我应该是吧。希望午餐不要是咖哩。

总有人告诉我,静坐于他们而言犹如天方夜谭。打坐时,他们心猿意马、浮想联翩。听说过不少关于冥想的益处,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也强迫过自己,却总以挫败收场。他们问,究竟怎么做,才能在打坐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如自问自答,他们很快地下定论,总结自己不是打坐的料。
我时常想起二十来岁时初打坐的经历。在古北程家乔支路老旧的商务楼里,一处简单的房间,十个人就地盘腿围坐。那时我初到上海,急迫地渴望在两千万人的灯火通明与车水马龙之间找到安住的锚点。带领打坐的女老师喜欢温柔地给新人说,想像你坐在岸边,望着悠悠的河水,河流上漂浮着一个个物品,有些是你熟悉的,有些十分陌生,还有你遗失的、特别喜爱的东西,但也有你厌恶、恨不得一世不再见的。
河面上漂浮的东西,犹如你心里那一个个不断浮现、瞬息万变的思绪。而打坐就是,你注意到它,你单纯地望着那一件件物品,一条条思绪,看着它漂浮,逐渐地远离你的视角。你发现它的存在,但你不去捞捡它,也不去为它贴上标签、深入地探究它。你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它为什么是这样,它从哪里来,它又要去向何处。你只望着它,让它来,让它走。老师笑着说,如果你真的忍不住了,打捞了起来,那么要不,看一看就放回去?也没关系。在打坐里,你不必完美、批判没有意义。
唯一需要做的,只是关注你的一呼一吸。从一个吐息开始,到第二个吐息,第三个,第四个,也许这时你禁不住捡起一个东西,你挂念着的代办事项,想完就再回来,再回到你的呼吸,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
即便如此,我还是给自己留有一手。我将Kindle电子书老老实实地裹藏在厚重的外衣内侧里,以备不时之需。一早我已盘算着,真的坐不下去时即以尿遁法躲进洗手间里阅读(接下来的每一天至少有15分钟我的确这么做)。我曾在一本由长途健行客写的书里读到,背包减量是摆脱恐惧的过程。我们带在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代表一种恐惧:受伤、不舒服、无聊、攻击。
后来我认识了一名同样参加过内观喜爱读书的朋友。每天早餐时,他会贪婪地阅读麦片盒子上的文字,一遍遍重复读,仿佛麦片盒子上印制了旷世文学著作,一个字也不能漏掉。十天后,他可以清楚背出家乐氏麦片盒上的每一句广告词以及麦片的营养成份。我没有追问,他尝试想抓住些什么,我清楚明白我内心拒绝碰触的恐惧。
时间缓慢、深沉,一秒一瞬都令人坐立难安。无论我抬头看钟几次,都只过了一分钟。此时此刻,我的世界只剩下脑海中不受束缚的猴子。没有手机、平板、或电视的分心。语言交流、文字、旁人皆不存在。我挺直背脊,却无法控制记忆迴圈里反覆出现的那些人那些事,长时间盘起的双腿酸痛得颤抖不已。我将无法专心于呼吸归咎于双腿的不适感。我依然坐在河岸,浑身却胶着难受。我开始后悔来到内观中心,给自己拦上不必要的痛苦。我自主地走进思绪漩涡,任其滋长,懊恼曾做的每一个决定。我告诉自己,只要完成今天,明天起床就走,再一天就好,再一天。我来回重复这句自创咒语,在脑海里搜索坚持下去的理由。
我是个不断寻找答案的人。不止一次,我启程上路,遍地找寻我所谓、向往的自由、真理与生命意义。我的探索之旅启始于目睹母亲的骤然逝世、之后一系列的生命变故,自十一岁那年起。
后来又后来,离开京都群山后的几年,我走的更深、更远。以苦行僧的方式行旅,走到了柬埔寨、缅甸,在深山寺院简陋的土楼里搭设帐篷,老鼠与蟑螂在床铺边上奔跑。我去了悉达多的故乡,徒步王子行径过的道路搜寻他的踪迹。坐卧在京都的山,我不曾设想几年后,我到了菩提迦耶,在王子盘坐七天七夜的那棵菩提树下席地而坐。彼时的我,仍然埋怨盘旋脑海的烦恼太过庸俗,一个渴求开悟的人不过如此,满是凡俗的念想,总是庸人自扰。
每每有人说,打坐时他们无法控制脑海中的思绪万千。我失笑,我也不过如此。虚实交错,庸俗却真实,浮躁又灵动。我唯一能做的,只是望着它,察觉它。在心里,我向一个个躁动不安的念头低语,原来你在这,你想得到我的注意力,那你得等等。又或者,你可以离开。在心里,它来,它走。
似乎,当盘腿而坐成为日常,我方才听见內里的波涛与汹涌。

每天中午饭后,开放短短的半个小时,有疑问的同学可以排队向约翰提问,一人两分钟。约翰只接受关于打坐技巧的问题,谢绝任何哲学、宗教问题。第四天,我终于加入发问队伍。
“我的腿痛到坐不住了,怎么办?”我问。
“你不是你的疼痛,”在诺大无人只剩下约翰与我的打坐大厅里,约翰安静地说。“尝试去感受、去分别你所谓的疼痛,有几种疼痛呢?只有一种吗?还是有好多种、不同层次的疼痛呢?记住,你不是你的疼痛。”
不是不讨论哲学问题吗?我不禁想。我只想知道解决方法,如同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我想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立刻解决问题。我渴望快效药,我只要万灵丹。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追问, “但如果还是继续痛呢?”
“那你就活动活动腿吧!” 约翰笑着说。
就这么简单?我无法置信地看着约翰。约翰看看大堂外排队的学员,示意我们的时间结束了。

每隔一两天,总有人弃械投降,离开中心。从一开始的惶恐不安,而后我也逐渐习惯各种反应,见怪不怪。第二天,一名美国男子离去时号称这不是他平日的禅修法。第三天,不知国籍的男人强烈质疑,就这么坐着是否真的能成就什么,拂袖离去。第五天,状似内敛的日本男人抱头痛哭,在木头地板上号啕不止,哭声浩荡于百人之间,众人默然。
我想知道,他人为何而来?历经了什么劫难,为了哪些隐而不言的理由来到这座山头,使尽全力地留下来,独自一人自问自答,究竟为了什么?戴假睫毛的年轻女孩尝试想获得什么、放下什么?伤心欲绝的日本男子可曾在人前流泪?而那些选择离去的人们最后是否感到遗憾?
而我,是什么引我而来?我又为了什么留下?试图解锁那些生命里无法独自理解的大哉问,我一再再地发问,微小慎微地渴望终有一天得到解答。
我爱观察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一名约莫七十几岁的日本老太太。每一个小时的练习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移动坐姿舒缓僵硬的四肢。唯有她犹如入定,甚至在每段练习后的十五分钟休息时间依然纹风不动,可以连续坐上三个小时。老人没有开口说话,却散发着安定沉着的能量,隔着几排座位都能强烈感受,引人羡慕。
十天后,一被允许开口说话,我立刻上前与老太太攀谈。她能说几句英语,她告诉我,她已经有超过十五年的打坐资历,研习过各种打坐冥想法,每年都进行1-2次连续三十天的静默内观。连续三十天不说话只打坐,我瞠目结舌。
只要练习谁都能做到喔!你也可以。她温柔地说。

记不得从第几天的练习开始,葛印卡的录音里时常提及“Equanimity 平等心”这个词。
大师的话语引导学员扫描全身的感受,从头顶开始一寸寸地感受自己的肌肤直至脚底板,细微深入地体验肌肤与衣服、肌肤与冷空气接触的感受。觉察身体产生的任何微妙的反应时,葛印卡说,所谓的平等心就是,遇到讨厌的觉受对其抱以平等心,同样地,遇到喜欢的感受时也予以平等心。
讨厌的感受,平等待之;喜欢的感受,依然平等。
我按照约翰的指示,在双腿开始发麻难受的时候,暂时忽视内心的哀嚎,学着理智地观察我统称疼痛的感受。我数了数:麻、酸、刺、涨、压、僵、痒、抽痛,它们个别或叠加地分布在腿部不同区域。有意思的是,当我忙活着分别与概念化疼痛的感受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仿佛与疼痛抽离,它是它,我是我。它不是我,我也不是我的疼痛。那一刻钟,第一次,时间快进。
那几日,我时常想起长年跑马拉松的日本作家写,痛苦不可避免,但磨难可以选择。作家在脑海里反覆这句咒语跑完一个又一个马拉松,我也持续复诵我的咒语,再一天,再一天我就走。这世界上总有些人刻意将痛苦放置进自己的生命中,我也不例外,仿佛受苦是超脱的唯一途径。
每天傍晚结束当天十个小时的打坐后,晚上8点中心安排参与者观看葛印卡教授内观打坐方式与注意事项。能说日语者留在打坐大厅收看日语翻译版本,外国人则统一到一旁的小木屋观看英文版本。初秋的京都山上,仍时不时有小虫、蟑螂出没。一名同样是亚洲人、目测三十岁上下的姑娘每天晚上皆因害怕蟑螂紧张地跳到桌上,不能发言表达抗议则以行动逃脱。
我冷眼看着她的窘境,不肯共情于她的恐惧。我一样害怕蟑螂,却如同应对生命抛出的各式曲线球,不愿意轻易示弱,执意佯装地若无其事。在心里我取笑状似柔弱的女孩,为了一点小事惊慌失措。我想对女孩说,我们不是来打坐练习平等心的吗?蟑螂也是生命,讨厌亦或喜欢,皆以平等心待之。
结束时我才知道,女孩来自香港,是一名心理咨商师。

不说话的第九天,枫叶还未转红的京都府近郊的群山上,我终究成为一名自我定义下“合格”又“成功”的冥想者。整一个小时,我如如不动。
我的肌肤清楚又深刻地觉知,那一个小时,一根细发掉落在我的鼻尖处,搔弄着鼻头上一小寸的皮肤。往下移动,鼻根与上唇之间,吐息与吸气之际,温暖湿润的触感。我却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又或着过去八天反覆困扰我的腿麻,记忆轴线上一再出现的人。倒计时的第九天,流光静止。
且慢,别得意忘形。很有可能,你会同我一般,以为一次成功的经历注定开启今后的一帆风顺。我很快地发现,下一个小时的练习,一个走神,双腿的麻痛无情地将我打回原形,分针秒针再次止步不前。我仓皇失措地寻找好不容易获得的平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仿佛从来没有拥有过。如同我的生命轨迹,总是前进两步,退后三步。只是我不愿意放弃。
如剧中的角色,我们总是最后才知道尽头已至。结束最后一天上午的练习后,大伙一进入食堂便开始热络地交谈,仿佛过去十天的沉默只是一场迫不得已的冷战,众人许可配合出演的默剧。
一起在小房间观看葛印卡视频的外国人们自然地聚集在一起:美国的戈恩、在日企工作能说流利日语的上海女孩莹、香港谘商师史黛芬妮,来自芬兰难以发音的北欧名字情侣。莹告诉我们,她还参加过几个地区的内观修炼。看着我,她说,台湾的内观中心伙食最好吃,一定要去,好似参与内观仅是为了美食。

领回我的手机与平板,带上行李与睡袋,我搭乘中心安排下山的小巴。一上车我即迫不及待地打开久违的手机,再次与世界搭上线。
进入内关中心之前,在台湾的好友兴奋地告诉我,我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了。我提前恭喜她,提醒她记得发照片给我,我一出关就能看到。
如需坦承,过去十天,缄默于我是一种享受,丢弃无意义的嘘寒问暖,没有言不由衷,不需伪装自己。我感到通体舒畅、精神饱满,甚至有点渴望继续这样下去。我对自己过份热衷孤独感到一丝惧怕。心理学家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与人产生连结是幸福感的必要元素,离群索居的生活怕是不切实际。
一开手机,朋友的信息立刻弹跳出来。我在京都山上与世隔绝的十天里,昵称“美国队长”的小男孩如期来到了这个世界,但因肺部发育不全引发严重感染,紧急抢救后无果,孕育九个多月的生命在出世三天后离世,朋友全家悲恸不已。十天,这个世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却又发生了许多。生命来,生命走。
我不记得一路下山小巴窗外我钟爱的京都山林,只记得我抓着手机不自主地颤抖。我彻头怔怔地望着一旁的香港女孩,转述我读到的信息,眼泪潸潸落下。新朋友紧紧搂住我的肩,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由我哭泣。也许是心理谘商师的专业训练,她没有多余、无谓的话语,安静地、温柔地予以理解与宽慰。
我为自己早前对她害怕蟑螂的批判感到羞愧。我想,其他人也许不知道做何反应。大多数人在死亡面前只能手足无措、选择避而不谈,谁又能在生命消逝之际安然无恙、镇定自如呢?
网上能翻出许多纪录内观体验的文章。犹如悉达多的故事,记事中的主角在剧终落幕后得到升华,作者活生生的文笔描述仿如顿悟的心路历程与心境转向的清澈清明。而我,参与十天静默内观后的日子,奇迹没有发生。我没有成为现代悉达多。我依然急躁不安,世界没有因此成为玫瑰色,生活还是五味杂陈,徐徐行在前进后退的泥泞中。
我回忆下山后,随意走进京都市中心一座不起眼、毫无观光客,只有少数几名京都老人聚集的寺院。没人搭理我,我在角落添了香火钱,在高至天花板巨大的木质佛像前,于榻榻米上盘腿坐下。生活于两千五百年前的悉达多王子,在今日,威武庄严,以全知者的姿态视人,弯弯的眼隐含笑意。为什么而来?又要去向何方?我凝视追问。
十天,思绪如转瞬即逝的生命,它来,它走。我时常想起这句话,这个词,Equanimity 平等心。讨厌的感受,平等待之;喜欢的感受,依然平等。
书写往事时,我总担心自己的记忆偏颇、文字苍白,过于冷静地述写我行经的生命旅程与对生命本质的浅薄理解。书写的目的究竟为何?是寻找,是直面恐惧,是疗愈,是辩证,是揭开黑盒?如同几千年来人们对生存意义的大哉问,我没有答案,只能一步步举足前行,持续而固执地提问。
阅读作者其他作品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原标题:《在京都山里内观,我十天不说话 | 三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