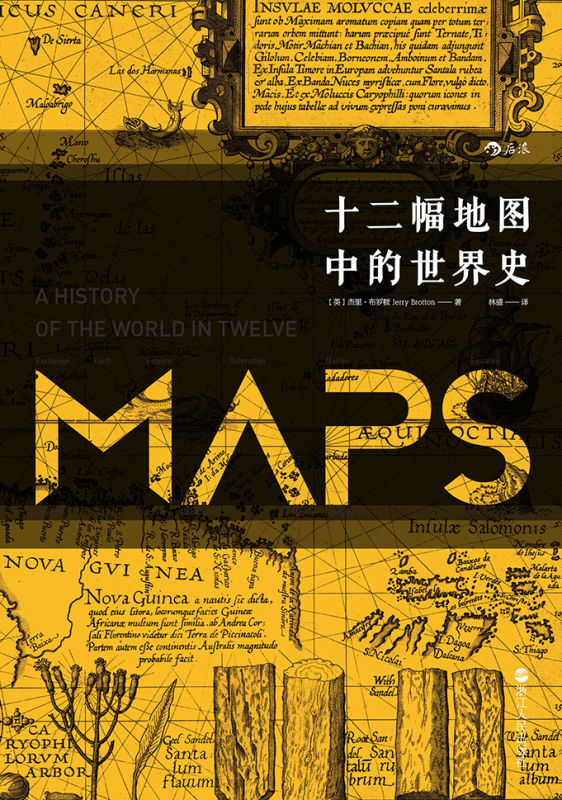《卡西尼地图》:帝国制图师的挽歌与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
法国最优秀的制图师为什么遭到迫害?
1793年10月5日,法兰西共和国国民公会颁布了《关于建立法兰西纪元的法令》。这部法令引入了全新的历法,用来标记一年前的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正式宣布诞生。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是为了扫除刚被推翻的“旧制度”的一切残迹,从专制统治的方法,到标记历法时间的方式。
就在启用这部历法的前几周,国民公会收到一位较激进的代表的报告,这个人是演员、剧作家和诗人法布尔·德埃格朗蒂纳。德埃格朗蒂纳已经投票支持处决国王路易十六,并且是新历法制定委员会中一位重要成员,他如今又将目标瞄准地图。
他希望国民公会重视“法国全图,即学院地图”,他抱怨这幅地图“绝大部分由政府出资制作;但却落入个人手中,被当作私有财产;而公众必须付出昂贵金额才能使用,而且这群人甚至拒绝将地图送给有需要的将军使用”。
国民公会认同德埃格朗蒂纳的观点,下令将与地图有关的雕版与图纸查封并转交给战争部的军事办公室。战争部的部长艾蒂安-尼古拉·德·卡隆将军对这个决定非常满意。他宣称:“此举让国民公会从一群贪婪的投机者手中夺回了国家的成就,这是工程师们花费40年的工作成果,一旦丢失或抛弃这项成果,将会是政府资源的一大损失,又会增加敌人的资源,因此更应该完全由政府掌控。”
德埃格朗蒂纳的抨击与卡隆的欢欣鼓舞,意在没收法国地图,并扳倒让-多米尼克·卡西尼(1748—1845年)。让-多米尼克是声名显赫的卡西尼制图世家的第四代,被公认为是法国地图的拥有者,但他不幸身为这个世家的最后一代,国民公会没收地图时,一个庞大的计划几乎就要完成了。

对让-多米尼克这样的坚定保皇派而言,地图国有化是一场政治灾难,更是个人的悲剧。他在回忆录中哀叹:“他们从我这里将它夺走,尚未全部完成,我还没有为它进行最后的润饰。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作者尝过这种痛苦。有哪个画家还来不及进行最后的润饰,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画被夺走?”
引发这番所有权争执的是革命者所谓的“法国全图”,卡西尼和他的合伙人以拥有者的身份将其称为《卡西尼地图》,这显然让德埃格朗蒂纳和卡隆非常恼怒。这是第一次有人尝试依据三角测量和测地法(即测量地球表面)系统性地测量全国土地,并绘制成地图。按照原定计划,《卡西尼地图》完成时共有182页,比例尺是统一的1∶86400,组合起来后是一幅约12米(40英尺)高、11米(38英尺)宽的全国地图。这是第一幅现代的国家地图,使用了创新的科学测量方法来全面呈现一个单独的欧洲国家;但到了1793年,问题在于:它属于谁?是它所再现的这个崭新的革命国家,还是耗费四代人心血制作它的那些保皇派?

国家面积大小是用什么方法测绘出来的?
这幅地图起源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从让-多米尼克的曾祖父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1625—1712年),即卡西尼一世开始。国王路易十四在1667年设立了巴黎天文台,乔凡尼是实质上的第一任台长。在100多年中,乔凡尼的后代——他的儿子雅克·卡西尼即卡西尼二世(1677—1756年)、他的孙子塞萨尔-弗朗索瓦·卡西尼·德·蒂里即卡西尼三世(1714—1784年),最后是与他同名的曾孙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四世)——依据可验证的测量与量化的严格科学原理,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全国性测量。
虽然这个计划经历了诸多实务、经济和政治上的变迁,而且卡西尼家族每一代人各有不同的追求方向,但他们将测地法和三角测量结合起来的方法影响了西方日后所有的地图制作。他们运用的原理依然被大多数现代的科学地图使用,从世界地图集到英国地形测量局和线上地理空间应用,全都是遵循着卡西尼家族最先提出并实践的三角测量和测地方法。这个计划开始时只是为了测量一个王国,最终却为之后200年绘制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图提供了模板。

三角图解,让·皮卡尔,《土地测量》,1671年。
1793年的公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私人制图计划收归国有。卡西尼家族每一代人都与提供了部分资金的法国皇室家族关系密切,这使它成为革命者鲜明的政治标靶,但像德埃格朗蒂纳和卡隆这样的人也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卡西尼家族的测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尽管这些经过测量印制出来的地图与皇室密不可分,它们最终却可以成为新的“法兰西纪元”的一个象征,以之为蓝图可以塑造法国是一个现代的共和民族国家的概念。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些地图的军事价值。当时敌对的邻近王国眼看就要入侵这个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卡西尼家族绘制的包括法国各地区和边界的详细地图对保卫新政权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国民公会已经在设法将国家的行政部门进行合理调整,将教省、司法辖区、商会、教区这些混乱的组织进行改革,重新划分为83个省,而收归国有的卡西尼地图在国家划定和管理这些地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地图还能产生更深远却难以察觉的影响。卡西尼家族的地图测量在共和国手中,能够逐渐让人们相信这是这个国家的地图,是为了这个国家而绘制的地图。德埃格朗蒂纳在申请将地图测量进行国有化时提到,它能让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
这些测量地图不仅响应也利用了孟德斯鸠男爵夏尔·德·塞孔达(1689—1755年)和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等思想家开始界定的贯穿十八世纪的“民族普遍精神”的出现。波旁王朝的君主们鼓励土地测量是为了歌颂他们以巴黎为中心的统治。而到了共和国时期,这将被视为把地图上的每一寸(或是每一米,1795年 4月起国民公会开始采用公制)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政治修辞现在宣称民族的实际领土和国家的主权现在融为一体,这个理念后来将输出到整个欧洲,最终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

地图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
《卡西尼地图》在制图史上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这是基于测地与地形测量制作的第一幅全国总图;“它教会了世界其余地方的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它所追求的“量化精神”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将制图工作在后来150年间转变为一门可以验证的科学,追求一种标准化、以经验为根据的客观方法,可以(也必将)推广到全球各地。制图师如今被视为超然的工程师,能够使地图和当地情况完全相符。这个世界被化约为一系列几何三角形,让人们可以认识并进行管理。
但卡西尼家族声称追求一种公正、客观的科学研究方法更像是一个心愿,而非现实。卡西尼四世在漫长的隐居生涯中回顾他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时的往事,惆怅地写道:“我被困在天文台里,以为那是一个避风港,可以逃离这个充满嫉妒与阴谋的星球,我们管它叫世界。在星辰的运行里,我只看到宇宙奇观中高贵而又美妙的规划。”他认为新共和政权以冷酷的工具主义态度对待他,这些话部分是他幻灭后的反应,但也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卡西尼家族四代都在为专制君主服务。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科学院成立以来,卡西尼家族测量并绘制法国地图,直接响应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先后进行统治的政治和财政需求。历任财政大臣都把测量工作和地图视为有效管理国家的工具。从柯尔贝尔开始,历任大臣都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地理学,帮助他们绘制交通网络图、管理各省税收、协助土木工程、支持军事后勤。卡西尼家族常常出色地满足了这些需求,而非以中立、超然的科学思考发展他们的测量方法。

从他们的方法中得出的结果,有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么精确和全面。这些工程师试图在恶劣的环境下,使用笨重且有限的设备进行精确的测量,光是这些外在条件造成的困难,就使得即便经过三次测量,《卡西尼地图》基本完成,拿破仑当局仍然发现地点的位置有错误,缺少最近修建的道路以及经度和纬度的测量。这些测量计划对于记录的内容也进行严格筛选。那些购买自己当地区域单幅地图的人抱怨,缺少诸如农场、溪流、林地甚至城堡等地标,尽管国家想要的是一幅“重要地点的位置图表”,用于征税等特定的行政目的。就连卡西尼三世也承认“法国的地形受到太多变动因素的影响,很难用固定不变的测量来把握”。矛盾的是,测量工作本身以及未完成的《卡西尼地图》这两者的局限性,反而正是它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因为这表明任何全国性测量都可能是没有尽头的。地形资料累积起来变得无比繁芜,压垮了首轮测量的几何学骨架。当我们发现卡西尼的雕版地图没有记录一些新的道路、运河、森林、桥梁和其他不计其数人为改变的风景,我们就会意识到,无论科学如何宣称能够精确测量土地并绘制地图,土地永远不会长期保持一成不变。
最后,《卡西尼地图》远非只是一项全国性测量。它能使个人将自己视为国家的一部分。如今,在一个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如果说有人在看卡西尼的国家地图时,看到的是一个叫“法国”的地方,并且认为自己是居住在这个空间中的“法国”公民,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十八世纪末,情况却并非如此。与民族主义的宣传正相反,国家不是自然产生的。它们是在历史的特定阶段,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民族主义在十八世纪抬头的时候,正值卡西尼家族展开测量计划,而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民族主义”一词诞生时,卡西尼地图也刚好被国民公会以法兰西共和国之名收归国有,这些都绝非巧合。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关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主张,国家意识是在宗教信仰和帝国王朝受到长期历史性侵蚀后出现的。随着人们不再那么确信宗教救赎,欧洲旧制度下的帝国也渐渐瓦解。在个人信仰的领域,民族主义让人们感受到了强烈的慰藉,即安德森所谓的“通过世俗的形式,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在政治权威的层面,国家取代了帝国,展现了新的领土概念,“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这和帝国截然不同,帝国“是以中心来界定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地方语言和对时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安德森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在十五世纪兴起,渐渐展示了代表皇权和教权的“神圣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终将衰落,逐渐被大批潜在的新读者所说的地方语言取代。小说、报纸和铁路随后在欧洲兴起,创造了一种对“同时性”时间的新感知,以“时间上的一致性”为标志,用时钟和日历进行测量。人们开始想象他们国家的各种活动都穿越时空同时发生,尽管他们一生只能造访或会见组成这个国家的地点和人口的极小一部分。

不过安德森一开始没有考虑到国家认同最有标志性的一种体现,这是一例典型的“历史学家对地图怀有莫名的反感”。如果说,语言和时间的变化“使人们‘想象’国家成为可能”,那么地图既然可以改变人们对空间和视觉的感知,就有可能将国家视觉化。《卡西尼地图》诞生于铁路、报纸和小说崛起成为主流文化的同一时期,这幅图像让购买它的人可以一眼就想象出全国的空间。从个人所在地区转移到全国,以标准的巴黎法语(由革命当局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开始标准化)阅读地图,地图的拥有者可以对一个地形空间及其居民产生认同。结果,国家开始经历漫长且往往痛苦的过程,发展出一种行政上的稳定性和地理现实,有助于激发国民产生前所未有的情感依赖和政治忠诚。
卡西尼测量计划代表着一种绘制国家地图的新方法的开端,但国内居民需要的情感依赖和政治忠诚对象,不能只是一个几何三角形。宗教已经无法提供答案。基督曾经统辖着地图的顶端,俯视整个世界,而卡西尼地图则提供了一种观察地球的水平视角,每一寸土地(也意味着每一位居民)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政治专制主义也难以维系。虽然最初的企图是建立一种新的制图方式,用来监督和控制王国领土,但由君主资助的这幅王国地图却在不经意间变成了一幅国家地图。
《卡西尼地图》所要传达的信息蕴藏在182幅地图的每一幅中,后世的民族主义者很容易就可以加以利用:一幅地图、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共享同样的一套习俗、信仰和传统。在为了国家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不断上演之中,《卡西尼地图》让法国子民看到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牺牲的国家形象。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足够高尚的动机,但这种不可动摇的民族主义失去约束所造成的后果,绝非只有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上下才感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