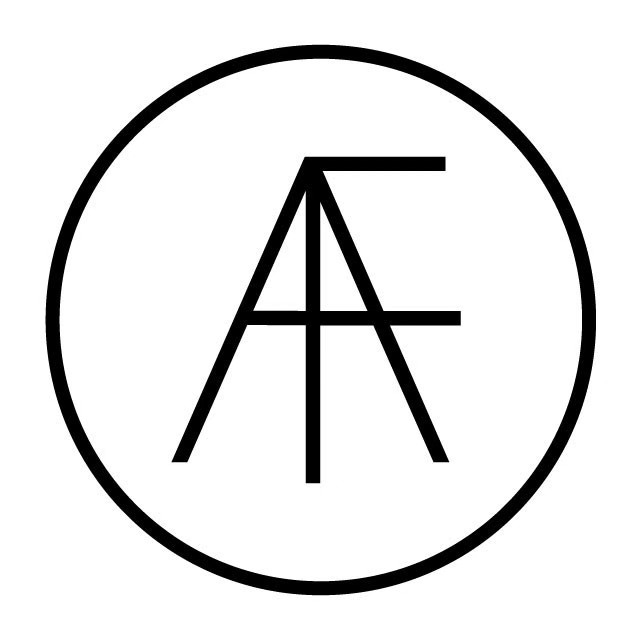他的镜头里,人总是飞起的:神童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格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维姬·戈德堡(Vicki Goldberg)是西方摄影评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以富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文章著称。《光影的要义》(Light Matters)首版于2005年,该书收集了作家写作生涯以来的诸多优秀散文和评论。
戈德堡对摄影的观察深入浅出且包罗万象,她的写作主题跨越极广:从流行影像到战争新闻,从肖像摄影快照亭到可后期数字图像,从乏味无趣的窥视到充满悲剧的现场等等。她还从摄影领域的“大师”作品中提炼出新的启示,其中包括沃克·埃文斯、约瑟夫·寇德卡和黛安·阿勃斯等,并以同样敏锐地视角书写和剖析了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森山大道和巴斯蒂安娜·施密特(Bastienne Schmidt)等当代影像先驱者的作品。
此外,维姬·戈德堡的著作还包括《摄影的力量:照片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The Power of Photography: How Photographs Changed Our Lives)、《作为印刷品的摄影:从1816年至今的影像写作》(Photography in Print:Writings from 1816 To the Present)等。1997年,戈德堡获得国际摄影中心著名的“无限奖”,1999年,她荣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约翰斯顿奖。
雅克·亨利·拉蒂格
文 | 维姬·戈德堡
译 | 吴雪红 唐冬雪
雅克·亨利·拉蒂格视他的第一台相机为上帝给予他的恩赐,抑或是某个为他而设的纰谬。他在一篇回首童年的日记中写道: “爸爸简直就是上帝[也许就是上帝在乔装成他]。他刚刚同我说:‘我送你一台真正的照相机。’”拉蒂格的父亲拍摄照片,并教授这个男孩如何冲洗照片。那是在1901年的年末,雅克·拉蒂格年仅七岁。
十三岁时,这个男孩深信上帝会保佑他得到幸福,郑重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爱上帝,我将永远感激他。”他这一生,最早从幼年开始,就以一种宗教热情来极力维护上帝承诺他的幸福,并为神赐予他的摄影事业尽心竭力。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诙谐与创意,前卫与风情,以及阳光、风、慵懒和梦幻构成了拉蒂格相机里的世界——这个世界有酷炫的汽车,优雅的阳伞,以及海滩上穿着白色裤子的悠闲的人们。没有人在那里哭泣,每一个人的欲望俱能得到满足。唯一能够让人想起悲伤的或许只有大海那浩瀚而无情的孤独。
拉蒂格感到幸福既是一种恩惠,亦是一个目标,悉力守护自己那与生俱来的满足感。在年幼时,他发明了称之为“视觉陷阱”的东西。眼睛睁大,然后眨眼,大脑中就会留下一个生动的场景。但在几天之后的某个清晨,他醒来后发现这个重大的发明不再起效,为此惆怅了良久。待他重新振作后,他决定通过其他方式去重构这一发现。
他经由三种方式守护内心的幸福:摄影、绘画与写作。当父母赠予他第一台相机后,他决计用摄影记录去这世间中的一切,以此将自己从放弃乡村生活而辗转到了巴黎的悔恨中解脱出来,他将那里一切统统塞进了照片里。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他希望一辈子都当个孩童。正如六岁时在日记里写的那般,他对成年人的世界感到彷徨和沮丧。孩子们不愿长大的念头其实并不鲜见,当他们被宠坏时更甚。小哥哥五岁的拉蒂格,似乎还对他的母亲分享过他想一直当她的宝贝的想法。
拉蒂格在许多方面都安常履顺。他出生在对的地方,对的时间,对的家庭。他的一家既富有,亦智慧。既有冒险精神,亦充满热忱——其中几人是发明家和工程师。他们并不以文凭为重,而更注重培养拉蒂格对文化的依恋,并激发他的潜能。而他的弱势在未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他最初的事业有所裨益。
当他长大成年之后,他愈发具有魅力、自信且情感超然[尽管是在恋爱中],他起誓要做一个绝对的旁观者,他对幸福的专注亦使得他尽可能地从自己的记忆库中删除世俗之弊。在他的画作、照片和文字中也罕见那个时代如地狱般的一面。所有的这一切成就了他设想中的作品,一部使人夷愉,引人遐思,亦令人惊诧的作品。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拉蒂格早期摄影的魅力源自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和依附于这个时代的怀旧感。他从一个独特的国内视角来看待《贝勒·波克》(Belle Époque)的结局,即以一个男孩异常警觉的视角,幸灾乐祸地强调运输与速度的变革。卓越的家庭本身就已使得他的照片别具一格。他的胞兄,同他的祖父和叔父一样,具有发明的天赋——自制飞机、汽车、用轮胎制船。他的亲戚和玩伴在诸如赛跑、格斗、摔跤中竞技。但拉蒂格较为年幼,比他大的孩子不让他参赛。他这一生都是一个旁观者。
1902年初,这个小男孩拿着笨重的照相机,经长时间的曝光,留下了几张相当标准的家庭肖像。同年,他八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一台斯皮多格蒙特(Spido-Gaumont)立体相机,拉蒂格不久便掌握其以拍摄。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照相机便一直在捕捉一些运动,在此期间,乳剂和快门速度得以发展。早在十八世纪,立体相机就成功地捕获了较为缓慢的运动,譬如男人和女人在街上行走,至此世纪末,快门速度和乳剂足以捕捉到疾驰的骏马,并使快照成为现实。
拉蒂格痴迷于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不忍时光白白流逝。猫纵身一跃;毫无防备的人冲下山坡;挑战失重:抛球、滑下楼梯、跳墙。他将那些流光瞬息凝固成了永恒:猫腾空而起;一架失控的滑翔机离开地面;身着长裙的女人在沙滩上奔跑,她的面纱和外衣随风舞动。拉蒂格享受这摄影背离万有引力定律的神奇瞬间。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正确的家庭与时代:1902年,他的父亲购买了一辆电动汽车,并在接下来几年间买了更迅疾的汽车,他热切关注赛车和早期的飞行尝试。在近代,没有任何一个男孩能抵挡住汽车和飞机的魅力,但在拉蒂格出生的那个年代,科技已经开始改变一切。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的巴黎博物馆让年幼的拉蒂格感受到了这场革命的浩大。尽管如此,他仍指出:“这些复杂的事物于我而言索然无味。”那一年,法国人庞阿尔(Panhard)以平均时速为62公里从巴黎开往里昂,赢得了第一届国际汽车锦标赛。同年,柯达(Kodak)推出了布朗尼(Brownie),即使是不如拉蒂格般专注的孩子亦会使用这种小型相机。仅仅三年后,威尔伯·赖特(Wilbur Wright)驾驶一架飞机在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小鹰号沙丘的上空飞行了五十九秒钟。
这个世界在永无止境地运动。无论是出于异想天开抑或是自视过高,拉蒂格的每一次奔跑试验,悉使用轮子或是翅膀以追求跑得更快、更远、更高。1912年,当他拍摄在A.C.F.格拉纳大奖赛(A.C.F.Grana Prix)中的德拉奇汽车(Delage Automobile)时,所有的事物都在移动:他焦平面快门上的一条窄缝同窗帘一般快速穿过成像平面,因此场景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晚了零点几秒。画面中的观众似乎在倾斜,车轮亦变了形。拍摄另一辆赛车时,拉蒂格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那就是在移动自己的同时保持相机不动:“我拍摄它[每小时行驶18公里]时,稍微旋转一圈,以保持它在视野中。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去做。”
大地飞驰而过,机械装置侵入曾经熟悉的天空;男孩激动地拍下这一瞬间。一对夫妇推着婴儿车带他们的孩子去户外散步,然而一切正在悄然生变:一架飞机在距离地面很低的地方盘旋,破坏了这一场景,与此同时,在地面的上空,另一架飞机划过天空。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拉蒂格对他那个时代怪异而复杂的事物有着独特的想法:女人头上戴着的饰品可能是奢侈的甜点和不能飞行的翅膀;外星人的建筑物或许是巨大的风筝;滑翔机和飞机像是用来捕捉空气的奇特而精致的笼子。
他要么是真正理解,要么就是他足够幸运能够拍到并且没有删掉,那些走路时奇怪的人影,以及那些因没有拍摄及时而虚焦的眼睛轮廓。他亦能描绘出重叠的图形所产生的更为复杂的轮廓,甚至更不可思议的人与物之间模糊的无形形状。
届时,他的相机会记录下意外闯入场景的人物、船只或树木,并通过呼应、反转、颠覆或合成对前景的那些轮廓做出妙趣横生的照应。简而言之,拉蒂格拥有一种特殊的摄影视觉,这种视觉不时会在作品中展现,但没明确地提出来,亦没正式地成为一种个人风格。
这样的风格意味着对瞬间的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的高度重视;拉蒂格同孩童般幸灾乐祸的视角以及新世纪的科技创新将这一点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汽车和飞机以外的日常生活中,瞬间通常表示不经意、无意识、不能观察到的[或至少是未被观察到的]动作、表情或关系——在公开场合的动作之间发生的不可倏忽的事件。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画家们已经开始把这样的瞬间事件放在画布上,作为他们激进的尝试的一部分,以所有不规则和随意的形式描绘当代生活。马奈(Manet)对其十分敏锐;德加(Degas)将其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这两位画家追求艺术品质的过程中,摄影影响了他们,并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种机械媒介。
摄影师无意之中发现的人类以前未探索过的领域,抑或是人们相遇时产生交叠时所产生的图像,会被认为是科学发现或是摄影的“错误”,但不会是任何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事实上,在35mm相机问世之前,由两顶的遮阳伞形成的尖形、放大的人脸或人物的裁剪、人与人之间精心勾勒的空间所形成的摄影图像,并不称为艺术。
然而这种风格早在拉蒂格的创作初期业已形成,主要呈现在一些早期的街头摄影之中,与此同时,因为相机的发展,业余摄影的范围不断扩大。当拉蒂格开始摄影创作的时候,他还尚且年轻,除了他父亲的照片和一些书中的插图以外,他并不知道艺术影像,他所表达的只是当时一种很小众的风格。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受家庭和时代的影响,拉蒂格以极端的热情或是歧视来记录戏谑、刺激、悬疑与荒谬。他在各个方面都异常专注,比同龄的任何人都更具慧眼。这个时代提供拉蒂格以大量的发明,包括配有快速镜头的照相机,他回应以孩子般的热情和成年人的视角。
实际上,他是摄影异类:神童。尽管愈来愈多的孩子能在学校里接受摄影的教育并拍出好照片,但很难再出现一个像拉蒂格般的同龄人能够拍出如此出色的照片来。他在选题材上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仅仅是幸运并不足以支撑这样一部作品。吸引我们的部分可能是那个小男孩的精神世界,因为他在这样一个充满刺激游戏和发现的世界中成长。摄影通常依赖于人的感知力、鉴赏力和微妙的判断力,而这些通常不会认为能够出现在如此年轻的人身上。
拉蒂格的所有感官都特别活跃,视觉和听觉更为尤甚——“我想捕捉的并不是某些想法,而是我幸福的场景!”他个子矮小,体弱多病,因此有大量时间来培养和锻炼他的判断力、绘画技巧。以及敏锐的观察力。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他很早就把视野转向女性与女性饰品。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从八岁开始描绘佩戴帽子和戒指的女人,十二岁至十四岁,沉醉于去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to)寻找“埃勒(Elle)”。“埃勒”是一位虚构的,非常时尚、幽默与美丽的女士。尽管有时候她的身边会有位绅士对他发怒,但仍会拍下她的照片。
另一个让他那嗷嗷待哺的相机大饱眼福的奇观:从他镜头前走过的女人们光彩夺目、自我展示、精心打扮,如同热带鸟类一样充满异国情调。拉蒂格注意到有些涂抹了口红的人,好似在舞台上那般光彩照人,这标志着这个时代女性魅力观念的改变。如若人们觉得需要保护自己免遭摄影之害,这又是时代的另一个标志: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来,当自动相机使得户外摄影变得更简单时,女人[和一些男人]就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大批量的业余摄影爱好者的荼毒。
拉蒂格捕捉到了身着高跟鞋和泳裙的女性之间所有的细微差别:同建筑物一般大小的帽子,带褶的三角巾,刘海儿,精致讲究的狗,以及适合调情的女性身材。至少有两次,他捕捉到了那些自以为没有被注意到的人对那些展示者投以赞赏和猜测的目光。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他同女人一样喜欢这些衣着,以及那些让女人变美丽的策略。虽然拉蒂格既不知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自己出版了什么照片,但可以称拉蒂格为第一位时尚摄影师 [直至1914年,《Vogue》才雇佣了第一位专职摄影师,阿道夫·德·迈耶(Adolph de Meyer)]。塞席尔·比顿(Cecil Beaton)借鉴了《马车日,1911年6月23日》[1911年6月23日,巴黎奥特伊尔(Auteuil)赛马会的马车日]后,拉蒂格先前不为人知的照片最终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这是部关于电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中臀部和条纹的狂想曲。15[拉蒂格在法国曾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画家,他的摄影作品被人们偶然间发现后,于1963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由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展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拉蒂格就退出了他那个时代[在他漫长的余生中,他一直置身于历史之外]。16由于体重过轻,不能在军队服役,他被分配到巴黎各地担任司机。他很少拍摄战争与看到的丑恶情节。他的日记几乎不提:“战争还在继续。朋友去世。祈祷能有个好天气。我的第一个情妇[最令人向往的巴黎女人]。”
他向一些评论解释道,他的退出是自发的。他在1907年重新开始记录日记中把他的幸福归因于扬弃不好的记忆和美化美好事物的习惯。如今他写道:“如果这本“日记”没有提到战争,首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日记”。它是我保存的快乐或是幸福,我的幸福充满了难以言说的东西。同时它也是一种保护机制,以防止‘过度的快乐’。”当世界战争爆发时,他悉心呵护自己的幸福,避免陷入悲痛而无法自拔的境地。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1919年,拉蒂格娶了作曲家安德烈·梅塞尔(André Messager)的女儿比比·梅塞尔(Bibi Messager),开启了并不富裕的百万富翁生活。为妻子和花卉作画;在里维埃拉、巴黎和伦敦四处滑翔;每晚去剧院看他的朋友萨夏·吉特里(Sacha Guitry)和伊薇特·普兰当(Yvonne Printemps)的表演;拍摄妻子、赛马、阳光和大海——一种真正美好的生活。他创造了一种生活艺术。
在欧洲马其诺线以东的某个地方丧失了希望,幻灭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拉蒂格仍致力于记录自己的存在,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存在。汽车和自行车比赛仍在吸引着他,而科技的发展还是没有。他有一个儿子和女儿,都在刚出生不久过世。比比和他离婚后,嫁给了另一个男人;他也随即娶了第二任妻子,这个女人法西斯主义,并且患有抑郁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以设计晚会为生,有过短暂的第二次婚姻和稳定的第三次婚姻。但他始终坚定地将目光集中于人间快乐的花园。
当他还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摄影构图,现在变得愈加老练。他用科卡普一耐特勒(Klapp-Nettel)双镜头立体相机拍摄了两张6×6厘米的照片,可以转换成单镜头格式的一张6×13厘米的照片。拉蒂格利用这细长的框架,平衡了不稳定的并置、不间断的海浪和坐在机翼上的神秘人物。
他把相机举到离赛车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如此彻底破坏了比例,以至于远处的观众可能从另一个空间误入。他的身影在来袭的波浪前奔跑,在黑暗中被与他毫无联系的庞然大物所遮蔽。拉蒂格早期画作中,人物之间的生动关系已开始破裂,规范的空间时不时被破坏。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 Jacques Henri Lartigue
一些画面中残留着淡淡的忧郁:他深爱过的比比站在一个似乎在膨胀的物体旁边而显得渺小;她的身影在寂静的城市中孤独而无助;她与他的母亲站在广阔而空旷的大海前的露台上。
那些拉蒂格选择遗忘的生活越来越困扰着他。“我对自己的自私感到恐惧。我的内心有一个旁观者,他不关心具体的事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严肃的、悲伤的、重要的、有趣的或是不重要的。他是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只是为了享受这一奇观。他是一个观众,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木偶人,甚至——尤其是——我!”
本世纪前十年拍摄的几幅照片,拉蒂格正好在观察者所处的位置,聚焦于一个孤独的背影,就好像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看着大海猛烈地拍打着岩石或墙壁。这是一个浪漫的主题:人类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相抗衡。这也是在绘画中反复探索的形象,比如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1809海边的和尚》(1890 Monk by the sea)。
年幼的拉蒂格已在担心成长会有代价:“突然发现作为一个小人物来面对事物的真相是多么无助,那是‘成长’吗?”。他这一生都是旁观者,而我们是受益者。他试图一直保持孩童状态,他的精神做到了,不过时间并没有——当然,照片亦做到了。
作者
维姬·戈德堡(Vicki Goldberg)是西方摄影评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以富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文章著称。《光影的要义》(Light Matters)首版于2005年,该书收集了作家写作生涯以来的诸多优秀散文和评论。
译者
南艺翻译小组是由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曹昆萍副教授率领摄影专业在读硕士生组成的翻译团队,作为一个翻译团体,我们希望通过对《光影的要义》这本书的译介为广大影像爱好者与研究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机会,并以此作为一个起点,期待在今后不断地学习与完善的过程中,为大家译介更好的影像读本。由于这是南艺翻译小组成立以来译介的第一本书,在翻译实践中有不少译文在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方面或许还存在一些瑕疵或疏漏,在此敬请广大读者及时发现并给予指正。
原标题:《神童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