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桀骜难驯之邦:西方世界在阿富汗的灾难性纠葛
“历史开始重演”
驻贾拉拉巴德随军牧师——G.R.格莱格牧师1843年自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杀戮场归来后不久就写了一部回忆录。他写道:“发动这场战争的目标并不明智,战争进程中鲁莽与慑怯匪夷所思地缠夹不清,英方蒙灾受难后罢战息兵。对于指挥作战的政府抑或参战的主力部队而言,没有多少荣耀加身。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英方都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我们最终撤离该国,无异于败军溃退。”

描绘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油画《残兵败将》(Remnants of an Army),1879。画中人为威廉·布莱登,自喀布尔撤退的英军的唯一生还者。
威廉·巴恩斯·沃伦(William Barnes Wollen)闻名遐迩的画作《第44步兵团的背水一战》(Last Stand of the 44th Foot)描绘的是随着普什图部落民步步逼近,甘达玛克山丘顶上的一群衣衫褴褛却顽强不屈的军人在一排稀疏的刺刀后站成一圈。这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形象之一。与之齐名的有巴特勒夫人(Lady Butler)的油画《残兵败将》(Remnants of an Army),描绘出所谓的最后幸存者布赖登医生,骑着行将倒地的驽马到达贾拉拉巴德城垣前的情景。

《第44步兵团的背水一战》(Last Stand at Gandamak)
2006年冬,正值西方列强对阿富汗的最新武装入侵的形势渐趋恶化之际,我萌生了撰写一部新史书的念头,旨在讲述不列颠意图掌控阿富汗的首次失败尝试。轻易征服异邦、成功扶植亲西方的傀儡统治者之后,傀儡政权面临日益广泛的抵抗。历史开始重演。
在前期调研工作中,我参访了与这场战争相关的许多地方。……越是近观细察,就越发觉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新殖民主义的轻举冒进似乎清晰重现了西方世界在阿富汗的初次灾难性纠葛。1839年的战争是根据经篡改的情报发动的,情报论及的威胁事实上并不存在。有关俄国使臣只身前往喀布尔的消息,被一群野心勃勃、受意识形态驱使的鹰派人物夸大并操纵,在这件事上,造成对捕风捉影的俄国入侵的恐慌。正如恐俄的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尔1838年自德黑兰所写:“我们应当声明,不与我们为伍便是与我们为敌……我们必须保卫阿富汗。”由此引发一场徒劳无益、代价高昂、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
我渐渐意识到,这两次武装入侵的大同小异并非只是逸话趣谈,而是凿凿有据的事实。170年后,在新的旗帜、新的意识形态以及新的政治傀儡操纵者的幌子下,相同的部族抗争和诸多战役继续在同样的地方展开,敌对双方斗个你死我活。相同的城市由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外国士兵驻守,遭受来自同一片绵绵丘陵和高海拔山口的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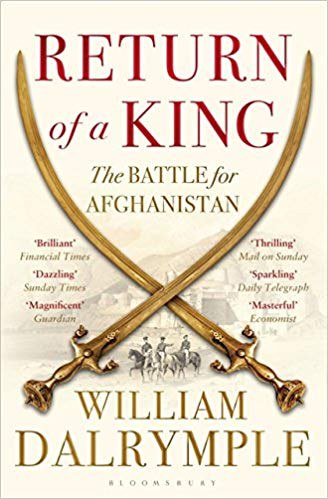
本文作者出版于2014年的 Return of a King: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
在这两起事件中,侵略者都认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入侵,实现政权更迭,而后会在两三年内全身而退。在两起事件里,他们均未能避免自己卷入更广泛的冲突。英国人无力应对1841年爆发的起义,不仅由于英国阵营内部领导失败,而且是麦克诺滕与沙·苏贾之间战略关系破裂的产物。如出一辙的是,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领导层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一直是最近兵戈扰攘、局势失控的关键诱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阿富汗扮演着麦克诺滕的角色。2010年我参访喀布尔时,当时的英国特别代表谢拉德·考珀科尔斯爵士评述称,霍尔布鲁克是“一头蛮牛,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的瓷器店带到哪儿”。这段描述完全可以用来概括174年前麦克诺滕的作风。谢拉德在回忆录《来自喀布尔的电报》(Cables from Kabul)中,对当前占领失败的原因做出分析,读起来惊人地类似于解析奥克兰和麦克诺滕缘何折戟沉沙。“对于如何抽身而出没有任何实际想法就搅和进来;几乎蓄意误判挑战的性质;频繁更换目标,没有环环相扣、协调一致的计划;大规模任务蠕变;政治与军事指挥不统一,各执己见、一盘散沙;劳师袭远的军事行动的关键阶段,将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另一场战争(当前情形下是伊拉克战争,当年是鸦片战争);本地盟友选择不当;软弱的政治领导层。”
过去和现在一样,阿富汗的贫瘠不毛就意味着不可能向阿富汗人征税,以资助占领者的侵占行动。在如此难以抵达的领地维持治安代价高昂,反倒耗尽占领国的资源。现今,美国每年在阿富汗的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在赫尔曼德省的两个辖区保留海军陆战营的开支,比美国给埃及全国提供军事和发展援助的费用还要高。在这两起事件中,定夺撤兵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几乎与阿富汗无关,换句话说,取决于侵略国本土的经济状况和变幻莫测的政局。
随着我的调研工作继续进行,令人着迷的是,看到当今社论专栏中唇枪舌剑热议的同一类道德问题,如何在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来往书函中以同等篇幅加以讨论。何为占领国的伦理责任?正如一名英国官员1840年所述,是应当殚精竭虑“为人类谋福利”,拥护社会革新和性别变革,取缔诸如以石击毙通奸妇人一类的陈规陋习,还是应当心无旁骛地坐稳江山,莫无风生浪?倘若盟友开始生烤活煮仇敌,是否予以干涉?是否尝试推行西方政治制度?正如间谍组织首脑克劳德·韦德爵士于1839年武装入侵前夕的警告所言:“我认为最为可怕并需有所警惕的莫过于妄自尊大。我们如此目中无人,往往习以为常地将自己的制度习俗视为佼佼不群,一心想把它们引入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如此干涉即便未促其诉诸暴力,也总会引发激烈争议。”
对现今身处阿富汗的西方人来说,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灭顶之灾提供了令人忐忑不安的先例。绝非偶然的是,驻喀布尔的外国通讯员最喜爱的酒舍叫作甘达玛克小屋(Gandamak Lodge),阿富汗南部的一座主要英军基地依照第44步兵团背水一战的唯一幸存者的名字被命名为苏特营(Camp Souter)。
与之相反,对阿富汗人而言,1842年挫败英国人已成为从外国侵略中获得解放的象征,标志着阿富汗人拒绝再一次被任何外国列强奴役的坚定意志。毕竟,喀布尔使馆区仍以维齐尔阿克巴·汗的名字命名。如今在巴拉克扎伊的民族主义宣传中,阿克巴·汗作为1841-1842年首屈一指的阿富汗自由斗士而被世人铭记。

阿克巴尔·汗(Akbar Khan)
这段历史的种种细节让阿富汗人对外国统治深恶痛绝,西方国家的人们或许早已忘记,阿富汗人却刻骨崩心、千古不忘。具体说来,在阿富汗,沙·苏贾依旧是通敌叛国的象征。2001年塔利班诘问手下青年:“你们想作为沙·苏贾的后人遗臭万年,还是想作为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子孙流芳百世?”奥马尔毛拉上台掌权时刻意效法多斯特·穆哈迈德,像多斯特·穆哈迈德一样,他从坎大哈圣祠取来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圣斗篷披裹在自己身上,宣称将师法自己的楷模“信士的领袖”。此举有意直接重现第一次英阿战争中的诸事件,全体阿富汗人即刻了悟其中的特殊寓意。
历史绝不会毫厘不差地重现……然而,由于该地区在地形概貌、经济状况、宗教抱负及社会结构上具有延续性,170年前的败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的确仍是不容忽视的前车之鉴。从1842年英国人犯下的错误中汲取一些教训为时未晚;如若不然,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第四次战争看来无疑会未果而终。鲜有政治收益不说,结局必将与前三次毫无二致:蒙羞溃败后狼狈撤兵,又一次让阿富汗陷入兵荒马乱的部族纷争,阿富汗很可能再由同一个政府统治,而这场战争原本是为了推翻该政府而战。
30年后,不列颠行将稀里糊涂陷入第二次英阿战争之际,就像乔治·劳伦斯致函伦敦《泰晤士报》所言:“冉冉升起的新一代非但没有从悲壮的覆舟之戒中受益,反而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让我们卷入那动荡不幸的国度的纷乱事务中……即使有可能避免军事灾难,但现在大军推进,无论从军事角度来看何等成功,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上的徒劳无功……撤离喀布尔蒙受的无妄之灾,应永远作为对未来政治家的一种警示——警告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切莫再贸然实施1839-1842年结出那般苦果的政策。”

第一次英阿战争的入侵和撤退路线

1842年从喀布尔撤退的路线
来自阿富汗的史料提供了一面镜子
尽管这一地区具有核心战略意义,但是论及阿富汗历史的好作品出乎意料地寥寥无几。存世的文章无不采用印刷的英文报告,抑或遭严重歪曲的伦敦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Archives)。虽然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故事已被讲述多次,叙事方式涵盖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三卷本史书以及弗莱什曼的滑稽动作等多种形式,但是已出版的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几乎没有采用19世纪早期阿富汗方面的同期原始史料,未呈现被侵略占领的阿富汗方面的记事,亦未使用反殖民主义的阿富汗抵抗组织的记载,甚至在最专业的学术刊物中也几无可寻。
第一次英阿战争是一场独树一帜、记载翔实的冲突。书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使用了来自诸条战线各个方面的种种新的原始资料。过去数年间,伦敦周围各郡(Home Counties)阁楼箱子里数以百计的破破烂烂的信札和血迹斑斑的日记现身于世,它们属于参与那场战争的英国人。我在林林总总的家族收藏品、切尔西国家陆军博物馆以及大英图书馆中查阅到这些新素材。
在德里的过去四年间,我彻底查阅了印度国家档案馆(Indian National Archives)馆藏的车载斗量的1839-1842年占领时期的卷宗,这些材料几乎囊括所有往来信函、备忘录和手写批注,论及奥克兰勋爵治下加尔各答行政部门和其麾下军队提出的问题。其中的亮点有:发现先前未公开的亚历山大·伯恩斯的若干封私人信件,伯恩斯是这段史话中英方的一个主要角色;对英军种种暴行展开的调查,读起来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版本的维基解密;一些非常感人的受审讯的印度兵在军事法庭上的庭审记录,这些印度兵曾沦为奴隶,设法脱逃并最终成功返回所属诸团,接着就面临擅离职守的指控。
印度国家档案馆还藏有之前未经引用、未作翻译的波斯语战争记事《喀布尔和坎大哈的战斗》,作者是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这位还乡的波斯秘书曾在卷入那场战争的一位英国官员手下当差。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称,着手展开撰写19世纪50年代初那段历史的计划,“希望排遣暮年的孤寂,教导身处这个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的子子孙孙”。不过他补充道:“那些事件现在看似与印度斯坦特别有关联。”字里行间之意,可被当作隐讳号召在印度掀起反抗东印度公司的起义。这样一场起义的确在1857年继之而来,首先爆发于1842年撤离喀布尔期间遭英国军官离弃的印度兵所在诸团。
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旁遮普档案馆(Punjab Archives),我挖掘出几乎未被使用的克劳德·韦德爵士的案卷。克劳德·韦德是“大博弈”的首位间谍组织首脑,1835年在他的监管下创建了西北边境代表处(North West Frontier Agency)。在旁遮普档案馆能找到韦德的“情报员”网络的所有报告,这些情报员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旁遮普地区、喜马拉雅山脉,越过兴都库什山区远至布哈拉。旁遮普档案馆还藏有涉及沙·苏贾在卢迪亚纳的流亡生活以及他千方百计返回喀布尔重祚的所有往来信札。
在俄国方面的史料中,我设法获取了打印的佩罗夫斯基伯爵及其门徒伊万·维特科维奇的案卷。佩罗夫斯基伯爵是沙皇时代与韦德差堪比拟的人物。此前外界一直臆测,维特科维奇在圣彼得堡旅舍房间内举枪自戕前,销毁了所持的文件资料。但事实证明,仍有一些情报报告留存了下来,其中包括论及伯恩斯的书面报告、揭示布哈拉的整个英国谍报网的报告。这些报告在本书中首次呈现。
然而,真正的突破是该时期包罗万象的阿富汗史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喀布尔。2009年,我在阿富汗国家档案馆展开调研工作时,借宿于罗里·斯图尔特的泥堡。泥堡在遭焚毁的寇松时代英国大使馆的废墟附近。档案馆位于喀布尔市中心一座19世纪奥斯曼风格的宫殿中,这座瑰丽的宫殿出奇地完好无损。结果令人沮丧,档案馆鲜有沙·苏贾和多斯特·穆哈迈德时代的资料。但就是在那儿东翻西找的时候,我与加旺·希尔·拉西赫——这位阿富汗青年历史学家是富布莱特学者——成为朋友。一日午餐时间,加旺·希尔带我去见一位二手书商,书商在老城区的朱伊希尔租了个看起来风雨飘摇的摊位。结果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阿富汗显达家族移居国外时,这名书商曾大量买进名门望族的私人藏书。不到一小时,我就成功购得八卷先前未使用过的第一次英阿战争同期波斯语史料,它们全都是在英国战败期或战后余波期写于阿富汗的,不过有些史料刊载于印度的波斯语出版物,于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酝酿阶段供本国印度人阅读。

阿富汗国家档案馆
这些史料包括两部隽绝的英雄史诗: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的《阿克巴本记》和穆罕默德·古拉姆·科希斯坦·古拉姆(Mohammad Ghulam Kohistani Ghulami)的《战地书》。两部史诗读起来就像阿富汗版本的《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是在19世纪40年代仿效古波斯菲尔多西(Ferdowsi)的《列王纪》(Shahnameh),用堂皇铿锵的波斯语写成,以歌颂阿富汗抵抗组织诸领袖。当年献给胜利的诗歌或许比比皆是,最后遗存下来的似乎只有这些史诗。大部分诗歌经歌者和吟游诗人代代口耳相传。毕竟,对阿富汗人而言,战胜英国人几乎奇迹般地拯救了自己的祖国,那既是他们的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又是他们的滑铁卢战役,还是他们的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
1951年,《战地书》为人所知的唯一誊抄本在帕尔旺省现身——被誊写于东印度公司纸张上,缺少扉页和尾页,显然是从英国驻恰里卡尔指挥部被抢掠而来的。该书聚焦于科希斯坦抵抗组织首领米尔·马斯吉迪的事迹。尽人皆知,这位纳克什班迪教团的苏菲派导师一直在起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份手稿提到他是抵抗组织核心人物。《阿克巴本记》也于1951年重新露面,这次是在白沙瓦。与前书形成对比的是,该书赞颂了维齐尔阿克巴·汗。克什米尔毛拉写道:“在本书中,就像鲁斯坦大帝(Rustam the Great,菲尔多西的波斯史诗《列王纪》中人物)一样,阿克巴的赫赫英名将千秋不朽、万古流芳。这部史诗现已完结,它将在世界各国流传,为伟人的集会增光添彩;它将从喀布尔云游至每一场聚会,犹如春风拂过一座座花园。”
《编年史》立足于阿富汗西部与波斯交界的赫拉特,滞后一步地概观了这场起义。19世纪末的两部史书《苏丹传记》和《历史之光》则是讲述阿富汗列王的官方宫廷史,从多斯特·穆哈迈德继任者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一位主要的抵抗组织首领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残存波斯语信札,在塔利班大肆抢掠前一直留存于喀布尔的国家博物馆。不久前,这些书信由其后裔付梓,名为《独一无二的勇士、赤胆忠心的首席侍从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复仇》(Paadash-e-Khidmatguzaari-ye-Saadiqaane Ghazi Nayab Aminullah Khan Logari)。
义愤填膺、怒火难平的阿塔·穆哈迈德王子著有《战斗之歌》。作为来自希卡布尔县(现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当时名义上归属喀布尔统辖)的卑官下吏,阿塔王子以独特的视角鞭辟入里地讲述了战争故事。他最初在沙·苏贾手下当差,但后来逐渐对主公依赖异教徒支持的举动大失所望,在书中对抵抗组织表露出越来越多的同情。阿塔王子的波斯语因袭了华丽迂腐的莫卧儿风格,不过相比那一时期其他任何作家,他的措辞最为机智明快。这部著作对英国人的失败大放厥词,更不乏恶言怨语,但出人意料的是,竟有可能是受希卡布尔县首位英格兰收藏家爱华德·巴克豪斯·伊斯特威克(E.B.Eastwick)之托撰写。阿塔王子在序言中颇为忐忑地寄语资助人,恳恳悱悱写道:“恰如俗语所云,‘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尽管力求用千般婉言、万般讳语道出诸事件的是非功过,但仍要祈祷切莫冒犯那些君临天下、坐拥江山的人们。”他补充道:“不管怎样,这个不忠不信的尘世,千载有如白驹过隙,苦乐悲喜皆是过眼云烟。‘世事如梦,不管如何在心头描绘,一切终将伴你而去。’”
所有史料中最具启发性的大概是合乎沙·苏贾本人心意的回忆录《沙·苏贾实录》。这部内容颇为丰富的回忆录为他战前流亡卢迪亚纳时撰写,1842年苏贾遇刺后由一名臣子更新相关内容。苏贾在序言中开宗明义:“聪明睿达的学者皆知,杰出的帝王一一记载当政时期的重大事件。一些天赋异禀的人亲自书写,大多数人则交由史官和文人撰写。随着时光流转,著作得以在历史长卷中留下永恒不朽的印记。是故,苏丹苏贾·乌尔木尔克·沙·杜兰尼(Sultan Shuja al-Mulk Shah Durrani),仁慈真主朝堂上的这位谦卑祈请者萌生此想法,记载在位期间的战役和大事件,俾使呼罗珊(Khurasan)的历史学者知悉这些事件的真实始末,善于思辨的读者亦能由这些先例鉴往知来。”在这部回忆录中,我们得以对阿富汗方面的首要局中人的期望和忧惧有所了解,这是对文献资料至关重要的补充。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些原始资料大都为讲达里语的阿富汗历史学家所熟知,他们将这些史料运用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撰写的弥漫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达里语史书中,但此类记载似乎未被用于任何用英语写就的战争史,在英语译本中也完全没有现成可用的素材,尽管从《沙·苏贾实录》中摘译的若干篇章确曾登载于19世纪40年代加尔各答的一本杂志上。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目前正在筹备《历史之光》全译本,他慷慨地任我使用手头资料。
这些丰富翔实的阿富汗史料告诉我们许多欧洲方面的史料疏于提及或不知情的事。譬如,英国方面史料谈及己方军队不同派系时消息灵通,然而阿富汗一方亦由不同叛乱团体组成,英方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对分裂这些团体的紧张局势浑然不觉。阿富汗方面的史料有清晰记载,称阿富汗抵抗组织实则四分五裂、离心离德,不同指挥官旗下的不同团体在不同地点安营扎寨,通常只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协同合作。此外,相互竞争的诸团体目标不同,为一己私利还会不断改弦易辙、更换盟友。令人尤感意外的是,起初偌多叛乱者希望沙·苏贾留任国王,他们只想将苏贾的英国靠山赶出去。英军起程踏上不归路,在库尔德喀布尔山口全军尽没,同一批亲保皇派武装力量中的勤王者立即就复归沙·苏贾旗下。正如20世纪80年代苏联军队撤离后,谁都没料到,苏联扶植的傀儡纳吉布拉(Najibullah)能苟延残喘那么久。因此,若不是大逆不忠的教子妒火中烧并在一怒之下刺杀了他,沙·苏贾或许能长时间在阿富汗称王。
相较英国方面的史料记载,阿富汗史料中抵抗组织的剧中人略有不同。米尔·马斯吉迪及旗下科希斯坦人,阿米努拉·汗及麾下洛伽尔人,均比英国方面史料乃至稍晚的阿富汗方面的记载卓尔不凡得多。后期史料受巴拉克扎伊族人赞助撰写,着意强调获胜王朝在起义中起到的核心作用,这种说法实则仅对革命的最后阶段而言是成立的。
更重要的是,多亏有阿富汗方面的史料,阿富汗抵抗组织众领袖丰满的形象才一下子得以跃然眼前,他们才成了有着多彩感情生活和个人动机观点的活生生的人。而英国方面的史料所呈现的只是一道由奸诈的大胡子“盲信者”和“狂热分子”堆砌成的毫无差别的人墙。幸亏有这些新资料,现在才有可能从个体角度理解,缘何许多忠诚拥护沙·苏贾的阿富汗首领会选择奋不顾身拿起武器,与貌似所向披靡的东印度公司军队兵戎相见;德高望重的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受到一名英军基层军官凌辱,因拒绝向王国政府缴纳有所增加的赋税而失去领地;年轻气盛的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的情妇被亚历山大·伯恩斯勾引,试图寻回她时遭嘲弄;米尔·马斯吉迪正打算向朝廷自首时,英国人袭击其城堡、残杀其家人,此举有悖双方达成的所有共识,其城堡随后被攻占并变成英国地方政府办公中心,其领地遭仇敌瓜分。众人之中最着笔墨、被细针密缕加以描绘的当属老谋深算、性格复杂的人物阿克巴·汗。他喜爱希腊化的犍陀罗雕刻,想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在喀布尔被看作抵抗组织领袖中最具锋芒的一位。《阿克巴本记》甚至还绘声绘色讲述他洞房花烛、鱼水相欢的情景。英国方面的史料以夸张讽刺手法描绘的这位“揣奸把猾的穆斯林”,在我们眼前一跃成为阿富汗的万人迷。
阿富汗方面的史料还向我们呈现出一面镜子,用亚历山大·伯恩斯的堂兄弟拉比·彭斯的话说,就是让我们能够“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依照阿富汗咏史诗人的描述,伯恩斯远非西方史料所载的浪漫探险家,而是一个魅力超凡的欺诈者、阿谀奉承与背信弃义的能手、腐蚀喀布尔达官显贵心灵的魔鬼。“外表好似谦谦君子,内心暗藏恶魔”,一名贵族如是告知多斯特·穆哈迈德。在阿富汗人看来,西方军队以丧尽天良、匮乏骑士精神的基本价值观,尤其以对平民伤亡漠不关心著称。在《阿克巴本记》中,多斯特·穆哈迈德警告阿克巴·汗,称:
因睚眦必报
他们的毒燎虐焰会让屋宇墙垣深陷火海
他们借此耀武扬威
震慑斗胆反抗之人
日以为常这般降伏苍生
便无人分庭抗礼
此外,阿富汗方面的史料一致抱怨的是英国人不尊重女性,所到之处强奸凌辱事件频发,“不舍昼夜地乘着欲望的骐骥恣意驰骋”。换句话说,在阿富汗方面的史料中,英国人被描述成诡诈多端、暴虐无道、蹂躏女性的恐怖分子。料想不到阿富汗人竟以这种方式看待我们。
阿富汗方面所有史料的焦点是谜一般的人物沙·苏贾。透过苏贾本人及其拥护者的描绘,浮现出的是一个八面莹澈、聪明绝顶、将往昔帖木儿帝国诸君主奉为楷模的人。《沙·苏贾实录》中的自我描述,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得到证实,称他展露出勇敢决绝、不屈不挠的气魄,经受住命运的千锤百炼。这般描画与遭自高自大的英国行政官员废弃的堕落懦夫形象判若天渊,英国官员起初辅佐这位杜兰尼帝国继承人重祚,而后设法将其边缘化,这也与经巴拉克扎伊族人170年宣传灌输后,在现代阿富汗被妖魔化的卑怯卖国贼形象大相径庭。苏贾在自己周围营造出极其知书知礼的波斯化天地,没有迹象显示沙到底懂不懂普什图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曾用普什图语写作。就像昔日的莫卧儿人一样,贵为天子的沙·苏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为帖木儿帝国的末代国王,他在许多方面脱颖而出——他治国施政时,阿富汗仍处于伊朗、中亚、中国及印度斯坦的十字路口上,而非后来的穷山恶水荒蛮之境。
追溯起来,沙·苏贾当政标志着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开始。尽管有许多代价高昂的失败,但第一次英阿战争仍产生了持久的重大影响。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设定出一道稳固的边界。几年之内,英国人就吞并了锡克教团盘踞的旁遮普地区以及早先由信德诸埃米尔掌控的印度河下游领地。不过,有前辙可鉴的英国人心中有数,白沙瓦是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
对阿富汗人而言,这场战争永远改变了自己的国家。多斯特·穆哈迈德复归后承袭英国人实施的改革,这些变革有助于巩固阿富汗的统一,使该国较战前有了愈发明确的界定。确切说来,苏贾及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从不使用“阿富汗”这个字眼——对苏贾来说,有一个喀布尔王国,它是破碎的杜兰尼帝国硕果仅存的部分,处在所称的“呼罗珊”地理空间边缘。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阿富汗”的说法就被广泛标识在国内外的地图上,那一地理空间内的民众也渐渐开始将自己称为阿富汗人。沙·苏贾的归来,以及旨在令他复政厥辟而发动的殖民远征告败,最终摧毁了萨多扎伊王朝的势力,终结了由萨多扎伊族人创建的杜兰尼帝国的最后追忆。第一次英阿战争以这种方式,对界定现代阿富汗国界立下汗马功劳,一劳永逸地强化了存在一个名为“阿富汗”的国家之理念。
如果说第一次英阿战争有助于巩固阿富汗这个国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前西方的干涉会否促其消亡。撰写本书之际,西方部队再次随时准备弃阿富汗于不顾,将之交由普帕扎伊族人执政的软弱政府掌控。无法预知该政权的命运,亦不可能预言阿富汗会否陷入支离破碎、分崩离析的状态。不过,阿塔王子于1842年战后写下的一段话,现仍确切不移:“毋庸置疑的是,侵略或统治呼罗珊王国绝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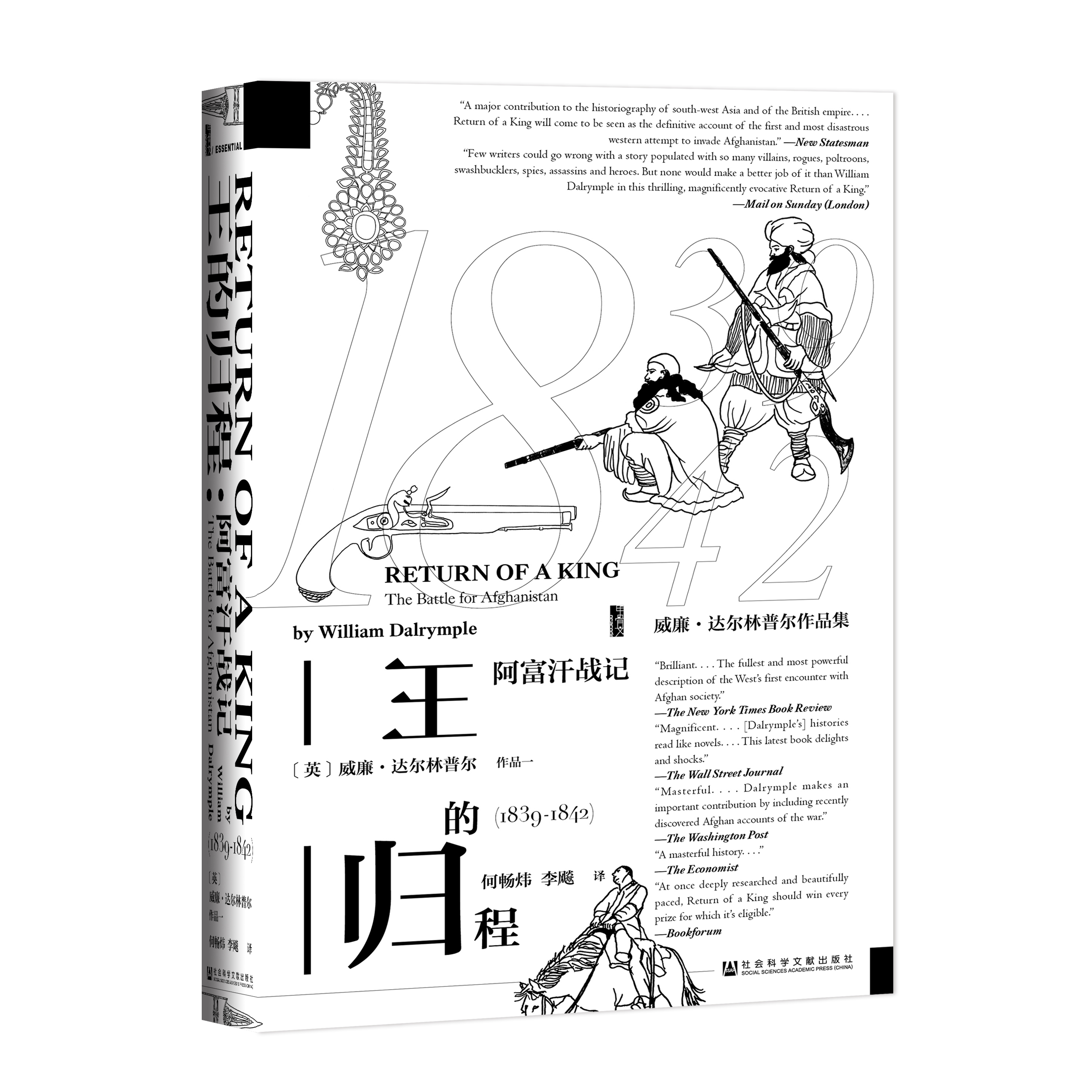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英]威廉·达尔林普尔著,何畅炜、李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