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为何错失收回香港的历史机遇
1997年前后,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历届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努力多有思考,问题意识多纠结于一个命题:太平洋战争期间和战后数年,历史似乎留给国民政府一个契机,但最终结果是这个政权错失良机,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并未有多少进展。
那么,国民党是如何与收回香港的功绩“失之交臂”?尽管这个命题多少带有些历史研究者“后见之明”的意味,但也并非一个伪命题。历史发展的轨迹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呈现出多重的可能性,殖民统治的终结已是世界潮流明确的指向,中英之间在香港问题上可选择的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
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学界一般着落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强调国家实力,彼时中国虽位列“四强”,却名实难副,于香港问题难有作为。二是批判政权属性,即国民党反共亲英美的政治立场决定其不可能采取强硬态度,自然不会不惜与英国闹翻以争取港九主权。三是检讨时局限定,内战烽火迭起,国民党面临全局崩溃已无暇自顾,遑论外交得失。客观来说,上述观点均有一定见地,当然,历史往往不似一两句话的总结那样简单。而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也许可以帮助深化对国民政府在战后香港主权问题上的评价。
国民政府是否真的想要收回香港?
首先,收回香港是否是国民政府在战后既定的政治目的与外交方针?
1943年中英新约签订后,国民政府并未放弃争取香港主权。中国曾通过照会,向英国声明对于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的权利。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也重申了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决心。有一点可以明确,自中英新约签订之后,国民政府对于香港问题,无论是作为外交构想还是政治承诺,就策略而言始终坚持以两国协商的形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基本上否定了用其他方式收回香港的可能性。

然而,国民政府并没有为解决香港问题开出明确的时间表,只是多次表示将在“战后”“合适的时机”,没有时间限制的政治承诺显得目标模糊而诚意不足,很难由此判断其是否愿意竭尽全力。从现已公布的史料来看,战后国民政府曾考虑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但最终停留在了试探的阶段,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
1945年8月22日,当中英之间为香港受降问题激烈纷争之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公开表示,即将举行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将讨论香港问题,而英国对此表示极为“诧异”。中国外交部欧洲司由此拟定了《收回香港问题》的报告,但外交部在何时向英方提出这一关键问题上过于谨慎,在报告中写道:“我国此次对香港问题究应如何提出,在会上或在会外讨论,事先应与英美商洽后办理。”据驻英大使顾维钧回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均主张向英国提出,但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中英双方最好能援交收威海卫租借地之先例“通过双方都满意的步骤进行”。
外长会议期间,宋子文从美国取道英国回国,在伦敦他曾同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见面,但两人均表示英国政府不会放弃香港。王世杰亦向英国朝野人士试探工党政府的态度,同贝文关系密切的法律专家克利浦斯爵士(Sir Cripps)向中方透露,工党政府上台伊始,立足未稳,担心在香港问题上让步会遭致保守党的攻击。其实,无论是工党政府还是保守党政府,都不会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妥协。外长会议后,直至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国民政府都没有正式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

国民政府在处置涉港事务时,有时会提出主权问题,其用意并非表达中方收回香港的要求,而是以此对英方施压,谋求打破交涉的僵局,“收回港九”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高高悬起而无法达到的目标而已。战后中国政府处置涉港事务,不可避免牵连主权问题,而无论民意舆论如何波涛汹涌,中英双方交涉仍是就事论事。主权问题更多地是弥散在交涉过程的无形压力氛围中,国民政府注重利用这种压力,而其本身亦受到民意舆论对主权诉求的压力。香港主权问题虽在双方交涉之中隐而不现,却贯穿始终。两国外交部门有时唯恐避之不及,而民意舆论却常常欲提还休。可以明确地说,无论战后中英围绕香港如何摩擦不断、纠纷迭起,起因皆非国民政府为收回香港而故意生事,中方在处置涉港事务时亦不打算借此提出收回香港。所以,国民政府在战后并未认真准备收回香港,这多少是个令国人遗憾的结论。
作为“四强”不够强:“弱势外交”的无奈
其次,国际环境对战后香港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制约了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
较之于北伐建政时期的“革命外交”,战后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常被目为“弱势外交”。尤以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为典型。在“非殖民化”的国际环境中,面对势力收缩的英国,“四强”之一的中国却往往“息事宁人”“态度软弱”。战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十分微妙的国际环境。
一方面,抗战胜利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之位列“四强”之一。按照战争期间中国与英美之间订立的平等新约,中国将逐步收回近代以来失去的国家利权,并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同这种表面现象极不匹配的是,由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国际新秩序使中国再次陷入窘境,国际环境异常险恶。在国际格局的调整之中,战时列强给予平等地位的承诺尚未兑现,新的国家利权又接踵丧失,中国虽获“四强”名号,却仍为列强宰制,虽具大国意识,却难有大国作为。

战后中国的多边外交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一边”,香港问题受到美国立场与政策的深远影响,有些甚至是决定性的。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存在两面性,而这种两面性主要缘于英美两国关系的特点。一方面,基于共同的文化脉络、政治理念和国家利益,英美同盟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外交传统;另一方面,英美之间在战后远东,尤其是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国家利益的竞争。重返远东并维持在此地的权益是英国在战时的既定政策,而一个英帝国色彩浓厚的远东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意愿。此外,尽量削弱苏联在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又是英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
具体到香港问题上,中英受降之争时美国态度的转变尤能体现英美间这种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战争期间,美国曾一度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由中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本就是美国提出的既定方案,杜鲁门(Harry Truman)并不希望英国以武力重返香港。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撰文指出,香港被英国霸占就如同“曼哈顿被其他政治势力霸占”一样。英国驻美大使馆向伦敦报告,香港在美国人看来是一个“旧时代的标志”。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在紧要关头不惜修改“一号命令”,劝说中国向英国妥协。其核心原因,是雅尔塔协定所设计的战后政治格局的限制,苏联由此重新攫取了日俄战争之后沙俄在中国东北失去的特权。正如英国外交部官员基臣(George Kitson)指出,苏联在中国东北拥有旅顺海军基地,并在大连商港保有特殊地位,那么,英国有什么理由要在战后退出香港?因此,杜鲁门政府不得不牺牲中国的利益以维持雅尔塔体系构建的平衡。
对于中国来说,战后中外关系波折不断,事端频生,如东北问题、外蒙问题、新疆问题等,皆万般棘手。处置不当引起国内政局动荡,外交部疲于奔命,尚无招架之力,对于香港问题又怎可能有机会、有力量主动出击?战后中国刚刚在国际社会扮演“四强”的角色,但她毋庸置疑只是“四强”中的弱国。老牌殖民帝国英国这时候仍挟其余晖,以强势外交相对待。英国在战后的衰落,并不是其国家整体实力的全面败落。在殖民统治问题上,英国只是在从“日不落”帝国向欧洲回缩过程中进行了符合自身实力的调适。因此,英国对不同的殖民地持不同的态度,其在香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恰恰是这种政策的体现。以历史研究者的后见之明来检讨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未免过于苛求,毕竟,在1949年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中,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已走得最远。
“弱势外交”背后的“弱势心态”:国家利权靠谈判
再次,国民政府对自身实力的判断是怎样的?民族情绪裹胁下的社会心理又在香港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战后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难有作为,国家实力的孱弱当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国民政府对该问题的自我认知。中英受降之争时,蒋介石就发出“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的感慨。据葛量洪回忆,在国民党政权“似乎还是十分稳固”的时候,宋子文曾对他说:“二十五年之后,我或者我的承继者会要求收回香港的,而我们一定会收回的。”宋子文当然是在表达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但他开出25年的时间表,多少暗示了国民政府此时自知无力收回香港。葛量洪也正是这样判断的,他认为:“假如中国不是积弱的话,是不会把香港割让予英国的。而后来的各个政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收回这个地区。”对于国民党组织在香港异常活跃的事实,葛量洪似乎并不十分担心,他表示:“他们会制造麻烦,有时是很大的麻烦;不过他们对这个殖民地不能构成威胁,因为基本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政府仍然没有能力向英国的地位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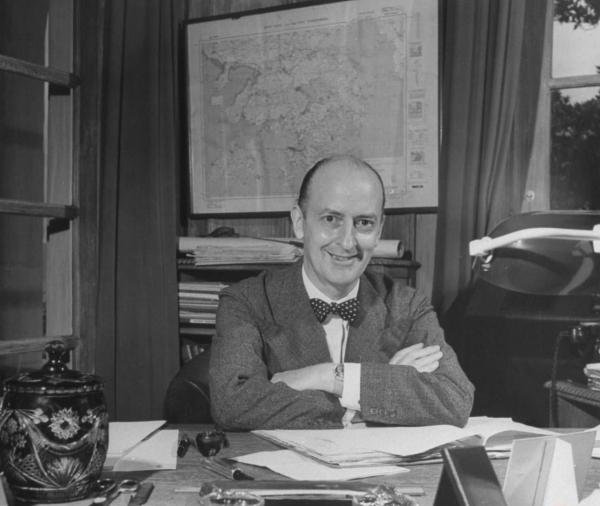
然而,战后中国,推而言之以至整个民国时期,中外关系演进的逻辑有着另外一面:较之于国家政权对于自身国力认知的相对“消极”(主要针对外交方面而言),民族情绪裹胁下的民众心态和社会舆论却在收回国家利权的意识上十分高涨,这个问题亦是整个民国时代政治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再次空前高涨,争取国家利权渐成一种社会共识和各政治势力“进步”与否的评判标准。标榜民族主义的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这一尴尬的处境。
一般来说,一个政权的政治实践应当与其意识形态相匹配,而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窘多少源于两者之间的脱节。国力不强、政局混乱自然是国民政府未能收回香港的原因,然而,历史的发展也曾呈现出“另类”的线索。国民革命时期,高擎反帝旗帜的武汉国民政府挟民众运动之威,一举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彼时国力也弱,政局亦乱,足可见在民族主义暗流汹涌的民国时代,外交的强势有时也并不以国力为后盾。而在战后,国民政府的“弱势外交”,一定程度上是“外交心态”的弱势,外交策略若此固然是基于对国家实力的判断,但“弱势心态”又反过来制约了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

在民族情绪处于巅峰之际,“外交”成了尴尬的词语。国民党建政之后,基本坚持通过交涉谈判争取国家利权的外交政策,在香港问题上也大体如此。战后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印度、缅甸等英属殖民地相继独立,不少中国民众认为,英国更加没有理由继续占有本就属于中国的香港。然而,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难以满足民众的期待,“外交解决”几成“示弱恃强”的代名词,外交当局成了众矢之的。九龙城寨事件中,一些报刊甚至鼓吹“撤办外交当局”“进兵港九”“血洗国耻”,足以体现民众情绪的激昂。
对于民族主义情绪裹胁下的民众运动,国民政府却骑虎难下。一方面,国民党依然保持着动员型政党的某些特征,发动和引导民众运动本是其惯用手段。在香港问题上,若处理得当,因势利导,可将民众对政府的压力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另一方面,战后国内不靖,政府形象败坏,民心渐失,民众运动中各势力暗流涌动,往往借机掀起惊涛骇浪,严重威胁当局自身。民众运动的发起与演进本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管束不易,放纵危险。战后屡屡被“运动”得晕头转向的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对于民众运动的心理更多的还是疑虑和戒备。国家实力与民众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悖论,名为强国、实为弱国的处境中,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更平添对外交涉的变数,由此,战后香港问题尤显风云激荡。
(本文摘自孙扬《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