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自然|湿地站站长:自然保护,立法只是第一步

1934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部名为《候鸟狩猎和保护邮票法案》,俗称鸭票法案(Duck Stamp Act),法案规定,每年狩猎者在狩猎野鸭、水鸟等水禽前,需购买一张“鸭票”贴在狩猎许可证上。贩卖邮票所得收益则用于购买和保护水禽的栖息地。
1985年后,联合国发布的全球首份环境法治理评估报告指出:尽管自上世纪70年代来,环境相关法律数量增长了38倍,但执法不力,导致其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污染以及防止大范围物种和栖息地丧失的效果并不明显。
中国自1979年通过环境保护法草案后,自然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案相继出台。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森林、渔业、野生生物、海域、防治沙漠化等领域。今年年初,全国人大首次针对湿地保护立法公布草案,将来还会为河流湖泊和岛屿立法。那么自然保护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一部保护法是如何诞生的?如何破解执法难的困局?

1935年第一版联邦鸭票和2021年的联邦青少年鸭票。图片来源:U.S. Fish & Wildlife Service
立法前,苏州湿地资源每年减少一个金鸡湖
冯育青是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下文简称“湿地站”)站长,12年前,他开始推动地方湿地保护立法相关工作。2012年2月2日,《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苏州成为最早一批有湿地保护法的城市。冯育青是南京林业大学生态学博士,担任苏州市林学会理事长已有10年,并建立了10所苏州自然学校,主编了教材《苏州野外观鸟手册》。他爱观鸟,爱摄影,爱探险。
经济发展是自然环境保护绕不开的话题。 苏州是鱼米之乡,湿地资源丰富,境内有太湖、阳澄湖、金鸡湖、尚湖等湖泊323个,总面积达到320万亩。而早期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全市湿地生态功能明显下降。据2009年统计资料显示,此前18年,减少了超过130平方公里的湿地,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苏州的金鸡湖。
2009年,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成立。与此同时,苏州市人大常委也开始着手保护生态环境,并于2010年成立工作小组,展开立法调研。工作小组搜集各个省市已有的湿地保护条例,进行实地考察并起草了《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截至2012年5月,全国共有12个省出台了省级湿地保护条例,5个地级市出台了市级湿地保护法规,4个省、直辖市针对重点湿地制定了保护法规。而且当时已经立法的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立法首次尝试湿地征占用审批
作为先发性城市,怎么协调经济发展与湿地资源保护成为一个难题。其中,经济发展对于零散湿地生态斑块的扰动,是发达地区湿地保护的核心问题。
冯育青认为,在讲湿地保护时,容易聚焦于大面积的湿地资源,比如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然而根据生态学的动态平衡原理,这种生物种类越多、食物网和营养结构越复杂的生态系统相对稳定。反而是小面积生态斑块,比如苏州300多个小湖泊和2万多条河流,对外界干扰反应敏感,抵御能力小。在它旁边开一条路,挖一个渠,都会对该地区的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而这些影响也更容易被忽视。
湿地站参考国外案例,提出设立湿地征占用许可,来减缓小斑块的受扰。也就是说,任何在湿地斑块周围的开发,都要经过湿地管理部门的审核,获得许可才行。
湿地站项目科科长范竞成表示,在提倡“简化审批流程”的时代背景下,新增湿地征占用前置审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的部门就提出疑问:为什么已经有环境评估和国土等手续的审核,还要再加一个湿地征占用审核?
冯育青认为,一些便民事务的过程可以简化,但是针对稀缺性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需要一定时间的评估。在生态问题上,“立等可取”式审批不一定最好。而且,湿地征占用审批是为环境保护增加了一个维度,以前的环境评估并没有聚焦鸟类等生物多样性。
得益于苏州市人大相关工委的同步介入,组织国土、水利、林业等各个部门召开座谈会,解决了关于湿地保护认知的差异问题。苏州的湿地保护立法很快达成了“综合协调,分部门实施”的管理共识。2011年10月27日,苏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其中包括:新增湿地征占用前置审核,组建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实施湿地生态红线制度,明确法律责任。

2009年苏州湿地保护立法时进行的野外生物多样性调研。
主动普及湿地法
湿地保护法出台后,“宣传”成为立法执行的第一步。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在全国率先尝试把湿地保护红线与市国土部门的用地红线进行融合。以往,规划项目都是先去找国土部门审核规划用地范围,如果能把湿地生态红线和其他用地范围都画在一张图上,那建设单位就能在立项早期规避风险,提出审核申请。
冯育青团队将苏州102块重要湿地的地界经过图形化、数据化,做成苏州湿地资源分布图。再与县市区国土及相关部门反复对接,将边界线一条一条比对,进行调整。为了增强基层配合意愿,湿地站还根据不同的项目给出阶段方案,比如已经规划、正在规划和尚未规划的项目触及到红线,分别该怎么办。
眼看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征占用项目的申报却迟迟没有来。冯育青意识到,一方面可能普法做的不到位,社会大众还不知道有这个法律;另一方面还缺少实时监管途径和“警示性”案例作为参考。
于是,他发动大家走出办公室,主动寻找可能影响苏州湿地的工程项目。他们关注新闻;向林业条线人员了解辖区最近的变化;核实各项工程是不是占用湿地。终于在2015年迎来了第一个申报项目:吴中区西山岛出入通道(太湖大桥)扩建工程。 2018年,湿地站向市里争取到财政资金,用卫星图片对全市湿地斑块开展动态监测,实现了湿地保护流程的全闭环。
近年来,很多项目在了解了苏州湿地保护条例后纷纷调整策略。比如最近规划的沪苏湖高铁,按原计划铁路要从吴江许多湿地穿插而过,受湿地立法的影响,最终将笔直线路修改成S形弯道,以避免原生态湿地的破坏。

2020年冯育青与湿地站工作人员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汾湖进行调研,右为冯育青,左为范竞成。
法律之外,个人理念转变是关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说过:法律是对人最低的要求,它在解决社会冲突时,又可能制造新的冲突。虽然湿地保护条例的出台,看似在法制程序上实现了闭环,但要让湿地保护进入良性循环,光靠法律的底线约束是不够的。
最早加入湿地保护的是一群苏州本地业余观鸟爱好者。2010年秋冬时节,他们在太湖观鸟时留意到湖边芦苇被大面积收割。虽然芦苇收割有利于第二年芦苇的生长,但太湖边的芦苇也是雁鸭类越冬候鸟重要的栖息地。

2012年姑苏晚报报道了太湖芦苇收割与鸟类栖息地减少的现象。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观鸟爱好者们找到了刚成立不久的湿地站反应情况。这时的冯育青也在发愁:立法后,如何提高湿地的功能?他的专长在林学和水岸带修复,虽然对于湿地功能最直接的指标——鸟类的需求——并不了解,但他认为,要培养一支专业的团队,为湿地保护、恢复和重建建立评价指标。
于是,冯育青经常跟观鸟爱好者一起去苏州各个地方观鸟学习。 “湿地好不好,鸟说了算”,成为了苏州湿地征占用审核中的一道手续。2015年,观鸟爱好者们在冯育青的鼓励下,成立了专业的湿地生态资源调查机构。

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里栖息的水鸟。
自从与观鸟爱好者们成为朋友后,冯育青意识到政府管理部门与其他自然保护组织协同共进的重要性。2016年,他请来台湾关渡自然公园专家为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做生态修复,并在2017年成立了“苏州昆山天福实训基地”,为全国近400家湿地公园提供专业人才培训服务。后来又邀请台湾环境友善种子的老师来苏州,与天福国家湿地公园联合开展2019年湿地公民科学家调查课程,培训苏州各个湿地公园的宣教人员。
冯育青认为,自己的目标是集合一帮愿意为湿地保护出力的有志之士。苏州湿地志愿队伍已经培养了98名生态讲解员,媒体、老师、观鸟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都能成为湿地保护的主力军。生态文明用什么来衡量?或许观鸟人数和各类自然保护从业人员的数量增长是一个不错的指标。

在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组织的公民科学家活动中,湿地公园的管理人员穿青蛙装下水。
或许在外人看来,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的成就得益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冯育青认为,湿地保护与场馆设计不一样,不是有钱请好的设计师就能立马出效果的。自然保护中很多事情急不来,也不是光靠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就能做出来的。
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像两只刺猬在冬天需要相互取暖,但是远则不暖,近则互伤,不远不近恰适宜。以前的人,因为生产技术有限,需要依赖自然,所以知道不能涸泽而渔。如今,技术的提高,生活和工作的重担,让我们离自然越来越远,对于自然的边界也越来越麻木,甚至出现了湿地公园里饲养黑天鹅、建造花海等人工景观。通过湿地保护立法与原生态的倡导,冯育青希望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作者王婷系香港大学景观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中国当代环境史和湿地景观的文化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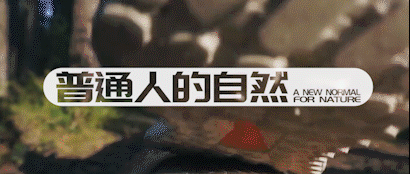
个人能为环境做什么?普通人如何在自然中自处?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专栏将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