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帝国》读书会①︱棉花的全球史:老故事与新故事
4月13日,复旦大学董少新教授发起的东亚海域史研究团队,联合艺术考古读书班,共同习读并讨论了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此书出版之后,在学界内外均引起广泛反响,并在近日格外成为中文知识界的焦点。
十余名校内外师生围绕此书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讨论。话题涵盖物质文化的全球流通、资本主义与全球史书写范式、“棉花帝国”与中国、陶瓷与棉纺织品的差异等等。本文在尽可能保证对话临场感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润色,并经发言人审阅。限于篇幅,本次读书会整理稿分三篇发布。本文为第一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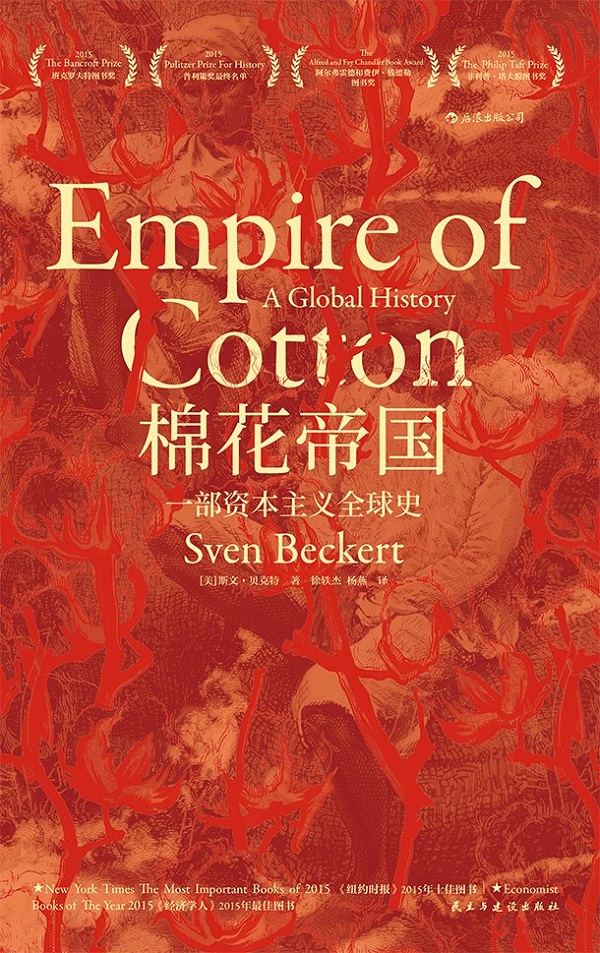
《棉花帝国》
谢程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硕士生)
我的演讲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在这一部分回顾了斯文·贝克特的学术关怀、对话者以及他选择棉花作为题目的正当性。第二部分是对前七章内容与论述方式的梳理。第三部分是对斯文·贝克特写作视野与方法的评述,聚焦于他的“看见”与“未见”。
《棉花帝国》的关怀与路径并非无迹可寻,早在斯文·贝克特的第一本专著The Monied Metropolis中,他已经关注到美国内战对于纽约资产阶级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层面的触动。资本家开始放弃自由劳动观点,转而拥抱自由放任主义。在贝克特新近编著的slavery’s capitalism一书中,他更是将《棉花帝国》中重点探讨的奴隶制视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进行讨论,这无疑也构成了对《棉花帝国》第四至第五章讨论的延续。
在千万种物质中,为何唯独棉花成为幸运的宠儿,被贝克特选作透视资本主义形成的透镜?其实,这个问题在本书的绪论中便有回答。贝克特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棉花是一种主要的制造业,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次,棉花工业的兴起,是更广泛工业革命的跳板。再者,棉花工业也是“大分流”初始阶段崛起的工业。检视它的历史,或许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大分流”。在这本有关棉花的新的历史书写中,斯克特渴望矫正以往有关棉花的论述,重建一部重视资本集中与转移过程,关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与全球农村(global countryside)的全球史。上述关怀与态度也注定了这将是一部与以往仅着眼于重工业、城市、欧洲和北美、男性、资本主义纯洁性与经济层面截然不同的全球史著作。贝克特曾坦言,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都对他有着不小的影响。前者启发了他帝国在主导与分配全球经济权力中的作用,后者对于资本主义全球性的坚持触发了他对于棉花帝国全球性的思考,以及全球南方在其中更核心、更具活力的位置。
在全书中,贝克特构建了“工业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三者来勾勒不同历史时期的棉花工业形态。前七章主要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两者的框架下展开的。贝克特采取了宏、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从塞缪尔·格雷格(Samuel Greg)的阔里班克纺纱厂(Quarry Bank Mill)、利物浦商人皮尔-耶茨合伙公司(Peel, Yates & Co.)、埃伦·胡顿(Ellen Hooton)等案例出发,讲述了棉花种植地如何从哥伦布时代前的墨西哥、秘鲁地区的棉花,扩散至美洲大陆,向西至西非和亚洲。在这一过程中,棉花走出家庭,经由外包网络、国家组织和全球贸易,从一种高保值的区域性作物变为越洋贸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不仅通过对战争资本主义阶段的暴力遗植,不断攫取劳动力和土地,塑造新的“商品边疆”与外围(making of a periphery)。如在美洲形成军事-棉花综合体,通过土地的攫取获取低成本的铁路和河流运输,并使用大量强制劳动力等。国家也通过保护主义、工业间谍等手段,振兴了国内的市场并不断革新技术,最终通过政治动员和规章建立吸纳大量无产者以受薪者的身份进入工厂。因而,“工业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这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交织复杂的:战争促进了全球性经济空间的重组和知识技术自亚洲至欧洲的流动,也构成了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工业资本主义又重振了战争资本主义。
斯文·贝克特的“看见”在王希的序言中已十分清晰。无论是他“共时性”的自觉,还是对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把握,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是,这本书仍然有许多视角未有展开,如技术、消费等方面。全书对促进棉花工业的技术史与棉花的消费史仅如蜻蜓点水般提及,但缺乏深入的探索。虽然全书在愿景上声称希望跳脱欧洲中心论,但是本文跳脱欧洲中心论的主要方式是将印度、南美、西印度群岛等地纳入棉花帝国的版图重点讨论,有关东亚的情况依然极为有限。关于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棉花种植、贸易、技术革新以及纺织业等状况,其实有大量史料与研究。徐一夔记录的“织工对”、江南的“高乡”与“低乡”、黄宗智与彭慕兰有关棉与棉布消费问题的争论、薛凤(Dagmar Schäfer)的《工开万物》、有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反思与讨论等都可以被视为思考全球版图里中国棉花问题的起点。
霍司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
这本书是相对好读的一本书。它既有详实的数据,同时也能让非经济史专业的读者抓住叙述的主线。该书的后半部分,主要关于棉花帝国的全球扩张。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一直紧扣两个要点:一个是国家角色的增强,另一个是对全球农村的改造。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前者。
第八章题为“棉花全球化”,围绕商人在棉花帝国中锻造关联的活动展开。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贸易方式日益呈现出抽象化的特点。第九章阐述了美国内战对全球棉花市场的震荡。美国奴隶制度的解体,催生了新的全球劳工、资本和国家权力网络,导致了第十章所说的“全球重建”。伴随着秩序重建而来的,还有对原有贸易方式和新兴原料供应地的破坏,这在第十一章中得到了详细论述。而在第十二章“新棉花帝国主义”里,国家的重要角色再次被强调。经过民族独立运动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南方的竞争力逐渐回升,具体可见该书的第十三章。作为结语的第十四章描述了近几十年棉花帝国的新图景,并对资本主义及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做出了解答。

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棉花种植园
《棉花帝国》被公认为全球史写作的一个典范。关于全球史的由来,可参看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全球史导论》中详细梳理的世界史之发展史。康拉德还总结出了六点全球史应有的独特之处,我们在《棉花帝国》中处处可见它们的影子,例如对共时性的重视。贝克特基本上做到了超越单纯的“关联性”,深入探究其背后物质、文化和政治层面的结构整合。于我而言,《棉花帝国》带来的启示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第一,对于大问题的思考。贝克特以小小的棉花为主角,却能观照到历史学中的重要问题。第二,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如今学者讨论全球化的时候,往往强调要超越国界去看待一个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忽略国家角色的存在。第三,对全球农村的关注。外来的东西如何进入、改变、或是采取方式适应有着传统土壤的农村,以及农村的回应,都是很有趣的研究视角。
姜伊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
首先我想用乔吉奥·列略的《棉的全球史》做一下对比。近十来年有大量的物质文化史著作出版,包括食物、纺织品、武器、工艺品等等。这些著作刚开始让人耳目一新,但现在让人审美疲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物质都是在同一个全球贸易网络内流通的,尤其是新航路开辟之后。如果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网络存在,那么A地的物品出现在了B地,东方的物品出现在了西方,这件事情就并不稀奇。一艘船可以装载各种各样的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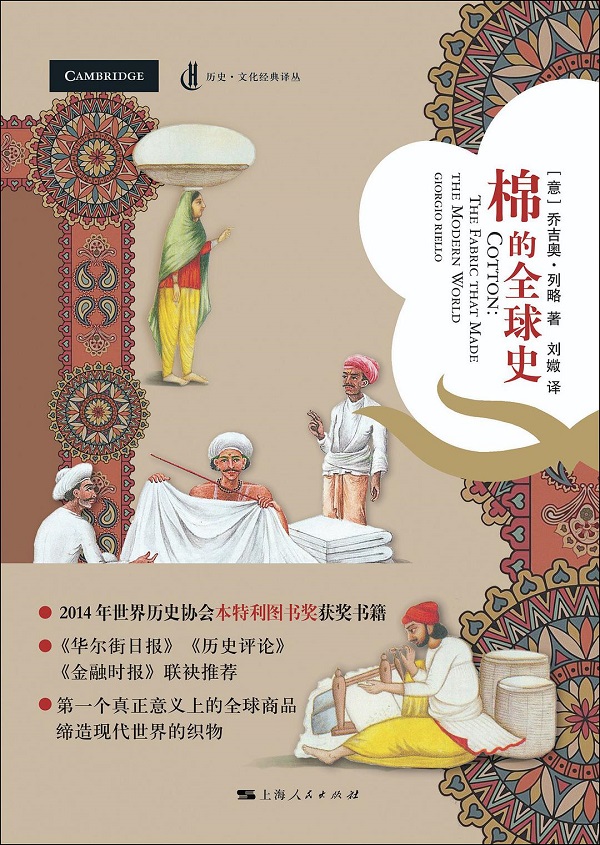
《棉的全球史》
在这种情况下,物质全球史应该怎么继续深入下去?我想有两个路径。首先是glocal的方法,也就是讨论某个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在物质输入输出的过程中产生的变革,譬如太田淳写过蔗糖对东南亚岛屿社会的影响。另一个路径,就是对全球网络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棉花帝国》就是做的这种工作。当我们仅仅讨论物质流通的时候,似乎地球是平的;但地球实际上不是平的,《棉花帝国》如果只提炼一个关键词,我认为是“分工”,分工体现了“地球不平”这个事实。
从狭隘的史学标准来看,《棉的全球史》采用了很多新材料,而《棉花帝国》用二手文献,也就是老材料居多。但后者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前者。这是因为列略曾经在V&A博物馆工作过,展示新的材料并非难事,然而他只是用新材料讲述了一个物质流通的老故事。《棉花帝国》则是用老材料讲了一个新故事。新在两个地方。首先,他着重讲述了南北战争对于全球棉纺织业版图的重塑,其次,他采用了南方化视角,讲述了棉花帝国重心从全球南方转移到全球北方、并再度回到全球南方的故事。这本书也深得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的精髓,即着眼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看到棉花帝国的历史就是它的交易成本在不断降低的历史。道格拉斯·诺斯强调过衡量费用和意识形态也应该被纳入到交易成本的考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棉花帝国》这本书里面强调期货市场对棉花的分类,以及战争或革命等等问题,棉花帝国在这个过程中运转愈发流畅,也就是它的交易成本不断在历史过程中降低,都应和了诺斯的经济史思想。
接下来,我结合自己对穆藕初的研究,聊一下《棉花帝国》跟中国棉纺织业历史的研究。首先,在这本书的帮助下,我界定了中国棉纺织业从前近代转向近代化的几个特征。(1)海关设立和马关条约之后,棉织品的生产进入了明确的国际贸易核算中。如此一来,棉花、棉纱和棉布的生产便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区域性消费,而是要抵御国际贸易和国家财政上的赤字。(2)为达到上一目标,需要大规模的机器化生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分野从此更为明确。(3)机器化生产对棉花原料最基础的需求,也远远大于明清时期中国纺织业最为发达的阶段,因此棉花生产的地域分工更加明确,并以科学实验的方式对原料进行改良,使棉花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能够适应机器生产。(4)从劳动力来看,在“近代早期”阶段,棉纱的生产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兼职性质的,而机器化时代的纱厂少则数百、多则上千人,遵循严格的时间表,使社会结构深刻转变。(5)棉织品被纳入全球金融市场,与汇率和大宗期货市场密切相关。(6)现代形态的同业公会出现,在上海以华商纱厂联合会为典型,新型同业公会的出现一部分模仿了美国和日本的垄断形式,其根本目的突破单一纱厂的规模局限,汇集更大规模的资金,降低共同的信息成本和生产边际成本。
我们可以看这几个要素,都能在《棉花帝国》中找到对应。和大家分享两个小小的个案,也都和南北战争以及之后的棉花种植传播有关系。
首先是晚清时期的“洋布自织论”。《棉花帝国》里提到,南北战争导致英国等工业国家失去了物美价廉的南部棉花供应,因此要在全球寻找替代商品。所以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中国棉花大量出口,这给洋务派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中国的棉花可以进行机器纺织。实际上,中国棉花虽然大量出口,但并不能单独使用,而是要和印度棉花拼起来才能进行机器纺织。中国原本生产的棉花从分类上叫“普通中棉”,写作“G.Nanking Type”,纤维很短,不适合机纺。因为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盛宣怀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后整整十二年才开工。最适合机器纺织的仍然是来自北美的大陆棉。
《棉花帝国》也提到,南北战争之后,全球北方的纺织工业资本家要在其他地方推广美棉种植。我带了一份史料,是19世纪末如皋一个人写的《劝种洋棉说》,这种文章或者登在报纸上,或者做成小册子分发给棉商和棉农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时期这类的小册子非常多。在中国,美棉的种植和美国农学的引入是同时的,并且中国最初的农学科也跟上海的纺织业有密切关系。穆藕初在美国拿到了农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就在上海设立了试验农场移植美棉。之后留美回来的农科生还有邹秉文和过探先,他们都是专攻遗传学的,回国后建立了东南大学农科系。当时的南京还有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请了美国农学家郭仁风主持农科系的工作。这两个农科系都投入了大量的工作进行美棉移植,上海的纱厂联合会给他们提供了资金和实验场地。我在论文里有专门的篇幅讲这个过程。
胡竟良写的《中国棉产改进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美棉在中国移植的历史。美棉的移植对中国的农业地理、区域经济,都有非常深远的改变。彭慕兰的博士论文《腹地的构建》里有一章提到,美棉种植对于山东地区经济格局有深刻影响。再举几个例子,广西历史上从来不种棉花,但是穆藕初等人推广美棉的时候,广西督军谭浩明也和他们索要种子。冯玉祥在陕西也要种美棉,一方面肯定是为了开发当地经济,另一方面陕西当时种罂粟很凶,改种棉花也是为了杜绝烟患。1920年前后,松江县农会长吴步蟾在当地试种美棉,这个事件我认为有象征性,百年来衣被天下的松江府,种上了新大陆的棉花。因此,可以说中国棉纺织业的近代化转型,也是和棉花帝国的运作息息相关的。

《腹地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