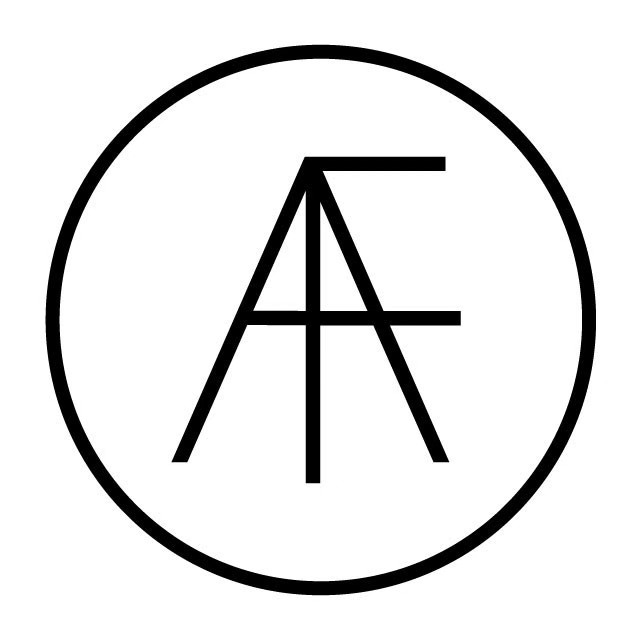杰夫沃尔:摄影师与飘忽不定的题材

© Jeff Wall
在1970年代末,当杰夫·沃尔(Jeff Wall)开始制作在大型灯箱中以透明胶片形式呈现的剧画图像时,当时的普遍预期认为这并不会是一种进展。因为那时很少有摄影师进行大尺寸的摄影工作,很少有摄影师进行彩色摄影,而且几乎没有人考虑过把图像作为一个单独个体脱离于任何系列或背景之外。而今天,他是最重要的摄影艺术家之一。
我在1980年代末学习摄影和电影时,第一次遇到了沃尔的图像和他的原创文章。我发现他既有在图像上的野心,又具备批判性的思维,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虽然我并不总是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无可否认,看到一个艺术家对自己和他的媒介的要求如此之高,真令人兴奋。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左右,最后,我以他的一张照片《女人的照片》(Picture for Women,1979)写了一本书。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发表了几次访谈的内容。其中《发生的领域》(The Domain of Occurrence)就是最近的访谈之一,是在西班牙Concreta杂志的委托下于2014年完成的。
我们探索了许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都很感兴趣的主题:照片作为是“图画”和“文献”;摄影在艺术领域和作为艺术的态度转变;以及主题与图画的挑战之间的关系。

© Jeff Wall
杰夫·沃尔访谈
文 | 戴维·卡帕尼 × 杰夫·沃尔
译 | 杭添
戴维·卡帕尼:
杰夫,你曾经谈到图片制作是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通常不受题材约束,甚至完全自由。你探索出一种图像形式或方法,而表面上的题材反而可能是次要的。这与某些具象艺术画家的工作方式很接近。
但是你已经围绕过特定题材,在不同的时间为它们制作了不同种类的图片。例如,《伊万·塞耶斯》(Ivan Sayers,2009)与三十年前创作的《女人的照片》具有相似性。《模仿》(Mimic,1982)与《人行道上的人》(Figures on a Sidewalk ,2008)有共同的元素。这里有很多动机上的循环或者回归。你对图像处理的变化是否与你所描绘的题材的态度的变化相对应?《模仿》与《女人的照片》是直接的且具有对抗性的。《伊万·赛耶斯》和《人行道上的人》则是更坦然的充满深情。
杰夫·沃尔:
我认为图像问题来自偶然相遇后题材的自然显现。它们并不是摆脱不了它,而是从中诞生。但是,我可能是想处理某种图像问题,比如,面部与图像平面上图形的接近程度。但是我并没有真正察觉到它,或者如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模糊的冲动。然后,这可能有助于我注意到本来没有注意到的某些东西。或者,这只是一个随机的相遇,使整个事情朝向我不曾参与过的方向。我从来都不知道。某些事物也可能比其他事物更吸引我,我也不想对此有太多的掌控。因此,题材从来都不是次要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像其他摄影师那样把题材看的过重。摄影师往往想要在同一个题材上花很多精力,全神贯注于此,拍摄一系列的图片。而我就用一张图像完成它,这就够了。
我的态度似乎一直在变化,不是向着一个方向,而是纠结的。我对《模仿》中的人物有很深的感情,与我对《伊万·赛耶斯》中人物的感情没有太大不同。这种感情在于他们是怎样出现的。你需要对所描绘的所有事物具有相同的喜爱之情,否则就无法很好地看到和描绘它。在我看来,将描绘作为艺术的一种过程或模式是基于全然喜爱拍摄对象的显现状态。

© Jeff Wall

© Jeff Wall
戴维·卡帕尼:
你是否曾经感受到在这种对显现的喜爱与他们过去所说的“再现的政治”之间的张力?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你似乎对描绘公然的社会动荡和不安局势很感兴趣。那些动荡具有自己的图像力量。我认为今天,至少目前,你很少做那一类的作品了。你看起来对那种“喜爱拍摄对象的显现状态”更得心应手,而这开辟了其他图像的可能性。
杰夫·沃尔:
如果你只是在谈论题材,我想我最近做的很多事情都和80年代的照片处于同一范畴。但是我现在对它们的处理可能有所不同。那类题材可能是具有自己独特的图像力量,但我认为它们不需要任何可预测的方式来表现。所以我正在寻找展现方式,创建事物显现的方式,无论它是处于紧张状态还是什么别的状态。另外,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更恰当的题材,尤其是因为题材通常是偶然出现的。
如果你思考下绘画艺术的一般题材,例如静物、肖像、室内裸体、风景等,在我看来,有时候它们就像是替身,因为它们必须成为绘画的题材。任何稍微不寻常的题材都可能会通过某种不经意的相遇而出现在艺术家面前。但在没有这样的偶遇时,你仍然可以通过选择一个一般题材作为起点来继续工作。一旦你开始了,你会再一次面临如何将那个特定的题材变成一幅好的油画、照片或素描的问题,这可能跟油画或素描关系更密切,但这仍然与摄影有很强的关联。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像画家一样,当你在无所事事或者没有特殊安排的情况下在工作室(影棚)里做一些事情,那些作品会和你会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成功。因此,要保持忙碌,去工作,行动起来,去发现,只要它看起来是最直接的可能性你就可以尝试。而且,如我们所知,这种工作室类型的摄影现在变得非常流行,也许是因为这个空间提供了一系列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并不依赖于不可预知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影棚的内部本质上是一种现象发生的空间框架,即有些东西等待着被拍摄。

© Jeff Wall
戴维·卡帕尼:
你提到的这种趋势我很同意,目前在艺术摄影领域很普遍,去接受并使用一般题材。但令人惊讶的是最近,正如你所描述的,最近出现了以“扩展的工作室”实践的形式。曾经摄影师渴望拍摄图片,但对某个题材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只是直接带着相机记录世界。也许不是室内的裸体,但肯定是静物、肖像、风景和街景。我想你会称呼它为在记录模式下的图片制作者。在那种模式下,摄影师确实会偶然发现他们主题和体裁的可能性。您曾以那种方式制作图片,但是通常,正如你常说的那样,制作一张成功图片的前提是“从不拍照开始”。接着是“准备与合作”。你注意到一般题材了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注意到一般题材而不是特定题材意味着什么?
杰夫·沃尔:
也许我们都是在盖瑞·温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的最后几年之后工作的。很有可能,他只是对拍摄这个照片更感兴趣,而不是打印、评估它们,甚至是冲洗他的胶卷。温诺格兰德用他的话语:对与不可预见的发生说“是”,对在那里、在某处说“是”,在一瞬间按下快门,把它拍下来。
在那之后,摄影对他来说似乎已经完成了,也许他不想花漫长而费力的时间在所有的底片上寻找最好的照片。也许那时他想,如果有“最好的照片”,它们最终会通过别人的学习与评判进入大众视野,但他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人是谁,而他似乎对此可以欣然接受。由于他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人们担心其他人会从温诺格兰德从未看过的素材中选择了一些图片,质疑原作性在哪里,我倒是认为这对摄影反而是好事——它重申了摄影根本没有规则。完全有理由相信,温诺格兰德会感到或者预见到这一过程本身会成为理解艺术形式的重要时刻。你可以说温诺格兰德想要尽可能地与一般题材保持距离;他希望每张图片都是与某些事物特定相遇的结果,因此,他可以被视为认为反对摄影需要与一般题材相关的典型。也许吧,但是它更加复杂。也许对他而言,无休止的相遇似乎就是无穷无尽的“发生”,而常常不看取景器,不知疲倦地记录了这些,也许这个过程达到了目的。因为他认为“发生”本身是人与动物能量的一种简单连接,尽管通常是在结构化的空间中并在有记录设备的情况下形成的,没有规律可言。

© Garry Winogrand
或者在没有那些连接的情况下,又或者记录设备未能抓到,因此它只拍摄到在它消失后的尾迹,等等。“发生”本身就变得很普通——这些照片只是展示了一连串无尽的“发生”——里面包含了它的缺失,或者它已经过去没有被记录的部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不用看就能拍摄——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在事件的领域之中,所以,他也不会失败。
温诺格兰德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认为摄影作为艺术所必需的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他非常激进的教训,我们可以认真地接受他的教训,因为他达到了通过体验严谨的工作,以街头摄影的方式“捕捉一个独特事的件发生,拍摄出一幅伟大的照片”的高度。他似乎已经穿透了那个空间的背景,进入了一个非常抽象的空间,与摄影有着非常抽象的关系。我觉得我的“从不拍照开始”一直非常接近于维诺格兰德最后几年做的事情,一直到1984年。

© Garry Winogrand
戴维·卡帕尼:
我认为它可能比那更开放,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把摄影行为本身包涵在那些潜在的无限“发生”中。
当我们观察温诺格兰德时,是的,我们感觉到世界曾经/正在按照它不可预知的模式前行,但实际上世界本身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的发生。只有观察它的行为,在它周围放一个感知的、象征性的或摄影的取景框中,才能把它变成发生。温诺格兰德的相机从日常生活的“虚无”中召唤出“一些东西”。但与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等人希望制造一种强烈的画面秩序(强烈的观察力,强烈的感性/象征/摄影式的取景)不同,维诺格兰德似乎在调侃这样一种想法,即摄影行为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将事物转化为一幅画面,而“构图”完全次要的。
所以我同意你所说的关于你自己的作品,无论有多么充分的准备,无论有多么好的“构图”,如果你正在拍摄活生生的东西,甚至只是在变化的光线条件下拍摄,你永远不可能摆脱总会出现意外惊喜。身体的形状。光线照射物体的方式。布料的折叠方式。脸上的表情。一次偶然性的对焦。这本身就是彻底的、令人不安的和自由的,超出了作者的范畴。
世界本身比任何艺术都更丰富、更陌生、更复杂、更刺激、更可怕,但摄影有某种有条件进入这种非艺术。你是否这样认为?
杰夫·沃尔:
当然……但让我补充一句,也许这个问题,联系上我们所谈的温诺格兰德,与剧画(tableau)有关,不是每张图像都是(或想要是,或需要是)剧画,剧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精巧的构图行为,当一幅图像没有那么敏锐地构图时,它就没有那么的明显。温诺格兰德的实验,如果这就是它的目的,那就是看到一个人只需要做很少的刻意构图就可以得到一张剧画,去看看其中包含了多少的自动性。而他证明了有无限的量。因为没有规则,只有案例,任何随机拍摄都可以产生令人信服的剧画。剧画的形式,就像任何可识别的艺术形式一样,不能按照规则去制作,或有趣的制作。它只是以某种方式制作出来的,如果它是好的,那就是这样。这就是它如此有趣和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它可以在任何时间出现在任何地方,可以经过极端的深思熟虑,也可以甚至不需要,等等。而偶然,或意外,总是在这个过程中徘徊,扮演这样或那样的角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温诺格兰德在不看和不处理的情况下拍摄,与我深思熟虑的方法只有一点程度上的区别。他的偶然性可以出现在我的工作过程中的任何阶段,而且经常出现,他的努力工作,即便不强调什么但仍然每天花很多小时四处走动并拍摄,其实相当于我所做事的另一种形式。
假设(只是为了讨论而不是做任何申明)他的方法是一极,而我的是相反的另一极,其他的都在它们之间。在两极之间的渐变光谱中,我们获得了一个领域,而事件变成了剧画。假设有1000个摄影师,每个人在光谱上占据一个点,拍一张照片我们会得到1000个剧画的灰度。如果我们做这个实验,我们会让1000人都拍同样的东西以便比较结果。所以,在实验中,发生,或被拍照的对象,就代表“发生”本身。
也就是说,发生和剧画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结构、美学上的,因此,至少作为一种结构模型,存在着抽象的发生,或者发生本身。然后,从那个抽象概念回到不同摄影师的实际操作上,我们会再一次看到各种各样的照片被制作出来,但是我们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它们被拍摄出来的共同基础。

© Jeff Wall
戴维·卡帕尼:
我对摄影中剧画形式的形成(和未形成)的方式印象深刻。这种情况的提出需要两种相关但不同的力量。一种是艺术的意愿——摄影师想要塑造一些艺术上令人信服的东西的愿望。另一种集中在观赏者的“形成意愿”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一张照片作为一个剧画,而不考虑其意图。但是,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过去的印象带入与对象的接触中,或者是“在画面中”的一些东西。
上个月,我给我的姐夫看了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的 《不同寻常的地方》(Uncommon Places)。他的主要兴趣是在斯蒂芬的照片中再现的MGB敞篷车。他没有提到斯蒂芬在构图方面的天赋,尽管明晰的构图总会指明我们所处的背景。斯蒂芬那天要来吃午饭,我姐夫问他,上世纪70年代的中西部是否有很多MGB,或者他是不是被这些MGB吸引住了。斯蒂芬回答说,他确实是被它们吸引了。他的妻子有一辆MGB,他喜欢这种类型的车,所以当他出去拍照的时候,他似乎总是注意到它们。
正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将任何摄影类的文献被作为艺术摄影或剧画来查看一样,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将任何剧画摄影被作为文献来阅读。每张照片都是剧画,也不是剧画。每张照片都是文献,也不是文献。我当然是在简化,因为摄影如此吸引人的是艺术作品和文献之间的张力或辩证。过去许多伟大的摄影师都从这种紧张中汲取灵感或将其戏剧化。维吉(Weegee)、埃文斯(Evans)、卡蒂埃-布列松、海伦·莱维特(Helen Levitt)、阿勃丝(Arbus)、弗兰克(Frank)、克莱英(Klein)、肖尔,还有很多其他人。他们都在新闻报道和艺术之间有一席之地。几乎可以这么理解,即轻微地宣称摄影是艺术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但一个强有力的宣称可能会摧毁它。埃文斯曾被问及摄影是否是艺术,他回答说这曾经是一门艺术。我怀疑你可能不同意这一点。

© Stephen Shore
杰夫·沃尔:
我同意摄影是一门艺术,就像所有其他艺术一样,而不是“艺术”本身。但我不同意这种轻微或强力的二分法。我不认为预先存在比较好或最好的方式来制作任何艺术,并可以将其转化为指导方针或标准。轻微的主张是有效的,但它只能代表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它也反映了那一代摄影师的背景环境与感知。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他们的方法似乎是更受欢迎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情况不会永远如此,即使只是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化。
“轻微”的宣称反映或表达了一种对艺术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是先锋派或先锋派时期的特征。但是这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少有理由去破坏艺术,特别是“大写的艺术”,而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可能性保留下来,因为它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受到融入大众文化或全球数字文化的威胁。一百年前,一定程度上大写的艺术看起来像是帝国主义的合谋者。但目前,艺术作品本身和它们处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细微差别似乎更重要,这种微妙的感觉可能是“艺术”传递给我们的,并且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比以往更接近。“轻微”的宣称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可以减少艺术的自命不凡——如果不是艺术自身——至少是它周围的光晕和社会接受和操纵艺术的方式,作为艺术自我批评的一部分,这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欣赏曾经被认为是如此自命不凡的艺术,即它看起来不再那么自命不凡了——至少不再是好的艺术。(不太好的艺术总是带着那种自命不凡的感觉,因为它在假装成好的艺术。)例如,我注意到过去几年里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画意摄影的兴趣的复苏,如果没有真正的情绪和态度改变,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总之,“轻微”的宣称现在是一种恒久有效的途径,但是在1930年甚至在1970年说就没有这样的独特性。
然后,关于MGB敞篷车,没有办法去阻止观者欣赏图片本身而不去注意上面显示的东西。但这是图片的伟大品质之一,因为图片可以把美传递给即使没有在看它们的观者,传递给在观看的瞬间并没有察觉到美的观者。然而,美已经跃入他们的意识中,并停留在那里等待被认识,也许永远等待着。

© Stephen Shore
戴维·卡帕尼:
有一种非常神秘的事实,那就是某些照片的美可能在没有被认识到的情况下对我们产生影响,即使它被认识到了,也可能仍然是无法理解的。这可以发生在任何描绘类型的媒介中,但它在摄影中尤其强大,是因为它的纪实属性。回到你之前的观点,我同意历史上的先锋派对艺术的怀疑,而这些怀疑确实塑造了人们对摄影的某些态度。正如我们所知,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也非常反感任何剧画形式,特别是在摄影领域(现在仍然存在强烈的怀疑!)。我也同意,那个漫长的时刻已经结束,没有规则或标准。我赞同剧画可能是对那种令人担忧的融入大众文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抵制。但我认为我刚才提到的摄影师并不是特别被那些先锋派的怀疑所驱使。我想他们觉得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只是通过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相遇,以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获得了活力。
我看得出,你与那股活力也有关系,尽管你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调节它。我刚刚又看了一遍在布鲁塞尔BOZAR举办的展览目录《杰夫·沃尔:弯曲的道路,2012》(Jeff Wall: The Crooked Path, 2012),在其中你展示了一些与你作品相关的、你欣赏的艺术。我注意到你们囊括的摄影师主要来自“纪实风格”:埃文斯、齐尔(Zille)、布兰特(Brandt)、莱维特、维吉、温诺格兰德、肖尔、古斯基(Gursky)的早期作品。一些以一种更具构造性、寓言的方式拍摄[沃尔斯(Wols)、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Christopher Williams)和詹姆斯·韦林(James Welling)的静物]。但是,有没有照片是采用你的那种“电影”的方式拍摄而你很喜欢的?

© Jeff Wall
杰夫·沃尔:
我认为他们都被先锋派反对“艺术”的情绪所驱使,也许是以一种不那么明显或直接的方式,但观点仍然存在。而且,没错,纪实项目是反方采取的一种非常合适的形式,因为它有许多社会的,甚至是激进的优点,而(以往的)“艺术”不具备,或再也不具备了。但你也可以说,从1860年到1960年,艺术中所有有趣的事情都是由先锋派的立场推动的,因为那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有趣、最引人注目和最有成效的立场。甚至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们也能从中被启发,即使是消极的。整个还原的过程是不可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艺术”被减负为更轻、更快、更丰富、对日常生活更开放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么庞大、那么沉重、那么缓慢、宏伟。然而,当我转向摄影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个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所有“轻微”“微弱”都已经成为了老生常谈,不再那么鲜活了。
我一直喜欢罗伯特·弗兰克和其他人,他们从十几岁起就是我的灵感和榜样,但我只是觉得,以那种先锋派或新先锋派的方式去打破和进一步细化艺术概念是无用的。这不是说回到之前的某种状态——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觉得这是对70年代初那一时代艺术环境的真实反应。“艺术”在那时已是如此的“过时”,以至于它不可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有趣。我对剧画的理解是由我很早与绘画的联系而形成的,绘画作为剧画的模式对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并不是要“通过摄影去绘画”或类似八九十年代的陈词滥调,我是以一种从摄影在诞生之初就有的方式在摄影,但这种方式在摄影被发现具有记录的优点的浪潮中黯然失色。而这个阴影空间对我来说是开放的空间。因此,对我来说,这不是关于纪录模式或纪录风格与电影之间的某种区别——我认为,摄影,是通过这些模式之间无限细微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的。所以我并不对一些让我感兴趣的摄影师和一些我认为很接近但通常不被认为很电影的摄影师,例如埃文斯、阿杰(Atget)或齐尔感到好奇。这并不是说我“在他们的纪实实践中发现了电影的痕迹”——这是另一个陈词滥调。我没有找到,也不需要找。我的灵感来自于他们作品中所缺乏的电影摄影。
文章
David Company, So present, So invisible: Conversations on Photography, Contrast, 2018, pp. 128-143.
作者
杰夫·沃尔(Jeff Wall),加拿大艺术家、艺术史家与艺术评论家。他的早期作品借由摄影回应观念艺术。1976年,沃尔开始运用彩色摄影,其标志性风格是灯箱中的大画幅彩色透明片。1991年,他开始使用数码蒙太奇,并从1995年开始创作大画幅黑白照片。他的作品在国际上广受赞誉,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与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等举办大型回顾展。
戴维·卡帕尼(David Campany)是一名享有声誉的英国作家、策展人与艺术家,现为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策展部主任。著有《艺术与摄影》《摄影与电影》《沃克·埃文斯:杂志作品》《大路:摄影与美国公路简史》等。
译者
杭添,1990年出生,2013年毕业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现工作、生活于南京。他的研究方向是探索身体体验与其再现之间的关系。作品曾于英国Bonington Gallery、法国Barzion Artists’ Gallery以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等展出。
原标题:《杰夫沃尔:摄影师与飘忽不定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