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波拉大访谈:最后的乌托邦守望者
原创 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Francis Ford Coppola

翻译:乎乎
白灼红烧爆浆炒上浆看片码字
翻译:于SQ
巴黎三大电影学硕士在读,重新学习看电影

最后的乌托邦守望者
《电影手册》专访科波拉
采访人:Marcos Uzal (线上采访)
采访时间:2021年1月14日
Q:
许多导演都表示不会再看自己之前的电影,因为它们属于过去。您却相反,多次重剪了自己此前的作品。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影片仍贴合您当下的工作和生活吗?
科波拉:
您知道的,要向观众呈现一部新作,尤其当这部作品试图给观众带去全新的、不寻常的体验时,是要经历很痛苦的过程的,因为您必须得听取所有相关方和投资方的一揽子建议和意见。您必须跟所有那些逼你尽快定下最终剪辑的人抗争。可往往也是这些时候,您可能会因为固执己见而犯错。所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我重看自己的影片还会觉得不满意,这很正常的事。所有艺术都是这样。
《蒙娜丽莎》之所以收藏在巴黎,是因为列奥纳多·达·芬奇认为这幅画没完成,这才把它带到了法国。我不是要把自己比作达·芬奇,不过自从我拥有了我大部分影片的所有权之后,我终于可以修整它们了。但是《教父3》不同,我是借着这部影片的名气,趁着它拍摄三十周年的机会才说服了派拉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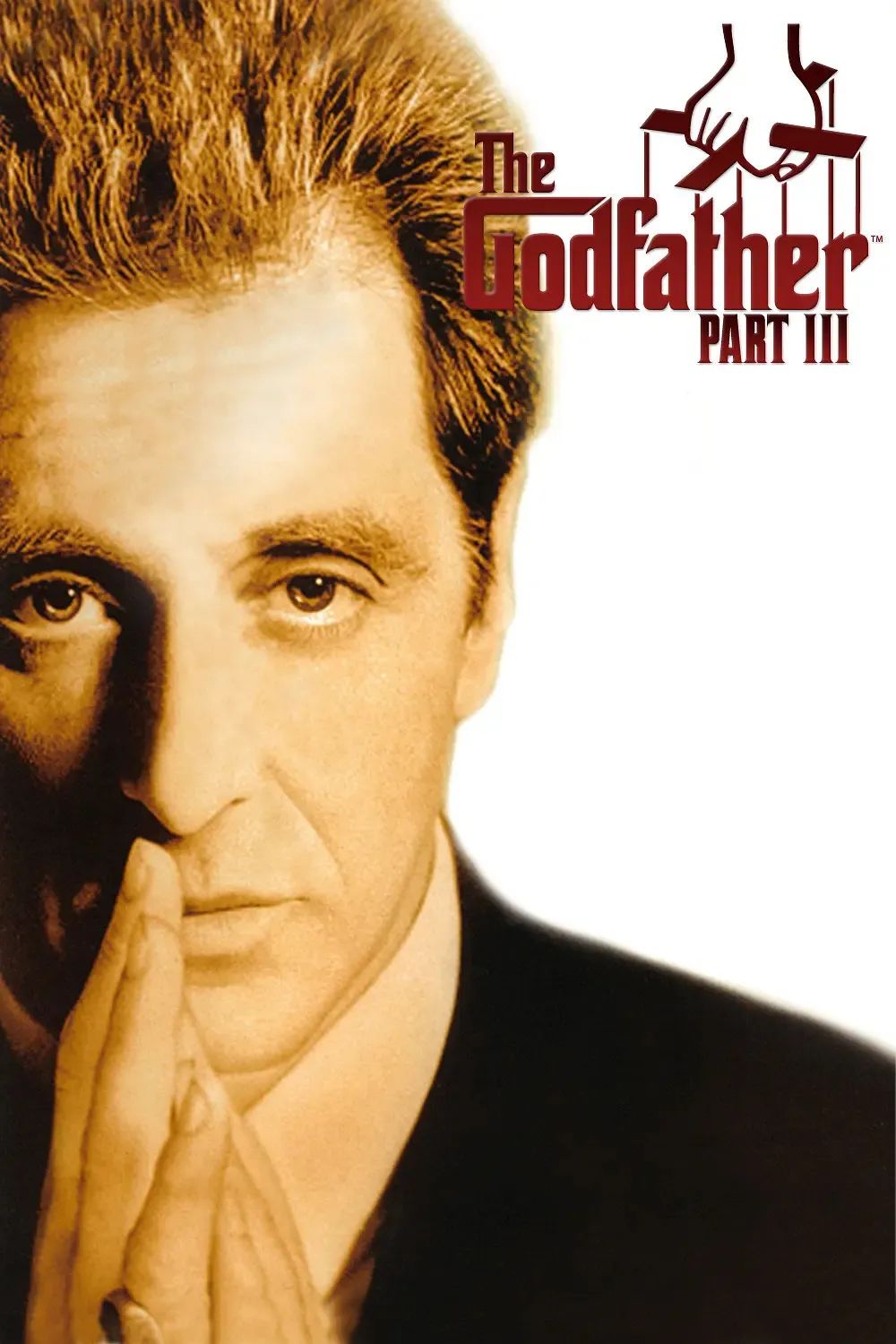
《教父3》海报
Q:
您为什么如此坚持重剪《教父3》?
科波拉:
最开始这部电影是计划圣诞节那天上映的,这个安排野心勃勃,因为这么一来必须缩短后期制作的时间。正常来说,一部电影从拍摄结束到上映需要九个月的时间,跟怀孕的时间一样长。我们当时要把这段时间缩短成四个月,就必须请多位剪辑师同时工作。这很麻烦,因为每个剪辑师性情不同。我们尽全力保证影片如期上映了,我必须得说明一下,派拉蒙没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任何负担(当时制片厂的主管Frank Mancuso是位真绅士)。
但是成片之后,我还有些拿不准和不满意的地方。从片名开始,为了跟之前两部的片名保持一致,他们否决了我提出的名字——《马里奥·普佐的教父-终章:麦可尔·柯里昂之死》(The Godfather, Coda: The Death of Michael Corleone)。

《教父3》剧照
这太讽刺了,我当时花了好大功夫才说服他们把第二部的片名定成《教父2》(The Godfather Part II)。我那时候是受了苏联电影,尤其是《伊凡大帝》(Ivan the Terrible, 1944)的启发(这部影片由爱森斯坦执导,影片分为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分别于1944年和1958年上映-译注)的影响,那时候好莱坞喜欢给续集起《科学怪人之子》(Son of Frankenstein)、《基督山归来》(The Return of Monte Cristo)和《两傻大战科学怪人》(Abbott and Costello meet Frankenstein)这类的名字,保证观众知道这是另一部不一样的电影。
但是我从没想过要把《教父》系列拍成连续剧,我只想拍一部古典悲剧。这第三部影片不是一部续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章,就像音乐上所说的尾声。正是为了强调这层含义,我和马里奥·普佐才坚持要将影片命名为《麦可尔·柯里昂之死》。

《教父3》30周年全新导演修剪版
《马里奥·普佐的教父-终章:麦可尔·柯里昂之死》
Q:
我认为有点讽刺的是,影片虽然以此命名,但是麦可尔·柯里昂在片中并没死。
科波拉:
是的,我和马里奥就是这样设计的:用片名宣布他的死亡,但是不在片子中呈现出来。因为他是以另一种方式死去的,那是另外一种死亡、一种更深刻的死亡。我觉得这样更有美感。
Q:
这样一来让他活下去反而更有悲剧色彩。
科波拉:
是的,因为死亡是最轻松的面对永恒的方式,死亡不是一种惩罚,只是一夜好眠后长卧不醒罢了。古罗马人处死奴隶最残忍的方式是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仁慈些的人会斩断奴隶的四肢,这样他们能快点死去。因为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临死前的等待,是必须活着去承受那些令人心碎的记忆,最痛苦的不是肉身的死亡,而是灵魂的死亡。
Q:
这也是德古拉的宿命。
科波拉:
是的,永生就是德古拉的诅咒。

麦可尔·柯里昂(阿尔·帕西诺 饰)垂暮
Q:
我感觉重剪的版本跟前两部的联系更紧密,新版的开头和第一部《教父》的开头呼应,结尾则令人想到第二部的结尾。
科波拉:
是的,没错。不过分为几部分的作品通常都这样。我能想到的有劳伦斯·达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重奏》、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或者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些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的最后一部基本都是建立在对前几部的重复之上的。
Q:
新版本除了开头和结尾之外您没有做太多调整,但还是让人感觉这是两部十分不同的电影。
科波拉:
电影是幻觉的艺术,一个细微的调整就会带来很深刻的变化。这很像我小时候用的汽油打火机:如果你加油太多或太少,或者你滑动滚轮的方式不对,都打不着火,但是某一下,不知怎么的,火突然一下就打着了。电影跟这个差不多:你得做很多细微的改变,才会实现那个幻觉,有时候只需要极小的改动。不过说到底,还是要观众去体会这个过程,因为影片本身不输出情感,情感是在观众身上产生的。

《教父3》剧照
Q:
您在重剪版本中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变化之一是加入了用眼镜杀人见血的一幕,为什么特意添加这一幕呢?
科波拉:
是为了强调这种奇特的杀人手腕:杀手没有武器,而他要杀的人刚好戴眼镜,眼镜就成了他的凶器!这也是对黑泽明的小致敬,他是第一个拍摄血喷溅而出的导演。我在《棉花俱乐部》(Cotton Club, 1984) 里也拍了类似的场景,那部片子里的凶器是刀,我重剪那部片子时把这这个场景也剪进去了。拍摄电影的那个年代,许多人都认为这太过于暴力。我对暴力没有特别的偏好,但是在对的时机、对的方式里,它可以有强大的力量。这也是黑泽明教会我的。

《棉花俱乐部》剧照
Q:
您觉得麦可尔·柯里昂这个角色跟您本人有相似之处吗?我觉得就他与权力的和家人的关系而言,他既在某些方面是您的化身,同时又代表着您拒绝和反对的一切。
科波拉:
人们总是觉得你就是你创作的人物。我拍完《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979)以后经常看到人们说我变得跟科茨上校一样狂妄自大了!的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些角色和我自己有点像,或许太像了,甚至让我觉得害怕,麦可尔·柯里昂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我比他情感丰富多了,也比他重感情多了。你可没法说麦可尔是个重感情的人……不过,在我看来他的确是个重情的人,只不过是方式不同,他并不像我这样直接表达情感,也比我冷酷得多!我太多愁善感了,这也是我作品最大的缺点。

《教父3》麦可尔·柯里昂(阿尔·帕西诺 饰)
Q:
现在一部以您拍摄《教父》为主题的剧集正在制作当中,由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扮演您。您要成为剧中人了,您对此感觉怎么样?
科波拉:
其实挺有趣的,如果几年前有人跟我说要拍一部我的传记片,我肯定会说我不想跟它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很尊敬这部剧集的导演巴瑞·莱文森(Barry Levinson),他的很多作品我都很喜欢,比如《餐馆》(Diner, 1982)、《豪情似海》(Bugsy, 1991)和《完美盗贼》(Bandits, 2001)。而且由那么一位优秀英俊的演员扮演我,还是很令人激动的!所以我很想看看会拍成什么样。

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
不过有人告诉我,剧集里我的角色好像比较粗鲁,他总是骂人,我本人很少会用那些粗鲁的词汇,我会有意避免,尤其是在有女士在场的时候。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如果我的角色在女士面前说一个脏字,他每对谁说一次,就得给对方一美元!”这是我给他们的唯一一条要求,我不想影响这部作品的制作。
Q:
还有其他片子您留有遗憾吗?有您想重新剪辑的吗?
科波拉:
有的,还有几部片子我想要制作新版本:《没有青春的青春》(Youth Without Youth, 2007)、《泰特罗》(Tetro, 2009)和《从此刻到日出》(Twixt, 2011)我都想做一些小调整。

《没有青春的青春》(Youth Without Youth, 2007)

《泰特罗》(Tetro,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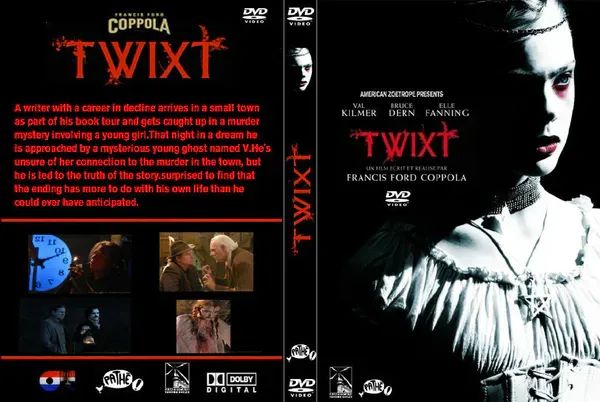
《从此刻到日出》(Twixt, 2011)
我很想把 Twixt 的片名换成 Twixt: Twixt Now and Sunrise。还有部片子我很想修改一下,但是以后可能没机会了,是《没有伊佐的生活》(Life Without Zoe)(该短片系多段式电影《大都会传奇》(New York Stories, 1989)中的其中一段,另外两段分别由伍迪·艾伦和马丁·斯科塞斯执导原文注)。制片厂觉得这部片子太长,所以重新剪辑了,他们完全毁了这部作品。但是它其实比它呈现出来的样子有趣的多。您看到了吧,很多片子我已经无权修改了!
伟大的马丁·斯科塞斯、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法国电影资料馆等许多人、许多机构都在努力寻找和修复那些拷贝丢失或无缘面世的影片,但是我们也应该关注另一类“遗失”的作品:就是那些因为缺少资金或其他形式的支持以致胎死腹中或未能制作完成的影片。您看奥逊·威尔斯,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一直在为能够完成一部作品而奔走抗争。不过,他六十年初拍摄的几部影片——比如《审判》(Le Procès, 1962)——都堪称杰作。包括金·维多在内的许多电影人都曾因为现实原因放弃过他们十分珍视的电影项目。

《审判》(Le Procès, 1962)海报
Q:
您呢?有没有没拍成的电影给您留下遗憾的?
科波拉:
在皮克斯动画成功之前,我曾想过拍摄《匹诺曹》。那个时期3D动画与真实影像的结合还处在萌芽阶段,可惜最终电影并没有实现。我曾经有两到三部电影都是因为预算的问题没有实现最终的拍摄。

《旧爱新欢》(One from the Heart, 1981)剧照
Q:
您对《旧爱新欢》(One from the Heart, 1981)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刚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嗤之以鼻,但如今却有人认为它是您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科波拉:
从电影技术发展方面来看,这部电影出现得太早了。我更希望它是直接在现场一镜拍摄而成的(科波拉将这种拍摄方式称之为“现场电影”(The Live Cinema),原文注)。但这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无法实现,我们那时还依赖于胶片,而每卷胶片只有几千英尺,因此拍摄多于十分钟的镜头是不可能的。
有声电影出现后,茂瑙曾说:“有声音是好事,只是它来得太早了”。对于《旧爱新欢》来说,我想说数字电影到来得太晚了!”我们可能仍然会运用迪恩安·达沃拉利斯(Dean Tavoularis)和维托里奥·斯托拉罗(Vittorio Storaro)绝美的镜头和画面,但是声音和配乐还是应该现场录音,因为这样做才更加符合这部电影的表达。另外,这部电影最美之处在于汤姆·威茨(Tom Waits)的配乐和歌曲,它在演唱者的歌喉和表演下熠熠生辉。然而,在那个年代,好莱坞没人再做歌舞片了(十年之后,随着《芝加哥》的出现,歌舞片才重回大银幕)。要知道,所谓“机会”,其实是 “时机(timing)”的问题。做的太早或太晚,你都得完蛋。

芝加哥 Chicago (2002)剧照
Q:
您是否一直对电影技术的发展保持关注?
科波拉:
是的,只要我还对电影有兴趣我就会一直对它关注,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能更加突出演员表演的技术。正因如此,我一直有做“现场电影”的想法。
所谓“现场电影”,是指借助数字技术,将话剧的连续时空与电影剪辑有机结合在一起。人们应该恢复对表演在电影中的认可,过去,电影表演主要是由剪辑和后期制作而不是由演员决定的。如今,通常是剪辑师为演员创造表演节奏。但是我相信,电影如果没有演员的良好发挥就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演员应该被认为是电影的共同作者。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演员和编剧是一部电影的氢氧元素。

《教父》拍摄现场
Q:
您恢复了颇具野心的新作《大都会》(Megalopolis)的制作,这部电影好像有着巨额预算,它是如何制作的?
科波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部电影确实很花钱(剧情讲述一名建筑师想在被灾难摧毁的纽约城的废墟上建造一座乌托邦城市,原文注),预算可能跟雷德利·斯科特或者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差不多,这两位都当得起巨额投资。
但眼下一切都因为疫情暂停了,甚至我的葡萄酒公司都停业了。不管怎样我都会想办法拍摄这部电影的,也许是不寻常的,新颖的方式。现在的电影产业一片惊慌,影院关了,我很心痛。越来越多的演员选择出演广告,一些演员为了拯救事业而不加选择的参演电影,或许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也有可能是一些他们过去从没想过会出演的类型片。
至于我,则和我的家人被隔离在纳帕谷。这已经很幸运了,此时有些东西比我们的事业还要令人忧心:比如亲友的健康。纽约和巴黎的人们所经历的远没有美洲中部和非洲人民那么糟糕。当我看见那么多洪都拉斯的孩子都在苦难之中时,我就想,那是比我的事业发展更要紧的事情。

科波拉与女儿索菲亚
Q:
《大都会》是您梦想已久的一部电影,而它本身讲的就是一个乌托邦的故事不是吗?
科波拉:
是的,乌托邦而非反乌托邦。法国许多十九世纪的哲学家,比如夏尔·傅立叶和亨利·德·圣西门都曾构想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人类共享文明成果的世界。而我相信这个世界。
比起霍布斯我更信仰卢梭。我认为所有问题都是伴随文明的建立而产生的,但是人类的本质是好的,就像我们在疫情中看到的一样。帮助他人的意愿和团结战胜了自私。人类进步的大事件与改善他人生活的意愿不可分割。唯一让人对此产生怀疑的原因,则是信息资讯总是强调或者夸大负面的东西。在这样的滤镜下看待事物只会让人担忧和恐惧,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当下,观察那些日常的现实,你会发现今天的世界比八百或者四百年前变好了很多,未来还会越来越好。
正因如此,我想要《大都会》的观众们想:“我多么希望世界成为这样,世界就应如此。”我想要参与这样的未来,并不是信口开河,我的的确确是这样相信的。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Q:
这个项目停止于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之后,这部电影是否会表现美国和世界在那之后的经历?
科波拉:
是的,当然。我想做这部电影很久很久了,并且不停地放下拾起。我越来越感受到它的必要性。我构想了片中一些纽约暴动的画面,跟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情形很相似。
您知道我并不认为自己天赋繁多,但有一样我很确定:我看得见未来(笑)。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后的人们还是会对我的电影有兴趣。这部电影有关作为大家庭的人类世界。您别说,我和您在遥远的过去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祖母,所以说我们是一家人。在家庭中胜于一切的不是爱,而是友谊。我并不完全懂得爱,它过于神秘。但是友谊却是触手可及的。蒙田在他关于婚姻和家庭论述中对友谊做过更精妙的描写。
Q:
您与好莱坞总是保持着距离,尤其在《造雨人》(The Rainmaker, 1997)之后,您完全与之背离。如今的好莱坞对您意味着什么?
科波拉:
我爱好莱坞。我的整个事业全要感谢它。好莱坞一直都对我不薄,它先后给了我做编剧和导演的机会。但是我背叛它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愿拍两次同样的电影。
我永远都希望一部电影可以教会我一些东西,我希望它每次都任由我去探索新的领域。只要去看《教父》《现代启示录》《旧爱新欢》和《斗鱼》(Rusty James, 1983)就知道:每一部作品的形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一直认为我每一次都能够从头开始,可能甚至都不清楚将会进入怎样的历险。我从不愿意自我重复,不愿探索相同的风格或类型。

《现代启示录》剧照拼图
Q:
您在导演前三部电影的时候都说您自己又重回初学者和学生的身份,您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吗?
科波拉:
是的,完全是。总是有人邀请我去讲今天所谓的“大师课(Master Class)”,这是玛利亚·卡拉丝(Maria Callas)为了她的课发明的词。我总是说我不想、也不能做一节“大师的课(Leçon de maître)”。我想要的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因为在电影行业,我们永远都是学生。我的年龄并不意味着什么。我真的觉得,比起一个二十岁的人要跟我学的,我应该跟他学的东西要更多。我愿意为了了解我们曾孙子辈的人的电影付出任何代价。这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电影这个美妙的发明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Q:
在拍摄《没有青春的青春》、《泰特罗》和《从此刻到日出》时您作为“学生”都有哪些心得?对之后的电影有何影响?
科波拉:
我们随着时间学会的唯一东西是:我们往往会选择一些道路而不是另一些,有些事情我们做起来比另一些更加自在。如此累积,我们就建立了规则和方法。比如说,对一名导演而言,在拍摄过程中,没有比坐在监视器前、摄像机旁更加合适的位置了,因为这样演员就看得见你从而演给你看。
今天的我与年轻的我相比最重要的区别是,今天的我积攒了一大堆不同的经验。我在和戈登·威利斯(Gordon Willis)工作时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跟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学到的则与之相反!我就是如此收获了大量不同的、自相矛盾的课程。它们塑造了今天的我,一个虽然年事已高却仍旧充满了激情的我。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始终没有放弃“现场电影”的科波拉和他的学生们依此想法在2016年创作了《远景》(Distant Vision) 。

编辑:十一
在学习了
-FIN-
原标题:《《电影手册》x 科波拉大访谈:最后的乌托邦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