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榷︱深求其故,自出议论:杨雄威评《思变与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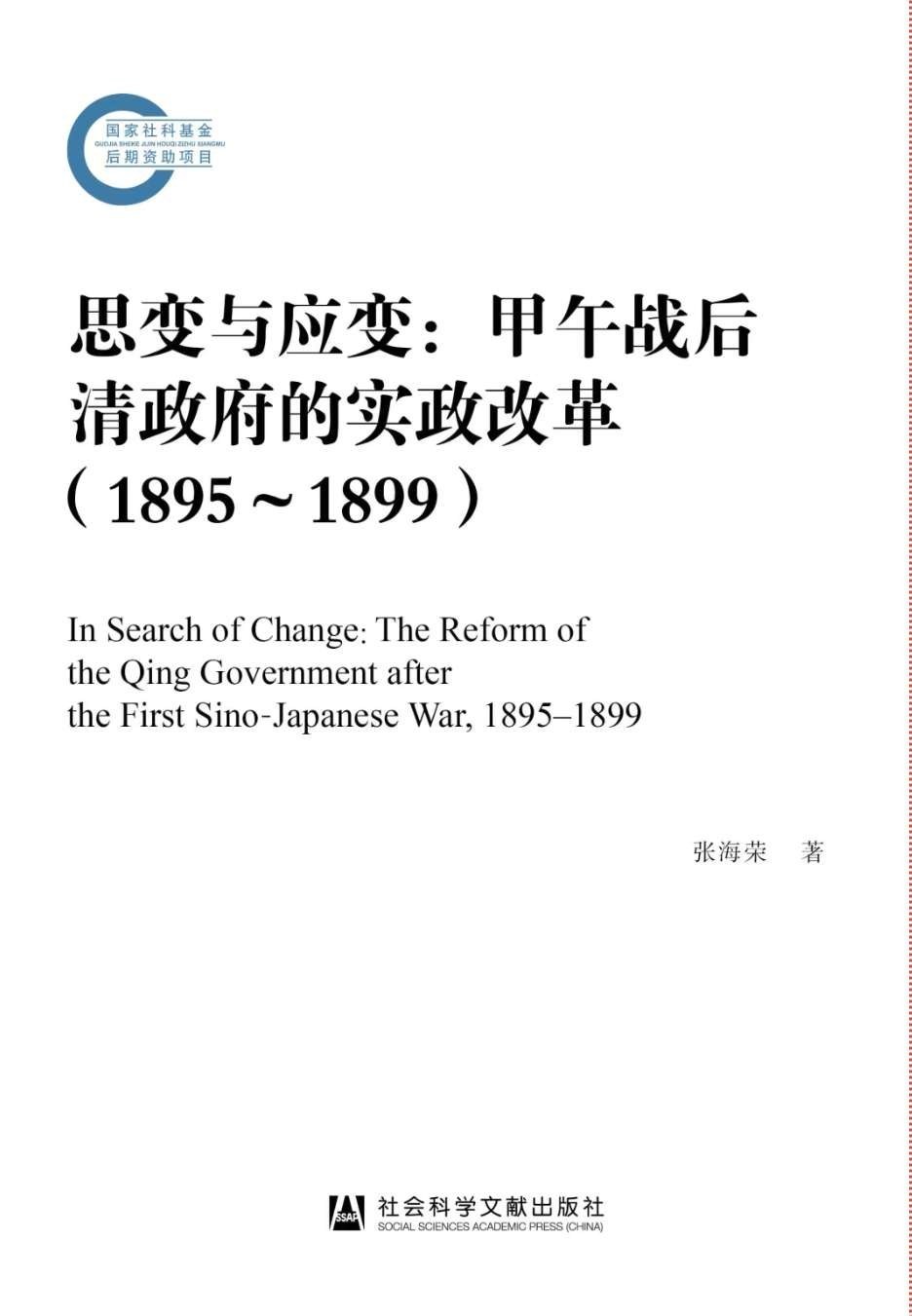
《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张海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443页,158.00元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甲午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接续这一历史的是几年后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清廷又经历了庚子之变的致命打击,最终痛下决心宣布施行“新政”。在这个关于晚清改革史的宏大叙事中,有一个环节始终静悄悄地隐藏在“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和“己亥建储”这些“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背后,它就是1895-1899年的“实政改革”。张海荣博士独具慧眼,在其新著《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一书中全面而详实地将这一段重要史事公之于众。笔者不揣浅陋,勉强草此小文,向同业读者聊作推介。顺便在史观和具体论证方面略抒陋见,冀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
本书分为导言、正文七章和余论。本节尝试依次摘要介绍,并根据情况稍作评点。
在导言部分,著者摘要讨论问题的缘起。开篇即指出晚清改革举措相对于政治事件的暗淡,进而指出,在康梁变法的背后,尚有另一个素为学界忽略的改革路径,即清政府主导的“实政改革”。“实政”一词出自原典,1895年一份上谕即有“力行实政”之说。这段实政改革,由1895年始,至1899年终,上与洋务运动衔接,下与清末新政承继。三个阶段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晚清改革史。用著者自己的话说,研究这一时段的改革,“既有助于系统认识戊戌前后清政府的改革动向,切实评估清政府可能的决断力和行动力,深化对百日维新、戊戌政变的相关研究,也有助于增进对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之间的过渡时段清朝改革的考察,使晚清改革史研究贯通一气”(第3页)。简言之,导言部分问题意识清晰明了,一针见血,令人信服地提出“实政改革”概念并阐明其学术价值。
第一章讨论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失败。在著者看来,洋务运动、实政改革和新政是晚清递相接续的三个历史阶段。故而在开头一章回顾洋务运动,是“使晚清改革史研究贯通一气”的必要步骤。在这一章,著者将洋务运动概况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军事、外交改革和洋务人才培养为重心的起步阶段”(第28页),二是“军工建设持续推进、经济建设升温的深化阶段”(第30页),三是“以海军建设为最大亮点,重工业稳步推进,轻工业日益活跃的高潮阶段”(第33页)。这是著者“依据现实需要、认识程度和发展重点的同”的标准划分的。著者的结论是,“洋务运动虽然在若干层面取得一些枝节的进步,但总的来看,过于地方化和分散化,既未实现扭转国运的关键性突破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无力改善清朝应对外患的捉襟见肘。”(第58页)这一结论,间接回答了洋务运动是否失败的争论,也为接下来评判1895-1899年的实政改革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参照物。
第二章考察甲午战后的朝野动向与清政府的改革大讨论。著者指出,甲午战后的这场讨论是“清朝执政集团在重要历史关头,就关乎自身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核心议题,展开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系统讨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年间国家改革的总体方案及其施政重点”(第60页)。著者对这场大讨论做出一个重要论断:改革的“原动力在中央,而非地方”(第24页)。需要指出的是,著者可能为了凸显实政改革相对于洋务运动的进步而有此论。实际上,从书中论述可以看出,部分地方大员对实政改革的呼声亦彰彰可考。甲午战争创巨痛深,无论中央地方还是在朝在野都有深切触动,似不必仅仅依据上奏的先后顺序厚此薄彼。当然,著者这一论断在更具体的改革条目层面确有佐证。如在盘点练兵问题时,著者的观感是地方督抚大多不予响应。考虑到中央层面对练兵的迫切需要,说中央动力在此问题上大于地方自无不妥。
第三章讨论练兵问题。首先梳理了北方新军的发轫,即从胡燏棻的定武军到袁世凯的北方新军;继而又考察了江南自强军与湖北护军营洋操队等南方新军的并起;随后又陈述了反映清廷中央军事集权的武卫军的组建。所述各军的建立和发展,皆注意到人事关系的影响,其余各章亦无不如此。可以说,本书忠实践行了著者所说的“新写法”,即:“将‘人’还原到历史情境中,致力于刻画清朝实际政治运作的特点和改革背后的种种隐情,包括改革方案的设计、讨论与调整,改革决策者的素质、行为与心理,各派政治势力的构成、取向及其对改革进程的实际影响,资金、技术、人才诸问题的解决,社会舆论反响,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等等,尤其关注政坛里层、官场规则对于改革进程的左右。”(第23页)需要指出的是本章引用奕䜣“内外臣工条陈自强之策,莫不以练兵为今日第一要义”一语(第107页)。本章以事实陈述为基调,并未涉及舆论和观念层面的内容,对此语准确性亦无交代。但如前文提及的,根据著者的统计,练兵问题实际并未得到地方督抚的普遍响应。故在引用此语时似应做适当说明,以反映当时朝野在练兵问题上所呈现的另一种观念乃至历史面相。
第四章考察铁路问题。著者认为甲午战后清政府将铁路建设视为一项国策,在此认知下出台了芦汉铁路和津芦铁路“一干一支”规划。本章对芦汉铁路的办理进行了详细论述,对参与其间的历史人物盛宣怀等人的考察细致入微,分析引人入胜。在此基础上,清晰展现了围绕芦汉铁路形成的复杂微妙的人事和外交关系。王汎森先生曾指出当前史学研究存在“人的消失”现象,笔者认为这一弊端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学界史料解读能力的退化。就此而言,本书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可谓难能可贵。可以说,本章对芦汉铁路的论述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著者的史学功底和大著的厚重。从金冲及先生所作的序中可知,张海荣博士此书经历了十余年的磨砺,足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芦汉铁路老照片
第五章考察开矿问题。甲午战后办矿以开源的观念充盈朝野,本章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矿务钩沉索隐,考察了陈宝箴主持湖南矿政的史事,并论述了晋、豫、川等省矿政的误入歧途和北洋两大矿局的陨落。正是以此广泛的考察面为基础,著者从多方面对比了实政改革相比洋务运动时期在矿务方面的进步,结论自然扎实可靠。同样,因为著者对此时段的矿务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故能以小明大,通过矿务问题举重若轻地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第274页)。顺便指出,当今学界个案研究盛行,市面文章的论述对象多局限于一隅之地,而又缺乏比较视野,结论只得强行拔高,往往与正文脱节。此书适足为今日史学界一大榜样。
第六章考察银行和邮政问题。银行与邮政本非一事,本书巧妙借用时人“办银行以塞漏卮,兴邮政以浚利源”之语(第275页),将两题并为一章,分别围绕盛宣怀和赫德两人展开论述。尤可称道的是,著者对张之洞在开办银行问题上的态度及其与盛宣怀关系有整体把握,故对细节的论断也驾轻就熟。如光绪帝特旨批准盛宣怀开办银行后,张之洞来信祝贺,著者一眼看透其中“酸意”(第282页)。章太炎所谓“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对这类人物心理细节处,非有对历史情境的洞察实难落笔。

盛宣怀

张之洞
第七章考察此时期的教育改革。先论述了从缓进、激进到保守的政策转变,继而勾勒各地改革实况,随后对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进行了细致的个案研究。对时务学堂的考察以新旧势力之间的博弈为主题,对京师大学堂的考察则进一步从国家政策层面展开。最后著者将此时期曲折多变的教育改革的主旨概括为“实学”二字。应当注意,此时所谓的“实学”不仅仅包括今人所熟知的西学,也常常包括传统的“经史之学”。相对于空疏的八股之学,经史即是“实学”。也就是说,实与虚的区分未必如今人所见,故而需要特别解释。
本书余论部分对甲午战后至庚子事变前清朝改革进行了总结和重新审视。著者借用民国学者陶孟和之语强调历史事实的连贯和衔接。晚清改革史在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之间存在一段缺口,即本书所研究的1895-1899年的实政改革。故此这一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提示性。在这一贯通性视角下,三个历史阶段在相互比照中确立了自身的历史定位,进而也勾勒出一部完整的晚清改革史:“晚清改革史,既不是在同一改革模式下的持续推进,也不是一连串截然不同的改革模式的相互衔接……晚清改革史就是由这样一系列从认识、实践、总结,到再认识、再实践、再总结的承继递嬗过程所构成的。”(第402-403页)。在史学“碎片化”现象泛滥的今日史学界,对一个重大历史进程做整体判断已殊为不易。
二
清晰的问题意识加上丰富的内容和扎实的考证,将本书视为近年来晚清史少有的力作,断无疑议。笔者对书中具体研究领域涉猎无多,原本无力置评,不过拜读之时多次感受到与著者在治史路径上的差异,故而希望一述谬见,供著者和同业读者批评。
本书囊括了练兵、开矿、办银行、兴邮政、改教育等实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不过,正如著者导言中指出的,1895年的力行实政上谕中所列举的是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裁除冗员等十四项内容(第2页)。书中的结构,固然抓住了其中的荦荦大端,但也难免遗漏不少“委曲小变”(借司马迁《史记》语)。这或许是由于专著章节结构所限,但这些“不可胜道”的部分淡出研究视野,是否会影响对这一段实政改革的总体评价?练兵、开矿、办银行等从现代化视角来看,的确称得上诸多改革项目中的荦荦大者,但诚如著者提到的,本书所关注的改革恰恰是相对传统的那一派的路径。故而,1895年上谕所罗列的十四项内容,如果以当时视角排序的话,矿山、银行、邮政、教育等是否位居优先地位恐怕都要打个问号。在这个问题解决前,将近三分之二的改革内容排除在讨论之外,难免影响对此次改革全貌的评判。若以新旧两分,实政改革在设计上原本兼具中国旧法和泰西新法,且条目以旧法居多,但本书各章考察的对象则以后者为主。是旧法改革多未实行,还是成效不足,抑或新法创设与添置执行更力,过程和成效更受瞩目?诸如此类的解释当有助于对这段实政改革的整体理解。
在此详举一例,正如著者所概括的,此时“富国强兵”是朝廷的首要关注对象。清廷受辱于蕞尔小国继而发愤图强,其心理自不难理解。问题在于,传统中国在解决富强问题时是如何着手的?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的直接意图是对西夏用兵。对于宋神宗而言,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获得新财源以用于兵饷。因此,王安石变法难逃与民争利之嫌,变法者不得不背负“小人”的污名。无独有偶,明季张居正改革亦以税收为核心目标,以至于饱受“聚敛”之讥。据此推导,如果晚清朝野在财富观上没有决定性的理论飞跃,其富强之术基本上也难以摆脱传统思维框架,势必要重点围绕财政的开源与节流问题下工夫。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没有强大的财政支持,就不会有充足的兵饷,也就无法做到强兵。就上述十四项改革而言,铸币、关税、厘金、冗员、南漕、兵员等等内容,无不与财政收支直接相关,恰恰多为本书舍弃不顾(此处就章节结构角度而言,实则著者在书中有所交代)。
传统中国的财富观一如司马光所见,天下财富总量是恒定的,非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故此富强二字从这条思路贯穿下来,意味着要强兵便须聚敛。比至近代,在华传教士率先在“富强”二字内注入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知识,中国士大夫的富强观逐渐受此浸淫,开源之法大增。不过,这一影响具体进程如何,在此次实政改革中有何体现,恰好需要借助对诸多改革内容的统一观照才能得出确切结论。
1895-1899年的实政改革有强烈的应急色彩。何时复仇姑且不论,当下自保已迫在眉睫。相应地,其最为紧迫的改革内容自非练兵莫属。正因如此,此时的国家财政问题便空前突出。1898年《定国是诏》中谈及当下弊病时首先便提到“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即是此理。因此问题就来了:非有充足财源不足以支持新兵的编练,而丰富财源又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急一缓,自相矛盾,是清王朝必须面对的一个悖论。1895年的力行实政上谕中专门提到实政改革宗旨是“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第75页),但在现实层面“急务”与“本源”能否兼得,实在大成问题。疆臣陶模之子陶葆廉在给锡良的上书中写道:“国家推行新政,原欲扶危定倾,无如百事竞兴,胥资财力,未收寸效,已损本根。其立名最正、耗帑最巨而酿祸最不可测者,莫如添练新兵之策。”随后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得出一个结论:“兵愈练,饷愈匮,终岁诛求,则舆情离散,一朝不给,则骄卒必哗,是以扬威尚武之虚名贾瓦解土崩之实祸。”(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第135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669-670页。)此说并非庸人自扰,实际上陶葆廉的时政著述在晚清颇为朝野称道。更有说服力的是,他的这一说法随即应验。清末一系列新政看似积极有为,但也大大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以致民怨沸腾,最终花费巨资所编练的新军发生叛乱,导致大清王朝的“瓦解土崩”。练兵未及救国,先已亡国。且其影响并未就此止步,民国时期天下大乱,严复推源祸始,将眼前的“武人世界”归咎于晚清的练兵。更有甚者,严复还对其当年高唱“富强”一事心生悔意。这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晚清的重事功轻义理是时势所迫,由此推行的“实政”也多是急就章,自然难言必成。从一个更长的时程来看,近代中国正是在“一摘再摘”(章士钊语)中实现蜕变和重生的。
复略举一例,本书将教育放在最后一章进行讨论。从当时不少人的论述可知,教育所涉及的“人才”问题至关重要。陶模即谓“根本莫要于取士用人”(第92页)。其背后的观念直到民国还十分流行,但学界通常只是将此问题简单置换为现代知识体系内的“教育”问题,如此一来,不仅其重要性大打折扣,且有乖时人本意。
概言之,单就本书的章次安排而言,似乎更多反映了一种“现代眼光”。
更能体现著者“现代眼光”的是书中所用的大量现代语言。比如“改革”“经济建设”“重工业”“轻工业”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概念固然更便于今人对历史的理解,但稍有不慎,又有可能遮蔽历史的本来面目。如书中提及“经过朝廷高层的改革大讨论,清政府正式将发展铁路定为国策”(第162页)。笔者以近年来做观念史和概念史的敏感,第一反应是想要找到当时关于这一“国策”的论述。就像南宋对“国是”的讨论以及当代称“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提示的那样,“国策”一词,很可能有其观念史上的特定含义。但经初步检索,当时文献中似无此确论。另,第六章讨论银行与邮政时,著者提到“经济硬实力”和“经济软实力”之说(第285页),其实就算以现代术语而论,铁路、矿业、银行和邮政在行业上各有所属,若分别归入“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列,便觉勉强。
以现代眼光看历史,固然能享时人所不能享的后见之明,但似乎也容易远离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情境”,相应也容易苛责古人。比如书中评价洋务运动时说“这些努力仍嫌稚嫩与肤浅”(第36页),检讨北洋海军时说其“创办伊始,就未能建立完善的军事制度”(第47页),在谈到北洋海军建设的军费问题时,批评说“一旦外部的压力有所削减,清朝中央又转入无所作为、因循苟安”(第58页)。从特定角度来说,这些批评似乎并无不妥,可一旦稍有过当,便可能妨碍“还原”被批评者所处的“历史情境”。
举例而言,著者在总结清朝战败教训时,其中一条提到“大战当前,仍继续筹办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置国事于不顾”(第56页)。随着战况的演变,慈禧太后一再压缩自己寿宴的规模,恰好说明办寿与开战确实有一定冲突,但也说明慈禧太后并不拒绝做出让步和调整。总之二者未必达到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其实,慈禧太后的大寿究竟是个财政问题,还是个作战意志问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战事影响究竟几何,都需要进行严肃的讨论才有可能获得准确的理解。
又如书中提及恭亲王在铁路问题上的“推诿”(第36、38页)。按,李鸿章主张兴修铁路,希望恭亲王奕䜣游说两宫皇太后。但奕䜣表示“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奕䜣婉拒李鸿章,说是“推诿”似无不妥,但问题是此事涉及清廷高层之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是谏言的话题、时机和尺度等问题,属于需要专门考察的政治文化史题目。因此,与其批评奕䜣推诿,不如平实陈述为其自认无把握说服两宫。

李鸿章

奕䜣
论断本已不易,批评尤难。诚如著者指出的,此时段“内在施政理路的一贯性”是“富国强兵”。(第22页)据此似乎需要追问的是,在这一段实政改革中,以富强为目标的开源与节流究竟成效几何?但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又不成立,因为揆诸二十四史,一国的富强通常需要数十年时间,以五年计对施政者是不公平的。从这个角度说,对这段实政改革的“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第24页),其提示性或者说其“史鉴”功能实难高估。著者在导言中曾引用其师茅海建教授“看得最少的”是中国人所犯的“错误”之说(第23页),笔者倒是觉得,历史学家似乎更容易发现“错误”,而不容易宽恕。清人魏禧有云:“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其实相当有限,盖因历史决策者所掌握的大量一手信息早已随风而逝,后人的判断依据往往处在严重不足状态,品藻历史人物多以结果论英雄,难以“忠恕之道”待之。
当然,此节所述异见,皆是学术取径不同使然,很大程度上是见仁见智之事。既然史无定法,学者尽可各奉所学各遵所好。
三
梁启超尝借用朱子“当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一语,主张“学者凡读书,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议论为主,久之触发自多,见地自进,始能贯串群书,自成条理”。(梁启超:《学要十五则》)读书认真若此,著书更是马虎不得。作者需要作出无数论断方能成书,个中艰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即便如此,也很难一切圆满尽如人意。故而唐人韩愈有“且惭且下笔”的自嘲。著述者别无他策,惟有时刻警醒而已。
不难发现,本书参考了大量公私文献,资料详实,可谓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如对胡燏棻上书的代笔问题,著者即通过翁同龢日记等材料进行佐证,又如对参与议复的地方大员奏折清单逐一开列,均是史料功夫。此类案例,通篇皆是。但历史学难在需要句句征实并深求其故,一些重要论断尤其如此。如前文提及,著者对实政改革曾有改革的“原动力在中央,而非地方”的论断,揆其论据,似仅在于大讨论“是由光绪帝发起”(第24页)。但光绪帝作为决策者,其思想资源和决策依据恐怕才是更上游的“动力”。另,前文提及“国策”一词,征诸著者本意,当是指铁路建设“被正式纳入国家决策层”(第169页)。此说若针对甲午战前的铁路政策尚属圆融,若无此条件限定,则其他各项实政改革被纳入国家决策层的所在多有,铁路自不能独称“国策”。而若各项皆称国策,则此二字极易泛无边界。本书主干内容下笔颇有分寸,罕有此类论证不妥洽处。不过在一些旁干侧枝上,因疏于论证而致问题稍多。
史学无闲笔,闲笔处往往疏于论证,而疏于论证处最易犯错。仍以对甲午战败“教训”的检讨为例,著者指出李鸿章“因顾忌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和低估了日本开战的决心”而坐失先机。有不少人都提到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对甲午战争的影响。特别是那句“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似乎成了慈禧太后为一己之私阻挠对日作战的最佳注脚。然而细究之下,慈禧太后是否说过此话其实大可质疑。战争伊始,慈禧太后并无主和的表示。正如李鸿章会低估日本的开战决心,中国朝野也大都低估了日本的实力。如能一战胜之,大可以树国威,小可以助寿兴,何乐不为?同样,李鸿章一开始是否顾忌慈禧太后寿辰事,既需要道理上的解释,也需要材料上的证明。
著者检讨的甲午战败诸多原因中,其中一条还提到“各省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长期坐视北洋孤军奋斗”(第56页)。此说若用来批评庚子之变时的“东南互保”,自无问题,但以此批评甲午战争中的地方督抚,似乎有罚不当罪的嫌疑。若要坐实这一罪名,理应附上疆臣拒绝调遣甚至拒不勤王的史料证据,并说明具体情境以便读者把握其行为的“恶劣”程度。若谓刘坤一在接到调令之后故意迁延不前,亦当对其所述“借口”做考察与分析,以免落入前人窠臼,不惟厚诬古人,亦且自蔽视野。
在论述“公车上书”时,著者引用时人的说法,称其“声势最盛、言论最激”(第66页)。公车上书是在野士子自发组织的联合上书,从社会传播角度说其“声势最盛”似无不当,但“言论最激”之说严格地讲并不是事实。最明显的就是御史安维峻的上书,直接点名慈禧太后,其言论激烈程度远在此次上书之上。由于种种原因,时人的说法每每失于偏颇,引用时若不特加深求和说明,就难免受其连累。前引奕䜣“第一要义”之说便是如此,其意本在进言,自然要挑有利证据讲。
又如著者谓:“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不得不承认,海防筹办多年,‘迄今尚无实济’,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第44页)之前海防“无实济”,固然可以推导出需要进一步“大治水师”的结论,但也可能产生相反的顾虑:既然所练海军已被实战证明“无实济”,那何必将大量经费花在此处?实际上,甲申战后,左宗棠上奏呈请调拨海军军费,当时尚未亲政的光绪帝在模拟御批中即谓“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建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4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32页)这条史料提示,所谓的“清政府”在海军问题上的意见可能并非铁板一块。后来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在甲午之役全军覆没,有批评者将矛头指向翁同龢主政户部时在财政拨款问题上的作梗。但平心而论,对于清廷的财政负担而言,现代海军就是个吞金兽。只要结果是败局,则无论多少财政拨款都会被后来人视为投入不足。同理,所谓的海军“大治”与否也难有定论。实际上,对于当政者而言,海军拨款涉及一系列海防、塞防的战略预判以及对和战大局的判断,更不用说一国财政还要用于军事之外的方方面面。诚如书中所见,北洋海军的壮大与主管海军事务的醇亲王奕譞有关,正好提示其背后特定的机缘巧合。
本书的宏旨在于晚清改革史,构思宏阔,气象磅礴。规模越大,工作量越大,越难免百密一疏。笔者本节所列诸条,固属吹毛求疵,且亦不免为个人喜好左右之处,但所涉皆为论证环节,是各种史学研究取向都不可或缺的工作。鉴于其具有广泛的共同讨论空间,故而强为杂凑一节以就教于方家。
结语
概言之,张海荣所著《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一书以1895-1899年的实政改革为研究对象,补足晚清改革史缺失的一环。其思路清晰流畅,规模宏阔可观,不愧是近年来晚清史研究难得的佳作。无怪乎金冲及前辈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开篇即以“十年磨一剑”诗句相嘉许。尽管以不同史观而言不免见仁见智之感,且文中个别细节在论证层面不无可议,但无疑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