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帝国”的幽灵在美国
1958年夏季的中东地区,被笼罩在西方列强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敌对气氛中,并伴随着激烈的政变与冲突。7月25日,美国报纸《奥斯汀国务家》(The Austin Statesman)刊载的一篇文章写到:
从历史的长远视角看,中东危机的关键人物不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而是一位骑着骆驼的人,名叫穆罕默德,他于公元570年出生在阿拉伯城市麦加。
穆罕默德创建了伊斯兰教。今天,这个宗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里最具活力的统合因素。
……
1000多年前,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世界,开启了其第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穆斯林的哈里发凭借着宝剑,把他们的信仰传播到整个北非和西班牙。直到公元732年,查理·马特在图尔斯山打败了他们对法兰西的侵略,否则整个西欧都似乎注定成为伊斯兰的一个省份。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听到开罗广播后,必然会想起这段历史,呼吁泛阿拉伯统一……
文章作者卡塞尔(Louis Cassels)或许不甚知名,但这篇文章却在半个月后就被另一家美国报纸《芝加哥卫士》(The Chicago Defender)转载。又过了半个月,《华尔街日报》的著名记者维克尔(Ray Vicker)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今天,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的强势发展,更多是被消极因素催生的,而不是积极因素。如果阿拉伯人的怨念没有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恐怕很难找到新的整合力量。
过去的历史,有许多案例能证明阿拉伯人团结起来反对某些东西的能力。当伊斯兰精神在公元7世纪第一次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时,狂热的穆斯林很容易团结起来对抗“异教徒”。
将眼下西方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矛盾,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文明冲突史”,这种脑洞大开的想法,无论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文件中,还是中苏谴责美国侵略中东的《会谈公报》(1958.8.3),都是看不见的。尤其是纳赛尔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往往被视作世俗政治的表现。那为什么在这两篇媒体文章中,纳赛尔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却与伊斯兰教紧密相连,甚至让两位作者联想到了1000多年前穆斯林对欧洲的征服史?答案或许在于卡塞尔说的那个词——“泛阿拉伯统一”(Pan-Arab unity)。
早在当年2月21日,埃及和叙利亚联合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埃及总统纳赛尔顺利当选阿联总统。阿联的成立,让美国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阿拉伯统一”的威力,美国各大报纸都充斥着对“阿拉伯帝国”的恐慌。(参见拙文《逐鹿、冷战、“帝国”:埃叙联合60周年纪》)随后,黎巴嫩的动荡,让美国朝野感觉到这个“阿拉伯帝国”下一步的扩张目标。7月15日,美国政府为了制止纳赛尔“吞并整个(中东)地区”,迅速出兵黎巴嫩,维系亲西方的夏蒙政府。但军事介入并没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获得胜利感。相反,面对一个个亲西方政权危若累卵的处境,再看看阿拉伯民众对纳赛尔的“狂热”拥戴,这位十多年前纵横欧洲疆场的五星上将,如今却陷入了万般的焦虑,无奈地对副总统尼克松表示:“(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站在了纳赛尔一边。”而对纳赛尔深恶痛绝的国务卿杜勒斯,也不得不承认纳赛尔“俘获了阿拉伯大众的民心”。

图1,1958年2月23日《洛杉矶时报》刊载的一张漫画,指责纳赛尔“吞并叙利亚”后,必然得陇望蜀,还要吞并其他阿拉伯国家。
其实早在纳赛尔登上政治舞台之前,阿拉伯人对统一的追求,就已经萦绕于美国人负面的历史记忆中。作为欧洲人的后裔,美国人也牢记着曾经令祖先们“心虚骨震”的“伊斯兰征服”。
“泛阿拉伯主义者妄图重建阿拉伯帝国”
一战结束后,脱离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盛行着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诉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汉志王国的费萨尔王子就向协约国提出了统一与独立的诉求。但协约国并没有答应,而是将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分割成好几块,分别置于英法的“委任统治”。出席巴黎和会的时任美国国务卿兰辛认为,敌视伊斯兰教的欧洲列强可算等到奥斯曼帝国崩溃了,又怎能把奥斯曼的故土交给另一个穆斯林王国呢?
欧洲列强对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偏见与敌视,也存在于当时的美国舆论中。例如,当时的美籍匈牙利人巴格尔(Eugene S. Bagger)认为“欧洲文明史就是东西方3000年的斗争史”。“萨拉森人”与拜占廷帝国的战争,十字军与塞尔柱人的战争,以及后来欧洲列国与奥斯曼王朝的斗争,都是东西方斗争的延续。如今,奥斯曼帝国被排斥于巴黎和会,是“西方对东方的压倒性胜利”。巴格尔认为,“巴黎决议最为伟大的意义,就是将亚洲驱逐出欧洲”。
但奥斯曼帝国毕竟战败了,奄奄一息,不会再成为西方的威胁。所以,美国舆论对伊斯兰世界的警惕,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新兴的凯末尔帕夏是否会重新掀起一场穆斯林对西方的“圣战” (拙文《失望与愤懑:今天的阿拉伯人如何评价凯末尔》) ;二、“泛阿拉伯主义”对“阿拉伯统一”的追求。西方对凯末尔的恐惧与疑虑只持续了不到十年,但对“泛阿拉伯主义”的敌视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1919年3月13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就指责“阿拉伯人在幼发拉底河谷地掀起的排外运动,杀了一些欧洲人”,并渲染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也被“阿拉伯暴徒”攻击。文章作者塞尔登(Charles A. Selden)由此上纲上线,认为“现在的泛阿拉伯运动就是阿拉伯人沿着土耳其人的老路,迫害小亚细亚地区的其他民族”。塞尔登还指责在巴黎和会上“看似温文尔雅”的费萨尔王子,实则“野心勃勃,试图统治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次日,《纽约时报》又刊载了题为“泛阿拉伯者”的短稿,在塞尔登的基础上,称“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为“沙文主义”(chauvinism)。可见,“泛阿拉伯主义者”的统一诉求,被描述成了地区扩张的野心,并伴随狂热的排外情绪。
后来,巴勒斯坦问题的持续激化,以及很多美国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偏向,也在滋生类似的看法。1936年12月,美国学者麦考恩(C. C. McCown)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站在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上,指责阿拉伯人“愈发喜欢叛乱与暴力”,并渲染道:“7千万阿拉伯人和2.5亿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关注……使得巴勒斯坦正被一个阿拉伯帝国(an Arabic empire)所包围。”1938年9月,《华盛顿邮报》在报道巴勒斯坦局势时,也加了一句带有明显立场倾向的“编者按”: “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目前搞的血腥冲突,已经导致圣地数千人的伤亡……”
说到这,就要谈谈“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与“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任何概念在实际使用中,都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有些人就经常把“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同起来。例如,1937年7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概括道:“重视泛阿拉伯主义的人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人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威胁西方的利益。第二类人信奉伍德罗·威尔逊的理念,认为应该给弱小民族自治。”但另一些人坚决区分这两个概念,尤其是对“泛阿拉伯主义”或“泛阿拉伯”字样予以污名化处理,以区别于所谓“正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图2,1941年5月,英军悍然入侵伊拉克,重新扶植亲英派的统治。但英国殖民者清楚自己在伊拉克不得人心。所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当月29日发布声明,支持阿拉伯统一,以安抚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这既反映了阿拉伯人对统一的广泛诉求,却也刺激了阿拉伯国家间的内部纷争,进而也带动了美国朝野对阿拉伯统一问题的思考。
1942年6月,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东方学学者吉本(H. A. R. Gibb)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
绝对的政治统一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的……民族主义者接受地区政治组织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泛阿拉伯主义者不同于民族主义者,想要政治上的统一。泛阿拉伯主义是一股无知,缺乏包容的爆炸性势力……不仅仇视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实践和理念,还渴望将欧洲人和犹太人赶入大海……泛阿拉伯主义不关心治理问题……也不关心阿拉伯国家的贫穷……
可见,吉本明确将“泛阿拉伯主义者”区别于“民族主义者”,并将其描述成狂热排外,无心求治的颠狂形象,进而也就否定了他们向往的“政治统一”。吉本是英国人,但他的观点得到了《芝加哥每日论坛》的及时报道,还在十六年后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财政部长安德森等人复述。
1943年10月,美国历史学家卡迈克尔(Joel Carmichae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认为:“只有统一才能让阿拉伯人在世界舞台上成长起来,好让他们走出战争的残骸。”但他认可的“统一”是有限度的。卡迈克尔希望阿拉伯国家组成“近东联邦”(a Near Eastern Federation),但要保持各个国家的“内部自治”,因为这是“最切实际的”。至于“泛阿拉伯主义者”所憧憬的“阿拉伯帝国”,在他看来则是“极端”和“虚妄的”。因为“泛阿拉伯主义者妄图重建阿拉伯帝国,打败异教徒”。
可见,吉本与卡迈克尔都对“泛阿拉伯主义”采取了污名化的定义,区别于他们所认可的“民族主义”与“统一”,其实质就是试图按照西方的标准与理念,规训阿拉伯人的统一运动。再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1958年夏季。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认为美国可以与中东的“民族主义”和解,但“泛阿拉伯主义”却是反西方、反以色列的。美国共和党成员马丁·大卫(Martin David)也明确反对将“民族主义者”混同于“泛阿拉伯主义”。他在《纽约先驱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民族主义者”维护本国“自由”和“人民福祉”,“尊重本国与别国的关系”;而妄图统一所有阿拉伯人的“泛阿拉伯主义者”,犹如十九世纪沙俄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所以,在概念的实际运用中,英文“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或“泛阿拉伯”(Pan-Arab)字样的意涵,往往带有强烈的负面意涵。而经常被对译成“泛阿拉伯主义”的العروبة一词,在阿拉伯语中经常用来形容阿拉伯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民族凝聚力,带有鲜明的正面色彩。所以,这两个词在对译时,要格外小心。
而且,纳赛尔时代(1954-1970)恰恰又是美苏冷战激烈的时期。纳赛尔代表的“泛阿拉伯主义”又频频被美国人扣上了“亲苏”的帽子。艾伦·杜勒斯就认为“泛阿拉伯主义”是苏联用来“搞破坏”的工具。马丁·大卫也认为纳赛尔试图创建的“泛阿拉伯统一”(Pan-Arab Union)可能被苏联利用。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纳赛尔试图创建的“阿拉伯帝国”,就在美国人眼里就成了苏联向中东、非洲扩张的跳板呢?
“阿拉伯帝国”与苏联的纠葛
1958年12月,阿联总统纳赛尔发表公开声明,指责叙利亚共产党破坏阿拉伯统一,并以13世纪的鞑靼人(蒙古人)比附苏联,反苏倾向十分明显。(参见拙文《双拳出击:埃及总统纳赛尔如何对抗十字军和鞑靼人》)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发表讲话,指责阿联为打压当地共产党而采取的种种“反动”措施。3月,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爆发武装暴动,很快遭到政府军与伊拉克共产党的联合镇压。半年多前,还被纳赛尔吹捧的伊拉克总理卡塞姆,此时已经在阿联的官方舆论中成了苏联的代理人,阿拉伯统一的破坏者。
纳赛尔对伊拉克反政府暴动的支持,吸引了美国朝野的广泛关注,被当作苏联与阿联矛盾激化的表现。但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无外乎以燕伐燕的斗争。1959年3月22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两张漫画,就非常生动地表现了这点。在漫画中,纳赛尔对苏联态度极其强硬,但却看不出作者对他抱有一丝一毫的肯定。相反,纳赛尔在与赫鲁晓夫的较量中,透着十足的凶悍与狡诈,野心勃勃的奸雄形象跃然纸上。

这样的看法在当时美国媒体中非常普遍。1958年12月,《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就认为,纳赛尔不喜欢“共产主义主导伊拉克”,是因为他建立“阿拉伯帝国”的想法遭到了挑战。所以,美国应该支持“一个独立的伊拉克,既不屈服于共产党,也不屈服于纳赛尔”。文章作者的看法与当时国务院官员朗特里(William M. Rountree)、副总统尼克松等人的观点非常吻合。
其实早在这之前的若干年里,纳赛尔就频频表现出对埃及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的警惕与打压,也担心苏联向叙利亚、也门的渗透。所以,自从纳赛尔掌握埃及权力后,美国舆论中既有人担心纳赛尔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阿拉伯帝国”,但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双方潜在的矛盾。1956年3月,埃及已因捷克军购案、中东防务、犹太复国主义、苏伊士运河等问题,与美英法三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在此背景下,美国著名的媒体作家卡拉瑟斯(Osgood Caruthers)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埃及试图打造阿拉伯帝国”。卡拉瑟斯指责纳赛尔对抗西方,接受苏联军事援助,并“试图在这里创建一个阿拉伯大国。”但卡拉瑟斯也注意到纳赛尔追求的“阿拉伯帝国”不仅仅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且也“反共”。
再回到前文说的1959年。纳赛尔对苏联态度的强硬转变,确实推动了他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但没有赢得美国舆论一边倒的肯定。相反,仍然有很多人在表达着对“阿拉伯帝国”的反感。当年6月,《纽约时报》就有文章指责纳赛尔“建立帝国”的企图遭到苏联的反对后,就妄图在西方的“容忍”下,破坏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国际义务”,大搞“海盗”(Piracy)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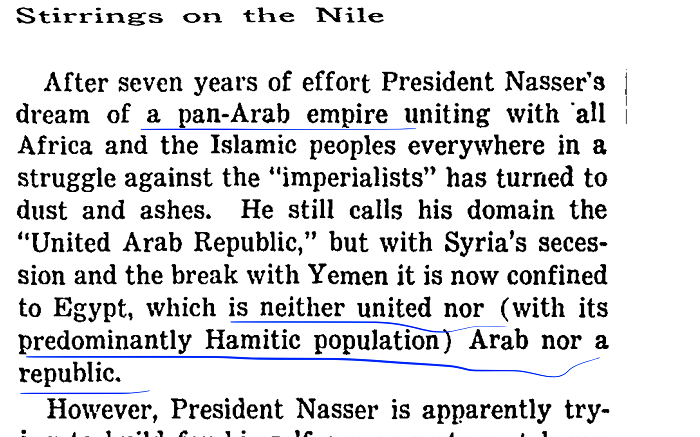
图4,1961年9月,叙利亚反对派势力通过政变退出阿联。纳赛尔被迫接受了叙利亚分离的事实,但仍然保留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国号、国旗,以坚守阿拉伯统一的理念。为此,《纽约时报》有文章模仿伏尔泰讽刺神圣罗马帝国的口吻,嘲讽仅存埃及一隅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既非联合,也非阿拉伯,更不是一个共和国”。
1963年2月-3月,复兴党先后在伊拉克、叙利亚掌权,沉重打击了伊共与叙共。对此,纳赛尔予以热烈回应。苏联在伊、叙受挫,美国人当然喜闻乐见,但对纳赛尔试图建立“阿拉伯帝国”仍是十分反感。3月12日,也就是叙利亚政变的4天后,《纽约时报》有文章写道:
纳赛尔总统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囊括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帝国的欲望,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亲纳赛尔的革命分子在也门和伊拉克得手后,又有一个军人集团在叙利亚发动了革命……
从西方的立场看,这些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激烈反共。共产主义者现在被捕下狱,甚至还被处决。
但是这些革命已经对整个中东和西方造成了广泛的(不良)影响。沙特阿拉伯和约旦是纳赛尔下一个目标,也是美国保护的对象。革命增加了这两个王国的压力,也威胁了所有阿拉伯人除之而后快的以色列,还刺激了阿拉伯人要把英国赶出阿拉伯半岛的冲动。
看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中,“敌人的敌人”并不一定会被当成朋友。
流传至冷战时期的千年“梦魇”
纳赛尔对苏联态度的强硬转变,按说是符合西方冷战立场的,也得到了美国朝野很多人的承认,但为什么没有因此赢得美国舆论广泛的赞誉与肯定?从现实主义的逻辑解释,是因为纳赛尔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霸权扩张”威胁了西方的石油利益、国际交通线、美国友邦的安全、美国对中东的主导权,还有以“主权国家”为元素的国际体系……。当然,我们也不忽视文化的作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长达1000多年的“文明冲突”,不管是否存在于客观的历史事实,但至少是存在于很多人主观的历史记忆里。而纳赛尔就刺激了西方世界的这种历史记忆。
纳赛尔,1918年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后来就读军校,以一个中下级军官的身份参加了推翻法鲁克国王的革命。不久后,36岁的纳赛尔就成了埃及总理,两年后取代纳吉布成为埃及总统,并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英雄。凭借着巨大的威望,纳赛尔刚满40岁的时候,就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出现在叙利亚地区首府大马士革。
纳赛尔的成就,离不开对伊斯兰教的敬畏。的确,他的平民底色与革命理念,迎合了社会底层群众的反抗精神,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与信仰的背弃。纳赛尔上台不久后,就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一本小册子——《革命哲学》。他不但呼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也呼吁伊斯兰世界的团结。这就刺激了西方舆论的神经。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前夕,就有人致信《纽约时报》编辑部,指责纳赛尔“正在寻求一个阿拉伯-非洲帝国”,并控诉他“到处支持极端主义者对付理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而“非洲人不一定都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也未邀请埃及的干涉”。这无疑是通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对立,将纳赛尔塑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扩张者。
1963年4月17日,纳赛尔与伊拉克、叙利亚的复兴党政府签订联合协议,准备将阿联(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联合起来,成立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三个月后,这个协议就因纳赛尔与复兴党的反目成仇宣告夭折,但毕竟将“阿拉伯统一”再次推向了昙花一现的高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应。在三国联合协议签订的3天前,《纽约时报》就有文章指出:
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梦寐以求的是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终极联盟。他们怀念穆斯林帝国占领西班牙的往昔时代,希望看见自己再次那么强大。
一周后,美国著名记者苏兹贝格(C. L. Sulzberger)也在《纽约时报》上也发表了类似看法:
……如果他的联邦凝聚起来,纳赛尔一定会考虑打击以色列,因为对他来说,以色列是扎在阿拉伯人身上的一根刺。无论他从哪买武器,抑或求助德国技术人员,他都会做自己的事情(意思是纳赛尔无论是求助于苏联还是西方,都不会受制于人——笔者)。他宣称只要以色列“存在”,就如芒刺在背。这就是纳赛尔第二个目标,终结以色列国家;他把之前整个巴勒斯坦(意指被以色列侵占地巴勒斯坦领土——笔者)都当作阿拉伯的土地。
纳赛尔曾经告诉我:“我们阿拉伯人总是把未来联系到过去。”他说的“过去”不是近几个世纪阿拉伯各个部落分崩离析,被几个外来帝国统治的时代,而是阿拉伯人从波斯席卷到大西洋的时代。
美国人因历史记忆而对“阿拉伯统一”的敌视心理,不仅仅存在于媒体,还出现在美国政界,影响了美国外交。1963年10月,共和党参议员格鲁宁(Ernest Gruening)为了迫使肯尼迪政府对纳赛尔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就在呈递给参议院的报告中竭力渲染纳赛尔的威胁。为此,他引用了海明威前妻、著名媒体作家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的言论:
一千年的穆斯林帝国(Muslim Reich),埃及统治的非洲大陆,可能是一个迷梦,但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迷梦以及做这样梦的人……希特勒的声音回荡在这片土地,只不过现在说的是阿拉伯语。
一个月后,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前的半个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格鲁宁提交的修正案,大大限制了美国对阿联(埃及)的经济援助,也将纳赛尔重新推回了苏联一边。
到了纳赛尔晚年,阿拉伯国家虽然遭受了六五战争(第三次战争)的惨败,但对以色列和西方的仇恨更是激化。左翼力量与宗教势力纷纷崛起,令美国朝野惴惴不安。为此,《华盛顿邮报》在1969年8月的一篇文章写到:
了解伊斯兰,非常有助于了解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怨恨……对于阿拉伯人来说,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历史都是一样的,都是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根源……他们怀念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统治地中海及亚洲世界大片地区的年代……尽管有许多差异,但阿拉伯语以及阿拉伯控制中东的历史却是共同的遗产……共同的历史使得阿拉伯世界的报纸谴责美帝国主义……
对“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念念不忘的到底是阿拉伯人,还是美国人?文章作者李维斯(Jesse W. Lewis, Jr.)自然是指责阿拉伯人对历史的沉溺。因此,他也指责纳赛尔“尝试用宗教狂热的身上纽带来刺激他的泛阿拉伯主义”,认为纳赛尔宣传“吉哈德”(圣战)是“完全的复古倒退”。但结合上文中什么“东西方三千年斗争史”、“重建阿拉伯帝国”这样的表述,恐怕美国人自己也走不出对历史的狭隘建构。

图5,1961年2月,纳赛尔正在大马士革的伍麦叶(倭玛亚)清真寺做礼拜。纳赛尔推崇的萨拉丁正是埋葬于此。与美国作者渲染宗教战争的叙事不同,纳赛尔将12世纪对抗十字军的战争,解读为“阿拉伯基督徒与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团结一致,抗击殖民主义”的民族战争。
在中东与欧洲的交往史中,战争自然无法回避。但如何建构对战争史的记忆,会深刻影响人们对于“他者”的认识。在今天的美国舆论中,仍然有人在片面渲染对伊斯兰世界的负面记忆,并将这种狭隘的历史认识,作为干预中东内部事务的根据。近年来,美国朝野就有很多人把自己对于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对内压迫”的片面记忆,延伸到了现实的中东政治。当然,土耳其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是非恩怨也极其复杂。但美国舆论的这种声音,恐怕也折射出警惕中东地区整合的一贯心理,至少很多阿拉伯人是这么看的。基辛格在2012年3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所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中东政策有几个关键的安全目标:阻止任何一个地区大国成为霸权(hegemony)……”。“霸权”与“统一”其实往往都是对整合与凝聚的表述,区别在于感情色彩上的截然相反。所以,基辛格这句话就被当今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萨瓦努(محمد شعبان صوان)当作“西方破坏我们地区统一与复兴”的罪证。
参考文献: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白云天:《“泛阿拉伯主义”在美国媒体的“帝国”意象》,《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2期。
白云天:《美国对“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认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