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经验”|刘康:读书其实都是“读人”
近日,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澎湃新闻经“悦悦图书”授权刊发该系列讲座稿和视频。
第六讲傅杰邀请到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刘康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文化研究、国际传媒中的中国报道与国际关系、中国综合研究等。英文代表著作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美学与马克思主义》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等,中文代表著作包括:《大国形象》《对话诗学:巴赫金文化理论》《全球化/民族化》《文化·传媒·全球化》《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和李希光等合著)等。

刘康在讲座现场
我在中国没怎么念过书,上学满打满算也只上了六年的时间。小学上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中学也没有好好上课,每天只是喊一些口号;后来上了四年大学。我在中国所有的学历,大概就是六年。去了美国后,我也读了六年的书,从1983年到1989年慢慢读完了博士。如今回想一下,我已经在美国待了三十八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是1976年初毛泽东发表的一首诗《西江月·重上井冈山》里的两句。那个特定的时代就是我长大的环境,所以我没怎么上过正规的学校,也没怎么好好念书,读书都是七零八碎地读。
如果要讲读书的话,影响我一生的读书经验大概有三条:第一,完全是碎片式的,有什么读什么,看见什么读什么。第二,喜欢故事,读的都是故事书,这是我一个终生的爱好。第三,对写书人的和书里的人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一个是故事,另一个就是人。
影响我一辈子的,我感觉都是这种碎片式的东西。今天我讲自己的读书经历和体会,大概也就是围绕这三条来讲,不成什么系统。
碎片式的阅读经历
小时候读什么书呢?反正也不上学,家里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家里的书比较杂。我妈妈是学医的,我爸爸是在中学里教历史的老师,所以家里有不少历史、医学的书。家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英文书、小说,以及妈妈的俄语书。当时我觉得俄语还挺好玩的,就把俄语书拿来翻,后来不知怎么就学会了几句俄语。《三国演义》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看的,是竖排本、半文半白的。我是大概八九岁时看的,当时虽然看不太懂,但也看得津津有味。还有《阅微草堂笔记》等各种很杂的老书,以及爸爸以前念书时留下来的旧书。还有一部分书是我哥哥弄来的。我哥哥那时是中学生,经常到学校的图书馆里去“偷书”,拿回家来看。除此之外,我还看了好多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小说。有些你们应该不知道,像《欧阳海之歌》;有些你们可能知道,像《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外国作家的小说最喜欢看,让我看得比较入迷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等。我当时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读书情况,非常混乱,非常碎片式,跟当时的时代还是非常吻合的。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我一边听着外面大喇叭里喊口号,一边在看《敌后武工队》……似乎处于一种超现实的、穿越剧的情境中。

刘康小时候阅读的图书
《敌后武工队》是抗日题材的,故事真的很精彩。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故事特别感兴趣。对故事的兴趣,也是我后来学文学的原因和很大的动力。
考大学的时候,当然也是和爸妈商量了半天。我没有念过书,对数理化一窍不通,只能学文科。我爸说,文科太“危险”,不能学。那学什么呢?想来想去,学一个文科里危险小一点、技术性强一点的外语吧,学完之后可以当饭碗。后来,就到了南京大学去学外语。到了大学,我看闲书、杂书的读书习惯并没有改变,仍然会在阅览室看各种各样的小说。学外语早上有一门精读课,从口语开始一步一步念下去,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念英文。但下午的时间基本是比较自由的。
南京大学那时是比较开放的。我们的老校长匡亚明是一个非常热爱文化、热爱教育的人,为学校引进了很多一流知识分子。我记得自己当时经常到中文系去,还听过大师级的程千帆先生上古典诗词的课。听程先生上课是一个极高的享受,教室也自然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程先生往往一边说着,一边板书,把自己讲的唐诗宋词一字不落地默写在黑板上。他的板书是极其漂亮的书法,他的课堪称现场书法表演。那时他用的是粉笔,竖排的繁体字在黑板上一写,粉笔灰到处扬着……令人陶醉。
其实我对古典诗词一窍不通,古文也基本上不会读,我会的所有古文就是从“文革”“批林批孔”中学到的几句,什么“克己复礼为仁”等等。有一门大学语文课,课上老师用的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当时我们上课特别开心,甚至热血沸腾。虽然就上了那么一个学期,我们也从古文中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那时候南大还有各种各样比较学术前沿的课,我就喜欢到处旁听。后来我去威斯康辛念比较文学的时候,还遇到了曾经在南京大学见过的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林毓生,选了他的课,也常常到他家去边听课边吃喝——研究生的课经常都这样上。林毓生先生差不多算是最早到中国大陆去讲历史的,70年代末到南京大学来讲中国现代思想史。他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对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化的解释等,让我们听着觉得非常新鲜、非常震撼。
读书,其实都是读人
我们英文系的教授中有一半都是外国人,多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还有很早出国留学回来的几位老先生,比如偶尔给我们开课的南京大学副校长、英语界的老前辈、1931年哈佛大学英语系博士范存忠先生,我们英语系系主任、1933年耶鲁大学英语系博士陈嘉先生。中国英语界所有那些后来的大佬,包括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都是范存忠先生或陈嘉先生的学生。可是他们那个时候“述而不著”,书写得很少,论文发表得也很少。所以我们读书,其实都是读他们这些人,比读他们的书更有意思。
陈嘉先生当时给我们开一门大课,叫“英美概况”,在一个阶梯形的大教室,几乎77届、78届以及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等好几个年级一块儿上。陈先生讲话慢条斯理,讲的很多好笑的地方,当时我们觉得听懂了,但其中深刻的含义其实要几十年以后才能明白。比如,一次陈先生问我们知不知道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叫1215年的British Magna-carta(英国大宪章)。他说:“About four or fiv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English Magna Carta defeated Spanish Armada”。我们听着觉得特别好玩,因为Magna Carta 和 Spanish Armada 放在一块儿是押韵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这句话的深意:英国大宪章是君主立宪的前驱,也是权力重新分配、现代政体的前驱。1215年英国已经提前超越了中世纪,超越了曾称霸世界的皇权专制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而这些含义,陈先生从来不说。
后来,我考取了出国的研究生,就挂在陈先生的名下。陈先生让我们上他的家里去,给我们七八个学生开了一门课叫莎士比亚。他从家里的书架上拿下一本一本他珍藏的莎士比亚,那是图书馆里借不到的书,也不方便带到学校里去。我们把莎士比亚捧在手上,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当时我们已经要读研究生,按理说英语水平应该不错了,但拿着书页泛黄的莎士比亚,翻到《哈姆雷特》,觉得自己像“白痴”一样,几乎什么都看不懂。现在回想起来,莎士比亚写的英文有点像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中文,半文半白的。陈先生上课的方式特别有趣,上课前会先说:“OK. Let's turn to page 12……”,然后他就开始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地给我们念起来,念得非常陶醉。剧本里角色很多,他就会变化不同的花样,一个人演独角戏就把莎士比亚的剧本给演出来了。陈先生当年在南京大学演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的是朱丽叶,我看到过陈先生穿着中世纪公主的裙子表演的照片……念一段时间,陈先生会休息一下,拿来水果给我们吃。吃完之后,我们接着听他念,一直到下课,最后陈先生会说一句:“OK. That's all for to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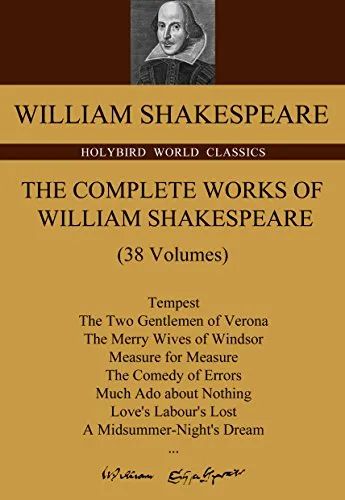
《莎士比亚全集》
一开始我们面面相觑——陈先生就这样念着给我们上课?也不解释两句?我们就这样把书还给他,不回去再看看了?当时我们还想着借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回去看呢,后来发现慢慢就不需要了。随着陈先生一直念下去,我们竟然都能看得懂原文了,尽管他根本没有给我们讲解。这是我记忆中在中国念书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体会。
外国老师也很有意思,我们很多英文书都是从他们那儿读到的。当时有个加拿大老师Ken Mitchell,没几根头发,留着个大胡子,非常像白求恩大夫,我们叫他“老米”。“老米”是个剧作家,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喜欢写剧本,也真的演过白求恩。他把教材拿来给我们念,我们总是非常开心,因为他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讲。他给我们念一本寓言小说,是乔治·奥威尔的Animal Farm(《动物农场》),给我们从头讲到尾……他也讲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只是书太厚了没有讲完。
还要提起一位给我们讲“英美文学史”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Bruce Flattery。以前中国的老师给我们上英美文学史,拿的教材是陈嘉先生编写的。当时教育部需要给英语系的学生出教材,于是陈先生基本上就是把曾经翻译成中文的苏联英美文学史的教科书,又从中文翻译成了英文。在我们看来,那本教科书非常非常无趣。而Flattery教授教的“英美文学史”,跟陈先生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方法是相似的。课上没有什么专门的教科书,就是找一些作品来给我们念一念,还能够跟当时的各种热点结合起来,有点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意思。我们听完之后往往会心一笑,都明白了。
外国教授的课都会让大家看很多书,会给我们开一些书单,推荐我们到图书馆去找。书单可把我们害苦了,让我对南京大学图书馆留下了唯一的“创伤”回忆。南京大学图书馆,也就是过去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是古色古香很漂亮的一栋建筑,但是进入很麻烦,要先排队。排队之前,我们还要先去找带着满是灰尘的卡片,找到卡片之后,把自己的小纸条写下来,再去排队等。学生很多,所以图书管理员就很不耐烦地收着小纸条,收满一箩筐然后进去了,然后“泥牛入海无消息”。我们学生就在外面等着,一直到等得不耐烦了,图书管理员才出来。我们一看,不对呀,我们递的纸条怎么看也有四五十本书,结果她就拿了三四本书来。把纸条往我们手里一塞,然后说一句:“没有!”
不同知识体系下的碎片式思维
我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如今还记忆深刻。根据我们当时那个“富布赖特计划”,我们要先做一个月的培训,了解一下美国。到了之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就去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图书馆。我们一伙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站在门口那儿,一开始左顾右盼不敢进去。但其实图书馆是开放的,可以随便进。进去之后,看到书山书海,我感觉天旋地转,两条腿打颤,扶着书架足足站了五分钟。图书馆里一个一个的书架没有人管,想翻什么书就可以翻什么书,看书很过瘾。我发现,那里竟然有很多讲中国的书,还有很多繁体字的中文书,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在一个很大的书架上,有讲南京大屠杀的书,身为南京人我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就在那儿看。然后我发现,那一整个大书架上千本书都是讲抗日战争的。看到书里的文字和图画,我的感觉可以说是“三观俱毁”,因为我第一次知道了:抗日战争竟然是这样打的!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这些把我吓到了。毕竟在那之前,我知道的抗日战争就是“三大战役”:地道战、地雷战和“小兵张嘎”。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英文,本科的时候又学了一门第二外语,是德语。去了美国之后,在威斯康辛大学读博士期间我又读了六年的德语。所以,我的德语还是不错的。法文其实比较好学,我基本上是自学的。日文里,有很多汉字是很好认的,尽管不会读。小时候我还认了几个俄文字儿,后来也读俄文书……英语、德语、俄语、法语,加上一点点日文,这样各种各样语言的书拿来读一读,是很有意思的。后来我养成一个很奇怪的读书习惯,这个“毛病”到今天都没改。可能是因为从小习惯了碎片式阅读,我现在依然喜欢同时把五六本书放在面前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五六本书是相同的主题,有的时候是完全不相关的主题,一本书看半个小时就放到一边,换一本书接着看一会儿……往往两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可以同时看四五本书。如今有了互联网,更多时间是在网上翻来翻去了。
碎片式阅读形成了我的碎片式思维。我常常觉得自己糊里糊涂的,跟别人说什么事儿都说不明白,但好像也无关大局——我照样当了个教授不是?在大学给学生上课时,我常跟他们讲:“你们千万别指望从我的课上学到什么。就算课上完了你们说啥也没学到,那我也就很满意了。” 到今天,我都没有从碎片式的人生观、故事观、对人的认知、对读书的认知中醒过来,可能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都不一定能够“醒过来”。
我到美国之后,读的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一个是关于中国的,做研究、写论文,我会选与中国有关的课题,可以叫汉学,也可以叫中国研究。另一个就是我所学的专业——比较文学。在我去美国的那个时期,正在兴起一场理论狂潮。法国人、德国人那些高深莫测的语言的、精神分析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新理论,或曰“后学”理论,即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 都是我们比较文学课上主要学习的内容。我接触的知识体系,一个是讲中国的,另一个讲欧美的,跟中国关系不大。但是欧美的理论却引起我高度的认同感。我觉得,我对中国所有的重新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出自于我对那些高深理论的理解,跟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对立。去美国前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我看来,美国的汉学或中国研究,跟我经历的中国才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当时我“初生牛犊”很年轻,很快学了一套让自己能够“诡言善辩”的理论,连我的汉学教授也经常被我驳斥得哑口无言。在那种吵吵闹闹的环境中,我经常跟很多人辩论,包括前面提到的林毓生教授和研究五四运动的周策纵教授。周策纵教授后来研究《红楼梦》去了,有一个老朋友是周汝昌先生,中国《红楼梦》专家,学古典文学的人大概都知道。周汝昌先生耳朵有点背,他的女儿陪在身边。因为住得近,我和我太太经常把周汝昌先生和他女儿请到我家里去包饺子吃,也跟周先生坐着聊聊天。周先生虽然耳朵背,但见到我很亲切,我们“海阔天空”什么都聊。周先生很博学,我常听他聊《红楼梦》,我也跟周先生聊我学的这一套东西,往往他讲他的《红楼梦》,我讲我的《追忆似水年华》……周先生曾说,《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在结构上、隐喻的描述上,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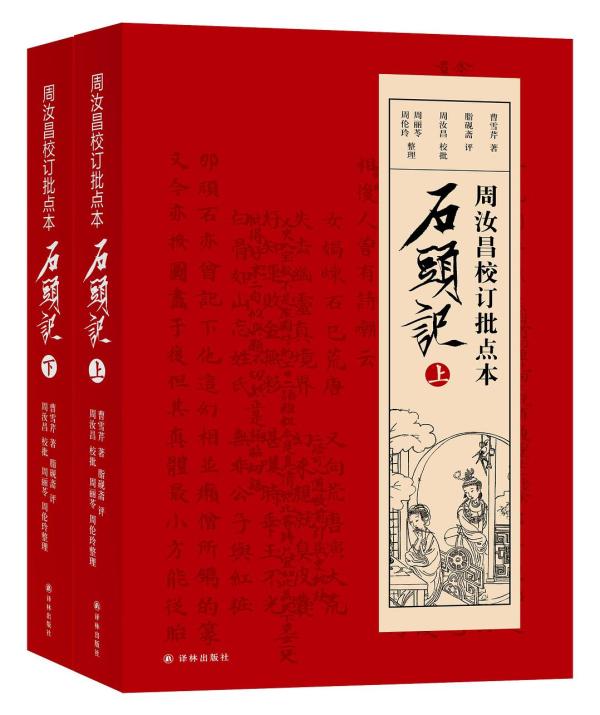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
这是我在美国读书觉得最有趣的一种感受,因为其中有一种强烈的陌生化的效果——这些人明明都是讲中国的,但是他们常常又让你觉得“不知所云”。后来我在美国做了教授,几十年下来,大部分的时间虽然都是在做所谓的“中国研究”,但我的“中国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从另外一边来的,从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那里来的。怎么理解古代中国,我不敢说,因为我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没文化了。但说到现代中国,我觉得,还真的是应该跟这些欧洲人、日本人等搅和、勾连在一起,理不清,道不明,难道现代中国不就是如此?
把理论书当成故事来读
这些年,我很多时间是在做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哲学理论、文艺理论等跟理论有关的工作。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你怎么会对这些理论感兴趣?其实,我并不是对这些深奥晦涩的理论感兴趣,而是对这些理论背后的人物感兴趣。人是特别有趣的。无论什么领域的理论书,我一概不把它们当作理论来看,而是当作小说来读。我看见的,是故事。我慢慢养成了一种很“奇葩”的习惯,偏要从那种很深奥的理论中读故事。我读那些很深奥的后现代理论,发现它们和我的人生经验有时候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有时候又会产生高度的吻合,特别有趣。
怎样把理论书当成故事来读呢?我会带着好奇去找寻他们人生的轨迹,寻找他们的故事——这些创造理论的人都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活生生的人,为什么能想出这些奇奇怪怪的晦涩抽象的理论呢?单单了解他们的人生轨迹还不够,因为有些人的人生轨迹其实很简单,比如思想最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康德。康德的人生经历很简单,一辈子基本上没有离开他的那个小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他的生活经历不足以让我们理解他,但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文艺复兴之后,人性抬头,神性低迷,人类走出了蒙昧的黑暗——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我对康德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靠看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历史书籍、小说而来的。按照学术的说法,他的文本叫text,他所处的环境叫context,也就是我们说的语境。这两个方面的东西放在一块儿,才给了我们对康德的认知。我一直想着,哪天一定要到去柯尼斯堡转一转。后来设法到了那里,那儿已经是俄国的加里宁格勒了。去康德的故居转了一圈,在里面仔仔细细看了很久,印象非常深刻。

康德故居
有一门学问叫现象学,跟现象学联系在一块儿的一门学问——解释学,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解释学,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我觉得,现代的解释学特别有意思。现代解释学领域,有三个来自德国的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三个人的解释学,叫怀疑论的解释学。他们对历史、故事、人生,以及宇宙的规律和非规律性等,都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弗洛伊德讲了很多关于人性本能的东西;尼采很多时候是在讲信仰的非理性成分;马克思是在讲我们的物质生活,他认为越是形而上的东西,越脱离不了形而下的东西。我们大概对马克思比较熟悉,马克思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他的批判的、彻底怀疑的解释学的态度等。可以说,我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同时发现了尼采和弗洛伊德,而这些发现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读书也好,做人也好,都脱离不了历史。当然历史就是故事。对于我们怎么研究历史,怎么看历史、看世界,有三个人给我很大启发。这三个人也是深受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影响的。第一个是20年代中国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的黑暗时代里,鲁迅以笔墨为武器,向旧中国发出震聋发聩的呐喊。《呐喊》就是他射出去的第一发炮弹,化成一道炽烈的光。他企图划破“铁屋子”里的黑暗,唤醒更多沉睡的人。但他最大的怀疑是,那些铁屋里的人,都在昏睡中死灭,他们真的能被唤醒吗?这就是鲁迅纠结一生的疑虑和忧患。第二个是30年代德国的流亡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他看了一幅现代主义的画《历史的天使》(Angel of History),对这幅画有一个寓言式的描述:历史的天使背负着进步、历史、前程,背朝天,人朝地,被一股强大的历史的风暴往后推着,被迫往后退。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弥合起来。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回来。……天使看到的历史,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废墟。这是本雅明对历史的认知,一个离去的天使。第三个是60年代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说,我研究的就是人类的家谱,知识的谱系、书的谱系,我跟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历史和事物都是连续的、逻辑的、有规律的,而我看到的都是断裂的、扭曲的、碎片式的,历史就是一地鸡毛。这三个人对历史的理解,跟我从小碎片式的经验有高度的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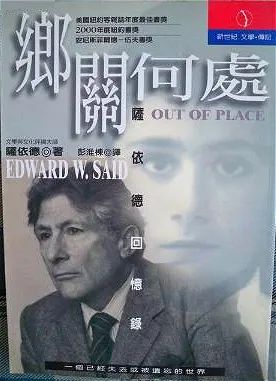
萨义德《乡关何处》
最后,我想说一个让我深受感动的人,一个德高望重的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萨义德写的书《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20世纪世界非常重要的经典,在中国也影响巨大。他还写了一本很精彩的回忆录Out of Place,中译本起了一个充满诗情的名字,叫《乡关何处》。在这本书里他说,我实际上是一个被流放的人:“知识分子就是被流放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不断被人推推搡搡,也不断推推搡搡他人” (Exile for the intellectual is restlessness, movement, constantly being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others)。这是他对流浪汉知识分子的定义,我觉得,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讲, 就是“一只打酱油的流浪狗”。他说,他只是个业余的知识分子,而所谓业余的,不是出于一种责任在工作,而是出于一种热爱(The amateur works not out of obligation, but out of love)。我觉得,这句话是爱德华·萨义德人生的写照,他的自画像。而这句话,大言不惭地说,也是我的座右铭。
傅杰:有些传统的办法还是有效的
我第一次见到刘老师是我在华东师大做博士生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成名的刘老师受邀来华东师大跟我们研究生座谈。刘康教授是世界一流名校的“洋博士”。他曾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南京大学外文系的本科生,一九八三年去了美国威斯康辛读书,现在在杜克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疫情期间交流不便,要请一位在美国任教的著名学者来给我们做讲座是不太容易的。幸运的是,正好刘康教授一个多月前从美国回到国内。
刘康教授关注的领域和治学领域非常广泛,人生经历也很丰富。刚才刘老师为我们分享了他从小到现在关于读书的回忆,虽然如他所说“非常碎片式”,但是既有哲理,又有诗意。刘老师讲的其中一点读书习惯是:把理论书当成故事来读。他的这个“故事”是比喻性的,总的来说,记载人类文化的书都可以看作故事。
我是读中文的,但在那个时候就知道,南京大学的外文系是了不得的。中国英语顶级的范存忠教授、陈嘉教授都在南京大学,尤其英国文学史最主要的教材就是陈嘉教授编的。但今天才是我第一次知道陈嘉先生的上课方式,原来是这么上莎士比亚的。陈嘉先生这个上课法,其实是中国古人的传统经验——“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和老前辈们回忆过的俞平伯先生的上课方式有些神似。俞平伯先生写过《读词偶得》《清真词释》那么好的诗词鉴赏文章,但是有他早年的学生回忆称,他上课什么都不讲,只是读,读到某个地方,突然叫一声“好!”怎么个好法,他也不讲,接着读,读着读着又叫一声“真好!”大家不断地听他读着,听他重复着“好”和“真好”……时间长了,慢慢就体会到了一首诗的味道。这种方法,可能是在学生有了一定的领悟力和基础的情况下,更能把学生直接引向文本的一个有效的办法。这样看起来,有的时候不一定新的才是好的,有些传统的办法其实还是有效的。
刘老师讲到,在南京大学读书时还主动去听了程千帆先生等其他学科老师的课。我们现在也搞通识教育,却通常是被动的。当时学生们的主动性,他们听课的兴奋和读书的欲望,远超过当今在被迫接受通识教育的大学生们。当然,作为老师我们也要反省——到底课的质量跟前辈们有什么差别。
程千帆先生被具有远见卓识的匡亚明校长请到南京大学的时候,已经很高龄了,但去了之后还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杰出人才的优秀博士生,包括莫砺锋、巩本栋、张宏生、张伯伟、曹虹、蒋寅、程章灿等。其实程千帆先生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一共就只开过几次的公开课,可以说正好让刘康教授赶上了。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崇拜程先生,把程先生讲的课记录了下来。正好在去年,张伯伟教授把同门师兄弟所记录的程先生的讲稿收集了起来,包括1979年初至1981年底程先生所授历代诗歌、唐宋诗、古诗、杜诗的课堂笔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程千帆古诗讲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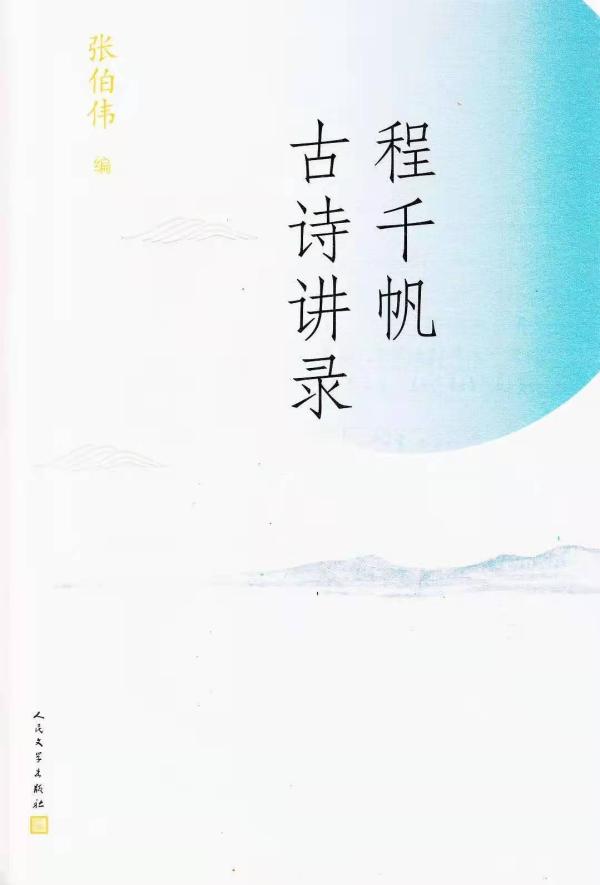
《程千帆古诗讲录》
《中华读书报》每年会请几个学者做年度好书的推介,今年我写的书单中就有这本《程千帆古诗讲录》,在推荐语里还特别提到程先生在讲课当中:通过古诗《长歌行》教导学生“做人要惜时”,通过刘桢《赠从弟》教导学生“做人要正直”,通过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教导学生“治学要谦虚”,通过朱熹《观书有感》教导学生“治学要得法”,把教赏诗与教做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专门带了一本《程千帆古诗讲录》来送给刘先生,当作他听过的课的一个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