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钦丨乌力波这个文学团体
2020年11月30日,法国书店重获开门的第二个工作日,中午十二点半,活在Blursday(指居家太久已经分不清今天是周几,本年度牛津词典新词)状态的笔者正漫不经心地吃着午饭,突然瞥到电视里出现了一个Zoom会议画面。在一种诡异的时代气氛里,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迪迪耶·德古安(Didier Decoin)先生通过Zoom和电视,在书房中宣布今年龚古尔文学奖授予俄淮·勒·特里耶(Hervé Le Tellier)的《异常》(L’Anomalie),该书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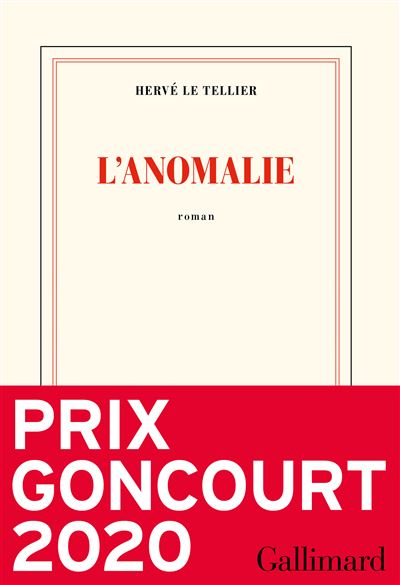
《异常》,伽利玛出版社2020年8月版
在获得今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之前,俄淮·勒·特里耶的作品可能还没有被引介到国内。1957年出生的他本是数学家,曾做过记者,甚至有一个语言学的博士学位。从2019年起,他担任“乌力波”文学团体的主席。
笔者拜读《异常》一书的部分章节后,觉得此书的语言风格、故事情节、哲学内涵均对我本人毫无吸引力。一些同样取向保守的文学评论者甚至认为,这本小说更像是某个科幻片的剧本。但也是因为这样,此书绝不会缺乏读者。对“乌力波”文学团体而言,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毫无疑问是一种胜利。
“乌力波”是数学家、诗人弗朗索瓦·勒·里昂纳(François Le Lionnais)和诗人、作家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为首的几位同仁于1960年创立的文学团体。最开始,这个社团名叫 “实验文学圆桌会议”(Séminaire de Littérature Expérimentale),而与此同时,创始人之一的雷蒙·格诺又提出三条并不能自证也不能自洽的原则:一、实验文学圆桌会议不是一种文学运动;二、实验文学圆桌会议不是一个学术圆桌会议;三、实验文学圆桌会议并不意味着任意文学(这里的“任意文学”指“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自动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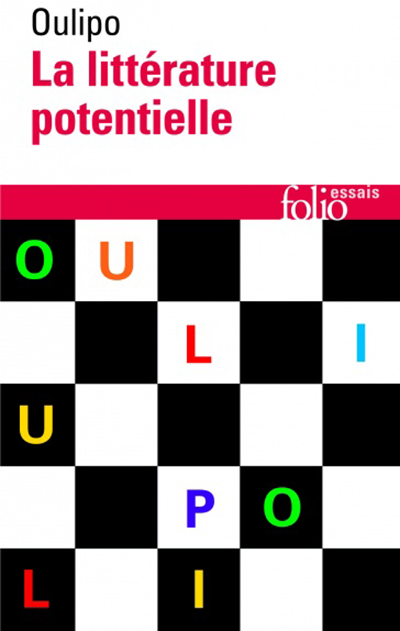
《乌力波:潜在文学选集》,伽利玛出版社1988年5月版
1961年2月3号,创始人之一,阿尔伯特-玛丽·施密特(Albert-Marie Schmidt,1901-1966)教授最终提议,将他们这个小团体命名为“潜在文学工坊”(L'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这里,“潜在文学”的意思是,通过主动追求形式上的限制来激发文学创作。大概是出于音韵漂亮的考虑,施密特教授取了这个名字里三个实意词的首个音节,而不是首字母,凑成一个新词“Oulipo”。不知这个词是何时进入中文的,但是“乌力波”这个译名真的非常有趣,仿佛这是一股“乌有之力”牵引的文学浪潮。“Ouvroir”这个词出现在十二世纪,最早指僧侣静思和工作的专门的房间,后来慢慢有了“工房”的意思,也不再专门用于宗教领域。但这个词始终有“不对外开放”的语义。事实上,“乌力波”和共济会一样,只能由现有成员内推和投票来吸纳新成员,不接受外部申请,因此,“乌力波”其实可以看作一个文学追求明确且自我圈定的社团。
虽然最开始的名字里有“实验”一词,笔者眼中的“乌力波”,无论是这个标签下的作品,还是这个社团形式,都既不实验,也不先锋(avant-garde)。它的实践反而是一种文学传统在二十世纪的重新投胎,只是这一次因为有不少科研工作者的参与,看似有一种跨学科的时髦。
为“乌力波”命名的施密特教授于1966年像后来的福柯一样,被一辆卡车撞倒而去世。专长十六世纪文学研究的他之于“乌力波”的影响,就像福柯之于整整一代法国哲学那样。他是这个团体的理论家,因为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太多乌力波创作,甚至出于新教信仰,生前主动销毁了大部分手稿和信件。施密特教授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国十六世纪的科学诗”(La Poésie scientifique du XVIe siècle)。他的研究涉及从中世纪起,尤其是到十六世纪发展成熟的一系列诗歌。这些诗歌和“日心说”的宇宙观关系紧密,它们都自发地对宇宙、世界、人类加以整体性思考。据其他成员回忆,施密特教授常在会面时给大家讲述古典文学中早已存在但从未被命名为“乌力波”的“潜在文学”(littérature potentielle)。换句话说,“乌力波”所追求和代表的,是早已存在的一种文学现象。现今从属于这个团体的作家可以被这个标签概括,至于过往的作品,即便符合“乌力波”的理念,也没有必要特别归类。
关于主动追求形式上的限制,诗歌方面很好理解,就是形式多样、约定俗成的“格律”。至于其他的文学类型,“主动限制”则指的是文本内在的建筑。对中国读者而言,最知名的“乌力波”作家当属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和《如果在寒冬,一个旅行人……》这些气氛陌生略怪异的作品都有着踪迹可循的文本内在建筑。卡尔维诺从塔罗牌的形式和游戏规则中得到大量关于文本建筑的灵感。这些作品也被认为是他加入“乌力波”后的积极成果。只是,对文本内在建筑的追求并不能真的算一种文学创新。意大利文学经典之作《十日谈》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乌力波创作,但这对该书本身的文学价值无关紧要。
被许多人认为是法国十九世纪诗歌现代性转折的波德莱尔,一生中绝大部分诗歌创作都是商籁体(sonnet)诗歌。他曾在和友人的信件中写道:“因为形式是约束的,思想却喷薄得更加激烈!”(Parce que la forme est contraignante, l'idée jaillit plus intense !)需要注意的是,波德莱尔用的词是“约束”(contraignante)而非“限制”(contrainte),程度上前者比后者要轻,并且,因为他仍认为思想是“喷薄”(jaillit)出来的而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其中显示出的文学观仍然可以划分为传统的“创作灵感说”。当然,波德莱尔是否真的代表诗歌的现代性转折,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二十世纪初,现代中文诗歌的开创和探索中也经历了诗歌“建筑美”的讨论,其中尤以闻一多为代表。他在《诗的格律》中说:“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事实上,闻一多不仅把“格律”视为形式,甚至当成一种可人为控制的“镣铐”,此时他其实已经将“格律”看成某种美学风格的标志——匀称、整齐、棱角分明的美学。这和他的个人风格也是吻合的。显然,这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的风格很难调和,之后也几乎未能被其他诗人继承。“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文学选择,也是一种文学技巧,甚至需要一点“天人合一”的运气。对大多数创作者而言,freestyle(即兴自由风格)大概是更为实际的出路。
“人为主动的限制”注定能让想象力和思想发散得更远吗?在创作这件事上,我们是否会像民国初期恋爱中的男女,因着世俗的藩篱,反而爱得更炽烈?也许是的。只是,据说就统计结果来看,包办婚姻幸福的概率其实比自由恋爱要高……
“乌力波”让笔者想到近几年流行于互联网的“蒸汽波”美学:夸张的粉嫩色彩和色彩种类的限定、上世纪九十年代或更古早的标志符号、技术上刻意装烂装懒。“蒸汽波”也是一种人造的理想。它是一种假装复古实则创新的美学风格。那么“乌力波”是一个看似创新其实复古,等于一种与“蒸汽波”道路相反、路径相似的文学理想吗?当然,这个问题也并不重要。

“蒸汽波”美学作品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