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艾伟:小说把可能性还给生活
在刚过去的2020年,作家艾伟发表了两篇深得业内关注与好评的小说,一篇是中篇小说《敦煌》,一篇是短篇小说《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

艾伟
《敦煌》是一个关于爱与自我的故事。婚前从未谈过恋爱的小项天真浪漫,和外科医生陈波由相亲步入婚姻。平淡的婚姻生活让小项接连对陈波之外的男人心生波澜,尤其在一次出差中和刚认识的卢一明发生了关系。此事被陈波发现,夫妻二人陷入了病态的生活。后来小项彻底离开陈波,却得知了两版和卢一明有关的截然不同的“敦煌故事”。
而《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从俞佩华在女子监狱的最后一天写起。俞佩华敬业依旧,唯一不放心的是自己一直照顾的年轻狱友黄童童,她答应黄童童有一天会送她一个玩具娃娃。出狱后,俞佩华去看了一部以她为原型创作的话剧。她本想让狱警把娃娃转交给黄童童,却得知黄童童已经不在监狱了。
在2020年各大文学榜中,这两篇小说频频上榜。《敦煌》登上“《十月》年度中篇小说榜”“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并成为“《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的中篇榜榜首之一;《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则登上“城市文学”排行榜·专家推荐榜和“收获文学排行榜”,并摘下“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榜的榜首。
“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这些,两篇小说屡被提及,我当然非常高兴。写作是寂寞的,作家也很脆弱,及时的鼓励对作家来说相当重要。”近日,艾伟就这两篇2020年度发表作品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2020年是个特别的年份,我相信史学家会详尽记述这一年,这个全人类被‘隔绝’的一年。这一年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段特殊的时光,一些我们习焉不察的问题得以显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反思,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社会和家庭,都需要重新审视和理解。”他说,希望大家的2021年一切平安,“至于我个人,我会继续写作,努力写好。我还会出几种书,希望这些书能找到它们的读者。”

艾伟短篇《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刊载于2020-4《收获》
【对话】
“剧中剧”:把艺术的深刻和生活的无解并置在一起
澎湃新闻:无论是《敦煌》里的小项、陈波,还是《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里的俞佩华,他们似乎都是有心理隐疾的人。身为小说家,你对现代人的心理隐疾有着怎样的观察和追问?
艾伟:我倒不认为小项有心理隐疾。她最多是在选择时有犹疑,而这些犹疑某种程度上是同她依然相信人是可以变好的、一切是可以从头再来的这样一种乐观主义观念有关。从我个人来说,我没去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现代人心理隐疾”,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个人禀赋”。
在《敦煌》里,陈波小时候被寄养在乡下这件事,我觉得不一定会造成陈波同父母沟通障碍,所谓的童年创伤不见得是养成今天的陈波个性的原因,只是陈波的父母这样认为而已。我觉得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个人禀赋。在生活中,人是各种各样的,弗洛伊德理论似乎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人。
至于俞佩华,我在一篇创作谈说过,作为作者我不理解她,我只知道她深不可测。我写了不可理解之理解,以及对所谓的“理解”的小小嘲讽。俞佩华我觉得也可以从“个人禀赋”去理解她。
澎湃新闻:《敦煌》与《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还都有戏剧元素。《敦煌》里有舞剧《妇女简史》,《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里有话剧《带阁楼的房子》,它们都与小说人物之间构成了某种互文关系,读者可以通过剧情设置对小说人物“冰山一角”之外的部分有更多自己的理解与想象。你选择“剧中剧”的结构设置,有何考虑?两篇内置剧有何种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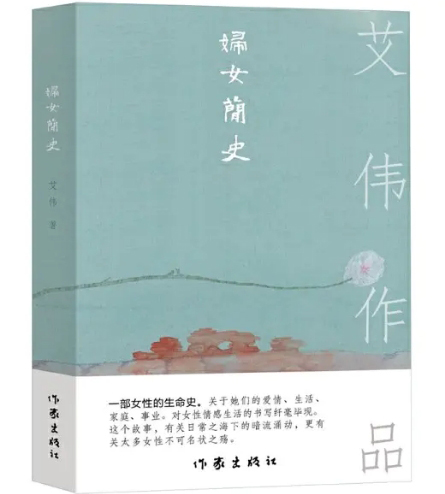
《妇女简史》收入《敦煌》与《乐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艾伟:我发表在新年《钟山》第一期的中篇《过往》讲的就是戏剧。我熟悉戏剧,因为家里有人唱过戏。关于这两篇,可能《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中戏剧元素更为重要。因为既然我不理解俞佩华这个深不可测的女人,我就让一个编剧去理解这个女人,那个编剧写了一个极其“人性”的剧,但是不是真正理解俞佩华,不知道。
这是生活和艺术的区别。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把艺术的深刻和生活的无解并置在一起,显得特别有意思,使这篇小说的空间特别广大。我个人偏爱这个短篇。
澎湃新闻:我也很喜欢《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看这个故事,我会想:“‘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来的人要么特别聪明,要么特别傻?”“阁楼里的秘密是什么?”“黄童童自杀得救,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不在女子监区了?”看《敦煌》时我也会想:“卢一明的车祸和陈波有关吗?”“月牙泉命案的真相是什么?”
两篇作品都给人一种看悬疑小说的感觉。一个个问题接连冒出,有的在后文中得到了解释,有的直至全文结束还让人浮想联翩,这个过程是紧张的,刺激的,抓人的。评论家申霞艳还为《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写道:“今天小说家不仅要跟经典的《哈姆雷特》竞争,也要跟类型小说竞争。艾伟在二者之间做出了可贵的尝试,让叙述的根深藏在泥土里。”
你如何看待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之间的关系,二者有可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融合吗?如果可以,那是不是也存在一个不那么清晰但写作者自身很清楚的界限?
艾伟:《敦煌》有开放的暧昧不明的叙事,文本中也讲了,“真相有好多种,关键是你信哪一种”,因此好些地方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脑补,我觉得这样很好,使得这个文本有更多的可能性,对人物的理解也可以有不同的路径。包括最后的短信,读者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愿望去想象究竟是谁发来的。
我没有想过我的写作要和古典文学或类型文学竞争。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对我自己负责,对我自己的生命、思考、想象和经验负责。我也不同谁比,只同自己比,希望能越写越好。这个态度就是一个界限。每一个作家,纯文学作家也好,类型文学作家也好,都有自己的擅长之处,要写好都不容易,我从来不小看所谓的类型文学,我认为一个惯于严肃写作的作家不一定能写出好的类型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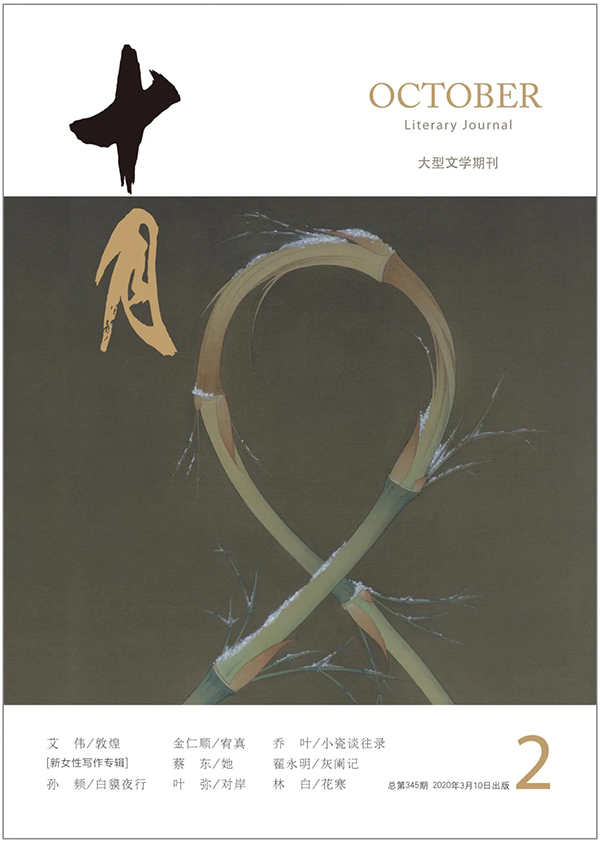
艾伟中篇《敦煌》刊载于2020-2《十月》
用具体的“个人”,刺穿观念的堡垒
澎湃新闻:《敦煌》写到了小项在婚后“旁逸斜出”的情感与欲望。从道德上讲,小项是一个对婚姻不忠的女人,但在小说里,好友周菲得知小项因为情人在两性关系中有了前所未有的愉悦,马上转念觉得:“这是小项应得的。”可以说,在你的小说里,个人的欲望、自由乃至尊严被放在了最高的位置。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在《十月》杂志公号上连载后,有读者留言说:“这不是在教唆么?”
你怎么看待文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怎样看待文学伦理和现实伦理之间的关系?
艾伟: 我不能对读者的反应有苛求,读者永远是从他的观念出发去感受小说,有时候会感到被冒犯,也可以理解。但话说回来,小说就是小说,不是生活指南,我不清楚这些读者在读外国名著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全世界所有的小说,如果要简单粗暴地归结,写的无非是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并且更多的是非正常的偷情故事。《红与黑》是个“偷情”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是个“偷情”的故事,《包法利夫人》是“偷情”的故事。我没看到这些书起到了“教唆”作用。
有次《妇女简史》的读书分享会,也有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我说,在生活中,我们当然要尊重伦理,但我们也不全然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总还是有点小心思的吧,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安全的方法,就是让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小项替我们去冒一下险,我们可以看着她,或者获得共鸣,或者很伤心,或者不认同而批判她一下。
澎湃新闻:《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写到俞佩华杀了自己的叔叔。从法律、道德上讲,这是一个杀人犯,更该受千夫所指。但小说不仅写到了俞佩华“魔鬼”的一面,还写到她“天使”的一面,充满母爱的一面,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人“恨不起来”。这是不是也是文学本身的一种魅力——在我们固化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观之外,提供更多的眼光和思考空间?
艾伟:人是非常容易被观念化的动物,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先天的偏见,对某类人怀有根深蒂固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固定概念和形象,这构成了我们判断事物的依据。
小说的可贵之处是,在小说世界里,作者塑造一个人物时,他的“个人”的逻辑是高于普遍观念的,小说不对人轻易作出道德判断,不轻易下结论,它试图让人看到比简单的观念更复杂的处境,更难以归类的人类生活。如果说,文学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用处的话,用处就在这里——小说用具体的“个人”试图去刺穿那个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从而可以将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将自由归还给人类。

艾伟
回望整个写作,才发现自己一直相信人性
澎湃新闻:《敦煌》里的小项,《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里的俞佩华,她们都是非常丰满、立体的女性人物形象。两篇小说涉及女性婚姻与情感、原生家庭、两性关系、母子关系等等议题,新出版的小说集更直接叫《妇女简史》。
但评论家李敬泽对《妇女简史》的阅读感受很有意思,他说小说写女性的命运,但最后重心变成了男人自身的显影。他认为,探讨女性命运时无法把女性当作一个单独的存在,这本书不仅是讲“妇女简史”,更是在讲男性,像是风月宝鉴,男女互为镜像。通过这种关系的描写,不仅揭示了女人的困惑,也展现了男人的无奈。
你怎么回应李敬泽的观点?你认为自己是有意在写女性的命运吗?
艾伟:作为作者,我的出发点是写女性的生命以及情感可能碰到的问题。但人不是孤立的,女性也不是孤立的,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的房间”可以写好女性,就像岳雯说的“女人和男人只有在互动中才能观察彼此真实不虚的处境”。
当作家完成一个文本后,其实作家说了是不算了的,批评家和读者有权做任何阐释。李敬泽说这本小说“更是在讲男性”这句话前面,他有释阐。在北京的那场读书分享会中,他说,陈波也是可怜之人——我也认为陈波是可怜之人,他甚至盼着小项把他毒死。敬泽对文本有强大的洞察力,他认为陈波之所以这样,涉及到男性权力在男女关系中所受到的威胁,是一种“弱”。他还认为陈波的医生职业是一个隐喻,医生是一种权力,同时也是一种暴力。当然敬泽不是在说“男权”“女权”意义上说权力,而是从根深蒂固的男女权力关系中说“权力”。同时他还说到,这部小说中,同小项有关系的四个男人中的三个,陈波、韩文涤、卢一明,几乎都没有表达爱的能力,他认为这涉及到男人在当下面临的问题。老实说,这些都是我写作时没有想过的。我一直认为好的批评和释阐能把文本照亮。
澎湃新闻: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女性书写”并不是这两篇小说最大的共性,它们更大的共性或许在于对人精神世界多面性的探寻和追问。
《敦煌》与《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都和案件有关,《敦煌》涉及情杀、车祸,《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开篇就从劳改犯的生活空间写起,更和杀人案有关。联想到《老实人》《杀人者王肯》《重案调查》这些早年作品,还有《爱人有罪》《离家五百里》《南方》等近作,你似乎对“罪与罚”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为什么?
艾伟:最近因为在编一本小书,想收入一些近作,于是把《离家五百里》翻出来读了一遍,不是太满意,于是作了一些修改,题目也改了,变成了《幸福旅社》。如你所说,这篇小说确实涉及到人所不能承受的罪感。
关于“罪与罚”这个主题,我确实在多篇小说中有所涉及。这可能同我对人性的理解有关,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直到我写完《风和日丽》,我回头看我整个写作,我才了解我一直是个相信人性的人。在早年的《乡村电影》里,我发现了施暴者守仁的眼泪,这是人性中依旧存留的善在起作用。人性或许会被很多东西蒙蔽,但我相信人性总会在某个时刻胜出,闪现其动人的光芒。
我也相信,人在他的生命中做出某种选择后,一定会留下后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比所谓的“罪与罚”更可以表达这一现象的了。虽然人间烟火以及中国式的世俗生活表面上可能会隐藏这些精神问题,但我相信它永远在,人是逃不过去的。我对平庸生活下的暗流涌动感兴趣,即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感兴趣。
澎湃新闻:你在去年《扬子江文学评论》第四期中谈到了“中国经验及其精神性”,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写世俗生活,在记录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上是有力的,但也是在这样的小说里,我们很难找到西方小说中人的“两难选择”“灵魂的挣扎”等等这样对人的精神性想象。
你还坦言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更愿意在小说中探讨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可否谈谈你的小说观具体受到了哪些作品或作家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你写小说的哪一阶段开始发挥作用?它是否产生过动摇?
艾伟:我是一个对所谓的“深度”感兴趣的作者。要说我写作有什么追求的话,我可能是中国作家中数量不多的向人物内心、向人的精神世界掘进的写作者。我相信人不是我们习见的那个平庸的面貌,而是有着像宇宙一样深不可测的、谜一样的领域,有待我去探寻。
当然,我写的是中国经验。我的写作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包括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浩大的革命经验。不过,最近我没那么大野心了,特别是写《敦煌》时,我是想把男女关系写得细微,写得准确,写得纤毫毕现。我希望读者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读过很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也有特别喜欢的几位,比如托尔斯泰和福克纳等。但具体受到哪个作家影响或哪部作品影响很难说。事实上我的作品我自己也很难看出受谁影响,更不要说一般读者了。
我的写作没赶上先锋文学浪潮,先锋文学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非常大,不少先锋文本背后都可以找到一个外国文学的母本。我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写作,当然也受到先锋文学的滋养。2019年,毕飞宇、李洱、东西和我四个人,在张清华教授的主持下做了一场“三十年,四重奏”的讨论,我们都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成就相当了不起,文本更自觉,也更为成熟,这一代作家没有所谓的“影响的焦虑”,并且及时看到先锋文学凌空蹈虚等问题,自觉融入人间大地,和中国经验紧密结合。但我们得承认,九十年代文学的影响力日渐变小,并且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没有被及时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