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在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
【编者按】
一直以来,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古德森教授以运用生活史方法研究课程和教师闻名。可以说,生活史研究和叙事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特色。《发展叙事理论》一书,基于古德森教授多年来在欧美各国主持和参与的以生活史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大型研究项目,通过呈现和深入分析大量一手访谈资料,归纳出了当代西方社会中人们的四种叙事类型或生活故事种类。本书揭示了现代人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持续地建构他们的生活故事的,深度挖掘了这些叙事类型与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认同、学习和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古德森强调,在所谓的后现代的状况中,虽然灵活应对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是必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把个人的生活叙事与更广阔的社会目的联接起来。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二章《个人生活故事在当代生活中的成长》,由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当我们谈论大事,比如政治形势、全球变暖、世界贫困时,一切看起来都很糟糕,没有什么能变得更好,更没有什么值得期待。但当我思考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的时候——比如你知道我刚刚认识了一个女孩,或者这首我们要和查斯(Chas)一起唱的歌,又或者下个月的滑雪,一切看起来都很棒。所以这将是我的座右铭——想想还是小的好(Think Small)。(Ian McEwan,2005:34-35)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叙事的时代”,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而事实要复杂得多,尽管叙事和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但叙事的规模、范围和理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叙事阶段:生活叙事和小规模叙事。正如麦克尤恩(McEwan)所说的,我们越来越偏好“从小处着眼”。
在过去的时代中,有许多关于人类意图和人类发展的“宏大叙事”。海威尔·威廉姆斯(Hywell Williams)在他对世界史的研究中指出,在19世纪中期人类历史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被塑造成宏大叙事,这种叙事方式不断发展,在当时呈指数级增长。他说,当时出现的发展叙事常常是“轻率和幼稚”的。
这种发展显然是建立在物质进步的基础之上的——突然带来的更便捷的交通、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疾病的减少,这些都给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时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胜利似乎也意味着真正的道德进步。
没有人认为人类在培养圣人和天才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但人们对于建设一个有序社会的可能性有了新的信心。过去只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的知识进步已经进一步传播开来。(Williams,2005:18)
在谈到与这些变化有关的公共生活时,他说:
曾经,18世纪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朝臣还嘲笑过八卦小团体中的迷信——一个世纪以后,更多的人们在公共集会中讨论宗教和科学、政治改革和贸易自由等重大问题。(Williams, 2005:18)
在最后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公众的参与度如今已大不如前——公众讨论社会重大问题的想法在当今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更可能去讨论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令人着迷的隐私生活或者维多利亚·贝克汉姆(Victoria Beckham)的舆论,而不太会去讨论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有严重影响的新的大萧条时代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叙事范围和理想的衰落有关。当然,这也与政治谎言的增长有关(或称之为“编造”(Spin))。从某一立场来看,这可以算是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一种小型的个性化叙事的新流派,以《你以为你是谁?》(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或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的一系列生活访谈类的电视节目为代表。
我们目睹了20世纪宏大叙事的崩塌。威廉姆斯再次提出一个有价值的总结:
人类科学中宏大叙事的观念已经不再流行。基督教的上帝旨意、弗洛伊德心理学、实证主义科学、民族自治、法西斯意志,所有这些观念都曾经试图提供某种用以塑造过去时代的叙事话语。但当涉及现实的政治时,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叙事的话语被证明同镇压和死亡相关。
20世纪的历史消解了物质与科学进步同更美好的道德秩序之间的关联。技术进步曾两次转向、改革,导致全球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人们认为物质的进步与道德的倒退交织在一起。福特T车型和毒气室都是20世纪标志性的发明。(Williams, 2005:18)
我们可以看到宏大叙事是如何失宠的,它不仅失去了叙事的范围和理想,也同时失去了人们对其总体能力的基本信念,即引导或塑造我们的命运,或提供基本真理或道德指引的能力。在宏大叙事崩塌而留下的漩涡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叙事方式的出现,它的叙事范围无限小,通常是个体化的——个人的生活故事。这反映了人类信仰和理想的巨大变化。除了这些小叙事,我们也看到一种向更古老、更原教旨主义的戒律的回归,它们往往基于偏见或意识形态化的主张。
叙事角色和叙事范围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新的叙事流派是如何进行社会化建构的?在1996年的论述中,我提出文学和艺术通常是先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文化载体,它们为我们提供新的社会脚本,并定义我们的个人叙事和“生活政治”。我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探明“我们对故事的审视,以此表明我们在讲述个人故事时所使用的一般形式、框架和意识形态来自更广泛的文化”(Goodson,2005:215)。
在这样的审视之后,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当代文化活动中看到,向更微观的、更个性化的生活叙事的转向正在兴起。有趣的是,这种转向也通常被称为“叙事的时代”,关于叙事政治、叙事故事和叙事身份的时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将这个时代同启蒙时代后的几个世纪相提并论,我们应该把这个时代看作是“小叙事时代”的开始,而不是“叙事时代”的开始。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个性化的社会中,我们的艺术、文化和政治正日益走向高度个性化或反映特殊旨趣的叙事,常常借鉴心理治疗、个人和自我发展方面的文献。这些叙事往往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情境完全脱离。
也许一些来自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偶像作品的例子可以很好地阐释这一观点。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美国摇滚明星,我认为他一直是最优秀、最有洞察力的故事讲述者之一。他写歌很认真,他的作品有时是关于人类理想的宏大图景的,比如他的专辑《河流》(The River)。在这张专辑中,他同鲍勃·迪伦(Bob Dylan)一样,反思了人类梦想的局限性,迪伦在最近写道,他“没有做过一个没有被收回的梦”。斯普林斯汀写道,“如果梦想没有实现,那它就是谎言吗?还是更糟糕的事情?”这种对于人类宏大理想引导我们生活叙事能力的反思,已经成为斯普林斯汀作品经久不衰的特征。他的专辑《汤姆·乔德的幽灵》(The Ghost of Tom Joad),意识到了叙事范围的巨大转变,深刻地反映在专辑的标题上,也反应在其专辑的实质内容上。汤姆·乔德(Tom Joad)是斯坦贝克(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的角色,它的故事情节与当时的群众运动有关,目的是在全球商业萧条时期寻找社会正义。一旦个人的故事与集体的理想之间的关联被打破,我们就进入了小叙事的时代,一个个性化的“生活政治”的世界。
在他更新的专辑,比如《魔鬼和尘埃》(Devils and Dust)中,斯普林斯汀不再提及大规模的历史运动。肖恩·欧哈根(Sean O’Hagan)写道:“它不像《汤姆·乔德的幽灵》那样具有突出的社会意识;相反地,这个专辑体现了一种亲密的、通常是碎片化的对于普通人困顿生活的窥探。”(O’Hagan,2005:7)斯普林斯汀阐述道,“在这个专辑中我所做的,就是描绘那些灵魂处在危险之中或灵魂正面临着来自世界威胁的人们——他们独特的叙事故事”(O’Hagan, 2005:7)。
在某些时候,斯普林斯汀试图将自己的叙事同更广泛的传统联系起来,但这一次这种联系主要是修辞意义上的,因为如今的故事是零碎的、个人化的,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无关(超越了模糊的“民间传统”)。正如他所说的,他现在写的是关于人的“具体的叙事故事”,对广泛的社会传统的反应的被动性反映在他的措辞中,即这些人“面临着来自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威胁,或承受着这个世界带给他们的危机”。这句话很精妙地阐述了叙事的范围和理想,并且描绘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叙事能力在范围和规模上的巨大变化。
同样地,在影视制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叙事能力的重新定义。许多电影人在当代电影制作中明确地指出他们运用了特定的生活叙事。以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un)为例,这位制作了诸多反响巨大的政治电影的西班牙电影人,在一次访谈中说: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氛围及其余波引发了人们对于政治电影的兴趣。但如今的气氛已经截然不同。如果你现在要拍一部政治电影,你就不能从一个国家或民族斗争的角度去拍摄,而要从个人选择的视角去拍摄。(Interview with Jorge Semprun,2004:4)
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文的历史学教授吉尔·特洛伊(Gil Troy)在思考当代世界人类行动的可能性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国家危机中寻找意义,而是在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Troy,1999:A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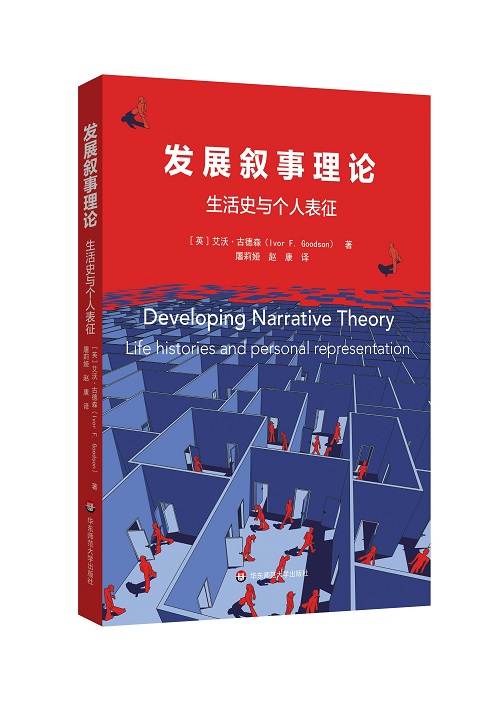
《发展叙事理论:生活史与个人表征》,[英]艾沃·古德森(Ivor F. Goodson)著,屠莉娅、赵康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