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画家”笔下的生命与死亡 | 象征主义大师:克里姆特
不论对画家克里姆特是否熟悉,相信不少人都见过这幅著名的堪称“史上最土豪么么哒”的《吻》,为什么说土豪呢?是因为画作上金灿灿的颜色并非使用了黄色的颜料,而是使用了大量金箔。所谓黄金打造的“浮世绘”,不外如是。
据不完全统计,以这幅画为主导的作品甚至占据了维也纳旅游纪念品行业的三分之一,家居装饰、马克杯、钥匙圈、手机壳、T恤……都摆脱不了这幅画的洗礼。

《吻》(The Kiss)1907 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
除《吻》外,克里姆特在很多作品中都运用了黄金元素,因此有了“黄金画家”的绰号。
若洞观克里姆特一生的画作,会发现他也经历了极其巨大的风格转变。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时常能感觉到爱、美、生命与死亡,在他的画笔下,任何事物都会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

《玛达·普里马韦西肖像》(Portrait of Mada Primavesi) 1913年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下面就让我们以克里姆特为切口,共同去看看新艺术时代迷人的风潮吧~
梦始之地
“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世界。”
对比成名之后的辉煌,克里姆特的社会出身其实并不好。克里姆特出生于1862年,他的父亲是一名由波希米亚移居来的金匠。在他出生的年代,维也纳正陷于经济危机之中,所以小克里姆特的童年算不上幸福。
他所受的教育是那种古老的家庭学徒式的教育,后来他的父亲才把他送去专门的艺术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田园诗》(Idglle) 1884年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1876年,克里姆特进入了维也纳的艺术与工业学院,在这所学校里,他学到了不同时代的装饰技巧,进行了不同风格的绘画尝试。
《寓言》这幅画可以看出克里姆特对学院派风格的一次尝试,女子白皙细腻的肌肤与舞台布景般的背景都令人联想到同时期法国学院派那种矫饰的风格。

《寓言》(The Fable)1883年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克里姆特这种细腻柔美、具有装饰性的风格广受欢迎,为他带来了不少订单。在他的弟弟恩斯特·克里姆特也考入了这所艺术学校后,克里姆特与自己的兄弟,还有同学弗朗茨·马什共同组建了一个小型的艺术社团。

《莎士比亚环球剧场》(Shakespeare's Globe Theatre) 1888年 维也纳城堡剧院
在维也纳东部的佩雷斯旧城堡剧院翻新之前,克里姆特被要求把剧院的场景画下来。于是他描绘了一次戏剧中场休息间隙时的景象。
画面中的社会上层人士们为了自己的座位先后与位置争论不休。克里姆特最后出色地完成了这件作品。城堡剧院的画作令克里姆特于当年获得了皇家金质奖章,也进一步打开了他的知名度。

《旧城堡剧院的观众席》(Auditorium in the Old Burgtheater, Vienna) 1888年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风格的改变也许与画家家中的变故有关。克里姆特的父亲和弟弟相继在1892年去世,之后他的友人马什也离开了工作室,即便如此,克里姆特也一直在原来的工作室里创作,直到1911年时才离开。
同时期的一幅画作《爱情》原本是描绘浪漫情节的画作,可观众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消极又感伤的氛围。

《爱情》(Love) 1895年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画面上方有几张不同的面孔,她们自上而下俯视着这对沉浸在爱河中的恋人,而下方的两人浑然不觉。这幅场景颇像从电影《惊情四百年》中剪出的一个画面:女人被爱情蛊惑,而男人被沉浸于爱情的女人蛊惑。
神圣之春与装饰风格
“当我创作一幅作品时,我不想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让所有人满意,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它取悦了多少人,而是它取悦了谁。”
1873 年,维也纳在举行世界博览会之后遭遇了经济危机。经济崩溃加剧了对社会改革的迫切需求。
和其他国家一样,青年人要以革命的方式来推翻旧的文化制度,这些叛逆者在维也纳被称为“Die Jungen”,意思是“青年一代”。这起初是一场文学运动,之后传播到艺术圈。年轻的艺术家们要冲破传统的束缚,以实验和革新的方式来寻找他们这个时代的艺术风格。

《音乐》(Music)1895年 慕尼黑新绘画陈列馆
作为一名原本享有皇家荣誉,在三十岁时就已经名扬全国的画家,克里姆特选择加入革命,他早先是以偏学院派的画家身份来工作和创作,这个举动无疑意味着和学院派的决裂。
1897 年,克里姆特和另一些先锋派艺术家一起组建了一个新的艺术团体“分离派”(Secession),分离是要从根本上与传统断绝关系。由此,克里姆特开始从一位令人尊敬、技巧高超的学院派画家转变为追求装饰风格的象征主义画家。

分离派展览馆正立面装饰
分离派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神圣之春》(Ver Sacrum),这个名字可能来自古希腊罗马的习俗——在民族危亡之际将年轻的子女献给神以拯救国家。分离派的艺术家们就这样表现了他们的决心:为了拯救文化他们宁愿牺牲自己。
而另一种说法是“神圣之春”这个词引自德国浪漫派诗人乌兰德的作品,这位诗人在作品中表达了将重生与艺术的崇高结合起来的愿望,正好契合了分离派艺术家们的艺术理念。

分离派展览馆的圆形金叶饰
这个新生的艺术流派并不是孤单的艺术势力,进步的史学家布克哈特为他们的作品辩护,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也参与了很多次分离派的活动。维也纳有一批富有的犹太投资人,给予分离派艺术家们很多赞助。
在政治上,1897年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卢埃格尔竞选市长成功后因为担心自己地位不稳定,于是允许他们建造自己的展览馆,这也是分离派这个艺术团体能够延续数十年的原因之一。

《贝多芬饰带》(Beethoven Frieze)之《对欢愉的渴望》局部 (Longing For Happiness) 1902年 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
克里姆特为分离派的第一届展览绘制的海报表现了一个古希腊神话主题:忒修斯杀死米诺陶洛斯。米诺陶洛斯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的妻子与牛生下的怪物,被国王关在克里特岛的迷宫里。
勇士忒修斯主动要求作祭品,最终在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得涅的帮助下斩杀了这个怪物。起初克里姆特创作的第一版中忒修斯的下身是赤裸的,经过审查不得不添加了黑色的树枝来遮挡。

《第一届分离派展览海报》(Poster for the First Secession Exhibition) 1898年 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
这张海报表达了分离派要与旧风格决裂的决心。上半部分表现了神话中最激烈的一个场景——忒修斯斩杀米诺陶洛斯的瞬间。右侧站着女神雅典娜,她握着绘有美杜莎头颅图案的盾牌。
这位象征智慧的女神,也是分离派的守护者和维也纳新城的守护神,要以尖利的矛去刺穿前路上的一切阻碍。

《贝多芬饰带》之《敌对的力量》(Hostile Forces) 1902年 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
对于分离派这种晦涩又颇具象征含义的风格,克里姆特本人的解释是:“当我创作一幅作品时,我不想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让所有人满意,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它取悦了多少人,而是它取悦了谁。”
而另一位分离派画家席勒的说法更简洁明了:“如果你无法用行动来取悦大众,那就让小众喜欢你,因为取悦大众并不是一件好事。”

《贝多芬饰带》之《敌对的力量》局部(Hostile Forces) 1902年 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
克里姆特吸收了其他分离派艺术家的意见,为“艺术之家”设计了一套以贝多芬《欢乐颂》交响曲为主题的壁画饰带。
《贝多芬饰带》长约34米,由克里姆特设计制作而成。这三面墙环绕着艺术家克林格制作的贝多芬雕塑,彩绘的饰带仅占整面墙的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的白色墙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贝多芬饰带》之《达到圆满》(Yearning for Happiness Finds Fulfillment in Poetry,局部) 1902年 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
这套装饰性的壁画表现出了极强的平面装饰主义风格,为了营造出更光彩夺目的效果,据说金色的部分还用上了真的金箔。
在创作这套壁画时,克里姆特已经迷上了浮世绘和非洲面具。各国此起彼伏的博览会,让艺术家们看到了遥远国度的种种新奇风格,他们吸收了这些元素并用在自己的创作里。

《贝多芬饰带》之《达到圆满》(Yearning for Happiness Finds Fulfillment in Poetry,局部) 1902年 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
克里姆特曾经引用过一句《圣经》中的箴言:“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世界。” 《贝多芬饰带》表现的是一种跨越尘世的精神性追求。维也纳的世俗社会是腐败而动荡的,只有在艺术中,人才能如勇士一样在天国的花园里获得最后的休憩。
1905年,分离派内部出现危机,一部分后印象派画家拒绝接受将艺术与应用艺术调和的理念而离开,而分离派的乌托邦式幻想也遭受了现实冲击。从1909年开始,克里姆特陷入了自我危机之中,他也意识到,分离派的风格也许走到了尽头。
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只有在艺术中,人才能如勇士一样在天国的花园里获得最后的休憩
分离派是一个在艺术上颇有革命精神的艺术团体,但他们缺少社会革命性,他们的革命只体现在艺术创作上,而这种创作是脱离现实的。
当时,各国的现代艺术风头日盛,分离派十分具有国际精神,克里姆特本人也担任过德国慕尼黑现代画家协会和其他欧洲绘画协会的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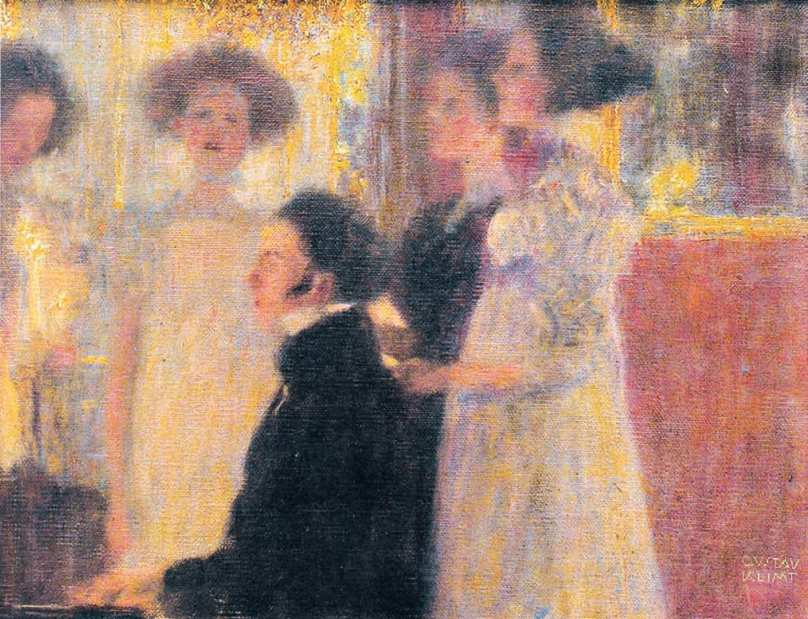
《弹钢琴的舒伯特》(习作)(Schubert at the Piano) 1896年 私人收藏
可以说,分离派是当时维也纳的一张名片,是维也纳在世纪末的代言人。克里姆特与官方决裂并非在于他选择脱离学院派传统组建分离派,而是与另一件艺术史上的著名事件有关,即维也纳大学装饰画事件。
大学领导层和文化部为克里姆特设定的主题是“医学”“法学”“哲学”,希望克里姆特表现出“光明终将战胜黑暗”这个主旨。

克里姆特为《医学》(Medizin)所做的草图
但此时的克里姆特正沉迷于向内心的探索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之中,追求尼采口中所谓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狂喜。
《医学》的天顶壁画毁于1945年,所以我们只能从草图、油画稿和照片中一窥这幅作品的面貌。画面下方是一位身着红衣的女祭司,她头戴金叶编成的桂冠,一只手上盘绕着一条金色的蛇,另一只手端着一碗清泉。红袍上缀满了金色线条,寓意生命的绵延与流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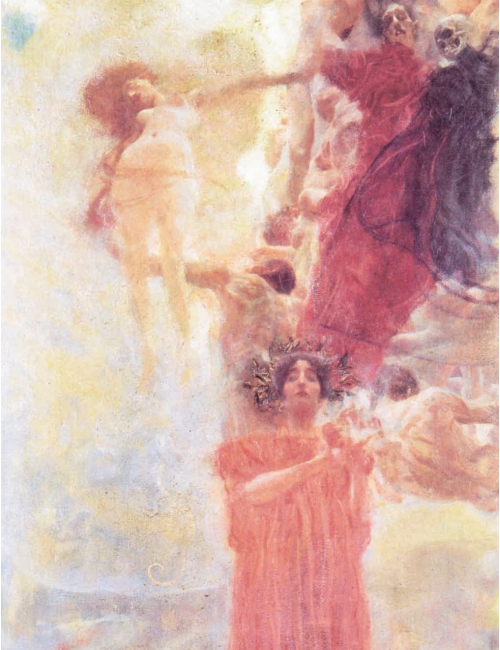
《医学》(油画稿) 1897—1898年 以色列博物馆
海吉娅背后的背景被一条流溢下来的光带分成了两部分。左侧是一名怀孕的裸体女性,右侧是奔涌的人生的河流。
人与人之间没有互动交流,他们飘荡在空中如亡灵,偶尔分离,偶尔纠缠。死神在右上角蠢蠢欲动。

《医学》(黑白照片) 1900—1907年 原作毁于伊门多夫堡火灾
只有左侧的女性逃脱了这种命运的束缚,因为她即将成为一位母亲。她代表着孕育新生命的希望。
克里姆特希望在《医学》中体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纯意志性的精神,那是永恒的生命欲望。这就是克里姆特眼中的医学观,即医学是一种关于生命的科学。

克里姆特为《哲学》(Philosophie) 所作的素描稿
之后,克里姆特开始着手《哲学》的创作。不幸的是这幅作品以及之后的《法学》都毁于伊门多夫堡1945年的火灾之中,只能依据留下的黑白照片来猜测其中内容。

克里姆特为《哲学》所作的草图
哲学本质是探讨人的存在的一门学科。画家高更曾经在他的巨幅油画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到哪去》中用肆意狂放的方式表达了人生在世的困惑与苦痛。而克里姆特这里的表达方式是诗意而冰冷的,带有一种超脱于人类情感之外的无情感。
左侧体态虬结的人群从上面的婴儿、孩童、少女,到下面的青年男女,以及最下边的老年人都处于一种人生的迷惘中。

《哲学》(黑白照片) 1899—1907年 原作毁于伊门多夫堡火灾
《哲学》是一幅冰冷的作品。也许在旁人看来过于消极,但在克里姆特心中,世界本身就是这副模样,世界就是意志的,充满了无意义的生命。《哲学》体现的这种思想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也为克里姆特之后与官方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克里姆特为《法学》(Jurisprudenz) 所作的素描稿
不久后,学院的几十名教工要求文化部弃用克里姆特的作品,揭开了一场论战的序幕,这场论战也是维也纳世纪末精神危机的写照之一。终于,就连艺术也无法弥合传统势力与新生思想之间的矛盾了。
坏消息接踵而至,克里姆特被选为美术学院的教授,文化部竟然拒绝批准,而是选择了克里姆特的反对者约德尔。

《法学》 1903—1907年 原作毁于伊门多夫堡火灾
原本支持艺术家运动的文化部长为了自身地位和他们撇清了关系,许多政客纷纷对他倒戈相向。他前一天还被尊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下一秒就变成了一个恶意丑化古典传统的罪人。

《阿黛尔肖像Ⅰ》 (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 1907年 纽约新艺廊美术馆
文化部拒绝接受用克里姆特的作品来装饰维也纳大学的天顶,但他们提议可以把作品送进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克里姆特却无法忍受这种侮辱。
他在1905年自己出钱从政府那里买回了这些作品。这几幅作品毁于一场1945年的火灾,之后再也没人见过它们。

《阿黛尔肖像II》 (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I) 1912年 私人收藏
文化从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他意识到了梦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分离派的运动依赖于文化部的支持,当文化部抽身而退之后,他们举步维艰。
《象征主义大师:克里姆特》

徐采韵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书至美
2020年10月
200余幅代表作,遍览象征主义艺术大师克里姆特的传奇一生,精致别册,由点及面感受新艺术运动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