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复兴前夕的黑死病,毫无疑问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也严重冲击了教会为首的传统权威的地位,给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提供了萌芽的空间。
文艺复兴前夕的黑死病,毫无疑问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也严重冲击了教会为首的传统权威的地位,给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提供了萌芽的空间。
【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校内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

一场瘟疫本来是一场悲剧,但在特定条件下有时悲剧也会成为历史的动力,文艺复兴前夕发生于意大利并传遍欧洲的黑死病就是如此。这场瘟疫所造成的苦痛、人口锐减、秩序混乱和人们的惶惑不安,意大利首当其冲,被推到了悲剧的前台。但是将黑死病置于欧洲社会从中世纪步入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下,它似乎又变成了促进社会转型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意大利人率先觉醒并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大门。
瑞士著名文艺复兴史研究名家布克哈特称赞 “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正是“这位长子”首先苏醒过来,扯掉了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所织成的纱幕,开始睁开理性的眼睛看世界,使人们对“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 尽管我们不能说,是一场瘟疫让意大利人有了扯掉那层纱幕的力量,但至少可以说,黑死病的爆发引发了一场社会集中的灵魂拷问,致使那层偏见的纱幕不再像看起来那么完整,甚至变得千疮百孔,从而腾挪出理性意识和现实思考的空间。
一般认为,黑死病在1331-1332年活跃在中亚地区,然后开始向南进入中国和印度,向西到达波斯,并在1345-1346年到达南部俄罗斯。此后,这种疾病迅速沿着重要的商路传播。1343年意大利热那亚的商人在加法城(Caffa)受到鞑靼人围攻,为染上瘟疫的鞑靼人所感染。这些染病的热那亚人在1347年逃到君士坦丁堡,并于同年到达意大利,黑死病在意大利爆发。从地中海开始,黑死病向北传播,染遍整个欧洲。1348年瘟疫洗劫了阿维农,并于6月到达了法国。与此同时向西传播,穿过图卢兹和波尔多,在加斯贡尼渡海于1348年夏天到达英国。瘟疫在英国迅速从港口燃遍了内陆,并于秋天到达伦敦。这场瘟疫断断续续在1349年结束,很快接连发生了几次同样的瘟疫,对这场瘟疫,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准确的称呼,只是笼统地称为瘟疫。该瘟疫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在腹股沟和腋窝下形成肿瘤,一种是脖子上有肿瘤,身体其它部位通常出现小水泡,伴随着突然发冷、发热和针刺痛的感觉,浑身倦怠。还有时会引起肺部感染,出现胸痛和呼吸困难的症状。这场瘟疫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灾难,几近三分之一甚至半数的人口死亡。

面对黑死病的大规模爆发,人们不禁要问,它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战胜这场灾难?事实上,人们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瘟疫普遍无知。正如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所说:“询问历史学家:沉默。询问科学家:没有表情。询问哲学家:耸耸肩膀,皱皱眉头,把手指头放在嘴唇上请求沉默。” 但是死亡的迫在眉睫和现实的紧张要求所谓的权威部门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本身又会立即为发生的事实所验证,于是,对黑死病的质问变成了对长期以来的知识传统和传统信仰的拷问,也是对传统权威的考验。
人们有理由让作为权威部门的教会出面进行解释,作为教皇国所在地的意大利更是如此。教会则老调重弹,告诉人们,黑死病的发生是上帝因为人类行为不端而愤怒的结果,教士宣传说“上帝经常让瘟疫、悲惨的饥荒、冲突、战争和其他形式的灾难降临,借此来惩罚人类和警告人们悔改和走上行善的道路。” 如果要想灾难停止,只能祷告上帝。但事实是祷告并未能阻止人们的死亡,而且教会把人们集中起来进行祈祷,反而加速了人们的感染和死亡。不仅如此,教会还从罪与罚的原理出发,认为面对瘟疫不能使用药物来对抗,因为用药物治疗就形同对上帝意志的对抗,因此“相对于用这种方法(忏悔和临终涂油),医生的所有治疗方法都是无用和无效的。瘟疫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除了通过他和他的力量不可能得到治愈” 。 因此,教会虽然给人们带来某种遥远的拯救的希望,但不可能提供真正制服黑死病的现实办法。在忍受即时的苦难和现实的死亡面前,教会这种虚无缥缈的神学原则阐释,无法给正在经受黑死病煎熬的人们带来真正的宽慰,反而引起人们更大的质疑。人们会问,如果上帝因为我们的行为不端而愤怒,那么到底这些不端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做?如果黑死病是为了惩罚罪人,那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教士死亡,为什么他们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都无法幸免?
人们也有理由让医生也出面解释,但是饱受教会所钦定医学家以及宗教信仰熏陶的医生们,大都不能理性和科学地解释黑死病的成因并提出合理的应对措施。大多数医生满脑子都是星相学、元素说的概念,将一切现象都归结于地、火、水、风四种元素以及冷、热、干、湿等物体性质,并用某种类似天人感应的学说解释一切。正如齐格勒(Philip Ziegler)在他的著作《黑死病》中所说:“在研究星相的学者们无法解释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很自然地从他们所理解的东西来推断,并从星星的运动来构建某种原则,用它来解释和告诫地上发生的事情”。 大多数医生认为黑死病的出现是星球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结果,星球之间的位置变化到一定程度,会产生某种弥漫于太空的有毒气体,气体刮过地面之处便会产生瘟疫。认为人们只要待在低处风刮不到的地方,并时常闻有香味的木头就会有效躲避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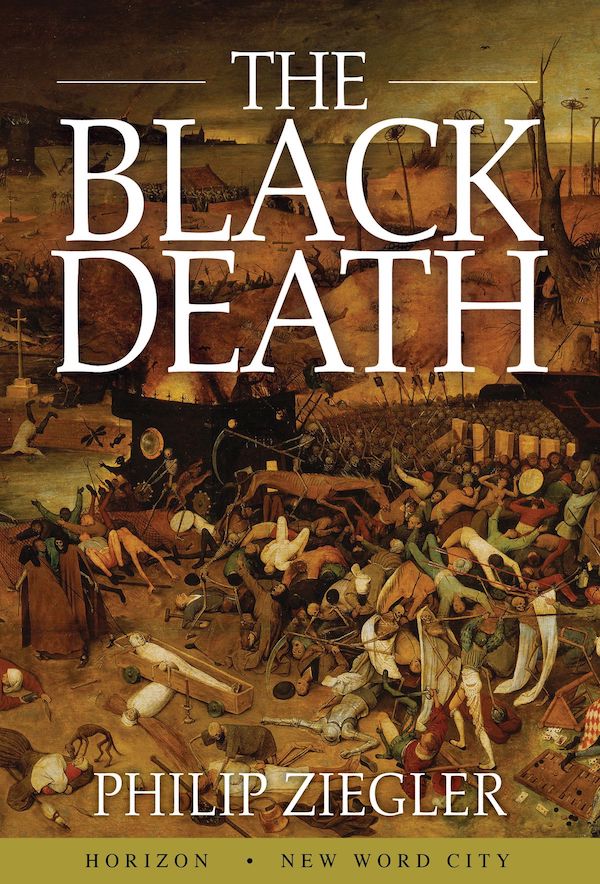
但是事实很快证明,这些解释和措施对阻止黑死病传播和减少人口死亡都毫无效用。在死亡当前,任何解释和措施都会立刻得到检验的情况下,那些看似权威和正统的部门,尤其是教会,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在黑死病面前,面对人们的拷问,看似严密而又坚固的信仰堡垒开始变得不堪一击,齐格勒说:“中世纪的人踏在一层薄薄的已知知识的冰上,底下是深不可测的、令人恐惧的无知和迷信,一旦这层薄冰破碎,所有的救命稻草,所有客观逻辑的分析都会失去。” 1893年一位红衣主教加斯科特(F.A. Gasquet) 出版了一部全面论述黑死病的著作《大瘟疫》。 尽管这部著作从教会的角度出发责骂这场瘟疫导致了教会的衰落,但他也承认黑死病导致整个教会体制都彻底瓦解了,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头开始。
正是在教会等权威遭到质疑、人们的思想产生混乱、社会秩序动荡的前提下,出现了对瘟疫的理性认识和应对措施,尽管这些应对措施未必一定科学,但确实为理性思维和新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土壤。
人们开始认识到,瘟疫和遥远的星球没有关系,却一定和现实的环境污染有密切的关系,瘟疫的源头应该是腐败的空气。所以,人们开始把眼光从天上降到地上,关注城市中的死尸、排泄物、水源对环境的影响,注意屠宰房、制革车间的难闻气味对空气的污染。针对这些污染源,每个城市开始自发地进行清除,他们清理街道,整顿血污遍地的屠宰房,一场城市卫生革命悄然来临。人们也开始认识到,瘟疫的传播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关,所以有些医生提出了躲避瘟疫的黄金法则:赶快逃出去,走的越远越好,不要急着回来。有些医生也认识到一个人的心情和疾病的关系,教导人们用平和的心境来抵御瘟疫。因此,在疫情面前,有些医生也开始大胆抛弃那些传统的理论,从更加现实的角度理性地去认识。
将瘟疫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去理解,也催生出科学的隔离措施。其中威尼斯总督和议会便任命了三人小组,负责建立许多站点,专门对东方归来的船员进行为期40天的隔离,严格控制移民进入城中。同时,在远离城市的海岛上开辟墓地,对因黑死病而去世的人集中深埋。米兰城则采取了严格隔离密切接触者的措施进行应对,规定若一个人感染则相近三个房间的人都要用围墙隔离起来。在皮斯托,政府颁布条例禁止任何外人和商品进入,设立专门的埋葬地并严格规定埋葬深度和参加葬礼的人数。佛罗伦萨则将政府权力暂时移交给8个最有智慧的贤人,由他们下达命令,组织将城内腐败的东西和受到感染的人们运往城外,并严格监督市场。卢卡则颁布禁运令,严禁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进入卢卡城,违者将被没收财产和受到处罚。
教会权威的丧失和理性的觉醒,导致人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以自我为是的方式理解生活。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就谈了黑死病给人们造成的影响: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开始抬头。哥特弗雷德(Robert S. Gottfried )在其《黑死病:中世纪欧洲的自然和人类灾难》中说:“薄伽丘笔下的人物崇尚与大多数前辈不同的品质。他们不再热衷于虔诚、军事技艺,而认为智慧和灵活对成功来说是必要的。……报酬和胜利属于那些活跃的或者自助的人”。 坎贝尔(Anna Montgomery Campbell)在其《黑死病和知识人》中甚至总结说:“十四世纪后半期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法无天的流行,以及在民众和思想界对权威的反抗”。
发生于文艺复兴前夕意大利的这场黑死病,毫无疑问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也严重冲击了教会为首的传统权威的地位,给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提供了萌芽的空间。因此,黑死病不仅仅是文艺复兴发生的背景,也是催生文艺复兴时代到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引用文献: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5页。
Samuel K. Cohn, Jr.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London: Arnold, 2002, p.225.
Rosemary Horrox, The Black Death,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94, p.113.; p.149.
Phillip Ziegler, The Black Death, Harper and Row, 1963, p.37.; p.42.
See Francis Aidan Gasquet, The Black Death of 1348 and 1349 , George Bell and Sons 1908.
Robert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The Free Press, 1983, p.79.
Anna Montgomery Campbell, The Black Death of Men of Learning, Columbia univ. Press, 1931, p.129.
本文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