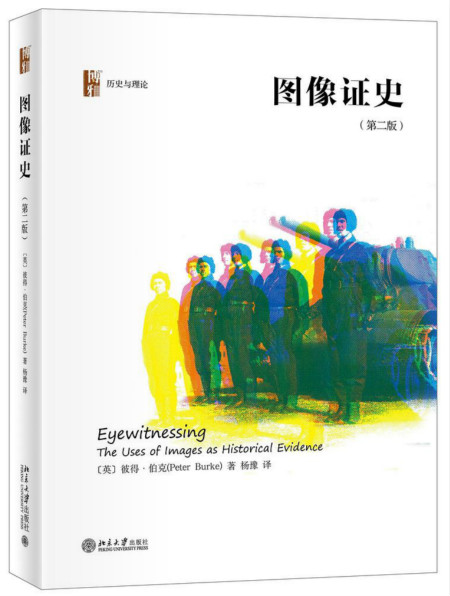导演和历史学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就如同导演与人类学家在制作人种学影片上进行合作那样,也是一种手段,可以利用影片来推动对过去的思考。
导演和历史学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就如同导演与人类学家在制作人种学影片上进行合作那样,也是一种手段,可以利用影片来推动对过去的思考。
作为历史解释的影片
早在1816年,在英国就出版了《作为历史学家的摄影机》一书。既然握摄影机的手以及指挥手的眼睛和大脑很重要,那么将电影制作人称作历史学家有何不可?这里的“电影制作人”应当用复数名词来表达,因为影片是演员和摄影师在导演的指导下合作的结果,更不用说还有电影剧本的作者和小说作者,因为电影剧本往往是根据小说改编的。通过文学和摄影机的双重过滤,观众才能看到这些历史事件。此外,电影是图像文本,通过展现文字来帮助或影响观众对画面的解释。在这些图像文本中,最重要的是影片名,它可以影响观众观看电影画面之前的预想和期望。最突出的例子是《一个国家的诞生》。这是一部关于美国内战的著名影片。在放映过程中,银幕上出现了一句话,“南方经历了磨难以后,一个国家才得以诞生”,从而增强了观众对影片名的理解。
电影的魅力在于它会让观众产生亲眼目击事件的感受。但这也正是电影这种媒体的危险之处,因为这种目击者的感受实际上只是一种错觉,就像前面提到的快照一样。导演给了观众这样的经历,自己却隐在幕后,观众见不到他。导演不仅关心实际发生的事情,还要考虑如何用艺术家特有的方式讲述故事才能赢得众多的观众。“文献纪录片”是个比较复杂的术语,表明了戏剧的观念与文献的观念之间存在的一种紧张关系,也表明了没有高潮和永无结论的过去与导演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的紧张关系,因为电影导演像作家和画家一样,都需要表现形式。
关键在于,用影片呈现的历史如绘画中的历史和文字写就的历史一样,也属于解释的行为。例如,把D.W.格里菲斯导演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同《飘》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看到,尽管这两部影片都是用南方白人的观点来表现美国内战和接踵而至的南方重建的时代,但它们使用了不同的方法看待这些事件。格里菲斯来自肯塔基,他的影片是根据一位名叫托马斯·迪克逊的南方人写的小说《族人》改编的;迪克逊是一名新教的教士自称为反对“黑色危险”的圣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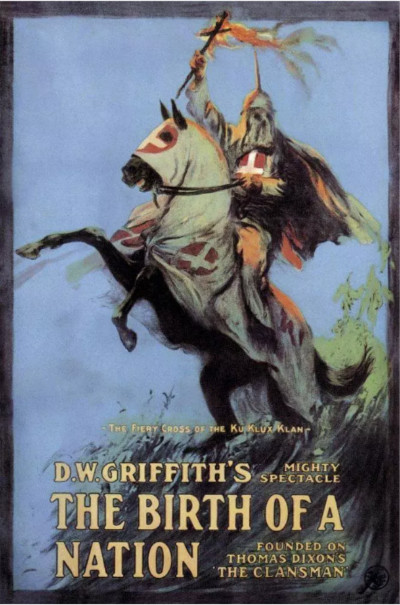
罗伯特·安利可和理查德·海弗朗导演的影片《法国革命》与安杰伊·瓦伊达导演的《丹东》在对待法国革命的观点上截然相反。前者用光辉的画面歌颂法国革命,是法国革命二百周年庆祝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后者从悲观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卡莱尔所说的名言:革命“吞食了自己的孩子”,为争夺权力而牺牲了理想。他决定这部影片从大恐怖而不是从具有积极意义的革命早期阶段开始,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解释来自何种动力。
如果把E.H.卡尔的话变一种说法,可以这样说,在研究一部影片之前你应当先研究它的导演。瓦伊达是波兰人,从他1945年开拍的《灰烬和钻石》到表现战后波兰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大理石人》等影片,他长期以来一直在用影片评论时事他导演的历史影片像前面讨论过的德拉罗什和其他艺术家的历史绘画一样,可以解释为对当代的间接评论。在他导演的电影《丹东》里面,秘密警察的角色,大清洗以及装模作样的审判都把他的讽刺意图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影片里面甚至还提到有人为了政治的原因而改写历史,其中有一个镜头显示画家大卫把后来变得无关紧要的革命者法布尔,从他纪念大革命的壁画作品中抹去。
历史影片都是对历史的解释,无论是通常情况下由职业导演执导的影片,还是由安东尼·阿尔杰特等职业历史学家制作的影片,概莫能外。阿尔杰特为爱丁堡大学导演过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影片,由约翰·格伦维尔和尼古拉斯·普罗奈等人组成的里兹大学摄影组也制作了一部名为《慕尼黑危机》的影片。历史影片理想的制作者需要同时胜任两种实际上互不相容的角色,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加君主一样。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用影片表达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吸引人的解决办法,可以妥善地处理我们在前面已经遇到过的把画像转化为文字的问题。美国批评家海登·怀特所主张的“影视史学”,即“用视觉形象和影视化的话语表达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它的思考”是对“史学”的补充。
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历史学家一直把图像看作文本的辅助手段,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忽视过图像的作用。现在能否更认真地对待图像所提供的证词,以便让历史学家有机会把图像本身作为证据呢?一些迹象表明,这样的可能确实存在,其中包括在历史学杂志上刊登影评。1988年,《美国历史评论》组织了一次关于历史学与电影的讨论,其中刊登的一些文章本书已经提到。1998年,《美国历史学杂志》在常设栏目“电影评论”刊登了对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两部影片,即《勇者无惧》和《拯救大兵瑞恩》的影评。有两位评论者对斯皮尔伯格的画面所产生的力量表示惊叹,但也指出了他在表达上的两个失误,一个是历史人物身上的失误,另一个是表现美国军队时的失误,把他们表现为“无视纪律”和“畏缩不前”的士兵。
影片可以用画面来表现过去,也可以通过表面和空间来概括过去的时代精神,这种潜力十分明显。但是,像历史小说一样,问题在于这种潜力是否被加以利用,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要说明这个关系,我们可以把以较早的历史时期——比如相当于瓦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艾凡赫》的写作时期为背景的影片,与较近的历史时期——比如相当于他的历史小说《威弗利》的写作时期为背景的影片做一番比较。把以较近的时期为背景的影片当作历史来看待时,特别是涉及时代的风格时一般说来比较准确一些。例如,在卢基诺·维斯康蒂执导的影片《豹》中,五光十色的镜头重现了巴勒摩人追求时髦服装的场面,勾起了观众对19世纪上层阶级物质文化的回忆。在马丁·斯科塞斯的影片《纯真年代》中,一些镜头反映了时髦的纽约;BBC电影公司摄制的《傲慢与偏见》,逼真地表现了地方绅士;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罗马》,则比较如实地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
相反,在反映18世纪以前的历史时期的影片中,能够认真再现过去的比较少见。那些反映外国过去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集体心态的影片尤其少——它们都与我们现在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集体心态有很大的差距。历史学家在观看以1700年以前的时代为背景的影片时,几乎都会发现其中出现了背景、姿态、语言和思想上的时代错置,并对此感到不满。
有些时代错置可能是必要的,因为这是让现代人得以直接理解过去的一种手段,也有一些时代错置可能是故意的,类似于前面讨论过的历史绘画的方式将较远的事件与较近的事件进行对比的方法。谢尔盖·埃森斯坦执导的影片《伊凡雷帝》第二集(1946年拍摄但到1958年非斯大林化的时代才公映)就属此例。同样,即使是在最优秀的历史影片中也可以发现,由于粗枝大叶或者由于没有认识到态度和价值观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所造成的时代错置。
有些影片虽然以前几个世纪为背景,却幸免了以上这类批评。例如,凯文·布朗洛导演的影片《温斯坦莱》再现了英国内战时期的掘地派。布朗洛的这部影片的情节以历史学家戴维·考特写的小说《雅各布同志》为脚本,正像他说的那样,要拍出一部“以事实为依据”的影片,因此认真地阅读过当时的一些传单,并向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咨询各种不同的历史观点,甚至从伦敦塔里借来了当时用过的盔甲。
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执导的一些影片主要以19世纪末现代化以前的日本为背景,但同样提供了对过去的严谨的解释。黑泽明带有一位批评家所说的“前现代日本的强烈感情”以及对“武士世界的特殊情结”,年轻时曾研习过传统的剑术。日本的武士影片大多数以德川时期为背景。在那个和平时代,武士主要发挥行政管理而不是军事的功能,但黑泽明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他们的战斗。他说:“我认为,拍摄有关16世纪内战影片的,只有我一家而已。”
例如,在《七武士》和《战国英豪》两部影片中,黑泽明逼真地传达了德川幕府统一日本以前,人们对不安全和混乱的感受。他用生动而系统的画面表现了理想武士的技能和素质,他们的内功主要源于佛教的禅宗。不过,黑泽明也表现了新的火药技术如何造成了传统武士阶层的没落并推动了从封建制度向现代性的转变。他在这两部影片中,正如他的所有作品一样,向观众提供了他对日本历史的解释。
罗塞利尼的影片《路易十四》
罗伯托·罗塞利尼执导的影片《路易十四的登基》也是一次试图再现古代感情的尝试,罗塞利尼这部影片以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埃尔朗热1965年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传记为脚本,他还聘请埃尔朗热担任历史顾问。他阅读过那个时代的一些著作,其中包括在影片的镜头中所展示的路易十四曾经读过的拉·罗什福柯的箴言录,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描述的宫廷礼仪生动地表现在影片中。《路易十四》的制作可以说遵循了“目击风格”,例如拒绝使用蒙太奇的手法,选用非专业演员担任主角。影片还有效地利用了17世纪的画像所提供的证据,特别是当时的人物画像,虽然这位导演表现红衣主教马扎然死于病榻的场景显然是依据保罗·德拉罗什的绘画,而德拉罗什却是19世纪的画家。

这部影片是罗塞利尼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他从此决定把历史影片用作平民教育的手段,帮助民众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继拍摄《铁器时代》以后,他陆续拍摄了有关笛卡尔、帕斯卡、苏格拉底、耶稣的十二使徒和奥古斯丁的影片,还有《科西莫·德·美第奇时代》。这里仍以《路易十四》为例,导演使用了传统的方法,表现一位陌生人走进法国的宫廷以后,对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断地提出询问,例如,王后在国王的卧室里拍掌是表示国王已经行了房事。他的这种做法显然带有解说的意图。
《路易十四》作为一部历史影片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20世纪60年代,当职业历史学家还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日常生活史”的时候,这部影片就对日常生活给予了关注。它给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观点“日常生活的整个领域中充满了无数的运动,而其中绝大多数是短暂的运动,这些只能在银幕上表达出来……电影揭开了烦琐小事的领域”,加了一个绝妙的注释。
例如,这部影片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画面,一群普普通通的人聚集在河岸边,讨论着政治事件。它还不断地展现正在进行的工程和已经完成的工程,例如正在建筑中的凡尔赛宫。我们不仅在影片上看到了王宫里的盛宴,而且目睹了在厨房里准备宴会的过程。船夫、厨师、石匠和仆役在影片中充当的角色就像国王和廷臣们在历史书中充当的角色一样。在室内和室外的画面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动物,尤其是狗。一些用品,例如尿壶和加盖的盘碟也不时引起观众的注意。
第二,导演把注意力集中在路易十四取得权力和保持权力的方式上,把焦点放在凡尔赛宫的背景下,表现国王如何利用它来驯服贵族。在埃尔朗热写的传记中曾经提到,威尼斯大使说过一句简短的话,描写这位国王为廷臣设计了一种斗篷。根据这句话,这位导演设计了路易十四与他的裁缝组成的一个画面,国王下令廷臣从今以后要穿上用昂贵和绚丽的布料缝制的衣服。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表现路易十四在书房里脱下华丽的衣服和假发,这个动作使他变成了一个终将会死亡的普通人。这个镜头也许是受到了小说家威廉·萨克雷所画的路易十四的著名素描的启发。换句话说,罗塞利尼以展示图像为手段,分析图像及其在政治上的使用以及所产生的效果。
达尼埃·维涅执导的影片《马丁·盖尔》也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影片。它叙述16世纪发生在法国南方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名叫马丁的农民从军后,留下了妻子和农场。几年以后,有一个自称是马丁的人回到这里,起初,他被马丁的妻子贝特朗当作丈夫接纳下来,但并不是每个家人都相信他的故事。不久以后,又有一个自称为马丁的人来到这里,先前来到的那个人只得承认自己的真实名字叫阿尔诺·迪蒂尔并被处死。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担任导演的历史顾问。演员读过一些有关那个时代的书籍后,围绕着他们扮演的角色向她提出了一些问题。“我无法想象,贝特朗会等待那么长的时间才在法庭上作证,证明他是冒充的,”其中有一位演员说,“一个农妇为什么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这位历史学家回答道:“真实的贝特朗并没有等待那么长的时间。”
影片的情节应当依据“历史记录”,这给戴维斯带来了一些麻烦。尽管如此,她在记载中说,“眼看着杰拉尔·德帕迪约带着他自己的感受进入假马丁·盖尔的角色,却给了我一种新的思路去思考真正在冒名顶替的阿尔诺·迪·蒂尔”,从而推动了她自己的历史研究,使她写出了一本新书《马丁·盖尔归来》。作为一个纯粹的观众,我同样应当感谢德帕迪约。当我看到他在前面讨论过的由安杰伊·瓦伊达执导的影片《丹东》中扮演的丹东,我也进入了那位伟大革命者的角色,包括他的慷慨大方,他的热情充沛,他的贪得无厌以及他的自我尊大,从而让我对他扮演的这位法国历史上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当代史
优秀的历史影片绝大多数以较近的过去为背景。因此我接下来将集中讨论20世纪的历史,以及电影导演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代人解释历史事件上发挥的作用。例如,1917年、1933年、1945年和1956年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他们活着的时代。这里的讨论将集中在吉洛·庞特科沃和米克洛斯·扬索执导的两部影片上。
吉洛·庞特科沃执导的《阿尔及尔之战》于1966年献映时,那场战争刚刚结束。这部影片并没有使用新闻纪录片的任何片断,却给了观众一种观看新闻纪录片的感受,也就是说由于影片使用的摄影风格和使用了许多非职业演员,让它看上去就像目击者的叙述。法国人拷打和枪杀嫌疑恐怖分子的场面是依据对警方档案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他有可能得到了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合作,这位导演还执导过另一部影片《烽火怪客》以19世纪初的加勒比海国家为背景。这两部影片都用带有感染力的画面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认为历史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而且后者注定要取得最终的胜利。与此同时,庞特科沃抵制住了把所有的造反者表现为好人而把殖民主义制度的所有支持者表现为坏人的诱惑。影片清楚地展现了双方在斗争中犯下的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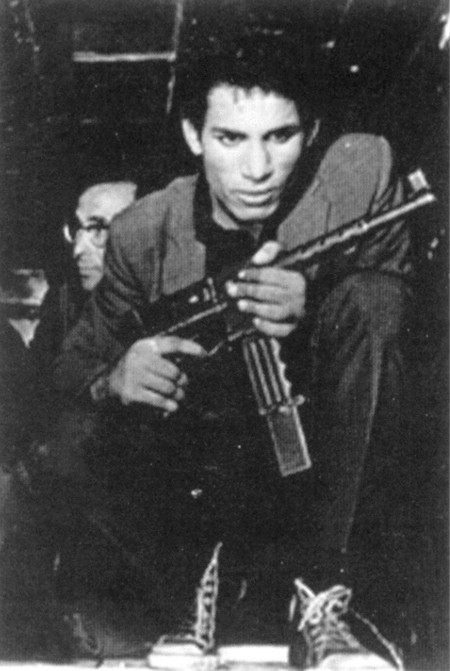
庞特科沃把一个重要角色马修上校安排在“错误”的一方,成了受同情的人物,从而把剧情设计得相当复杂。马修是一个勇敢的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这一角色部分地以真实的历史人物马素将军为原型。这位导演使用的另一种手法是选择了含糊的而不是胜利的结局。在影片结束时,观众发现当赢得了对法国人的胜利时,反抗者正在分裂成敌对的集团,相互争夺权力。
匈牙利导演米克洛斯·扬索的影片《红军与白军》原名为《群星与战士》,像影片《阿尔及尔之战》一样努力避免简单地从单方面的角度去表现苏俄的内战,尽管这部影片事实上是苏联政府为纪念俄国革命50周年而委托他摄制的。影片选择一个小地方作为观察角度,把背景放在红军(包括匈牙利自愿军)和敌对的白军反复争夺的一个小村庄里。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夺中,这个地方,包括村庄以及周围的林地、当地的一个修道院和战场医院,成了仅有的固定观察点。从这个中心来观察,双方的暴行显得同样恐怖,尽管在表现重大的细节时使用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例如,白军一般是职业军人,他们的暴行与红军方面相比似乎自发性较低,也更有纪律。
扬索在过去拍摄的一部影片《围捕》(原名《可怜的年轻人》)中,表现了一伙参加1848年革命的人落草为寇后遭到的镇压(影射人们记忆犹新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使用了宽银幕和长镜头。这两种手法也运用在《红军和白军》中,从而使得各个人物在影片中变得不那么重要,因而可以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历史事件的过程。然而,由于这部影片把背景放在一个村庄及其附近,因而也可以看作是对“微观历史学”做出的贡献。微观历史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被历史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但事实上早在60年代已经被电影史学家和批评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使用过了。
波·威德尔堡的影片《阿达伦31》也提供了一部微观的历史,讲述的是1931年在瑞典一个小镇的造纸厂里发生的罢工事件。这次罢工坚持了25个星期,最后,政府军队开进了这个小镇,借口保护工厂,向赤手空拳的游行队伍开枪。五名罢工者在这个事件中被杀,罢工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威德尔堡试图用个别来揭示一般,把镜头聚集在工人克耶尔与他的女友、工厂经理的女儿安妮之间的关系上,来表现对立双方的联系和冲突。埃德加·雷兹的影片《赫迈特》也把观察点放在一个小地方。这是一部长影片(为德国电视台制作),以莱茵地区的一个村庄为背景。赫迈特在希特勒时代生活了很多年,曾经从一个小地方的层次上观察过纳粹制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部影片的时间跨度很长,从1919年到1982年,既展示了社会变化、现代化的来临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社区失落的状况,又提供了对这些变化的解释。
无论在文字的历史中还是在用影片表达的历史中,聚焦于一个小地方,对于理解历史来说,可谓有得有失。有人可能会指出,在这两类历史中,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大家的共同愿望。贝尔纳多·贝托鲁奇导演的影片《1900年》就提供了这样一座桥梁。这部影片的名称本身就透出了这位导演抱有解释历史的意图。贝托鲁奇和罗塞利尼一样签署了1965年的《意大利导演的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宣告,他们制作电影的远大抱负是为了彰显人道,而人道是历史的根本趋势。影片《1900年》一方面探讨了贝托鲁奇家乡一个农场里的地主与农场工人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了两家人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又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历史上取得的重大进步,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影片都以各自的方式说明,在可视的叙事史中采用什么观察角度至关重要。它们通过在特写镜头和长镜头之间、仰视镜头与俯视镜头之间,与某个人物正在思考的东西有关和无关的画面之间不断地切换,取得了许多非常逼真而且难忘的效果。如果说这些影片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不同的个人和社会群体对同一个事件的看法存在着差异。在一部名为《斧战》的有关雅诺马莫人的非虚构影片中,导演提莫西·阿什通过讨论不同的角色对这部影片内发生的事件所做的不同解释,从而提出了这一论点。这一教益有时也被描述为“罗生门效应”,指的是黑泽明的影片《罗生门》的基本特征。这部影片把芥川龙之介的两个短篇故事转变为一个令人难忘的影视术语。影片叙述了不同的参与者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复述的一名日本武士的死亡以及他的妻子被强奸的故事。
路易斯·普恩佐导演的以阿根廷现代史为背景的影片《烽火人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对于过去,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可能看法。影片的主角艾莉希亚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属于中产阶级。她向学生讲授歌颂祖国的官方版本的本国历史,但有些学生表示怀疑。普恩佐叙述的故事是,艾莉希亚通过阅读非官方版本的历史书逐渐知道了阿根廷政府所犯下的使用酷刑和杀戮的罪行。影片通过这种方法鼓励观众去了解不同说法的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电影去魅和提高觉悟的力量。
但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给电影去魅的问题,即抵制“事实效应”,电影所产生的这类效应超过了快照和写实主义的绘画。剧作家布里安·弗里尔曾经指出,建构现在和未来的东西不是过去本身,而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有关过去的形象”,而用影片表达的形象能产生更大的力量。要从这种力量中摆脱出来,也许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鼓励历史学界去控制并自行制作影片,把这作为理解过去的一种手段。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朴茨茅斯工学院有些学生在历史教师鲍勃·斯克里布纳的鼓励下,制作了一部有关德国宗教改革的影片。在历史学杂志上发表影评的做法越来越普遍,也是走向这一方向的一个步骤。导演和历史学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就如同导演与人类学家在制作人种学影片上进行合作那样,也是一种手段,可以利用影片来推动对过去的思考。
(本文摘自彼得·伯克著《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