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76年初,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一千册很快售罄,“二版、三版也满足不了读者的要求”。“历史是最受读者欢迎的题材,既适合理解
1776年初,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一千册很快售罄,“二版、三版也满足不了读者的要求”。“历史是最受读者欢迎的题材,既适合理解
1776年初,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一千册很快售罄,“二版、三版也满足不了读者的要求”。“历史是最受读者欢迎的题材,既适合理解能力强的人,也满足吸收能力弱的人。我选择了一个耀眼夺目的主题。罗马是学童和政治家都熟悉的……我自诩一个光明而自由的时代将会接受对基督教的发展和确立的人性原因的研究而不加诽谤。”吉本晚年在其自传中回忆该书初次出版的情形时如此说道。他将大卫·休谟写给他的贺信抄录在自传中,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在吉本之前,休谟、威廉·罗伯逊这两位苏格兰人在历史写作领域中已是名声大噪。那时热衷于写史的英国作家也不在少数,但只有吉本的罗马史最终在史学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休谟的英国史虽在19世纪虽仍有影响,但逐渐淹没在麦考莱、卡莱尔、巴克尔、阿克顿勋爵等人的历史著作中了,而历史学家罗伯逊的著作在J.W.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中只有几段文字,相比于该著对吉本的长篇大论实在太微不足道了。苏格兰此时涌现出的其他历史著作,比如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在《历史著作史》中也仅一笔带过了。尽管如此,18世纪的不列颠尤其是苏格兰人创作的大量历史著作仍有其长远的意义。
18世纪苏格兰的文人作家很少只写历史主题的著作:休谟最开始撰写的是道德哲学,声名鹊起之后才落笔不列颠历史;弗格森以《文明社会史论》赢得了文名之后于1783年发表其《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和终结》;罗伯逊是个例外,1759年出版的《苏格兰史》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插入了一篇简短的欧洲经济史,其学生约翰·米勒最初出版的《等级差序的起源》显然不同于那时罗伯逊的苏格兰史或查理五世的历史,由其法学讲义衍生而来的《英格兰政府历史观》是一部宪政史,也不同于休谟的英格兰史。这些作者不仅写今天所谓正统的历史,还创作了大量今天可归结为社会史、语言史、科学史等领域之下的作品。在这类著作中,苏格兰人探讨社会的进展、宗教的起源、语言的形成、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等五花八门的主题。他们在这类著作中讨论人类社会的各种事务,根据他们分析的人类本性理解政治、经济甚至宗教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进程中诊治新兴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诊治:苏格兰启蒙史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的焦点便是这些问题,该书关注休谟、斯密、弗格森和米勒以及亚当·斯密等苏格兰作家的历史叙述和政治思想,剖析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宗教的功能、个人主义兴起后的家庭关系和商业社会的道德困境等问题的论断,理解他们对商业社会的政治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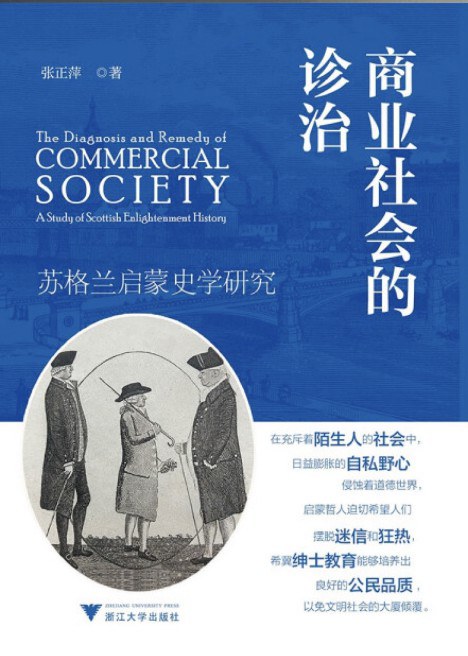
“另一种”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一词在18世纪并不陌生。1765年,伏尔泰的长篇论文《历史哲学》完稿。这篇论文讨论了遥不可及的年代里人类社会的历史,包括埃及、希腊、波斯、犹太、罗马、印度、中国等世界上各个民族的风俗和感情,这些历史多为古代史,而远古时期甚至史前史占据了大部分内容,最后的结尾是伏尔泰对自然法的肯定和对政治法律的批判。这篇论文尽管打乱了时空,但其对每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建筑等的讨论却足以成为《风俗论》“导言”,表明此书研究和讨论的内容。此前维科发表的《新科学》也致力于研究各民族共同性的科学原理,此后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也探索自然界背景下人类生命的历程,而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叙述了一部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发展史。18世纪启蒙哲人所写的这类历史著作不仅限于政治和军事事件,还包括了人类的一切活动,政府、法律、艺术、科学、风俗礼仪乃至人类的各种情感的历史等等。虽然“历史哲学”这一概念足以概括18世纪欧洲启蒙哲学的这一类历史写作,但当时的苏格兰人似乎很少使用该词。斯密的传记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讨论斯密“论语言的最初形式”时以“推测史”、“自然史”或“理性史”来描述这类历史,而对于苏格兰人来说,“推测史”这一概念或许更明确地界定了他们描述的历史写作及其意图。用唐纳德·R.·凯利的话说,“苏格兰之转向历史是在一个更大计划的阴影下开始的,该计划就是构建人性的科学”,有关人性的问题“要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启蒙哲人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进程,善于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恰如后来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划分。斯密在其《法理学讲义》和《国富论》中根据谋生手段将社会分为采集-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四个阶段。斯密的这一论断一度被20世纪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先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论断背后有关交换倾向、同情共感的人性科学逐渐被揭示出来。弗格森偏重以制度、礼仪、法律等所谓上层建筑的标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讨论文明社会的弊病及其解决方案。休谟与斯密和弗格森的社会史观不同,他没有将历史分成不同的阶段,而是根据社会规模分为小社会和大社会,而他对正义的起源以及政府的形成等议题的论述则以小社会到大社会的变迁为背景。

大卫·休谟
尽管休谟在《人性论》的导言中曾承诺要写一部文明社会的历史,但实际上并没有写出,他对社会的论述夹杂在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的论述中。在讨论正义的起源和发展时,休谟叙述了一段社会发展史。他抛弃了17世纪自然法学家们对自然状态的假设,强调人的社会性以及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无数“欲望和需求”,而与自然界凶猛强悍的动物相比,最初的人类在满足“欲望和需求”时只能依靠“薄弱的手段”,因此,人类有结社的需要。由于人类的另一种需要即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然欲望,繁衍后代、抚育子女时的依恋之情使得人类社会真正成为了现实。休谟认为,在时间、经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下,人类很快就会意识到维持这种家庭社会的好处。“家庭”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伯纳德·曼德维尔认为家庭社会的形成完全源于人类对外部环境的恐惧,但休谟认为血亲之情也是维系家庭社会的重要纽带。因此,最初的社会既不是敌对的“丛林状态”,也不是慷慨无私的人间天堂。而一旦形成了社会,很快就产生了“你的”和“我的”区别。即便在家庭内部,母亲对子女的爱慷慨无私,但成年子女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也是非常明显的。休谟没有详细讨论家庭的历史与家庭成员权威的变化过程,这一任务留给了约翰·米勒。
当休谟将同情和比较视为人类的两种基本秉性时,人类社会就开始形成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大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提供的稀少供给,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这两个条件是休谟论述正义起源的环境,后来被罗尔斯引为“正义的环境”。最初,一个成年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存,会在有限的供给中竞争生活物资,这种情形的确类似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但这些人很快就会发现攫取别人的物品会引起争斗和纠纷,甚至导致伤亡,于是逐渐形成一种“戒取他人物品”的习惯,以维持社会和平。在家庭社会中,每一位家长为了维持子女之间的和平,同样也会确立“戒取他人所有物、稳定每个人所有物”的规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当一个人感受到他人的苦乐和利益的激情并克制自己的自利之心、不去伤害别人侵犯别人的利益时,人们便形成了“普遍的公共利益感”,也就对上述规则达成了共识,此时正义萌芽了。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生活在同一片区域的不同家庭逐渐构成了一个群落或部落。在小型社会中,人们靠着与他人的同情共感能够直接感受到“公共利益”,清楚知道破坏这种公共利益的结果,因此家庭社会的规则开始推广开来,并围绕占有物的权利即财产权形成了三条基本原则:稳定财产占有物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诺言的法则。这里描述了一段正义的自然史。
这种叙述同样出现在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第一个时代”,“第二个时代”呼应了家庭社会扩大化的情形。当社会成员数量增多,小社会逐渐变成大社会时,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感受和同情变得淡漠和微弱,此时正义的执行就出现了问题。休谟需要解释,为何大社会中人们也必须执行正义,为何在大社会中遵守正义是人们最迫切的利益。当一个社会形成了已有的正义法则,一般来说内部不太容易引起争端,但当这个社会突然从对外战争中获得巨额财富时,“没有政府的社会”就极容易爆发内战,因为这涉及到利益的分配及其原则。虽然休谟论述到此时列举的是美洲部族的例子,但这种情形在欧洲的历史中也是数不胜数。于是,最初的政府便出现了,目的是“分配正义”,因为“大社会一方面有太多的占有物,另一方面又如此多现实或想象的需求”。这里也形成了一段政府的历史。休谟说,最初的民事政府总是军政府或君主制政府,然后才会逐渐发展为文明政府。而在这样的政府中,社会已是一个庞然大物,里面充斥着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变得微弱,为保障每个人的利益,政府的法律必须强制执行。当然,在休谟看来,政府还应该增进人们的福利,让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促进公共福利。这似乎是对曼德维尔“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这一论断的回应,但当休谟提出修桥筑路、挖掘运河、装备舰队等政府关切时,这种政府已是具备公共职能的文明政府,这样的社会即为文明社会。
文明社会的权威消解
这种充斥着陌生人的文明社会并非完美之物。在休谟眼中,这些单子化的个体很容易在宗教狂热和迷信中丧失自我,而文明社会的第一要务是祛除个人的迷信和狂热,让人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上帝的奴仆。《宗教的自然史》从后来所说的宗教心理学和“自然史”的角度分析了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自然史”可以描述自然界的演变历史,城市或村庄的过去与现在,也可以叙述一种情感或礼仪的历史,比如迷信的自然史、爱情的自然史等等。休谟“宗教的自然史”意在从人性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解剖宗教的最初形式和演变路径。最早的宗教是一神教还是多神教,是当时圣经史学与各种“异端学说”争论的问题。尽管自然神学和自由思想家对宗教的起源和形式有很多讨论,但圣经史学的强大影响并未消散,一神教的观念仍占支配地位。休谟说,“如果我们要考察人类社会从粗陋的开端到一个更为完善的状态的演进过程,那么多神教或偶像崇拜曾经、而且必定是人类最早、最古老的宗教。”此言表明休谟关注的是从“粗陋的开端”到“更完善状态”的漫长过程以及宗教的各种形式。这是休谟宗教哲学的核心问题
休谟认为,宗教史若是从最初的一神教堕落到偶像崇拜则完全颠覆了人类的认知过程。这种分析显然以人性和人的心灵发展史为基础。“根据事物的自然进程”——这是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常用语,“心灵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上升的:它通过对不完善之物进行抽象,从而形成一种关于完善的观念。”最早的神祇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纯粹精神”,还是一个“能力强大、有着人类七情六欲的存在”?若人类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全知全能的、洞悉宇宙规律的神祇,这种推测不符合心灵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休谟推测道,当野蛮人看到电闪雷鸣、洪水狂风等不规律的自然现象时,他们很难解释,便将这些未知原因想象为某些“看不见的存在”,甚至赋予他们和人一样的情感和外形,人们开始崇拜这些现象背后的未知力量,畏惧、敬拜它们,向他们献祭,祈求获得保护和希望,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祇。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诗歌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神祇,休谟以此作为多神论的证据。最初,一个能力有限的神祇只是被当作特定福祸的直接制造者,但俗世的各种经历让人们逐渐抬高某个神祇的地位、成为宇宙最高的创造者,于是,一神教从多神教中脱胎而来,但一个神的独尊地位并非一直延续传承。在《宗教的自然史》中,休谟论证了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循环往复,皆因人们对神的敬拜心理不断变化。
休谟将人的心理与宗教崇拜关联起来解释。最初的人们将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归因于“看不见的存在”的力量,是出于人类探索自然世界的好奇心驱使。人们对生存的希望和死亡的恐惧、对幸福的热切追求和对悲惨生活的担忧愁苦、对复仇的渴望和对未来的焦虑等等,这些欲望在人的内心不断发酵酝酿。而对神祇的崇拜多在于人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源于人类的情感,而非人的理性。即便是在一神教中,这种恐惧也无处不在。休谟在这里再次抨击了当时流行的一神论是理性产物的主张。他将一神论的形成与俗世的政治结构对应起来,认为一神论的观念只是源于“迷信中的奉承和恐惧”,“凑巧符合了理性和真正哲学的原则”。休谟后来在《英格兰史》中对肯特王国国王皈依基督教的叙述——君王们时而信仰基督教的上帝,时而又恢复偶像崇拜——恰恰印证了《宗教的自然史》中的论断。休谟深受17世纪以来怀疑主义的影响,他一边讽刺当时的宗教信仰之滑稽荒唐,一边批评宗教对道德的腐蚀,旨在祛除宗教迷信和狂热,为现代社会的道德义务清除宗教功劳的所有借口:“即使宇宙中没有神,正义之举也是他应该履行的,也是很多人本该履行的。”在道德上,人们可以是友善的无神论者。这是休谟对文明社会的宗教态度。
现代社会不需要宗教的权威,或许也不需要其他形式的权威。“人应该生活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凭借自己的力量,开辟自己的道路”。个人主义的兴起使得个体重新思考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能力和地位,思考历史上不同形式的权威。约翰·米勒在《等级差序的起源》中考察了丈夫与妻子、家长与子女、主人与仆人、君主与臣民的权利关系,重点讲述妇女地位的变迁。米勒遵循斯密的四阶段论,却将激情作为历史的起点。《等级差序的起源》开篇写道:“在我们所有的激情中,那些将两性结合起来的激情似乎最容易受我们所处环境的影响,也最容易受习性和教育力量的影响。因此,它们表现出最令人惊讶的多样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形成了最多样的风俗习惯。”这是米勒论述家庭史的关键所在,从这里出发考察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形成,尤其关注商业社会中父亲权威的消解。
根据斯密的四阶段论,最初的社会是采集-狩猎时代,女人因总体上力量弱小而地位卑下。但米勒根据当时已有的人类学资料承认,在历史上妇女曾在家庭中享有权威。这不是19世纪人类学家所说的“母系社会”或“母权政治”,而只是米勒笔下的一个例外。米勒对这种例外的承认及对早期社会妇女权威的论证源于他对人类情感的分析:总体上,母亲与孩子的联系要比父亲多得多,如果父亲常时间住在遥远的地方,那就很难在家庭中形成父亲的权威。除了这个例外,在大多数历史中,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是卑微而低下的,尽管一直以来,妇女都在家庭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家长的父亲一直在家庭中享有权威,到了商业社会,女性的真正才逐渐得到尊重和肯定。米勒认为此时女人的品行、才能、功劳才逐渐被社会看见,女人“不再是男人的奴隶和玩偶,而是朋友和伴侣”。
米勒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他在叙述家庭权威的历史过程中给予了妇女与男人同等的地位,一方面强调商业社会在消解父亲权威方面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担心家庭纽带被经济利益摧毁。对于后者,米勒只能寄希望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慷慨无私之情能够培养良好的道德,这希望也过于渺茫了。尽管米勒是法学教授,当时的法律也有家庭法,但他也不可能跳出18世纪提出有针对性的婚姻法。这一希望,大概只能寄托于爱情这种情感了。米勒的确插入了一段爱情的历史。他认为,野蛮时代是不存在爱情的,只有在生存条件逐渐变好时,情感愉悦尤其是两情相悦的爱情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米勒清楚财产和地位阻碍了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因此他才对中世纪骑士罗曼蒂克式的爱情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爱情产生了“最纯洁的行为举止,是对女性最大的尊重和敬意”。尽管实际上所谓罗马帝克式的爱情和“军事荣誉”一样是男人的“战利品”,但米勒希望伴随爱情而来的“礼貌、温柔和关注”成为现代家庭的情感基础,由此在家庭中培养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同情和仁爱之情,以缓解商业社会重利轻义、嫌贫爱富等弊端带来的道德败坏。
商业社会的道德困境
“财富与德性”的议题并不只属于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古罗马的哲学家们、14世纪阿拉伯的伊本·赫勒敦等都曾讨论过类似的问题。这个议题在18世纪变得如此凸显,改因商业繁荣后财富的增加速度远超过了之前任何时期。休谟对待商业社会的态度或许会被认为是乐观的,他在《论商业》、《论贸易的猜忌》等小品文中希望各国之间可以自由交易、想有频繁交换带来的好处。他或许没有十分关注财富对德性的腐蚀问题,但他注意到陌生人社会中的礼貌和礼节。休谟曾提到一个出身名门但境况困窘的人为何更愿意抛弃亲友故土投身到全是陌生人的社会中谋生,因为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们更可能保持一种礼貌得体的行为举止,在竞争中彼此合作并“为生活找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市场竞争自然充斥着各种伎俩和诡计,每个人会尽量为了维持自己的“骄傲”而追求那些足以引起“骄傲”的对象,比如权力、财富、地位、名誉等等。而斯密、弗格森、米勒等人担忧的正是人们在追求财富地位时导致的德性败坏。

亚当·斯密的雕塑
斯密等人清醒地意识到,人们对权威、高位者有着天然羡慕、钦佩、顺应之情,即便这种感情并非出于某种好处的考虑。当财富急剧膨胀、传统的道德秩序逐渐瓦解时,能够给人带来表面幸福的财富和地位,会极大刺激人类的这种自然倾向。斯密意识到,中下层通过德性之路和通往富贵之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时几乎是同一条路,但上层生活的情形并不总是如此,“成功和和晋升所依靠的并非那些博学多才、见闻广博的同侪们的尊敬,而是无知、专横和傲慢的上司们那怪诞、愚蠢的宠幸垂青”,“阿谀奉承与虚伪欺诈经常比真才实学更奏效”。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弗格森还担心,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充当国家中坚力量、履行公民职务的士绅们丧失勇武精神和爱国之心,导致政治技艺和民族精神的萎缩,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这才是苏格兰哲学家们最担心的问题。
无论休谟、斯密还是弗格森,他们都承认商业技艺或交换倾向源于人的本性。或许弗格森并不像唐纳德·温奇、理查德·谢尔等研究者那样对商业持深深的怀疑态度,或许弗格森远非商业现代性的怀疑论者。从《文明社会史论》《道德与政治科学原理》以及相关书信流露出的观点来看,可以肯定的是,他承认技艺是可以进步的,无论是手工技艺、商业技艺还是政治技艺。问题的关键是,一种技艺的发展会不会削弱其他技艺的能力,商业技艺的发展会不会削弱或妨碍政治技艺的提高?弗格森肯定商业技艺的积极影响:首先,随着商业技艺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依附关系,获得真实的独立,并想方设法确保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其次,德性的败坏与商业技艺的发展并无直接关联,因为腐败实际上一直都存在;最后,商业和贸易促进了人的社会性,每个人不得不维系与他人的联系,这便是斯密所说的“一个人人皆为商人”的社会。既然商业技艺与道德败坏并不是正相关连的,为何弗格森等人一再强调商业社会的道德困境?盖因在商业社会中,财富的本质更容易被商业民族曲解,让人们误以为财富便是幸福的真谛。盖因广泛的劳动分工更容易导致人的“异化”,“将造就公民和政治家的技艺分开,将制定政策和进行战争的技艺分开,试图肢解人的品质,摧毁那些我们想要改进的技艺”。
弗格森最担心的便是政治技艺的衰落,这一点在常备军和民兵制问题上尤其明显:常备军导致普通人不再练习守护自身安全所必需的技艺,漠视公共义务和民族荣誉。这是他对文明社会长吁短叹的原因。作为一位长期在大学从事教育的牧师,弗格森天生有一种教师使命。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养成良好公民的品质,希望他的绅士学生们能兼具政治家和军人的品质,希望他们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学会竞争、在对立和冲突中认清对手和自己的优劣之处,形成自己的见解,而不是轻易顺从他人的意见,在冲突和分歧的协调过程中获得公民自由。对政治领域中冲突和分歧作用的强调,让弗格森对文明社会或商业社会弊病的诊断与方案显得独具特色。
苏格兰启蒙作家考察了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过程,法和政府的历史,科学和技艺的历史,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历史等等,这些一方面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一套属于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政治话语。在追溯远古时代的人类状态时,他们明确抛弃了“自然状态”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设定,并将这一设定直接还原成真实的历史,把那些当时尚不能考察的人类早期史还原成“野蛮民族”或初民社会。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没有明显的鸿沟,“自然”与“技艺”或“人为”也不是对立的,历史与自然是统一的,而“文明社会”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当苏格兰人在历史中解释社会和政府时,他们便自觉抛弃了流传已久的“契约论”。在休谟看来,最初的社会是习惯和习俗的产物,最早的政府只是“人类的偶然为之”,人们服从酋长或君主的权威更大程度上源于习惯,而非“人民公平合理的同意或者自愿服从的伪装”。斯密和米勒都承认,权威和效用是组成政府的两个原则,而效用原则在边沁手里被赋予了更多内容,由此成为19世纪政治改革的思想源泉之一。
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还批判了一种悠久的传统,即将政治制度的建立归功于最早缔造法律的“立法者”。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最终形成源于整体的力量:人类事务中的制度与进步不是源于个人的努力,而是整个社会的活动。此言出自约翰·洛根,一个几乎被遗忘的18世纪苏格兰作家。这一评论完全吻合弗格森的那句经典名言——“众人迈出的每一步、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对未来而言都是盲目的,各国无意建立的机构,实际上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类意图的实施。”这种经典的“自由主义”远非19世纪所说的“自由放任”。当斯密说立法者或君主仍然需要在国防、司法、建设公共工程和维护公共机构等三个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时,这已经明示立法者绝不是“守夜人”,他们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苏格兰人的历史观中,推动社会前进的始终是人本身,他们期许的现代社会由摆脱了宗教迷信和狂热、享有平等权利的独立个体构成,正是这些个体以现代公民的各种技艺和道德品质来培育良好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