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一战结束百年,回首一战,法军的表现如何?坦克在一战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法国历史学家、记者,让-克洛德·德莱。
今年是一战结束百年,回首一战,法军的表现如何?坦克在一战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法国历史学家、记者,让-克洛德·德莱。
【编者按】
让-克洛德·德莱(Jean-Claude Delhez),法国历史学家、记者,1967年生于比利时洛林(Lorraine belge)法语区,1991年毕业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其后曾从事记者工作,也一直致力于研究洛林地方史与军事史,代表作为全景记录边境会战的《法军的哀悼日》(Le jour de deuil de l'armée française)一书。其著作在学术界广受好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哈特(Peter Hart)曾在其著作《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史》(The Great War: A Combat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中表示:“我发觉让-克洛德·德莱的作品绝对是无价之宝。英国的所有一战史研究者都应当阅读他的《边境会战:由亲历者讲述》(La Bataille des Frontières: racontée par les combattants)和《法军的哀悼日》。”今年是一战结束百年,回首一战,法军的表现如何?坦克在一战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作为一名法语学者,他对英语世界的一战研究,又有何评价?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让-克洛德·德莱。

从记者到学者
澎湃新闻:作为一位来自比利时的法国历史学者,是什么激发了您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兴趣?作为一位记者,您的职业是否对自己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有所启发?
德莱:我居住在凡尔登(Verdun)、色当(Sedan)、巴斯托涅(Bastonge)之间的边境地区,那里仅仅在一个世纪里就曾发生过诸多战争和战斗。从高卢人到马奇诺防线,土地上到处都是战事留下的纪念物:军人公墓、各类堡垒。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军事史就成了寻常的事情。作为历史学家,我对发生于1914年8月的边境会战尤为关注,这场在法德两军之间展开的会战虽然不算赫赫有名,却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场大战,它让取得胜利的德军得以长时间地攻入法国并占据具备战略意义的洛林铁矿,考虑到长达四年的堑壕战所需的庞大钢铁总量,德国的军事工业正是依靠边境会战才得以维持下去。此外,1914年8月22日也是法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写了八本书来介绍这场会战。
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记者,我在所有作品中都非常关注搜寻信息和核对数据。对于这类职业而言,它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是一种寻常举动,但它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普通。就我而言,对来自不同国家或是不同参与方的信息进行比较乃至让它们针锋相对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为了尽可能地趋近事实、趋近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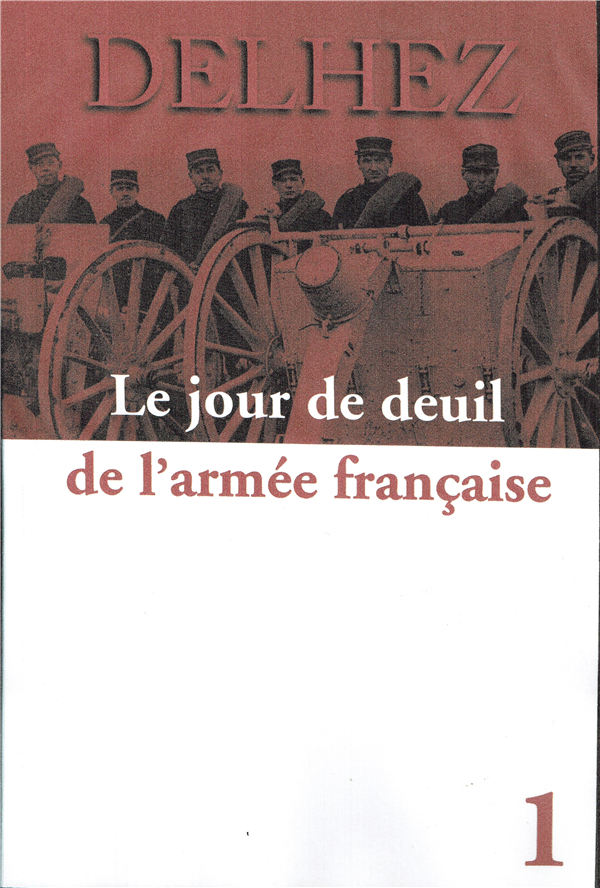
澎湃新闻:出于种种原因,中国读者往往通过英文图书了解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就是其中影响颇大的一本书。您对描写一战期间法国、比利时状况的英文著作评价如何?
德莱:就我的研究而言,我主要运用法文、德文的著作和档案材料。有关军事史的英文出版物的确为数众多,它们涉及到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各种军事问题,这也包括一战期间的法国和比利时。与一战题材的法国、比利时图书的情况相类似,英文图书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例如,美国人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尽管是本畅销书,在60年代取得过巨大成功,赢得普利策奖并受到肯尼迪总统的欣赏,但从学术角度来看,却很难说是好书,其中某些章节可以说近乎小说,不仅对法国的殖民军(Corps d’armée colonial)人员组成描述有误,甚至连吕夫(Ruffy)等历史人物的个性也自由创作。这可能正是它能够在出版后颇为流行,甚至直至目前仍然畅销的缘故。另一方面,我会推荐美国人罗伯特·道蒂(Robert Doughty)有关法国战略的著作《皮洛士式的胜利:大战中的法国战略与作战》(Pyrrhic Victory: French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the Great War)和英国人西蒙·豪斯(Simon House)有关边境会战的著作《失去的机遇:1914年8月22日阿登会战》(Lost Opportunity: The Battle of The Ardennes 22 August 1914)。这两本著作并没有落入传统英美观点的窠臼,前者拥有扎实的法军档案文献基础,后者则充分利用了法文与德文材料。
被德雷福斯事件撕裂的法国军队与社会
澎湃新闻:一战时期,上海法租界曾用霞飞、福煦、贝当这三位法军统帅来命名主要道路,或许出于这一缘故,他们也因此成为一战期间中国境内知名度最高的三位法军将帅,您对这三人的战争表现有何评价?
德莱:霞飞从1911年开始执掌法军并一直持续到1916年为止。这是一段漫长的任期,当你了解到法军总参谋长(战时自动转任为法军总司令)通常不会在这个位子上待很久之后,那就显得尤为漫长了。霞飞的继任者是尼韦勒(Nivelle)将军,但他在1917年“贵妇小径”之战受挫,接着遭到了解职。然后,由于“贵妇小径”战后的兵变影响,政府邀请贝当出任法军总司令,要求他重建能够投入长期作战的法国军队并谨慎地处理士气问题。他在法军总司令的位子上一直待到战争结束为止。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其中包括1918年11月的最终胜利——福煦成了协约国西线联军的最高统帅。福煦不仅是一位指挥官、一位将领,他还是一位战略家、一位军事理论家。福煦在当时声名显赫,但在此后却遭到了批评,而且他的思想看起来并不那么具备原创性。
不过,总司令的举动得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他是由政府选任的,并非孤身一人,而且必须和陆军部长合作——虽然由于克劳塞维茨著作的影响,在法国和德国,总司令或总参谋长是惟一负责指挥全军的人物。而且,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军队是由成千上万的军官(他们也需要肩负自己的职责)和数以百万计的士兵组成的。就军队的组织、训练、战术、装备……而言,这些归根到底都源于数年前做出的决定。我可以给出一个案例。在霞飞担任法军总司令期间,法国于1914年8月输掉了边境会战。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霞飞需要为这场灾难负责。可当你深入研究这场会战的细节后,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当然,这场失败首先要归因于德国军队的作战技能,在此之后,主要责任就得落到法军的中间指挥层身上,我用中间指挥层这个词组指代某些指挥集团军、军、师和旅的将领。此后,法军不得不进行人事迭代,解除了其中许多人的职务。
澎湃新闻:提到法军战前的备战状况,许多人认为德雷福斯事件对法国军队和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如何?
德莱:德雷福斯事件始于1894年法军总参谋部犹太裔上尉德雷福斯被控叛国,进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犹浪潮,尽管事后调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总参谋部却以维护军队威信为由拒绝平反,该案内幕被公开后演化为长达十二年的政治危机,对法国影响极大,它表明反犹的极端民族主义、天主教教权主义思潮在当时的法国具备极大的影响力,也使得温和共和派威信扫地,激进共和派掌握政权。当然,我们也一定不能忘记激进共和派掌权后的另一起事件——“卡片事件”(Affaire des Fiches),它的发生时间略晚于德雷福斯事件。当时,激进派的孔布(Combes)政府利用共济会网络秘密建立有关军官政治观点与宗教信仰的档案,打压信仰天主教的军官、偏袒世俗军官,此事泄露后导致政府垮台。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件,是因为法国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尽管共和国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军队里依然满是对过去怀有眷恋的军官,他们宁愿让法国成为帝国或王国,也不愿共和国继续存在下去,这种人里有很多是贵族。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一种将教权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等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反动政治思潮。德雷福斯事件表明,这样的思潮已经深深浸润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军官群体当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也正是法国政府决心政教分离(1905年通过《政教分离法》(Loi de séparation des Églises et de l'État))并确立世俗国家的时期,此后,掌权的共和派对法军指挥层进行了重组和整肃。这些事件都导致法国社会分裂为进步派与保守派两部分,其裂痕直至今日仍未完全弥合。就事件后果而言,1914年的法国社会所受影响比军队更为深重。当战争爆发时,统帅军队的是霞飞,他是一位共和派的将领,也曾是共济会员。不过,天主教徒、共济会员、贵族、平民都在军官团体中共存,意识形态冲突相对社会而言也较为缓和。
一战史中的神话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曾发现关于一战的大众认知往往存在谬误。例如,在《1914年的十二则神话》(Douze mythes de l'année 1914)和《攻击列日要塞》(L'assaut contre les forts de Liège)中,您指出列日要塞并未如传统说法那样有效延宕德军攻势、进攻至上(l'offensive à outrance)原则并非一战初期惨重伤亡的原因、巴黎的出租车并未对马恩河之战起到重大影响等,请问,为何这些与军事相关的神话会在法国、比利时乃至各个参战国流传甚广?
德莱:我们不仅应当考虑到一战历史本身,也需要理解历史是如何书写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就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们当然对这场世界大战兴趣极大。许多国家都出版了为数众多的书籍和文章。在那时,我们实际上仅仅处于书写一战历史的初期,可不幸的是,它并没有延续下去。因为欧洲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和平后就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极为重要,以至于让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都变得老套了。人们对一战兴趣不再。直到二十世纪末,有关一战的研究和出版才有所复兴。可是,这时的研究是从某些特殊角度出发的,尤其是在法国,对一战的研究与社会学的发展存在关联。从那时起,主要的关注对象是士兵的生活条件以及个人感受。至于有关一战的其他视角,此时仍然保持不变,有时甚至会出现一种与西线堑壕战相关的讽刺视角。时至今日,与对二战历史所做的研究和分析相比,一战所吸引的研究仍不算多。一般而言,纯军事研究已经不再是时兴的课题了。因此,就这些军事问题而言,通行的观点依然是间战期的看法。这就是某些持续百年的神话至今仍然存在的缘故。
澎湃新闻:我发现在您的新书《坦克:世纪欺诈》(Chars d'assaut: Un siècle d'imposture)一书中,您对一个世纪来的坦克战及其相关神话进行了精彩分析。请问您能否简单评述一战末期的坦克战?
德莱: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贝当将军告诉法军士兵:“不要放弃,坦克和美国兵正在赶过来!”实际上,坦克和美军都不是这场大战(以及另一场大战)的决定性因素。坦克是由英军在1916年发明的,这是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在考虑脱离堑壕战的方法,作为一种履带式的装甲兵器,坦克看上去是个好主意。可是,从技术层面而言,坦克并不可靠,甚至直到1940年都不可靠。坦克起初通常会遭遇的问题是机械故障。而且,虽然坦克起初带来了令人惊讶的效果,人们很快就在1916年秋季找到了反坦克手段,比如说将原有的火炮改为反坦克炮使用。德军在1918年第一次非常接近突破西线的堑壕防线,可他们的军队里几乎没有坦克。我在书中指出这种兵器已经被高估了整整一个世纪——直至现在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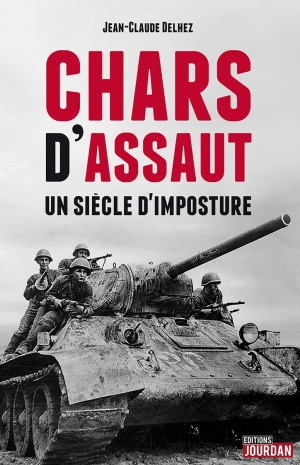
澎湃新闻:法国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最终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之一。您认为法军在战争过程中的表现究竟如何?
德莱:法军曾在150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与德军展开大战,当时,德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之一。法国在1870-1871年和1940年战败,交战有时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在1914年,法军开局非常不利,可是,由于马恩河会战的胜利,德军的入侵脚步被挡住了,协约国军队得以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维持堑壕战线并最终赢得战争。在每一场战争当中的每一个时刻,德军都能够凭借其质量优势——特别是其指挥优势——优于法军,甚至可能优于世界上的所有军队,1914年的状况也是如此。所以,法军最终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于我而言,法军与德军之间的差别往往就像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差别。法军倾向于服从,而德军倾向于自发。法国军队就像是一个庞大的公共管理部门,非常有组织、非常等级化,但反应非常慢。如果它能够像1914年那样成功度过战争的第一波冲击,它就有时间去适应、去进步。此外,一战并不仅仅是法国的胜利,其他国家也参与其中,除去军事层面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层面的问题。1914-1918年的战争是一场工业战争,经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英国的海上封锁给中欧帝国——德意志和奥匈——最终崩溃带来的影响。
中国与一战
澎湃新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北洋政府也曾向德国宣战,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等人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您曾著有《法国窥探世界(1914-1919)》(La France espionne le Monde (1914-1919))一书,对法军在一战期间的谍报工作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书中也曾引证法国档案,表明德国情报机关与孙中山之间曾存在联系。请问您当时是如何发现这份重要的档案文件?在您看来,这份文件可信度如何?
德莱:有位名叫格尔曼(Gehrmann)的德国间谍曾于1917年到中国与孙中山会面,并声称他与孙中山达成了协定,打算在中国发动战争,切断云南等省份与北方政府的联系。此人的行动应当放在德国全球政策(Weltpolitik)的背景下理解,该政策目的就在于通过革命、破坏、生物战……手段削弱柏林的敌人,其范围波及墨西哥、英属印度、中东等地。
这些信息源自德国情报人员间的电报。但法国军方破解了德方的密码,因而能够阅读敌人的电报。这就是一些与格尔曼谍报活动相关的文件会出现在法国档案里的缘故,这样的文件或许也会出现在英国档案里,因为英国的破译人员也能够掌握这种电报。虽然如此,这份文件仍然不过是格尔曼的回忆而已。他是否真的曾与孙中山达成协定,他是不是一个夸张自己作为的吹牛者?不幸的是,我在法国档案中并没有找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更多信息,德国档案则有相当一部分已在战时和战后被毁。
澎湃新闻:除了一战、二战相关著作外,我注意到您还出版了几本涉及比利时洛林地区的作品,请问您对地方史的兴趣缘何而来,日后还会涉及哪些研究领域?
德莱:我喜欢将历史与地理联系起来。除了军事史之外,我还致力于研究钢铁的冶金学和铁矿。我撰写了与洛林工业区相关的图书和文章。我现在仍然忙于研究这一领域,特别是热衷于一两千年前还没有鼓风炉时的冶铁方法。虽然冶铁鼓风炉早已出现在了中国,可当时的欧洲仍然没有这种设备。
当然,我仍然在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的下一本书将于今年秋季出版,它与一战期间谍报活动中的女性间谍有关。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荷兰舞女兼德国间谍玛塔·哈里(Mata Hari)被法国当局在1917年处以死刑,但在情报工作的秘密领域,还有许多效率远高于她的女性,这也是她们在历史上首次扮演此类角色。其后的作品同样会涉及情报,甚至可能与生物战相关。在一战期间,我至少可以举出德军和法军运用杆菌等细菌进行生物战的案例,这些病菌感染了欧美诸国的动物,我甚至怀疑这种举动可能与所谓的“西班牙流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