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史老张”又要出书了!继《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之后,《卿云——复旦人文历史笔记》编辑完毕,仍然是复旦大学校史散文,同样是细
“读史老张”又要出书了!继《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之后,《卿云——复旦人文历史笔记》编辑完毕,仍然是复旦大学校史散文,同样是细
“读史老张”又要出书了!继《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之后,《卿云——复旦人文历史笔记》编辑完毕,仍然是复旦大学校史散文,同样是细致耐读。“老张”是比我们高一年级(7814)的学长张国伟,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教历史,后到媒体任职,因曰“读史”。回想当年,我们同住复旦学生宿舍6号楼,一起在219房间看电视转播比赛,一起在大操场比赛踢球。光阴荏苒,这些年,1977、1978、1979年入学的大学生已经被称为“新三届”。在公众号上遇到“新三届”回忆文章,意识到“文革”后恢复高考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天宝遗事”,隔代说史,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写当年掌故,说说自己经历的人与事了。国伟兄在《相辉》和《卿云》里写了很多我们共同经历、后来逐渐淡忘的点滴事迹。还有一些人与事,本来知之不详,经过国伟兄的回忆、采访、收集和考证,今天读来更加清晰,有恍然开悟之感。展卷读来,最有感受的一篇是《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写得真好,就好像是那些年课堂情景的回放。篇中提到的所有老师,也都给我们班级授课,记得有好几门课程是两个年级合班上的。本篇记录系里的一批“老讲师”,就有胡绳武、邓廷爵、陶松云、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金重远、李孔怀、沈渭滨、许道勋、赵克尧、彭神保、夏义民等,这些都是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其中不少老师已去世,读来不胜唏嘘。这些老师当中,有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朱维铮先生、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华兴先生,还有因治学领域相近,后来常常遇见,每每请益的汤纲、许道勋、陈匡时、陈绛、汪熙、王苇、沈渭滨、黄美真、杨立强和庄锡昌等先生。国伟兄手上保存着四年本科的日记,栩栩如生,一一描述,复原了当年的课堂情景,真是弥足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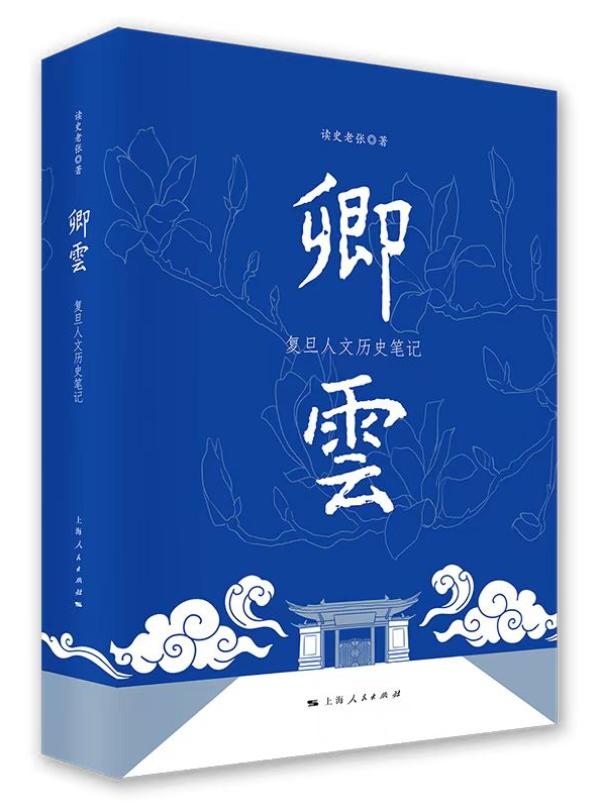
国伟兄概括得非常准确!20世纪80年代初给“新三届”开课的教学骨干、科研中坚,是一大批“讲师”头衔的教师。1957年以后,运动不断,动辄“反白专”。但是复旦文科毕竟底蕴丰厚,学脉顽强,在教研室一级,还靠老先生顶着。20世纪60年代培养的年轻教师,仍然以业务为重,积累了一批人才。那几年“拨乱反正”,各校还没有来得及恢复评定高级职称,一、二级教授之外,副教授都很少。“讲师们”重上讲台,不再害怕被扣上“白专”的帽子,都敢亮明自己的师承,编写自己的讲义,提出新问题,自觉摒弃“教条主义”式的讲授。老师们敢教,还有学生们不敢学的?根据“新三届”同学阅历丰富的特点,“讲师们”鼓励同学尽快投入学术研究,边学边干。于是,哲学、中文、历史系都建立了学生自主的学术社团。历史系1977级的刘申宁、马晓鹤、程洪、刘征泰,1978级的曹景行等人发起“史翼社”。二年级时,班主任张广智老师推荐我代表1979级同学参与社务。我清楚地记得,同学们的习作都是经过“讲师们”的指导,发表在油印刊物《史翼》上。
“蓦然回首,一个时代远去了。”(国伟语)今天看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复旦校园的师生关系算是非常融洽。学生找老师,老师见学生,全不须等office hour。有学问可讲,“讲师们”就会很兴奋,拉着学生聊。教我们“中国文学史”课的中文系骆玉明老师,教我们“逻辑学”课的哲学系郑伟宏老师,经常会在课后陪着同学聊。走着走着,到了6号楼的寝室里,放下书包接着聊;一起去食堂吃饭,继续聊。“风也过去了,雨也过去了”(流行歌词),老师们不再顾忌聊天后的结果中会有什么“小报告”,同学们便也借着聊天内容靠近了真学问。“新三届”经历的固然是中国大学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生源繁杂,年龄差很大,加上师生关系密切,学术热情迸发,问题意识强烈,校园氛围中确乎是出现了某种样式的精神升华。回顾复旦大学已近一百二十年的校史,我觉得,“新三届”在学的时代特征和震旦、复旦初创时期的精神气质十分相像。当年,马相伯受蔡元培委托,带着项骧、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贝寿同、胡仁源、黄炎培等一批高年资(举人、秀才一大堆)的学生,诀别科举制,追求“新学”和“西学”。他们在徐家汇天文台的一幢弃置的二层老楼上创校,吃、住、教、学在一起,自治校务,自编教材,相互教学。正是在那个因陋就简的初创时代,马相伯为震旦学院奠定了“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校训,为传唱至今的复旦校歌定了基调。

马相伯
如《卿云》《相辉》中描述的那样,我们那几届学生感受到的是“文革”以后大学里面的师生关系密切、情感融洽,相互之间有一种强有力的共识。三观一致固然重要,学术上的共识却更可贵。
“阶级斗争”理论不能再用,曾受批判的哲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理论应该恢复,新的研究方法应该重新引进。说实在的,新闻、政、经、法专业学生或许有跃跃欲试、投入改造社会的,文、史、哲的学生却在考虑更加深入的问题——“改革开放”能不能持续下去。未来社会的走向并不确定,“拨乱反正”能走多远也没有把握,但是师生们不走回头路的决心都很明确。这个师生共识,就是我们的初心;带着这个共识,记着上一辈、更上一辈老师们的嘱托,我们这一代人才走到了今天。
除了授课主力的“讲师们”,《卿云》和《相辉》中还写了很多复旦文科的“老先生”。国伟兄描写的更上一辈的老先生栩栩如生,也很精彩。“新三届”本科生能够见到老先生的机会并不多,多半是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或者是在一些重要讲座的时候。国伟兄翻检日记,在场景回放中方才记起,我们那几届拍毕业照,校长苏步青、书记盛华,还有周谷城、陈仁炳、蔡尚思、杨宽、程博洪、靳文翰和谭其骧等老先生都来了。我们年级的任课老师中,还是有不少是“文革”前评定的副教授,如秦汉史专家杨宽、日本史专家吴杰、南亚史专家张荫桐和世界史学者黄世晔等。现在记起来,谭其骧先生当系主任、黄世晔(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复旦附中原校长)先生当系副主任的时候,定了一个做法,即邀请外系相关教授专门开课,如哲学系严北溟教授、经济系叶世昌教授等。这个做法延续了老复旦文史哲不分家、各门学问相通的好传统。复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毕业生比较灵活,容易做“跨学科”的研究,和老先生主政以后一系列“拨乱反正”有关系。
给我们授课的高年资教授中,最为难得的是二级教授陈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先生,他给我们1978、1979级学生上了两年“专业英语”课。陈先生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同列为“大右派”,因始终不被平反,退而求其次,他力争给本科生上课的教师权利。从“牛棚”里出来后,多年的木工间体力活,让陈先生看上去异常衰老。但他拄着一根stick,坚持在上午从徐家汇搭乘校车,来江湾上课。陈先生从劫后存书中,选出《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是当时还很难读到的文章。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鲍斯威尔的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讲丘吉尔、罗斯福、马丁·路德·金,也讲他的父亲、著名神学家陈崇桂,还有他父亲的朋友司徒雷登,以及他们夫妇自己在密西根安娜堡大学的同事、邻居丁观海夫妇及其孩子丁肇中……陈先生把我们拉进他生活的年代,让同学们瞬间明白了百多年的“中国与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自己是在大二学完了陈先生的课,决定在“中国基督教史”的领域做一点相关的研究。国伟兄在《相辉》中已经写了不少陈仁炳先生的事迹,《卿云》中提到陈先生的地方就稍稍简略,读者们应该回过去参看那部姐妹篇。

复旦第一教学楼
我以为像陈仁炳先生这样的前辈的事迹非常值得读,他们是后人治学的一面镜子,放在那里,对自己的学业、专业和职业都会给予启示。20世纪80年代初期,复旦又一次焕发生机的时候,这些老先生才是专业内的精神支柱。他们阅尽沧桑,专业过硬,人脉广泛,还敢于直言。可能这样的人数不多,惟各系都有一二人,则足矣。当年考进复旦的时候,家里人经常的告诫就是“当心不要做右派”。在课堂上见到了陈先生这样的“大右派”,反复研读,潜心理解,知道了他们一生的甘苦,于是如何治学,如何识人,如何论世,心里也有了方向。这种有着一个个具体标杆的学习,正是理解复旦精神的钥匙。他们继承了自马相伯创校以来的进步主义和人文精神,坚守学术而对学术持开明精神,懂得政治而能全面看待政治,他们真正代表了复旦大学自创建以来的那么多的传奇,那么深的传统。
“新三届”正是在复旦又一次焕发生机的时期进入校园。“文革”结束前,复旦卷入了历次政治运动,校园再开,已是伤痕累累。那几年里,甚至在“讲师们”之间的“派性”还没有消退干净。但是,老师们在“文革”中遭遇了十年坎坷,一旦“解放”,便十分渴望把自己半辈子的经历,浓缩成为教训、知识和智慧,传授给我们。“文革”之前,北大、复旦的本科都是五年制,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课程开设是各综合性大学最齐全的。五年课程,加上老先生和海外学者的讲座、外校名教授的专业课,都要压缩在四年内教完,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毕业后立即就能投入研究工作。老师教得拼命,学生学得起劲,虽然设施简陋,但“新三届”的学习氛围之浓,可说是造极登峰。

复旦历史系1978级毕业留影
借着国伟兄的《卿云》和《相辉》,让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复旦校园,读着读着,心情确实难以平静。那是一个远去了的复旦,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仍然不失为一个美好的复旦。鸟瞰一下现在的邯郸、枫林、江湾、张江四大校区,文、理、医、工、政、法、经、商学院齐全,两相比较,复旦的建筑规模和系科建制堪称是一个综合性大学(“comprehensive university”)了。对比起来,20世纪80年代我们“新三届”在学时的复旦,好像只是一个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有的学者就是凭这些硬件设施来判断,认为现在的教育部大学水平已经超过了民国时期的公、私立和教会大学。但是,大学的办学质量,与图书馆、实验室、科研中心的学术质量有直接关系,而与校园规模和大楼高度只是间接关系,并不能纯以它为尺度。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都是各校历史上的办学高峰,他们因陋就简,传承了大学精神,培养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师级人才。那一时期,昂扬的学习热情、自由的探索精神、正确的研究方法,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最高峰。20世纪80年代,庶几算得上是复旦历史上的另一个高峰,我宁愿还要说,今天各大高校的办学质量,未必就真正度越了那个时期留下的高峰,至少在精神气质上是如此。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他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在各个校园里流传,成为名言。按梅贻琦的说法,这句话仿照的是《孟子·梁惠王下》句式:“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然而,据我们查考下来,梅贻琦这句名言,却是由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老校长在之前的20年首先说出来的。1912年10月22日,马相伯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天到校发表演说,略云:“大学者,非以校舍大,学生年纪大,及教习修金大,乃以学生有高等之程度及高尚之道德而大。”(《时报》1912年10月24日)参与编著《马氏文通》的相伯先生,精通中西经典,“四书”运用尤其熟练。他仿照的就是《孟子》句式,而且针砭大学教育的含义扎得更深。我们都知道,民国学界从前清遗老处接手的“京师大学堂”,又老又穷,师生积习败坏校风,国家津贴却拿得一点不少。据报道,北大师生听闻马老此言,“愧赧汗下”。
马相伯、梅贻琦这两位大师,是以他们的震旦、复旦、北大、清华治校经验来讲这样的话,当然是有他们自己体悟到的道理。我以为,两位校长说的意思是:办一个好大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师生们不能齐心协力地达成一种共同追求,校园内形不成一个坚强的学术共同体,达不成一种有真理价值的共识,即所谓的大学“学派”,那么纵有再高的大楼、再大的校区,也是徒劳无益的,根本就培养不出什么“大师”来。大学,在中古拉丁文unversitas 的原义中,就有由师生自主讲学结为群体的含义。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曾经有过一次相当程度的“思想解放”,释放出些许数量的“自由精神”,也慢慢开始结成一个个学术共同体,这就是我和国伟兄共同见证的那几年的复旦校园。
最后,还要感谢国伟兄把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些事情写出来,可以用作纪念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相辉》的序言,是国伟兄和我共同的“西方史学史”任课老师张广智教授写的。张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当年的“讲师们”之一,对我们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写论文。张老师是史学史家,一眼就看出国伟兄的《相辉》是一部史学著作,它“以独到的眼光,梳理校史”;“每篇立意明确,且问题意识彰显”;“笔法(和正史)不一样”,不严肃刻板……
这次出版《卿云》,国伟兄要我来写序言,我想他就是留了一块地方,让我来一起回忆,共同记录我们那个“远去的复旦”。我和张广智老师一样,真的认为《相辉》《卿云》中的许多内容,将来都可以进入复旦校史,占据独特的篇章。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校史编写组”撰写的《复旦大学志》;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编纂委员会”撰写的《复旦大学百年志(1905—2005)》。然而,官修的正版校史,未必能容纳下所有复旦人的经历,那就需要一些私修的民间校史作补充。学历史的都知道,清初修《明史》,有国史馆官建,更有江南士人的私修。朝廷版《明史》,必得是综合了多部私修史稿,才做出了一部“良史”。复旦是官方的公立学校,但自马相伯创建,李登辉呵护,上海和江南商绅以及大小校友、学生家长们的鼎力相助,复旦也是一座具有民间办学传统的名校。“谁的复旦”?它也应该是校友的复旦,民间的复旦。如今,复旦已经有了“自由而无用”的民间校训,当然也可以有“读史老张”写的《相辉》《卿云》民间校史。国伟兄自己谦虚地说,《相辉》和《卿云》的出版,“不失为校史细节的补充”。哪里!这两部民间校史姐妹篇,可以阅读,可以传世,将来可以进入正版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