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桥大学教授蒂莫西·布莱宁(Timothy Blanning)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开明专制君主与普鲁士强国之路》(Frederick the Great:Kin
剑桥大学教授蒂莫西·布莱宁(Timothy Blanning)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开明专制君主与普鲁士强国之路》(Frederick the Great:K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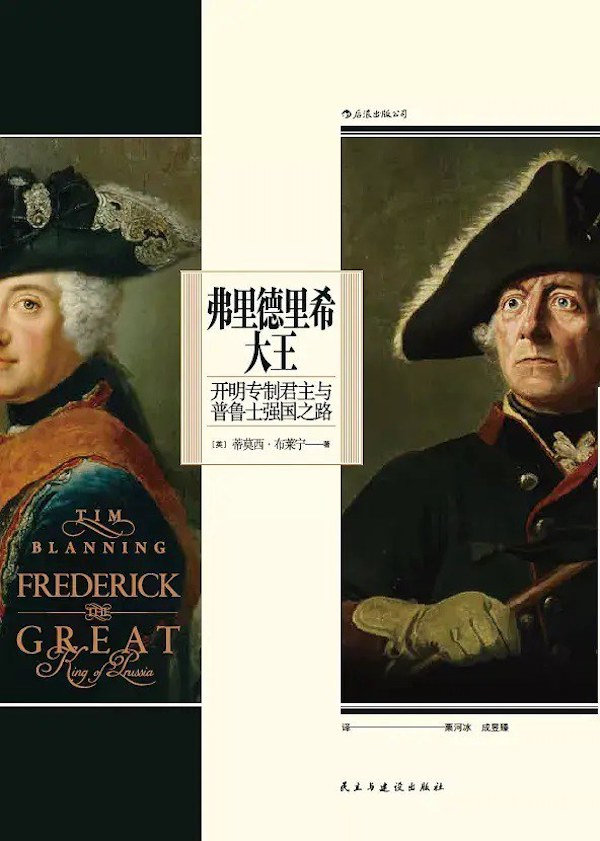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大王:开明专制君主与普鲁士强国之路》,[英]蒂莫西·布莱宁著,栗河冰、成昱臻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2022年1月版,536页,110.00元
剑桥大学教授蒂莫西·布莱宁(Timothy Blanning)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开明专制君主与普鲁士强国之路》(Frederick the Great:King of Prussia)曾在2016年荣获英国国家学术院奖章,被认为是目前有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最优秀、最具有批判意识的一本传记。在过往的中文介绍中,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常被译为“腓特烈二世”或“腓特烈大帝”。或许是因为弗里德里希(或腓特烈)的称号Friedrich der Große中有“伟大”(Große)一词,因此中文译者往往会约定俗成地将其译为威武雄壮的“大帝”。实际上,但凡熟悉欧洲历史者,都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和可商榷之处。布莱宁在著作中,同样详细地考察了一番普鲁士国王的头衔问题。
众所周知,在德意志地区乃至除俄罗斯以外的整个欧洲地区,仅有一个皇帝头衔,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Kaiser der Römer),自十五世纪后就长期由哈布斯堡家族把持。根据《1356年金玺诏书》的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选帝侯们选出,先后统治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即为其中之一。而霍亨索伦的统治者成为国王则是1701年的事情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祖父弗里德里希一世通过支持当时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对抗法国的路易十四,换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其“国王”头衔的承认。正如布莱宁所指出的:登基时,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国王头衔的全称是“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in Prussia),而非“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of Prussia)。此间的微妙之处在于,弗里德里希一世“晋升”国王前的头衔分别有两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勃兰登堡选帝侯与普鲁士公爵,而普鲁士地区并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疆界”内。
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登基仪式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即现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举行,排场极尽奢华:动用了一千八百辆马车、三万匹马把达官显贵们从柏林送到加冕礼现场;国王的长袍上镶嵌着钻石纽扣,而国王与王后王冠的花费甚至超过了整场加冕庆典的预算。或许为了与国王的地位相称,弗里德里希一世把“柏林从一个穷乡僻壤建设成为一座合乎国王身份的首都”,在柏林市中心和西北部修建了两座华丽的宫殿,甚至还效仿法国建立了当时颇为时髦的“科学院”,邀请莱布尼茨出任第一任院长。然而,当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即位后,却一改父亲暴发户式的奢华排场,遣散宫廷乐团,关闭图书馆,在宫廷内禁止一切戏剧、音乐与舞会,几乎把所有国家财富都投入了扩军备战的宏大事业,而他本人也以“士兵国王”自居。用布莱宁在书中的话来总结就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看来,“人民存在是为了国家,国家存在是为了军队,军队存在是为了勃兰登堡的领袖”。
弗里德里希二世自幼就笼罩在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专横跋扈的阴影之下,这个阴影甚至伴随其终生。正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彻底推翻其父弗里德里希一世奢华的宫廷风尚一样,弗里德里希二世自幼就站在自己父亲的对立面。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对文学、哲学乃至音乐嗤之以鼻,年幼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却会把父亲送的玩具士兵推到一旁,专心致志地弹拨着鲁特琴。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眼中,理想的教育是宗教性和实用主义的,任何人文艺术学科都只会培养“娘娘腔”式的无用爱好。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得不私下里悄悄购买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诗歌文学在内的法文、拉丁文、古希腊文图书,存放在自己的秘密图书馆里。父子间的矛盾在弗里德里希二世进入青春期后终于彻底爆发。1730年,在密友卡尔的协助下,十八岁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彻底摆脱“暴君父亲”的统治,逃亡到英国。这个笨拙的计划当然以失败而告终,弗里德里希二世被作为“叛国者”关进大牢,密友则被斩首。经此打击后,弗里德里希二世面对残酷的父亲选择了屈服,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而这种阳奉阴违的父子关系,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弗里德里希“分裂的人格特质”:一方面依靠漂亮的言论与高雅的文艺爱好为自己赢得开明专制的名声,另一方面却依旧贯彻承袭自父辈的威权统治风格。
继位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内政上奉行“宗教宽容”政策,声称“我在罗马和日内瓦之间是中立的”,而他的王国既欢迎新教徒,也欢迎天主教徒。这套政策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希望通过“宗教宽容”保持王国内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此外,很多证据都能表明弗里德里希二世可能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甚至不惮于公开宣扬他的怀疑主义论调。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期间,废除“酷刑”一直被视为其“开明”的象征。他自己也说过:“一个文明社会意味着其中的人们不会经常遭受野蛮和痛苦的折磨,无论是在绞刑架上,还是审讯室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酷刑就此在普鲁士消失,而是将施加酷刑的权力收归国王一人之手。用弗里德里希二世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刑事判决都要转交给我,否则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各省的人只会随意乱搞”。当遇到他认为罪大恶极或需要警告的罪行时,酷刑仍然是一个选项,例如1746年图谋叛国的但泽领事的头颅就被挂在长矛上示众。

阿道夫·冯·门采尔的油画《无忧宫的长笛音乐会》(185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有演奏长笛的爱好并颇有造诣,即便在战场上也会随身携带长笛
即便弗里德里希二世对音乐、艺术情有独钟,依旧不难发现他人格中的威权特质。继位后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终于可以尽情释放这方面的爱好,但他与音乐家、艺术家的关系始终是威权性质的。在表演歌剧时,他会直接站在乐队指挥身后盯着乐谱,监督、指导整个演奏过程,如同指挥他的士兵。一位同时代的英国音乐理论家在造访过柏林的宫廷后,曾这样评价:“(这位)陛下在音乐方面允许的自由并不比他在政府社会事务方面允许的更多。他不满足做臣民生活、财富和事业上的唯一君王,他甚至要给他们最无辜的娱乐制定规则。”当然,最能体现他这种人格特质的领域还是尔虞我诈的国际政治。
1740年12月16日,继位刚半年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给大臣的信中写道:“我大张旗鼓地渡过了卢比孔河。”这一天,他率领继承自父亲的精锐大军,攻入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统治的西里西亚地区。讽刺的是,就在发动战争前两个月,这位普鲁士的新国王刚出版了他用法文写成的大作《反马基雅维利》。在这部著作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本正经地写道:“战争如此的不幸,其结果如此不确定,其后果对国家如此具有毁灭性。”然而,他一旦得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并由其女儿玛丽娅·特蕾莎继承其家族领地的消息,几乎立刻决定向处于内外动荡之中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宣战。这种极端虚伪的言行不一,甚至让与之交好的伏尔泰也感到困惑:“他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写得这么好,同时又立即像马基雅维利的英雄一样采取行动……国王的位置已经改变了这个人,现在他像穆斯塔法、塞利姆或苏莱曼一样享受专横的力量。”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西里西亚的军事冒险取得了空前成功,最终于1745年迫使玛丽娅·特蕾莎同意将富饶的西里西亚地区割让给他。
凯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此后也就有了“大王”的名号。这种极端性格显然直接受到糟糕父子关系的影响。长期面对专横、威权的父亲,使他养成了一种近乎人格分裂的行为模式,极端的现实主义与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在这位国王身上共存。蒂莫西·布莱宁在书中论述他的政治手腕时评价道:“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证明了自己和父亲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在成为“大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身上,这种言行不一的特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而赌徒式的冒险作风也几乎葬送了他和他的王国。在1756年8月爆发的“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延续先发制人的战略,亲率大军攻入了领国萨克森。在随后漫长、残酷的战争中,普鲁士不得不同时与哈布斯堡、俄罗斯乃至法国作战,尽管取得了一系列诸如罗斯巴赫、洛伊滕会战等战役的辉煌胜利,但总体国力的差异依旧是难以逆转的。虽然靠着以少胜多的战例和普军优秀的军事素养,弗里德里希二世为自己赢得了“名将”称号,蒂莫西·布莱宁却在书中指出:“从七年战争的记录来看,普鲁士人绝不是无敌的。在16次主要会战中,他们输了8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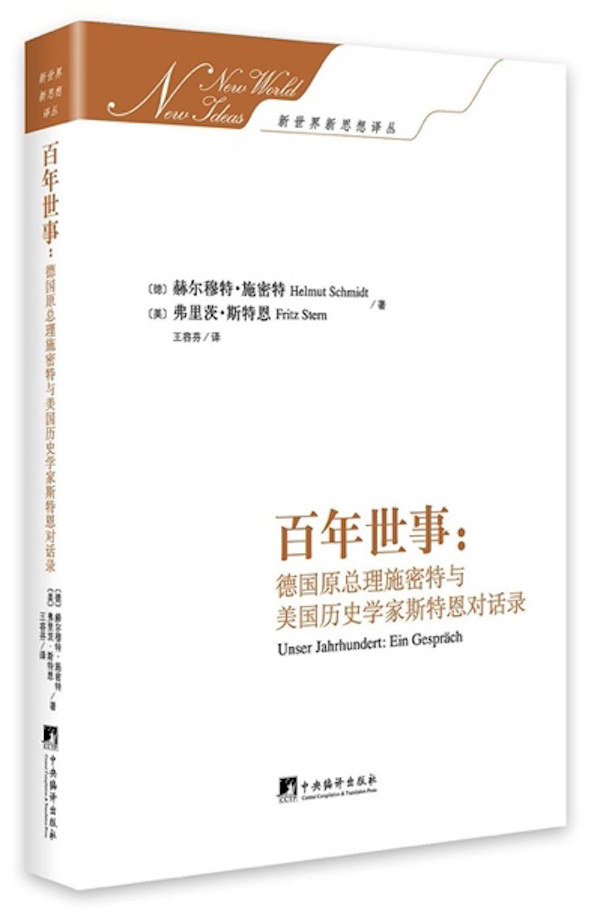
《百年往事:德国原总理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对话录》,赫尔穆特·施密特、弗里茨·斯特恩著,王荣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与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曾在2007年的对谈中,多次提及德国人对弗里德里希的历史记忆问题。在一段对话中,施密特将弗里德里希二世视作一个分裂的人物,认为他治下“内政自由”即实行所谓开明专制,外交上则是一个“小号的亚历山大大帝”。斯特恩则认为所谓“内政自由”有些夸张,至于对外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只是“很走运”。
1762年初,当时近乎破产的普鲁士仅剩下六万人的军队,俄奥联军再次向柏林袭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王国崩溃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在此时突然病逝,继位的彼得三世从小崇拜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威名,登基后立刻化敌为友,不仅宣布停战,甚至转而与普鲁士结盟。凭借这个近乎奇迹的转折,弗里德里希二世避免了亡国的命运,也保住了西里西亚。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世的历史记忆中,人们似乎总是津津乐道于他“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却忘记了“奇迹”发生前的困境。不同于过往绝大部分的传记作者,布莱宁认为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大的军事优点并不在于指挥,而是陷入绝境后仍然坚持到底的意志,这让他能够等到“奇迹”发生:“总之,他是一个中等水准的将军,但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军事领袖。”
尽管普鲁士的军事实力直至法国大革命前夕才恢复到七年战争前的水准,但出乎意料的战争结果依旧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王生涯镀上了亮眼的金色,似乎也巩固了“大王”的名号。这一名号在他死后甚至被进一步放大乃至神化。长久以来,最为人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传记肯定是苏格兰人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那部《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传》(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

托马斯·卡莱尔的六卷本《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传》
从1852年卡莱尔首次去德国搜集资料,到1865年全部六卷出版完毕,足足花了十三年之久,以至于卡莱尔将这个漫长而艰难的创作过程称为“我与弗里德里希的‘十三年战争’”。在这部传记中,卡莱尔将弗里德里希二世视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以伟人之姿、一己之力将普鲁士改造成了一个能与传统欧洲列强比肩的近代化国家,其本人也正是卡莱尔英雄史观最好的载体和实践者。毫不夸张地说,卡莱尔笔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形象几乎成为后世大众相关历史想象的主要来源,而他的英雄史观更凭借弗里德里希二世传记在德语世界受到追捧。
施密特提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形象在德意志地区流传的情况,并对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嗤之以鼻。用施密特自己的话来说:“可怕!那本书我上中学时读的,可把我害苦了。”在这位经历过二战东线战场的前总理看来,“上世纪我们崇拜的假英雄太多了”。而斯特恩则指出:“关于卡莱尔,他的名声之所以这么坏,这还得归功于德国人。德国人拿了他的思想。”以至于在二战结束前,德国人几乎只知道卡莱尔这两本书:《英雄和英雄崇拜》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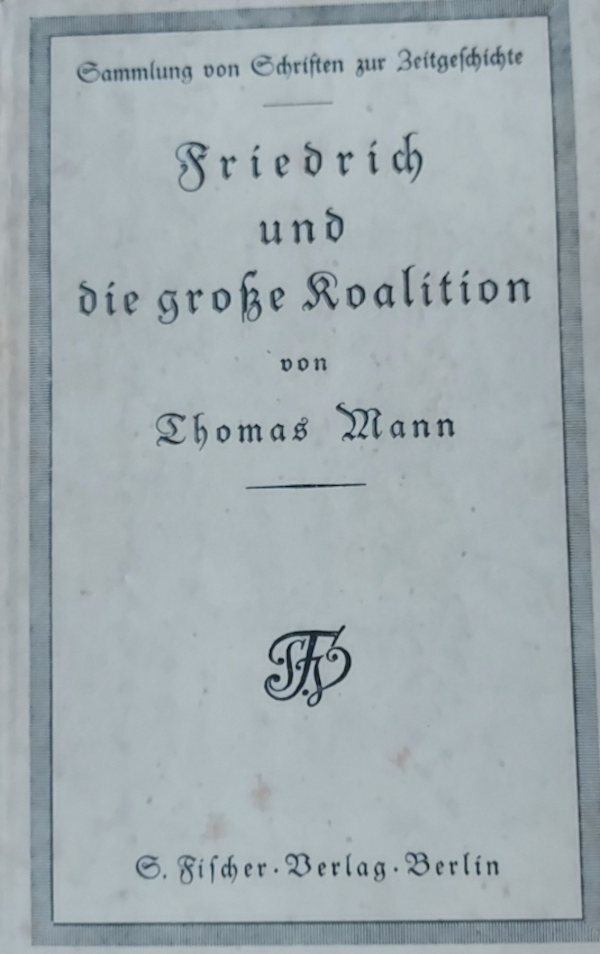
托马斯·曼的《弗里德里希与大同盟》初版
1915年,四十岁的托马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乌云笼罩下,也写过一本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记《弗里德里希与大同盟》(Friedrich und die große Koalition)。此书相较于卡莱尔的皇皇巨著只是一本小册子,主题和基调却极为类似。在这本小册子中,托马斯·曼将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在战争与国际政治中的起伏视为德意志命运的象征,而七年战争期间四面被强敌环伺的普鲁士正如一战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样。他还将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攻入萨克森的情景做了类比,认为“今日的德国就如同当年的弗里德里希大王。我们必须完成由他开启的斗争,我们必须再一次去战斗”。而托马斯·曼写作时最重要的参考书便是一本简略版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传》内容摘选。

纳粹宣传电影《伟大的国王》的海报
到了纳粹时代,弗里德里希二世同样被树立为一个可以借古喻今的历史榜样。1942年,当战争局势渐渐开始不利于纳粹德国之时,德国上映了一部以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主角的大制作“国策电影”——《伟大的国王》(Der große König)。这部传记片可以视为托马斯·卡莱尔传记的一次影像化尝试。戈培尔极为欣赏片中对弗里德里希二世陷入困境时不屈斗志的描写,认为“眼前的苦难都将会成为力量的源泉”,而片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形象自然影射着同样走向战争困境的希特勒,只不过,前者的运气要好得多。

电影《帝国的毁灭》中的一个场景,布鲁诺·冈茨饰演的希特勒在地堡的书房中,望着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画像
当希特勒躲在总理府地堡里时,手边就有一套戈培尔献给他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传》。在第三帝国即将覆灭之际,希特勒经常会在地堡的书房里,望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画像发呆,甚至将罗斯福总统的病逝想象成属于他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