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历史学诞生于19世纪,它是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工具而被构想和发展出来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欧洲的民族史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它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
现代历史学诞生于19世纪,它是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工具而被构想和发展出来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欧洲的民族史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它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
现代历史学诞生于19世纪,它是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工具而被构想和发展出来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欧洲的民族史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它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有毒的垃圾场,里面充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气,而且,这种毒气已经渗透进大众的意识中。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清除这个垃圾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怯步的挑战。
中世纪早期居住在欧洲的民族的真正历史不是从6世纪开始的,而是从18世纪开始的。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生活在遥远过去的人们曾经有某种民族或集体认同感,而是,过去两个世纪的文化活动和政治冲突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群体和政治群体思考的方式,我们不能再装模作样地对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分类提供一种“客观的”观点,假装这个观点没有受到这两百年的影响。根据我们当前的认识,不仅族群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两百年的发明,还要看到,我们假装用来进行历史学科学研究的分析工具也是在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偏见中被创造和完善的。用来研究和写作历史的现代方法不是没有倾向性的学术研究工具,而是特别用来推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既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不可靠,那么,只有在开始的时候简单地回顾一下导致它们被发明的过程,从而认识到我们调查的主观性,才是公平的做法。
族群民族主义与革命时代
民族主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的故事已经被讲过很多遍了。有人将当今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描述成“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认为它们是由19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创造出来的,是这些人将早期浪漫主义的民族传统变成了政治纲领。事实上,大量的书籍和文章——有些是学术性的,其他的则是面向大众的——都表明,很多“古老的传统”,从民族身份到苏格兰格子花呢,都是政治家或企业家们在近代的幼稚发明。这样的描述非常真实,尤其因为,它使人们关注到,在关于所谓古代意识形态的详细描述中,近期的个人和群体起到了形成性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如果因为这些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就推定它们应该被抛弃或被当成不重要的事情,或者认为“一定程度上被想象出来的”就等于“虚构的”或“无足轻重的”,那么,这将是非常荒唐的。首先,虽然当今这种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可能确实是由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创造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想象的民族——即使与近代的民族不同,它们却一样强大。19世纪的学者、政治家和诗人不是简单地编造了历史,他们利用了已经存在的传说、书写材料、神话和信仰。为了构建政治统一体或政治自治权,他们只不过采用了新的方法来利用这些元素。其次,虽然这些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它们非常真实和强大。历史上所有重要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心理现象,而心理现象——从宗教极端主义到政治意识形态——杀死的人很可能比黑死病(Black Death)杀死的人还多。
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出现的具体过程在欧洲各个地区以及欧洲之外的地区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在缺乏政治组织的地区,例如德国,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可以用来创造和提升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在政府强大的国家里,例如法国和英国,政府和思想家们则无情地压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关于历史的不同记忆,以便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历史和相似的语言、文化,进而把这种统一性扩展到过去。在多族群的帝国里,例如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那些以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自居的人不仅利用民族主义来要求获得成为独立文化实体的权利,还因此要求获得政治自治的权利。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激发独立运动的典型模式——特别是发生在东欧和中欧的独立运动——都假设创造这些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需要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小撮“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一个被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进行研究;第二阶段,一群“爱国者”向全社会散播学者们的观点;最后,民族运动在第三阶段被传播到最广大的群众中。从18世纪的德意志到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最后到20世纪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亚洲、非洲和美洲,想象的共同体被创造的过程都大同小异。
大多数信奉民族主义的人不会对这个关于民族觉醒和政治化过程的总体描述提出异议。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觉醒的”知识分子仅仅是认识到了一个已经存在的被压迫的民族,还是他们发明了他们所研究的民族。例如,与其他许多学者不同,克罗地亚历史学家伊沃·巴纳克(Ivo Banac)认为:“一种意识形态为了被接受必须从现实出发。民族主义可以尝试讨论一个群体被压迫的状态,但却不能创造这些状态。”在以下这个层面上,他完全正确:如果人们没有被压迫和被歧视过,那么,向他们做出帮他们摆脱这些困境的承诺是不大可能会起作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样公式化的观点却隐含着危险:它意味着,群体——例如历史上潜在的民族——早在被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对每个特定的群体来说,被压迫的境况都是独特的;民族主义是这些灾祸专属的解决之道。换句话说,即使民族主义并未编造民族被压迫的状态,但它肯定能制造民族本身。19世纪,在革命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随着老贵族阶层在政治竞技场上的明显失败,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创造了新的民族。接着,他们将创造出来的民族投射到了久远的中世纪早期。
近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文化背景起初是欧洲知识精英群体对古代社会的迷恋,法国和德国知识精英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对古典文化和古典文明的迷恋主要得益于尼德兰、法国和德国大学的培养,比如哥廷根(Gottingen)大学。这种迷恋为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的根本性逆转奠定了基础,彻底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
民族主义之前的群体身份
在中世纪中期和文艺复兴早期,“民族”与宗教、血统、贵族权力和社会阶层一起,为活跃于政治领域的精英们提供了一种相互交叠的、可以用来标识自己和组织协作行动的方式。然而,对一个民族的归属感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最为重要的纽带。共同的民族身份没有将社会高层与低层、领主和农民团结成一个深刻意识到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们更无法通过把民族身份投射到遥远的大迁徙时代来获得最基本的自我认同。相反,他们太过期望能在遥远的古代找到统一性,以至于他们自觉地认同了罗马的社会和文化。
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法国、德意志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却逐渐开始将自己认同为罗马帝国主义扩张的受害者了,比如高卢人(Gauls)、日耳曼人或斯拉夫人。产生这种身份转变的政治背景决定了它们后来不同的走向。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君主政体展现出了惊人的连续性,政府的存在从来没有受到质疑,反而是单一的法兰西民族曾受到过怀疑。在德国,虽然作者们从9世纪开始就偶尔地提起日耳曼人,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日耳曼人政府,他们对日耳曼人文化传统的认识并不一定与政治传统相对应。在其他地区,比如波兰,“民族”感情只是贵族阶层的特权,他们与那些在他们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之间很少有,甚至没有任何感情的共鸣。
法国人关于法国人身份的认识是在绝对主义王权与贵族或平民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国王与贵族,或者说第一等级,就统治权的归属展开了争论。国王和贵族要求获得统治权的宣言都基于这样一个观念:从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时代起,平民,也就是第三等级,构成了奴隶种族,高卢人被罗马征服之后就丧失了自由,因此,他们作为劣等人无权获得政治自主。这一描述利用了一个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古老传说,这个传说用各种思维观念证明了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这些思维观念将农民简化为一种可以遗传的、几乎非人的状态。相反,贵族阶层并不是高卢人的后代。他们是法兰克人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是那些进入高卢,打败并驱逐罗马地主,建立起了统治权的“自由”战士的后裔。这些观点利用了世纪罗马史家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所描绘的形象,他对自由的日耳曼人大加赞颂,和那个时期的罗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观点还要求对图尔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著作以及中世纪早期的其他材料进行特别的解读,以便突出法兰西民族(nation franҫaise)具有的自由的日耳曼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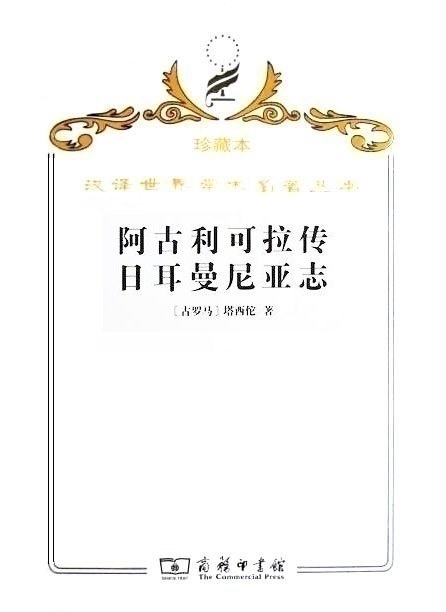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究竟谁才应该拥有统治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贵族阶层还是国王?这是讨论的要点。1588年,王室宣传者居伊·德·戈吉尔(Gui de Coquille)甚至认为,法国王室家族的创建者、所有法国国王的祖先于格·卡佩(Hugh Capet)有撒克逊人的血统。撒克逊日耳曼人的背景使他的王位继承者成为真正的法国人,用法语说就是“vrai Franҫois”。18世纪,像路易·德·圣西门(Louis de Saint-Simon)、弗朗索瓦·德·费内隆(Franҫois de Salignac de Fénelon)和亨利·德·布兰维利耶(Henri de Boulainvilliers)这样的贵族都赞同这个观点,即古代晚期的高卢人本质上是一个奴隶的种族。5世纪时,自由的法兰克战士通过征服获得了高卢地区。只有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贵族阶层——才是真正的法国人。国王应该与他们分享权力,就像查理曼(Charlemagne)所做的一样。
波兰也发展出一个类似的传统,波兰的精英们试图全然否认他们的斯拉夫人血统。早在16世纪中期,波兰的编年史作家们就已经宣称,波兰的精英阶层不应该把在土地上劳作的广大斯拉夫农民视作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而应该认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身份,因为萨尔马提亚人是一个曾被希腊和罗马民族志作者们提及的古老的草原民族。7到17世纪,萨尔马提亚血统论已经成为贵族(szlachta)精英们用来将自己与下等社会阶层区分开来的工具了。
革命的民族主义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一切,但唯独没有改变人们对过去的想象。尤其在法国,革命时期流行的宣传虽然接纳了法兰克人和高卢人的双元认同方案,但完全颠覆了这个方案包含的意义。法国革命理论家西哀士(Abbé Sieyès)撰写的关于第三等级的小册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虽然接受了贵族阶层的日耳曼血统论,却认为这让贵族阶层对法国而言成了一个外来的、入侵性的因素。真正的法国人是高卢人的后裔,他们长久以来忍受着外来者的奴役,先是罗马人,后来是法兰克人。是时候将这个外来的种族赶回到法兰克尼亚(Franconia)的森林里,将法国还给第三等级,也就是真正的法兰西民族了。
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言论却与官方的革命意识形态南辕北辙。因为官方革命意识形态在宣扬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该独立并拥有主权时,并不认为“人民”可以由语言、族群或血统来定义。相反,支持公益反对特别利益,接受自由和共和国的法律,这才是人民所应该具备的不过,从更实际的层面来看,这个隐含的假设却坚持认为法兰西民族应该用共同的文化传统来定义,尤其是用法语表达的共同的文化传统。
作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先锋,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哥廷根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也利用了塔西佗神话。但是,他们最初只是在语言和文化统一体的背景中对其进行解读,并没有预先假定或提出一个政治的统一体。自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在15世纪末被重新发现,人文主义者们就迷恋上了一个自由的、纯粹的日耳曼人的形象。从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的《日耳曼尼亚解说》(Germania illustrata,1491)到雅各布·温斐林(Jacob Wimpheling)的《日耳曼人简史》(Epitome rerum Germanicarum),再到海因里希·倍倍尔(Heinrich Bebel)的《日耳曼人的谚语》(Proverbia Germanica),以及其他作家,他们都在寻找一个德意志统一体以及关于它的历史。不过,这个统一体仍然是纯粹文化意义上的统一体,并非政治统一体。说德语的地区从来没有合并成一个独一的、文化上同质的王国。即使是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一直都包括了重要的斯拉夫语和罗曼语(Romance)语区。而且,宗教改革(Reformation)和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导致的深刻分裂使政治和社会统一体直到19世纪才进入文化视角的领域。
但是,在文化民族主义中出现了一些特点,一旦文化民族主义被政治化,这些特点就会变成进行政治动员的强大工具。这些特点包含了这样一个信念:德意志“民族”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公元9年,日耳曼人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曾在条顿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击败罗马将军瓦罗斯(Varus)并摧毁了他的军队。这些文化民族主义者还颂扬德语,他们不仅认为德语是德意志人身份的具体表现,还强调教育是延续和强化人们对这一民族遗产热爱之情的方法。
相信德意志“民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种政治使命,尤其不意味着进行扩张的使命。赫尔德的思想缺乏政治维度的思考,这一点比德国以及每个国家都有权在符合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的观点更能证明上面的结论。赫尔德对斯拉夫人的热情也许比对德意志人的热情更高,他竭力主张斯拉夫世界用自己的文化代替“正在衰败的拉丁-日耳曼文化”。赫尔德和哥廷根学派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文化活动而不是政治行动。
直到拿破仑时期,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才步履蹒跚地出现,它是对法国击败普鲁士和占领莱茵兰地区的回应。1804至1808年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m Stein)是引导民众抵抗法国人的重要力量,最终在民众中激发起了反抗精神。他强烈要求,在法国人被驱逐之后,诗人和作家们都要为塑造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形象添砖加瓦。德意志民族的边界显然是不确定的。先前的神圣罗马帝国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说德语。在普鲁士王国内,除德语外,人们至少还使用六种其他的语言,包括波兰语、拉脱维亚语(Latvian)、卢萨蒂亚语(Lusitian)和爱沙尼亚语(Estonian),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却说法语。说德语的地区不仅因为政治而分裂,还因为方言的不同、宗教和三十年战争以来相互仇恨的历史而四分五裂。不仅如此,就连普鲁士国王也对所有的群众运动充满警惕,生怕民众会参与到教育和政治领域中。
因此,像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赫尔德和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这样公开支持文化统一体的作家们一开始并没有在政治领域获得反响。德意志的诸侯们在政治统一中无利可图,而中产阶级则没有政治兴趣和政治纲领。瓦恩哈根·冯·恩斯(Varnhagen von Ense)是一位有教养的上等阶层的普鲁士人,当他看到国王因在耶拿会战(battle of Jena)中大败于拿破仑而不得不在1806年离开柏林时,他没有感受到任何爱国主义的忧虑。他与其他和他有着相似出身的人都为国王感到难过,但是,他们“就是无法鼓起任何真诚的政治热情,政治报道和公报甚至都没办法成为他们一整天唯一的关注点”。相反,许多对政治抱有兴趣的德意志知识分子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以乐观的态度迎接拿破仑的胜利。
支持把赫尔德的文化理想政治化的力量既不来自德意志的主流知识界,也不来自普鲁士国王,而是来自英国。为了继续向拿破仑施加压力,英国试图在法国东面引起民众的反抗。英国希望通过支持普鲁士的造反者开辟出“第二个旺代”(second Vendée),即一个内部的游击队式的抵抗运动,类似于法国保王党在旺代地区顽强抵抗革命的做法。英国的目标与施泰因男爵不谋而合,他确信容克(Junker)阶级已经没有能力挽救普鲁士了,为了能对法国进行更加有效的抵抗,他试图在王国内受过教育的文化精英中培养出一种爱国主义感情。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调动起前几代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感情中的一些元素:强调共同的语言(而不是强调共同的宗教或政治传统,因为这两者根本不存在);实施一项国民教育计划;强调公民地位是连接民族过去与未来的纽带。这样一来,施泰因的利益与英国人的利益变得一致了,英国对那些愿意将文化和政治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资助。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是这些德意志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他渴望将日耳曼文化政治化。他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将1世纪的罗马人等同于当下的法国人,将他和当代的德意志人等同于反抗罗马扩张的日耳曼抵抗者。这样一来,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人美德的描写和在《编年史》(Annales)中对阿米尼乌斯及其大败瓦罗斯和罗马军团的记述都成了检验统一的德意志人身份的标准。通过这样的解读,费希特找到了一个在神圣罗马帝国造成复杂政治局面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德意志统一体,而且还证明,德意志人历史上就曾经抵抗过罗曼语入侵者。费希特在他的著作《告德意志同胞书》(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中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德意志人身份:一方面,它与斯拉夫人形成了对比,因为“与欧洲的其他民族相比,斯拉夫人似乎还没有足够清晰地显露出来,以至于人们还无法明确地描述他们”;另一方面,它与罗马化的“条顿人的(Teutonic)后裔”,即法国人也形成了对比。与这两者不同,德意志人身份的核心优势在于地理和语言上的连续性。在19世纪,语言与身份之间的联系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法国哲学家埃蒂耶纳·博诺·德·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就已经提出,“每种语言都表达了说这种语言的人的特点”。然而,费希特用非常特殊和带有煽动性的方式发展了这一传统。在他的第四演说词中,他宣称,德意志人是众多“新-欧洲人”中唯一一个仍然居住在他们祖先居住地并且保留了他们原始语言的民族。尤其是德语这门语言,它将德意志人团结起来,使他们与上帝创世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像法国人这样接受了拉丁化语言的民族所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德语与罗曼语系的语言不同:罗曼语系的语言以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词语,而这些词根是在远离说罗曼语的人居住的地方形成的;德语则完全是在日耳曼的元素上发展出来的,从一开始就是用来描述现在仍然由德意志人居住的这个地区的。因此,德语这种语言可以很快地被所有说德语的人听懂并理解,它在说德语的人与他们生活的环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即时的、相互的联系。我们必须把费希特的《告德意志同胞书》放在当时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在人们普遍认为法国的占领将会持续很长时间的时代背景中,这本书里的文章可以被称作“活命主义的文字”,因为作家的目的是要给人们希望,鼓励人们在被法国人占领的背景下进行反抗。虽然法兰西帝国的迅速垮台结束了德意志人对这种情感的独特需要,但是这种情感经过转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虽然知识分子,比如费希特,对政治事业的参与可能对拿破仑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参与以一种新的方式将知识分子与政治界和现实斗争联系在了一起。当他们参与到政治活动领域时,他们获得了新的声望、财富奖励和官方的优待。虽然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在拿破仑之后重建了欧洲秩序,但是,德意志知识分子与政治界的强大联合并没有因此结束。为实现德意志统一,曾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负责招募知识分子的施泰因强化了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联系。1819年,他创建了“德意志古历史文化研究学会”(Gesellschaft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学会的箴言“对祖国的神圣之爱给人以勇气”(Sanctus amor patriae dat animum)看似陈词滥调,却概括出了一个纲领。这个学会是一个私人组织,它的创建征求了许多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建议,例如歌德、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格林兄弟(the Grimm brothers)、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和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博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来自德意志各诸侯国和德意志邦联(German Bund)的捐款为学会提供了资金,学会开始致力《日耳曼重要历史文献集》(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编辑和出版。起初,这些捐款很难到位,德意志的诸侯国没有强烈的捐款热情,而施泰因出于爱国的原因并不愿意接受外人的捐款,例如来自俄国沙皇的捐款。直到政治家们逐渐意识到爱国史学能对抗革命的意识形态后,施泰因才找到可以用来继续这项计划的资金。
然而,资金只是其中的一个难题。另一个难题是确定哪些是日耳曼人历史上的重要文献。筛选的依据是科学的印欧语文学(Indo-European philology)原则,它们是由荷兰的古典语文学研究者以及才崭露头角没多久的哥廷根古典语文学研究者们发展出来的。
印欧(Indogermanisch)比较语文学诞生于1786年。这一年,英国的东方专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认识到,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是从同一个源头发展而来的,而哥特语(Gothic)、凯尔特语(Celtic)和波斯语(Persian)也很可能来自这个语族。二十二年后,德国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冯·施勒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进一步发展了琼斯的观点,不过,他在著作《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研究》(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中提出,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族都来自梵语。在接下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中,德意志学者弗兰茨·博普(Franz Bopp)、雅克布·格林(Jacob Grimm)以及丹麦学者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Rask)接受和修订了这些刚刚萌发而且相当直观的联想,并发展出一个可以考查语言发展过程和近似性的方法,最终创造出一门新学科——印欧语文学。这门快速发展的学科不仅明确了语族的构成和分类,提出了斯拉夫语族、日耳曼语族、希腊语族和罗曼语族的概念,还使对这些语言最初形式的科学研究成为可能。自文艺复兴以来,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们就被当代日耳曼语族内各语言的相似度所吸引。他们对古代语言之间的联系感到好奇,例如,由传教士乌尔菲拉(Ulfilas)主教在4世纪翻译的哥特语《圣经》与“克里米亚的哥特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据说这一群体到16世纪时仍然说一种可以被识别的日耳曼语。这样一来,把有关欧洲各种语言的知识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在历史上存在细微差别的知识体系成为可能。语文学,无论是关注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的传统古典语文学还是新兴的日耳曼语文学,都是推动《日耳曼重要历史文献集》这项新的科学事业的重要方法论。
施泰因对德意志古历史文化研究学会的规划不只是以《日耳曼重要历史文献集》的形式编辑和出版关于德意志历史的原始资料。在编辑这些原始资料之前,先要建立一个用来登记德意志历史原始资料的标准。这意味着要在历史中定义德意志,并把这个历史看作德意志固有的历史。承担这项任务的学者们并不是极端的政治民族主义者。不过,他们的工作却极大地拓展了民族主义者们的野心。根据编辑们的主张,在说日耳曼语的族群曾经定居过或统治过的地区内写成的文献以及所有关于这些地区的文献都应该被认为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文献。《日耳曼重要历史文献集》的编辑们首先提出,曾被“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统治过的所有地区都应该被包含在内,即从意大利南部到巴尔干半岛的区域。此外,他们附加上了整个法兰克人的历史,包括在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和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治下的高卢地区,即今天的法国和比利时,写成的编年史和法令;收录了西哥特人(Visigoths)、勃艮第人(Burgundians)和伦巴底人(Lombards)的法律,以及那些曾在今天的意大利和罗纳河谷(Rhone valley)定居过的说日耳曼语的族群的法律;还将佛兰德尔伯爵领地和斯凯尔特河(Schelde)以东的尼德兰划入其中,因为说日耳曼语的弗里斯兰人(Frisians)曾经殖民过这些地区。通过出版一系列古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将一些非洲人并入了德意志历史中,例如描写过非洲日耳曼汪达尔人(Vandals)的维克多·维特瑟斯(Victor Vitensis)。同样地,还有高卢-罗马人(Gallo-Romans),如奥索尼乌斯(Ausonius);罗马元老院议员,如卡斯多里乌斯(Cassidorius)和斯马科斯(Symmachus)。《日耳曼重要历史文献集》采用的视角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它在德意志的定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野心,这样的野心是《德意志人之歌》(Lied der Deutschen)都不敢言明的,这首歌曾因“从默兹河到梅梅尔,从阿迪杰河到贝尔特”(Von der Maas bis an die Memel/Von der Etsch bis an den Belt)的诗句而臭名昭著。
通过定义德意志历史的原始资料,《日耳曼重要历史文献集》为德意志历史划定了边界。哥特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以及其他的早期“族群”被纳入同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中,它开始于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创建之前,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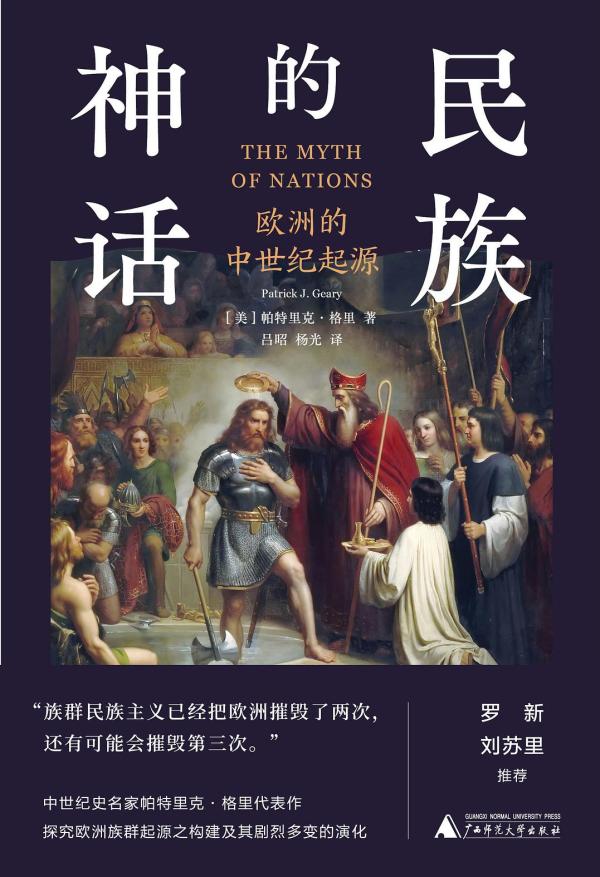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美]帕特里克·格里 著,吕昭 杨光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