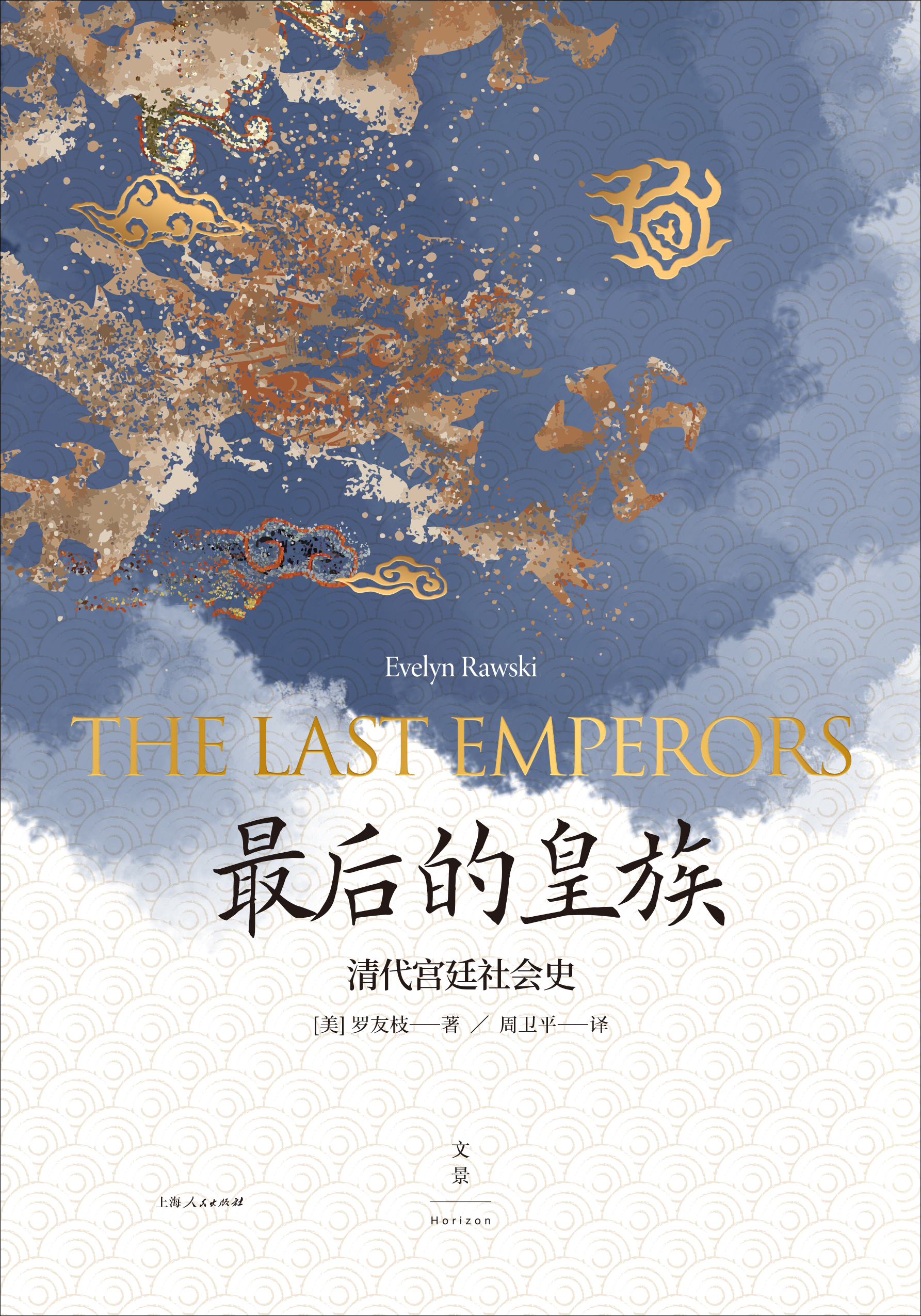编者按:《最后的皇族》首次生动揭秘了清代的宫廷生活,全面展示了清代宫廷服饰、语言、饮食、文化政策等方面鲜明的民族风情,深度剖析了宫妃、皇子、仆从等清廷内部人员的权利体系和组织运作,详细阐释了登基、寿礼、祈雨、丧葬等公共或私人仪式的举行办法和信仰文化意义。本文系《最后的皇族》绪论。
今日到达北京的旅行者看到的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其物质性的历史遗迹正在快速消逝,虽然过去的帝王居所紫禁城风采依旧,但其他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为修建环城公路和高速公路,高大的城墙已被夷为平地,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将天坛的神秘氛围破坏殆尽,以前国家祭坛的神圣禁地涌来的是普通的市民和游客。游客可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已没必要记住清朝这个自1644到1911年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了。然而,这将是一个错误。
许多困扰人的地缘政治问题都源自清朝。清朝(1644—1911年)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有人认为它是最成功的王朝。清朝也是最后一个征服者的政权。统治者来自东北亚,声称自己是建立金朝(1115—1260年)的、统治过华北部分地区的女真人的后裔。在16世纪末和17 世纪初,一位名叫努尔哈赤(1559—1626年)的小部落首领成功地将许多东北部落联合起来。其子皇太极(1592—1643年)将这些不同的部落变成了一个全新统一的满洲人群体。虽然皇太极在满人军队进入明朝的首都之前就已去世,但学者们仍然认为他是开创清帝国伟业的中心人物。
满洲八旗军在1644年席卷长城以南。在平定明朝境内的动乱之后,清朝便转向巩固内亚边疆,并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划定了与俄国的边界,蒙古草原、青藏高原以及塔里木盆地均被明确纳入清代版图(关于1820年版图,参见匹兹堡大学作者学术成就网站http://www.history.pitt.edu/sites/default/files/9%20Qing%20Dynasty.png)。清朝的征服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领土基础,但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清朝的政策也产生了民族问题。清朝认为自己是多元的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把居住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内亚边缘地带的民族看作帝国大业的重要参与者,这些帝国臣民与汉人地位相埒。他们操着各种与汉语相异的语言,笃信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在18世纪,其各自独立的文化和信仰系统在清统治者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和保持。他们是如何被纳入中华民族体系的?这是一个至今仍未破解的谜题。
本书试图从清朝统治者的视角出发,探讨清朝历史中的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它涉及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即早期满族统治者的成功关键在于他们采取了系统的“汉化政策”。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在关于如何界定这个民族国家的争论中,出现了柯娇燕所谓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化模式”之说。19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者有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向中国的读者引介了“种族”和“民族”的概念。“汉族”一词,意即“汉民族集团”,成为中国的政治语汇。由于其带有血统、宗族的含义,“汉族”使中国人将这个国家“想象”为“汉族世系”。
汉族与种族合二为一。一些中国思想家认为汉族主导着“黄色人种”,这样就可以展示一部杰出的文化成就史。满族人、日本人和蒙古人顶多只是处在“黄色人种”的边缘地带,有些作者甚至认为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不属于黄色人种。后来被奉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也曾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抵抗欧美的侵略,原因在于中国的统治者是满族人。由于满族人不是汉民族的成员,所以清朝就缺乏全力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决心。孙中山试图动员汉族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创建一个汉族国家。
那么谁属于汉族呢?孙中山声称“汉族”是一个“纯正的种族实体”。尽管史实表明许多不同的民族曾生活于中国,他仍坚持“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华民族就是汉族,他们具有共同的血统、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风俗—一个单一的、纯正的种族”。历史上侵入或迁入中国的不同民族与汉人融合:他们被汉化了。这就是孙中山在1912年之后发展起来的主要学说之一,当时他和其他民族主义领袖试图在曾为清帝国之一部分的地区创建一个新的中华民族国家。虽然孙偶尔也谈到有必要在中国众多民族的基础上构造一个新的“国家民族”,但他同时也认为少数民族最终会被融入占多数的汉族之中。
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言,“近代社会的历史意识基本上是由民族国家构建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和聚焦于民族认同的话语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学。依梁启超的说法,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任务是丢弃早期历史的王朝框架而书写“民族的历史”。在民族主义者的日程表上,对那些曾统治过近代中国领土的非汉族外来征服者政权的描述,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在20 世纪20年代,像傅斯年等人曾试图将中国历史说成是汉族的历史。在中国疆土之内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被重写为汉文化胜利的历史(不管另一方是什么文化)。征服者王朝也许通过蛮力击败了汉人统治者,但他们都俯首于更为成熟的汉人制度,并最终被融入汉族文化之中。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柯娇燕曾为之写过评论)是芮玛丽(Mary C. Wright)1957 年的作品,该著作是适用于阐释“汉化”的一个甚有影响的范例,它不仅对那些因19世纪帝国主义获胜而指责满人的作者(他们响应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作出回应,同时也对那种认为辽和清这样的外来征服者政权没有汉化的说法予以否定。芮玛丽指出,到19世纪中叶,隔开征服者上层集团和被征服者的文化藩篱已逐渐消失,清统治者和汉族的利益“实际上已难以区分了”。芮玛丽在著作中以同治中兴为例,认为同治中兴源于汉族的儒家政治思想,而改革的失败也是儒家思想的失败。
柯娇燕列举了数条理由,认为芮玛丽关于满人融入汉族社会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如芮玛丽所言,满族人的家园已被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渗入,清末旗人也失去了许多法律特权,然而这些变化却未能毁灭旗军防地的文化生活。柯娇燕论述苏完瓜尔佳氏的专著,用文献充分说明这个旗人家族在清末民初仍保持着明显的旗人特征。在满人和汉人眼中,满族与汉族是分开的,这一点可以在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中得到证实。柯娇燕认为,满族肯定没有消失在汉族群体之中,或者,由于汉族向他们展示出的敌意,他们也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更须指出的是,为了抵制不断发展的汉民族主义认同意识,20世纪的满族也形成了一种近代民族认同意识。
在芮玛丽写作的时候,供学术研究所用的丰富的清朝档案资料还难以获得。柯娇燕对旗军防地文化的研究依据的也是其他种类的资料。我的研究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从而可以说明芮玛丽的另一个看法也是不对的,而这是柯娇燕没有批评过的。芮玛丽断言同治时期的宫廷已经汉化。而在柯娇燕看来,“对宫廷生活的了解并不意味着了解满人在中国的生活……清朝诸帝的行为并不代表旗人。”目前所能获得的档案资料表明,统治者还保持着满族认同。对这一状况作出解释,需要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学界对“汉化”这个概念的使用一直不多。例如,对满语在宫廷使用状况的研究几乎都表明,满语已不是统治者和征服者精英集团的首选用语,这标志着他们已融入了汉族文化。如柯娇燕和我在其他论著中所阐述的那样,忽视有清一代满文文献的历史学家们为自己的这种看法付出了代价。2 满语不仅未在首都消失,而且还在新疆和东北的旗营中使用(参阅本书第一章),东北地区店铺的双语招牌和持久不衰的萨满教传统使一位满族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地区,满族传统与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的传统共存,它们紧密交错在一起,以致难以分清彼此的面目。”
更为重要的是,满族认同不视某人将汉语或满语作为其“母语”而定。19世纪的清朝统治者使用起汉语来似乎更加得心应手,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认同自己的满族身份。那些认为满族的民族意识来自满语的人,可以和讲英语的人的情况进行一番比较。美洲殖民者虽然操着英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自己构建一个独立的认同,并宣布脱离英国独立。英语也未能阻止印度民族主义精英利用这一语言促进印度的自治。因此,那些认为语言总是伴随身份认同意识的看法是可笑的。
越来越多的二手文献表明,关于基本身份认同意识的构建和维持的议题不仅复杂,且具有历史偶然性。民族性这一观念是随着19世纪民族国家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其他地区崛起而得到充分发展的。正如柯娇燕指出的那样,将这一术语用于更早的时期是时代性的错误,是对历史的扭曲。这并不是说清统治者缺少自我认同和认同他人的概念,而是说,政治环境的要求和对自我的界定完全是两回事。清朝的统治范式不是民族国家,统治的目标不是构建一种民族认同,而是允许多元文化在一个松散的人格化帝国之内共存。近代意义的民族性并不存在,国家也不想去创造这种民族性。
近代民族性不仅意味着创造一个休戚相关的群体,而且要把它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在女真人的故乡东北亚,这些界限是很不固定的,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蒙古高原、茂密的森林地区和肥沃的辽河平原—在该地区交错,使得依靠游牧、渔猎和农耕为生的民族能够互相交往。17世纪的女真人以农耕为生,他们与蒙古人共用的词汇显示了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女真人不仅讲蒙语,还用蒙古文字书写,努尔哈赤的一些族人还采用了蒙古人的姓名和头衔。依据有关八旗组织架构的蒙古文资料,戴维·法夸尔(David Farquhar)揭示出,早期满洲政权中的许多汉族因素实际上是通过蒙古人传入的。
满人把许多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纳入八旗组织,力图把这些人塑造为满人—用同样的法律、着装规范和社会规则来管辖。原有的各种身份认同意识被融入新的八旗认同意识中,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如此—到了18世纪,宫廷内部很大程度上转向以血统来确定身份。即便如此,征服者精英仍然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18世纪新被纳入清朝统治集团的穆斯林上层人士、藏族和蒙古贵族,使得征服者精英集团不至于具有单一的种族背景和认同。与此相似,尽管存在王夫之等人主张“严夷夏之防”,但大多数儒家士子强调儒家学说的普遍性和通用性,认为他们的主要使命在于“教化”和“文化”,而不必在意受教者的种族或民族背景。在两大族群中,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
此外,清朝统治者对于文化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关注的主题。作为个人,他们着意于保持爱新觉罗氏的血统和征服者精英集团的地位。然而,作为统治者,他们不赞成那些可能改变其臣民固有文化的政策。多民族国家统治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支持和促进臣民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并在帝国境内怀柔和笼络不同的族群。在清朝灭亡之前,大多数清朝最高统治者都会讲多种语言:他们学习蒙古语、满语和汉语。某些统治者(如乾隆皇帝)还不惮烦劳,学习藏语和维吾尔语。弘历如是说:
乾隆八年始习蒙古语;二十五年平回部,遂习回语;四十一年平两金川,略习番语;四十五年因班禅来谒,兼习唐古拉语。是以每岁年班,蒙古、回部、番部到京接见,即以其语慰问,不藉舌人传译……燕笑联情,用示柔远之意。
在17世纪征服时期,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试图以儒家君王的形象来赢得汉族文人士子的支持。他们学习汉语,把儒家经典当作科举考试的基础,把科举制度当作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满族皇帝支持和资助汉族艺术和文学,发布儒教政令,改革满族的婚丧以适应汉族的习俗。孝道成为统治的主要先决条件。这些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满汉之间一直存在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但是满人的恩惠逐渐消弭了汉人的抵抗,赢得了他们对清王朝的支持。
清朝统治的种种汉化表现,以及其对长城以南的前明领土管理的高度关注,使得许多研究者忽略了清朝统治者的非汉族背景,把汉化当作清代的历史主流加以强调。本书各章内容表明,清朝统治者从来没有在观念上淡化自己与明朝遗民的区别,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族认同。当政治上有利可图时,他们就采用汉人的习俗;当无助于他们实现政治目标时,他们就拒绝这些习俗。清朝统治者以同样的热情研究金代的历史,吸收了金朝的许多政策。柯娇燕分析了这些先例对清朝统治的重要性:“在金代,利用科举制度从百姓中选拔人才并限制贵族担任高级官位,是与金朝政府雄心勃勃的计划相辅相成的。这些计划是:限制贵族的特权和影响,加强中央集权,让王朝的支持者在维护官僚制度中发挥广泛的作用。这些做法都是大清帝国官僚政治的先例。”
近年来,关于10—14世纪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征服者政权的研究,对非汉族政权带给统治者的显而易见的政治风格作出了新的解释。契丹、西夏、女真和蒙古统治者都曾把汉族的官僚体制纳入自己的统治中,但与此同时,他们改革汉族的政治模式,以适应自己的环境。他们特别重视如何控制散布在内亚和东亚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所有的征服者政权都依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管理政策,对不同的民族采取不同的法律,从不同的民族中选拔官吏。此外,虽然汉人被选拔到政府中做官,但这四个政权都拒绝汉化。每个政权都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都奉行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政策。每个政权都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不仅在儒家学说中,而且在佛学领域为自己寻找统治的合法性。
清王朝既不是对汉族王朝的复制,也不是对以前的非汉族政权的简单重复。对大清的描述必须注意到其统治者的非汉族背景,还要更进一步分析其统治的创新方面。本书不认为汉化是清朝统治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本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清朝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它有能力针对帝国之内亚边疆地区的主要非汉族群体采取富有弹性的特殊文化政策。一般来说,本土王朝如果要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则必须抛弃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清王朝只需将以前征服者政权的模式加以扩大即可。这些发现间接地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考察早期内亚政权对中国历史作出的贡献。
《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
[美]罗友枝 著
周卫平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