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当代文学史,从柳青笔下梁生宝到路遥笔下的孙少安、孙少平,每一个社会时代,都有作家以强健的文学作品塑造出经典的文学“新人”形象。7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塑造新时代的新人”的重要意义和创作期待——

这样的“新人”形象,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承载着作者对时代和历史的理解与洞察。这些“新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时代对话、彼此建构,他们在展开自己故事的同时,也传达着一代人的信念和梦想、呈现着时代的形象与意义、勾勒出历史的逻辑和前景。与此相应的,为了成功地书写、塑造出这样的新人形象,我们的艺术观念、艺术方法,也需要大胆创新。新的时代内容需要新的形式,如何为新时代的乡村现实、为无数“新人”的人生寻找“适配”的表达,这是每一位乡村题材作品的写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课题。
站在2020年,我们的“乡土中国”经历着浩大的现代转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历史与未来的互动塑造都铺展在眼前。这意味着,“新人”的“新”,不仅是生活形态的新,更重要的是新的精神气质、新的生命追求,对自我、对生活、对中国与世界新的认识和新的想象。
去年,本报已关注此话题,邀请了弋舟、任晓雯、刘大先、李唐、王占黑、唐诗人、张熠如这七位活跃在创作和评论中的青年作者,请他们谈一谈自己理解的文学“新人”。今天为大家带来精要观点集纳,并期待更多相关的讨论展开。

文学报2019年1月31日

生于1972年,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春秋误》,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丙申故事集》,非虚构《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等。
在我的下意识里,“新”是“旧”的重温与唤醒。不过只是因为那“旧”已与我们隔膜太久,在我们习惯于“一人一行”这样“新”的遣词造句、整理世界的方式之后,对于那浩大的“旧”的重温,方才有了“新”的启发。在我的想象中,我们文学中的“新人”,大约就应当像那位救我于水火的小哥,他能够从古老文明的“旧”密码里汲取正大的能量,他因此自信从容,因此有着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因此在“一人一行”的逻辑里捉襟见肘时,山重水复,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就好比,当我以“一人一行”这样的语感指认世界、自我辩解日渐乏力的时刻,我开始想象我笔下的“新人”,他将回到自己文明的“古老要求”之中,以一句“疑邻盗斧”重新展开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教育。
——(点击标题阅读全文)

生于1978年,曾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著有长篇小说《她们》《岛上》《好人宋没用》《朱三小姐的一生》,短篇集《阳台上》《飞毯》等。
我始终坚信,写作者有某种不可言说的感知能力,它使得一个人的内心,可以生出超拔于生活的丰富性。它使得一个人看,并能看见;活着,并能感受到活着。在此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变得不一样了。人们认为作家要么关注现实,要么关注内心,好像这里存在两分法。其实一个人是无法仅仅通过描述自己的内心去构建一部小说的,当然一个人也无法在自我心灵缺席的情况下去呈现现实。小说家表述的现实,不是静止的死物,而是由一个个他人构成的集合。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一条隐形的坐标轴,作家可以在上面自由滑移,并最终决定将自己摆放在哪个位置。自我膨胀了,他人就会缩小。自我抬高了,他人就会降低。在每部小说作品里,其实都可以窥见作者的自我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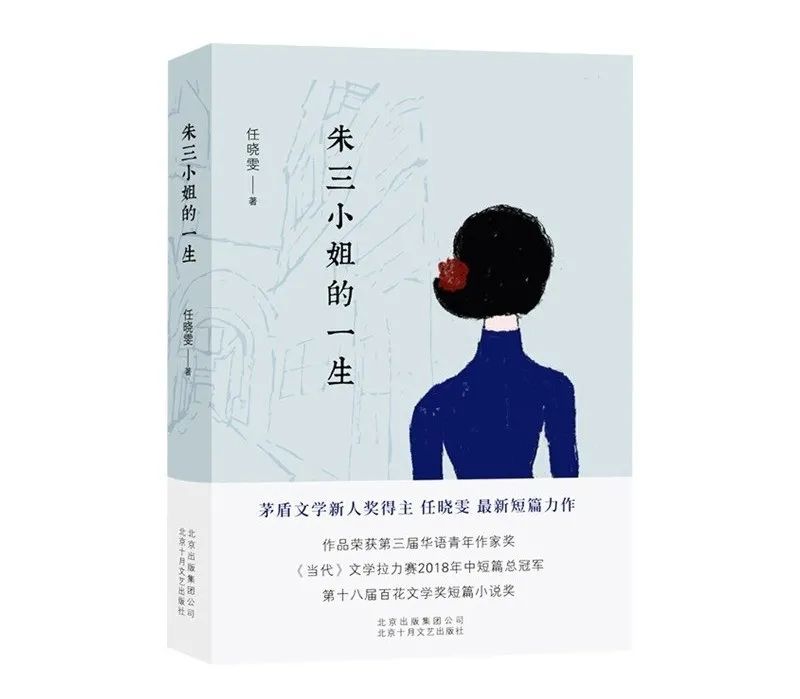
——(点击标题阅读全文)

生于1978年,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著有《文学的共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无情世界的感情》等。
近年来,年轻作家中不少人开始以回望方式深入历史、深入过往,试图重建自己的写作蓝图,多部家族史叙事作品在市场引起反响。很大程度上,这是作家阅历成长、自醒意识提升的体现,但这也引发了另一种争议:如果当下年轻作家都选择“向后看”,那么属于“同代人”的书写,又该由谁来完成?这种集体性的“回望”,是否意味着对于庞大、火热当下的某种无力感与回避?对此,刘大先认为,真正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品,永远是留下时代信息的作品,在此意义上,作家不应以“难以定性、难以描摹”来回避时代性的书写。“如今我们看茅盾的《子夜》,其中对于工商买办的描写其实并不那么精细,但却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图景,帮我们认知那个时代的丰富面貌。”

——(点击标题阅读全文)

生于1992年,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著有长篇小说《身外之海》,小说集《我们终将被遗忘》《热带》等。
我写的总是一帮内心并不坚定的人,试图去寻求坚定的故事。他们不是天生的勇者,甚至可谓懦弱。不过,他们在尽力认识到哪些是需要捍卫的价值,尽管看起来可笑或微不足道;他们在寻求什么,尽管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会不断迷失、后退,甚至变得更为不堪,因此,他们永远在路上。
我对“人”的理解就是如此。在世界面前,个人永远是渺小的,孑然一身,终生都在寻找着生命的意义。无论看似多么强大的人,本质上都是脆弱的,不过,我们就是在这种脆弱中学习着如何坚强起来。

——点击标题阅读全文)

生于1991年,曾获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著有小说集《空响炮》《街道江湖》等。
我们在提到城市的时候,会有一种固有观念,城市就是水泥钢筋丛林,城市就是由高楼大厦、写字楼这些空间堆积出来的。在我看来,城市丛林这个概念有另一个相对应的叫法,就是城市盆景。

关于那个地方,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题材,前辈们早就写到极致啦,你太老套啦。可是,每个人注册一个账号打游戏,有人玩到终点了,其他人不还是要前仆后继地玩下去吗。游戏永远不会因为一部分玩家率先到达终点而关闭,它随时向所有人敞开,这才是它对人人都充满魅力的地方。我想文学也是这样。
——(点击标题阅读全文)

生于1989年,暨南大学博士后,青年评论家。编著《当代文学见闻录》等。曾获第七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新人奖。
对感受的忠实,就是对写作的当下性的强调。突出“当下性”,意思是我们需要面对当下而写作。当下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现实?为了理解当下,我们或许又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各种主义、话语的解释,比如是现代的、后现代的现实,或者是后工业、后人类时代的现实。如果相信这些话语理论,我们的创作,必然又回到遵循既有话语秩序的“主义化”写作状态。对于这些主义、话语观念,不管它们多么前沿、如何时髦,对于作家而言,其实都是过时的,是要作家通过自己的现实感受去摆脱、甚至去颠覆的。
不要以往的、既有的各种主义、话语,那我们的青年作家能够创造出新的贴合当下现实感的主义、话语吗?这似乎又是很渺茫的。难以创造新的“主义”,我们又如何树立起新的文学旗帜?今天我们的文学创作,其实面临着一个世界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是文学界的,也是思想界的,困境的背后,却是历史性的。我们经常说,今天的哲学已死,只剩下哲学史,都是书本上的知识,与现实生活构成不了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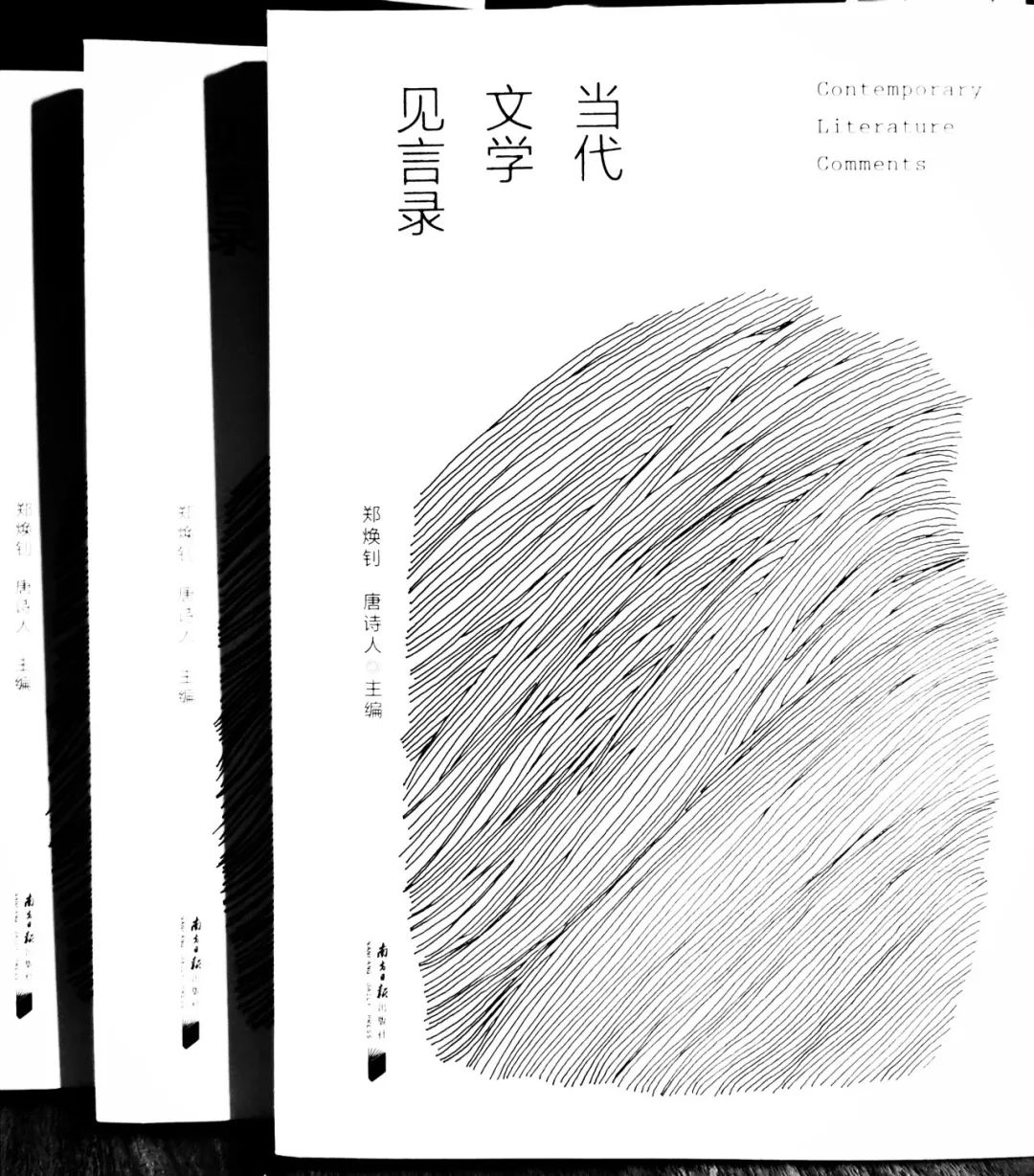
——(点击标题阅读全文)

生于1994年,译者、青年评论家,曾获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新人奖。
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并非因为作者的匿名而获得世界级的好评。许多评论都认为,“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对女性身份的探索之深,超越了绝大多数当代作品。从童年、青春期,再到中年和老年,“那不勒斯四部曲”跨越了两位女性的一生,她们的成长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主线。与此同时,大量的人物登场,大量的事件发生。在中译本里,正文之前会列有一张人物表,按照家族来介绍人物,数十年的意大利历史,在每个人物的轨迹里缓缓展开。

哪种叙事手法更好?人物和情节,该多一点,还是该少一点?年龄和身份的意义有多大?写自然还是写城市?我不觉得这是最值得关注的细节,它们更像是文学作为一个多面体的不同面。2016年布克奖主席阿曼达·福尔曼曾说,有些书可以超越体裁,这样的作品定义了文学,也让文学获得新生。同样,有时放弃对市场和评论的迎合、对新意和主题的追求,反而成为一种优势,正如大卫·范恩描述自己的写作过程:
“我没有计划、大纲、情节或者主题,只有一个地点,一个不安的人物……作者的潜意识,要比意识更为奇特和有力,因为意识只能产出有限的故事。最终,作者最应该避免的,就是已经定型的观念和主题。”
——(点击标题阅读全文)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出版书影;作者画像:郭天容 绘

文学照亮生活
网站:wxb.whb.cn
邮发代号:3-22
原标题:《七位作家评论家谈文学造“新”:不被定型的主义、观念与主题所束缚,创作始见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