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科学报 ,作者贺福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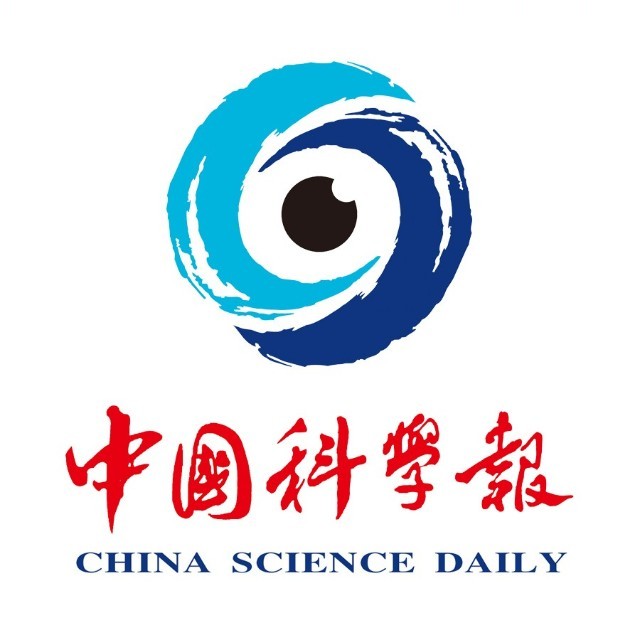
关注科教重要事件,网罗学术新鲜趣闻。


也怀目标笃行致运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时间分别是1977年12月和1978年7月。1977年高考时,15岁的我还是高一学生,被校长的一句玩笑话鼓动参加了高考,却出人意料地考了全县第一,被武汉大学录取。当时,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此前没有受过系统的中等教育,如果此时急于求成,将来一定难成大器,又因我对北京大学有所向往,便放弃了武汉大学,准备来年再考。
没想到,第二年看似囊中取物的高考,却因一个又一个的意外而让整个过程变得跌宕起伏。
再穷再苦也不放弃读书
我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一个农耕之家,家族世代务农,父母大字不识。政治的动乱、社会的动荡伴随着我的童年。在家中我排行第四,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大哥被伯父收养,二姐已出嫁,三哥夭折)。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粮食分配按劳动力的工分计 算。父亲虽上了年纪,但勤耕苦作仍相当于一个半劳动力,母亲虽为家庭主妇,但内外兼顾也算一个劳动力,我上初中后坚持半耕半读,也能挣到一个完整劳动力的工分。但家中按三个半劳动力分配到的口粮,根 本不足以支撑六口人的生计。
雪上加霜的是,“文革”期间,我们县是“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县”。为了保证每年给国家上交的粮食逐年递增,遇到天灾产量下降时,生产队只得将大家本来已很紧巴的口粮部分上交。为了生活,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迫不得已偷偷出去要饭。我们常常是话未出口就已泪流满面。
那个时候我既期待开学,又怕开学。期待开学有书可读,但我又怕交不起学杂费。虽然我们兄妹三人的学杂费不到10元,但对于务农、一年到头根本分不到10元钱的父母来说,这却是天文数字。无奈中,父母后来想到了养母猪、卖猪仔筹学费的办法。但好景不长,连续两场猪瘟几近中断了我们的求学旅程。最后,父亲只好当掉了他从事地下工作时所得的战利品换钱,我们才得以继续上学。
为减轻家里压力,自12岁起,我利用每年4个假期以及每天早上的出工和周末的一天半时间,半耕半读,这样一年可以挣出养活我一个人的工分。假期往往是农活最忙的季节,是挣工分的最好时机。虽然我年纪不大,却是割谷、插秧的一把好手,有时一天可赚30来个工分。
南方的夏天潮湿炎热,收割与插秧都在水田里,烈日把水田中的泥水晒得烫人,中午最热的时候,水温甚至可以达到五六十度。再加上泥水中化肥、农药等的长期高温 浸泡,蚊虫、蚂蟻等的反复叮咬,我的双脚、双腿和双手都是溃烂的,我只能晚上抹上药,第二天再继续干。
劳动间隙,我总爱捧着书本。其实,当时正值“白卷英雄”当道,“反潮流闯将”走 红,社会上流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读书无用” “知识越多越 反动”等风气。受这种氛围影响,我周围很多同学主动辍学回家务农,这样不仅可挣工分养活自己,还可帮衬家里,实现自己的“价值”。
但是,即使读书再看不到出路,父亲和母亲也只有一个心思:“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正是这种朴素的想法,支撑着我在最难熬的岁月里也没有放弃读书。
当时说是在学校学习,其实并没有系统地上课。我上初中时有3个班,即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和文体班。因我从小就是文艺骨干,唱歌跳舞都较擅长,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文体班,后来我还当上了学校乃至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队长。全县会演中,我带领公社宣传队夺得第一名。因我的突出表现,经反复考核,我被县文工团录取。这对一个农村少年来说,无疑是跳出“农门“的难得机遇,简直像“天上掉馅饼“,父母喜不自禁。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立刻去报到。因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一片欢腾,各省市县都在组织文艺会演。作为文艺宣传队队长,我先是忙着带队参加各类会演接着又带队下乡去各大队、生产队进行慰问演出。当慰问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公社的知青点传出了风声——可能会恢复高考。听到消息后,我告知了父母自己冒险的决定:放弃已经到手的进县文工团的机会,等待不知何时才会真正恢复的高考的到来。
高一考生成“黑马”
因为我是文体骨干,初中的学校推荐我上了高中的文体班,这样,我从红卫兵营营长,成为公社联校的红卫兵团团长,粉碎“四人帮”后又成为学生会主席。
记得1977年8月30日,我们原本商议好召集学生会干部讨论新学年的组织工作,但当时全公社举行高考摸底考试,占用了我们的会场。校长开玩笑说让我也一起参加考试。
于是,刚刚步入高中的我,没做任何准备,与“老三届”等往届高考生共四五百人一起参加了这场高考摸底考试。成绩出来,我的数理化成绩居然均是全公社第一,我一 下子成了别人眼中的“黑马”。
接下来,我作为高一在校生代表,参加了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无意中成为常德地区在校生中考上名牌大学的第一人,也是那年唯一的一人。
但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此前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如果此时急于求成,将来一定难成大器,又因为自己对北京大学有所向往,于是我果断放弃了众人求之不得的进入名牌大学深造的机会,甘冒风险,继续留在高中学习。
于是,我的高考复习正式拉开序幕。为了能考出好成绩,学校将公社所有成绩优异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称为“尖子班”。同学们都是早上5点起床看书,晚上12点睡觉,争分夺秒地学习。每天尖子班都要进行一次考试,每周学校还会组织一次考试,每个月县里也有统一考试。
在各种大考小考中,尖子班会按成绩排出第一到第八名,被戏称为“八大金刚“ 。而我一直稳坐第一把交椅,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最辉煌的时期。有同学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时会先去问尖子班的普通同学,如果得不到答案,会从“八大金刚”的老八开始问起,直到老二,然后去问老师,如果老师还是无法解答才会问我。印象中一共有3次我没有解答出来,皆是因为题目抄写错误而无解。
高中时,我一直住在家里。一是因为没有钱住校,二是为了每天早上出工赚工分 (农闲时1分、农忙时2分)。出完工有时是早上7点多,为了不耽误检査各班同学考勤,所以我几乎每天干完活都要拿着早饭团跑十里地去学校。到了冬天,我跑到学校后,汗水打湿了衣服,需要一上午时间才能靠体温把它烘干,以致我落下了咽炎的毛病。
临考前一个月,我开始住校。为了照顾我,班主任特批我可以不按照学校的时间作息。同学们学习的时候,我休息;同学们休息的时候,我学习。这种时间差让我的效率极高。
就这样我迎来了第二次高考。
人生的第一次失眠
1978年7月,我第二次坐在高考考场上。两天的考试,我顺利地完成了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4门考试,对4门考试的成绩也是自信满满。教导处老师跟我说,如果不出意外,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攻读任何自己心仪的专业。事实上,学校对我也寄予了厚望。
感觉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愿望就要实现,从不失眠的我,这一夜竟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然而,第二天还有语文和英语的考试等着我。英语得分不计入高考成绩,不必说;语文原本是我的强项,我写的作文常常被当做范文朗读。但因睡眠不足,第二天考试时我整个人昏昏沉沉,导致考试发挥失常,我感觉自己语文考试只能考得二十多分。要知道,当时大学招生反对偏科,如果考生某一科目分数过低,可能会名落孙山。
无奈,我放弃了一直向往的北京大学,将第一志愿改为上海复旦大学,专业则填报了我一直热爱的激光物理和理论数学。
高考结束后,我的神经一直紧绷,与考试有关的事情萦绕在我脑海中,要么无眠,要么噩梦:有时是名落孙山,有时是金榜题名,然而南柯一梦让人更难过。
9月15日一早,湖南省人民广播电台通报第一批高校录取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更沉重了。当日下午,父亲让我去距家三里多的米店打米。一百多斤的担子对于12岁就开始从事繁重劳动的我来说,并不算负担。但从米店回家的路上,我停停走走,想未来,想自己,只觉得被担子压得喘不过气。直到距离家门几百米时,已经出嫁的大姐从家里飞快地冲出来,对我大喊:“四弟,你被录取了!”忽然间,我刚才还觉得沉甸甸的担子顿时轻如无物,我大步流星赶回家。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很长一段时间还觉得在梦中,唯恐黄粱一梦后等待自己的还是惶恐。
为了奖励第一批被录取的学生,县里给被录取者每人50元作为奖励。我父亲用这笔 “巨款”宴请了一直对我们照顾有加的邻里,也算是为我饯行。但家里却没有多余的钱为我置办行李。于是,家里人用装化肥的袋子裁剪成衣服和裤子,并为了遮住上面的字而将其染成了黑色,再搭配上一双黑色的凉鞋,这就是我的新“行头”。
那次,16岁的我用扁担挑着行李(主要是书),从村里到公社、到县城,人生第一 次独自一人坐船到省城,再转乘火车来到了上海。
从折腾转系到激情燃烧
到复旦大学报到后,我开始为自己没有进入心仪的激光物理专业而是被遗传工程专业录取而折腾着要转系。因为最初看到“遗传”二字时,我习惯性地将这一专业与社里卫星大队的“遗传育种”工作关联在一起,因而极端地抵触,几次三番地要求更换专业。
为了追求我心仪的专业,大一时我几乎没进过教室,而是将自己“关“在图书馆,拼命地学习理论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知识。
当在大量文献中寻找方向时,我看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量子力学泰斗玻尔教导后辈的一则故事:德国哥廷根大学玻恩的博士生德布吕克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想跟随玻尔做量子力学研究,但玻尔指出“你生得太晚了,量子力学的问题已经被我们解决得差不多了!你要想有所作为,恐怕得到生命世界去寻找新的规律”。德布吕克因此从欧洲到了美国,跟随摩尔根学派研究基因,日后成为了分子生物学之父,后来还获得诺贝尔奖,不过不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则故事完全打破了我对遗传和基因学的偏见。再加上系里的谈家桢先生(摩尔根的学生、中国遗传学的鼻祖)关于遗传工程的精彩讲座,真是令我醍醐灌顶,让我不再执着于物理领域,转而将激情投入到基因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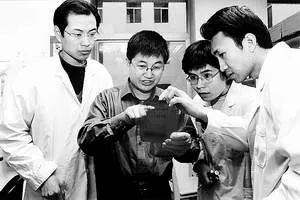
简单说,1978年高考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同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则改变了国家的走向,因而改革开放就像是我们国家的一场高考。这场国家的高考一直在进行中,并且越考越难——毛泽东同志带领第一代共产党人解放劳动力,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我国“站起来”;邓小平同志带领第二代共产党人开启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 “富起来”;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解放创造力,新时代的我们一定会“强起来”!
来 源| 湖南大学出版社的《两院院士忆高考》
编 辑 | 陈 卫
校 审 | 罗 瑶 杨 刚 李 丹
原标题:《贺福初院士忆高考 ‖ 也怀目标笃行致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