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杨帆 方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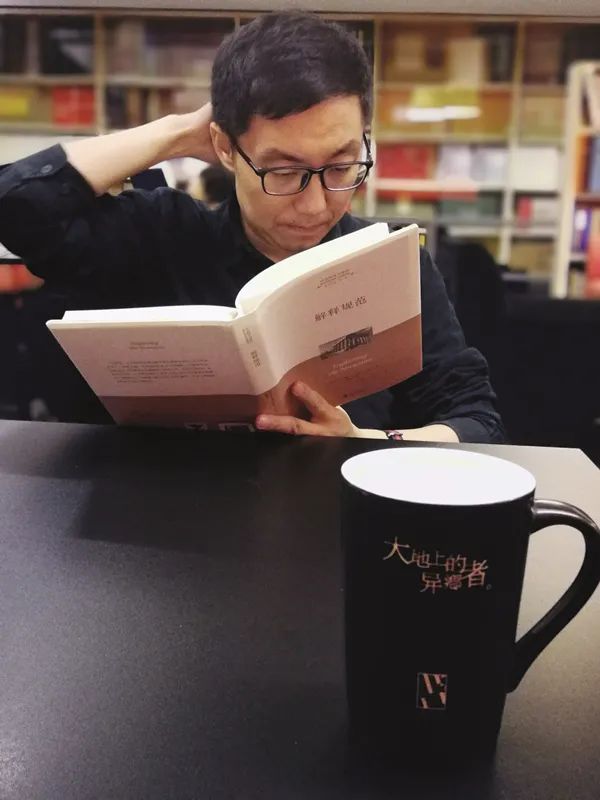
大约在七八年前,我接受了一本女性杂志(是的,你没看错)的采访,让我谈谈留学和读书生活。当时的我,年届而立之年,正处在博士留级的人生阶段,奖学金即将停发,大论文还没有着落,更别提像很多在读博士那样猛发核心期刊了。即便是在那样的状况下,我也对采访我的记者立下了一个flag,说我正在构思一本有关于旅游的书,叫作《欧洲思想地图》。这本书打算以思想史+景点介绍+随笔的方式,把我在欧洲各国旅行的地方,尤其是思想家的故居或者留下足迹的地方一一记述一遍。我甚至写了十几页的书稿策划,把我去过和打算去的地方都标注下来,想着有朝一日它也许能够成为大卖畅销书。
很显然,我并没有写成这本书。后来我总算博士毕业,也回国谋了一份教职,写书的事便不再提。能够毕业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没有奖学金了,不能到处旅游,只能待在家里,最后熬出了论文。这样看来,我今天想聊的两件事情——读书与赶路——似乎是有矛盾的?
在“自由探索”的路上“蒙头狂奔”
把读书作为自己重要的生活方式甚至谋生手段,对我来说,应该是比较晚的事情。虽然中学时候也很爱看书,比如科幻小说、杂文游记、村上春树,甚至一些学术著作、学者谈话录,都极大地充实了我的生活。但是那时我的最大的理想还是做一个“阅历”很广的人,可以到不同的地方走走看看、学习知识。“行万里路”对我来说一直比“读万卷书”更有吸引力。于是读大学对我最大的魅力也在于可以去一个离家很远、没有父母的地方,读书、旅游,自在生活。
一个这么“爱自由”的人,最大困难可能就在于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干成一件事吧,我拖沓了6年多的博士学业可以是最好证明。虽然有报道称法国文科博士平均毕业时间8年多,平均写论文时间是五年半,但那毕竟是散漫的法国人干的事。大学的专业虽然是法律,但是我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读专业书之外,以至于专业基础不牢的我考了三次司法考试才通过。
大学时我最喜欢去旁听的是地理系的课,尤其是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之类的。这也可能也跟我一直以来“行万里路”的偏好有关系(奇怪的是,作为文科高考生的我,考了地理,却没有资格报地理专业),再加上母校华东师大地理系的声名在外,于是我便常常去蹭课。很多次到地理馆上课时我都会在胡焕庸先生的塑像前沉思片刻,想象着沿着他画的线去旅行、考察,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后来有一次,冯象先生回到自己成长的华师大做讲座,题目叫《法律与文学》。我记得他给法科学生提出的建议是:除了专业主干课程以外,其他时间可以尽可能去其他专业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句话正好justify了我“不务正业”的作风,让我在“自由探索”的路上继续“蒙头狂奔”。
当时上海有些比较有意思的书店,我经常可以在里边一待就是半天。华师大后门有家很隐蔽的小书店,叫“博师书屋”,坐落在普陀区社会福利院的里边,隐蔽到不是常客根本不知道,不过却经常能遇到一些大教授在角落里闷头挑书。书屋的老板是位精打细算的上海老人家,有各种门路搞到打折学术书,甚至有些还是新书,但却从不让人拍照(也可能是因为那时智能手机刚兴起,我突然拿出来吓了他一跳)。
印象中最惬意的时刻,就是某个得闲的下午,去枣阳路的兰州拉面馆吃份盖浇饭,然后去那里选两本“闲书”,再到隔壁长风公园的长椅上看到吃晚饭。我读研时的室友是历史专业的,我俩经常一起去淘书,到毕业时我们宿舍基本已经被我俩用书摆满了。我俩还互相影响,我的历史书籍越来越多,其中吕思勉、陈旭麓、王家范等先生的作品带给我影响最大;他也做起了法律史研究,博士论文写的是日占时期上海的日常犯罪。后来我俩都出国读了书。大约是在第二次回国的时候,我跑去博师书屋,才发现“人去屋空”。那时候也是全国实体书店大面积倒闭的时刻。
大学时期,华师大后门还有一家大夏书店,在一个隐蔽的二层小楼上。里边的书都按照地域和出版社进行排列,不但可以看书,还可以包夜。所以也成了我最长驻足的地方之一。
印象中我在那里买了不少上海人民出版社灰色封皮的那套书,涂尔干、施密特的系列。跟老板混熟了以后才知道这家书店幕后的boss是长我几届毕业的学长、学姐,因此才以华师大的前身之一“大夏大学”之名命名了这家书店(其中一位boss现在也是法学界的知名青年学者)。大夏书店最多时在上海也有好几家,华师大闵行校区建成后他们也在研究生公寓开过一家店,但是好景不长,也在书店倒闭潮中消失了。
最近两年,这家书店又在华师大的中山北路正门重新开张了。我去过几次,书没有以前多了,大量的空间都被文创用品和咖啡区占据着。这也是最近一波实体书店兴起的共同特点吧,但比起那些以书店之名营业的咖啡馆还是有趣不少的。
还有一家可以称为我的精神家园的书店就是上海的季风书屋。它最早是位于陕西南路地铁站里边的一家书店,也偶尔卖畅销书和教辅书。虽然有点远,但是我也经常会去。巅峰时期在上海大概有四五家季风,其中华师大闵行校区的那家店非常大。那时我已经在闵行校区的哲学系读了博,所以几乎是天天长在这家书店里。
季风的前老板严搏飞老师是学者出身,也做出版业务,跟学界交往很深。我在那里也认识了同济大学的王晓渔老师等人。当然本校的许纪霖老师、刘擎老师等等更是这个书店的常驻嘉宾。
记得有一次,严搏飞老师邀请沈志华老师在书店里跟大家分享读书经历。近百号人围坐在一起,听沈老师话谈天说地四五个小时也不疲倦。我当时对这种美好的景象非常感动,仿佛是刚刚读过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描绘的18世纪巴黎咖啡馆就出现在了我眼前。
季风给我的影响很大,甚至有组织找我谈话了解情况,我都把他们约在那里。我还通过季风接触到了一些上海青年学生、学者,他们共同编了一本发行量较大的网络期刊,叫作《读品》,我有幸成为了最后一期的作者。后来季风搬迁到了上海图书馆的下边又坚持了几年。再后来,《读品》没了,季风也没了。
在哲学系读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陈嘉映老师。似乎陈老师对非常多的年轻人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我们当时有一门必修课,是陈老师的“语言哲学”。算上我只有三个人要修学分(其中有一个还是白俄罗斯的留学生),但是从全国各地赶来听陈老师上课的却有50多人,上课的会议室每天被粉丝挤满。这门课让我对很多问题都有顿悟开窍的感觉。一直到今天,我尝试着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司法审议和裁判说理、用语言哲学的进路去思考法学研究中的范式之争,都是受到了当时那门课的影响。
后来见陈老师的机会少了,除了他作为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的那次以外,但是他的每本书我基本都买来读,也都能有不同的收获。在这里也给陈老师的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做个广告。
这期间我还有幸选修到了李泽厚先生阔别多年之后唯一一次在中国大陆开设的伦理学课程,以及Richard Wolin教授开设的政治哲学课。李泽厚先生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位学者。我在读了他的《2010年谈话录》之后在豆瓣上写了一篇书评,后来这篇书评的语句有幸与刘再复、萧功秦等名家的话一起,出现在了李先生2011年谈话录的推荐语中。
总之那个时期是我作为初学者,思想被不断暴击和点醒的时代。我也真正体验到了不断开阔地阅读、不断地探索未知领域所带来的乐趣,感觉就像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远游一样。
钱包手机可以拿走,书能不能留下?
到法国读博以后,我就更加地“放飞自我”。那几年也是我把读书和赶路结合得最为紧密的时段,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带着书,边走边看成了一种习惯。
可能也是受到了巴黎地铁上全民看书的感染。反倒是回到国内,如果我在地铁上看书就会觉得特别不自然。尤其是在上海,看学术书籍的话总觉得旁边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记得当时为了把何包钢老师的《协商民主》看完,我甚至把它包了书皮才带到地铁上。
在2013年的某一天,我在巴黎南郊经历了一次打劫,三个带着防狼喷雾的黑人少年抢走了我的手机和包,包里面就有两本写满了笔记的中文书。一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再买到后一本书。当时我的愿望就是:钱包手机都可以拿走,能不能把带笔记的书给我留下。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欢坐火车旅行,一方面是因为我出生于铁路世家,另一方面我特别喜欢在火车上边走边看。一路欣赏美景,还能不被打扰地看书,走走停停,真是妙哉。从教以后听说,有老师可以在京沪高铁上一路完成一篇论文的初稿,相比之下我实在是弱爆了。
我曾跟朋友一起立过另一个flag,坐一次从欧洲到中国东北的欧亚大陆桥,其中俄罗斯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就是电影《囧妈》里的那段,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之一。当时希望能在30岁之前实现,现在的愿望是在40岁之前实现,嗯,再过几年……
记得有一年在北欧旅行,有一条从奥斯陆到卑尔根的铁路号称世界最美,我们来回坐了两遍,在路上我也正好看完了王绍光老师的那本《民主四讲》。还有一次跟朋友坐卧铺火车从巴黎去柏林,路上看了应景的电影《再见列宁》,这一路居然治愈了我持续多天的失眠,在火车上睡得很香。
还有一次去荷兰的火车上,我在读一本英文的东欧史,邻座的俄罗斯姑娘注意到就跟我聊了起来。她旅居荷兰做艺术,我俩侃了一路各自国家的后冷战时期转型。
还有一次很有趣的事,某年暑假,在亚德里亚海的游轮旅行,我穿了一件恶搞T恤,上边写着“Three reasons to be a teacher: June, July, August”(三个成为教师的理由:六月、七月和八月),还拿了一本书在那看,然后身边来了一群欧洲各个国家的老师搭讪。他们都是趁着假期出来放松一下,结果因为我这个“符号”聚到了一起,聊了半天的各国教师待遇和职业发展。
“学术猛男趴”
在巴黎也有很多书店可供消磨时间,尤其是在旧书店或者旧书摊淘书成了我那几年的一大乐趣。我去法国的第一年,我的导师童世骏老师正好也去那边出差,还是他传授给我了这种在一堆杂乱无章的旧书中淘到自己钟爱的技巧和喜悦。后来的这些年,无论走到哪里,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到当地的书店淘书,如果能有比较有名的旧书店就更好了。
我比较中意的是台北的茉莉书店,也去过香港、旧金山、卡尔加里、牛津等地的很多家书店。去的最多也最喜欢的是南京的先锋书店和北京的万圣书园。每次去南京、北京,哪怕只有一两个小时空余时间也会过去流连一番。
在法国我去的最多的不是莎士比亚书店这种小资圣地,而是一家叫作Boulinier的二手书店,就在St Michel地铁站(相当于国内城市最市中心的地方)旁边,有海量旧书,但好书绝对“手慢无”。最多的时候我一周会去几次,能清楚知道好书可能在什么位置出现。到最后回国的时候,我不但海运了几箱,还死皮赖脸托航空公司的朋友帮我带回来了一些。虽然可能很多书我也只是翻一下就没再动,但是淘书依然构成了我除了旅行以外最大的生活乐趣之一。
如今,实体书店凋敝,网上淘书成为了我的最爱,当然也包括去Libgen这样的网站冲浪,发现各种免费电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觉得现代知识产权和书籍出版体制是非常不利于思想的传播和创新的。
除了淘书、读书、写论文、旅行,留学岁月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群能跟你一起聊这些东西的人。我们最开始搞过一些读书会,还曾经跟着涂尔干文集的译者汲喆老师一起读过涂尔干。后来就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组织,核心成员是几个读人文社科的大龄男博士,专业有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宪法学的、城市规划的,我们将它命名为“学术猛男趴”,全称为“巴黎南郊学术猛男烧烤趴”。
特别像我们现在在吉大搞的“双德乡中年男子互助小组”(官方名称叫“观澜问学工作坊”),是纯民间的组织,没有任何势力背景,但交流起来没有禁忌和限制,能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为此我也练就了一身腌肉和烤肉的本领,巅峰时期光烧烤炉就有三个。
我还参与了一群在巴黎的华人青年朋友搞的互助讲座组织,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比较了解的知识经过准备分享给大家。这种活动各地其实有很多,比如巴黎花神咖啡馆二楼每周就有固定的读书会,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家里每周末也有规模不小的读书会,朋友圈里齐海滨老师也经常在武汉的家中搞读书分享活动。
我在巴黎这个论坛分享过几期的台湾政治与公法发展史。听众里有一位退休老先生,是曾经的欧盟驻中国大使。他20岁从台湾到法国求学,后来就在那生活了一辈子。最后一次分享的时候,他把家里一堆中文藏书都带了过来送给了我,包括《政治学》(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这些书都是他半个世纪之前从台湾背过去的。他的儿女不懂中文,想着也不会再用,就都送给了我,让我激动得无以言表。
那时觉得生活很苦逼,但现在想想却是难得的可以享受自由思考的人生阶段。
带着学生一起读书
也许就是因为我这种喜欢到处折腾赶路的性格,让我选择了到一所之前从没有过交集的大学教书,也在教书期间到世界各地访学开会,感谢吉大能够热情地收留我、包容我。而我真正的“学科规训”,可以说也是从入教职以后才开始的。以前虽然各种范式的学术套路都有所涉猎,但是并没有一定要模仿他们进行产出的压力,写的东西也是随笔居多,除了那本厚厚的论文。
从教以后,我还要尽力琢磨什么样的主题可以申请课题、什么样的文章可以在主流期刊发表。自己不断研究和实践的同时,还要把这些门道传授给学生。
这段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可能就是李连江老师的那本《不发表,就出局》。好在目前的学术市场,在我看来,某些方面还算是比较包容的。虽然有时也会怀念过去那段自由读书、旅行的日子,会抱怨现在读什么材料、去哪里开会都太有目的性,好多有意思的书根本没时间读、向往的地方也没机会去。但是在我看来,这种目的理性的规训过程却也是非常必需的。唯有经历这样的阶段,才能将过去那些思考以规范化的话语进行输出,从而让它们走向成熟。
现在我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搞读书会,带着学生们一起读我想读的书。虽然有那么一点自我,但也是最有效的分享思想、规训方法的一种路径。以后还计划着带领学生多去实践考察(又一个flag)。
今天的学生,尤其是法学院的学生,跟十几年前相比,要背、要掌握的知识实在是多了太多。光是制定法的数量,这些年就增长了很多,更别说各种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素材。因此他们可能也就没有更多自由读书和思考的时间。每次去图书馆,我都会看到一群法学院的学生拿着红皮书在那不停地背,他们占据了图书馆将近一半的座位。我不知道这是“后浪”们的幸运还是不幸。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人生需要有一个自由读书、思考和探索的阶段。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次次的远足冒险,会让人体验到突破边界的喜悦。
我也觉得最适合读人文社科博士的,也是那些有过一定生活阅历但却没有放弃思考的人。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纷争混沌的时代,我更希望所有热爱读书、思考和赶路的人,还能有机会继续这样,不回头地走下去。(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丨杨帆
原标题:《杨帆:希望所有热爱读书、思考和赶路的人,能不回头地走下去》
